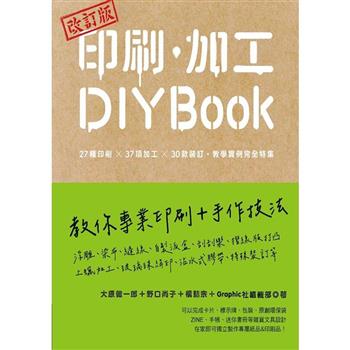「泰勒,你真是個怪咖。」
我檢查著我的腕式高度計,沒理會尼可。一千英呎。我提高音量唱著。「血腥、血腥,殘暴的死法。」
尼可用指關節輕敲我的頭盔,我的耳機再度傳來他模糊的聲音。「嘿!泰勒的地球之歌──首次獨跳的最佳主題曲。」
我把麥克風壓近嘴邊,這樣才能好好大唱副歌。「血腥、血腥,殘暴的死法。他將不再~一躍而下。」
「小怪胎,你長大的速度未免太快、你的歌聲未免太爛。」
「我的歌聲可能很爛,但至少我聽的音樂很有品味,你他媽這個──」
耳機傳來了另一人的聲音。「各位,專業,好嗎?不要用對講機閒聊。」
我咧著嘴笑,把額頭靠在窗上,這樣才能看清楚急速縮小中的加州景緻。兩千英呎。
尼可調整坐姿,給坐在我們對面的海莉一個甜笑。「小隊長,這又不是正式的空擊任務,好玩而已。」尼可向這位迷人的金髮美女挑眉示意。
海莉踢了他一腳。「你要學會尊重,不然小心今年暑假在軍校被修理。」
這兩人在國立空軍學校同窗了好幾年,一直以來就愛這樣拌嘴,他們一邊吵,我一邊再次檢查我的高度計。
三千英呎。
過去幾個月我們這樣練飛了很多次,但這是我們第一次自己獨自跳傘。教練在小飛機的機艙後方在和其他學員說話,他們都是大學生或年紀更大。海莉和尼可分別是十八歲和十九歲,我則剛滿十七。尼可一逮到機會就會叫我小怪咖。
我才不鳥他。希望幾個月後我可以順利進入真正的空軍團隊。到時的基礎訓練一定會有比這更惱人的事。但是我的年齡是申請下限,我必須在一大疊履歷中脫穎而出,所以需要跳傘經歷。尼可和海莉一得知我要考跳傘執照就也立刻報名了。我們三人之間存在著良性競爭,但也都互不相讓。我們都輸不起。
四千英呎。
小飛機旋到更高處,稍稍傾斜,引擎的隆隆聲震入我敏感的耳膜。我在座椅上調整了一下坐姿,試著讓自己舒服一點,背後一大包降落傘具使我必須坐直。移動身體的時候,我後背熟悉的疼痛感又發作了。
我想要隱藏身體的不適,但尼可見過我發作時的表情。他皺起眉頭,用手摀住麥克風,靠近我身旁。
「小伙子,我以為你的背好了?」
我望向海莉,但她忙著做跳傘前的各種檢查,沒在注意聽。
「沒事,」我邊說邊抗拒著想要往後摸肩膀的衝動。我知道其實有事。
五千英呎。
「泰勒,不舒服就不該跳。」尼可兩條又粗又黑的眉毛連成一線。我希望他可以不要告訴教練。
「我沒事,尼可,真的。你覺得我如果真的有事,我媽會讓我上飛機嗎?」
他露出了微笑,眉宇總算是放鬆了下來。「醫生怎麼說?」
我試著湊出一些合理的說辭。「嗯……她說就是有點發炎。那次我背靠地滑過半個體育館弄出來的。」
「喔,就是上週海莉跟你一起『拖地』的時候搞出來的嗎?」尼可大笑,放開了他的麥克風。
我感覺自己兩頰發燙,露出了微笑,這段回憶分散了尼可的注意力,真是鬆一口氣。
「講什麼這麼好笑?」海莉逼問。尼克興致勃勃地向海莉講起上次她在武術工作坊跟我決鬥時獲得壓倒性的勝利,我則是又望向了窗外。飛機已經距離停機坪相當遙遠,中間有雲出現了。
六千英呎。
我其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告訴媽媽。我有打算告訴她。我有試著要告訴她。很多次。但每次我縮緊肌肉走向廚房或站在她的書房時,不知怎麼就退縮了,然後我就只能蜷縮在被子裡,因恐懼和疼痛顫抖著。想要隱藏的感覺征服了我整個人。對抗這種感覺就像是對抗呼吸──可以憋住一時,但是接著本能就會開始發揮作用。好似我的身體不希望我告訴別人後背的詭異痛感,還有……其他感覺。
尼可都知道。有次在更衣室,我以為大家都離開了,卻被尼可逮個正著。不過還好那時是一週的開始,我背部的隆起還不到鐘樓怪人等級。
一開始我以為這是我這陣子快速「登大人」的其中一個現象。我最近無時無刻都覺得飢餓,甚至餓到反胃,我的衣櫥裡也多了一堆穿不下的衣服。然後我開始懷疑是不是因為我這幾年太魯莽,做了太多特技動作,還包含數度從大垃圾箱上面掉下來,所以我的身體開始要反撲了。
就讓我跳吧,我心想。我想著要獨力完成跳傘已經想很久了。讓我跳吧,之後我會告訴媽媽的,也會去看醫生。我不能讓任何事情影響我在軍校的表現。如果大家覺得我在獨立跳傘的時候退縮了,這個謠言就會傳到單位長官那裡,可能還會讓我被記上一筆。
最重要的是,我爸還向空軍請了特休,要來看我首度獨立跳傘。可不能讓他失望。
七千英呎。
我必須假裝背上那塊隆起不存在。我的肩胛骨後方現在已經凸起了好幾英吋,隆起處像個錐形一般向下延伸到腰部。有天早上我醒來,發現這個奇怪的白色突起變成了棕灰色,就像一個巨大的瘀青一樣,蓋住我三分之二的後背。但我不覺得害怕。至少不是害怕那塊隆起。不知怎麼地,我覺得被人發現比較可怕。
但是媽媽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妹雪瑞的芭蕾成果展上,而且只要穿上超級寬鬆的連帽上衣,我就可以成功不讓家人發現背部的腫塊。
八千英呎。
尼可的笑聲越來越大,有點吵。高度計上的數字越來越大,他的腿也開始焦慮地抖起來。
我覺得自己這輩子就是在等待這一刻。
畢竟,我的身體裡有著飛行的基因──有時我會覺得,這就是非裔美人空軍英雄老爸給我的最大禮物,然後媽媽再用她淺色的皮膚和淺褐色的頭髮做包裝紙。雖然我外表比較像媽媽,但大家都說我的內心就是年輕的羅伯˙歐文上校。現在正是時候,我總算可以從這架完美飛機上一躍而下來證明自己的能力。我在教練陪同下已經跳了幾十次了,但這是我第一次獨自高空跳傘,這一舉會讓我更接近飛行的夢想。過去這幾天,因為期待,我的心跳速度加快,眼睛和耳朵也因為一直保持在高度警覺狀態而感到疼痛。
就連我這幾個月以來暴風生長引發的持續饑餓感都被身體裡不停瘋狂攀升的腎上腺素給抑制住了。我試著慢慢深吸一口氣,但我的心臟跳得好用力,都快從喉嚨跳出來了。胸腔充滿空氣的同時,我身上的跳傘用具和連身服也緊了起來,很不舒服。在飛機引擎的隆隆聲響中,我想像著布料被撕裂的聲音。這下我真開始緊張了。
我第一次見到跳傘用連身服的時候,興奮地像個傻子一樣,連身服的顏色和戰鬥機飛行員的制服一樣是橄欖綠色。細看我才發現連身服原本的顏色應該更亮,是久用褪色了。這次我再套上連身服,不意外,胸口處變緊了。現在我很怕這身舊衣的車邊會裂開,我刻意吐氣,希望可以讓身體縮小一點。
跳傘裝備還是很緊,所以我把它稍微放鬆一點。
九千英呎。
我們的教練法蘭茲過來替大家檢查配備,便立刻要我束緊胸帶。接著他便開始二度檢查所有配備。我聽不太見他的聲音,尼可和海莉做什麼我就照著做,在需要的時候回個「好」。
法蘭茲把手伸過來打開架在我安全帽上的小型運動攝影機。我的下臂還綁著另一支攝影機。整個高空跳傘的過程都會以高畫質影像紀錄下來,供我日後反覆觀看。但我其實只想專注在這一刻。活在當下,記住這個感覺。
我們已經遠超過雲層,遙遠的地球就像一張地圖一樣。雖然此刻我已興奮到了最高點,想要把每一秒都深深地烙印在腦海裡,但是飛機引擎的聲音不停地攻擊我,使我頭痛。我決定忽略這個噪音。我要在跳傘前一分鐘好好感受一切。就快來了。
我只想往下跳!一萬英呎。
教練下了指令,我們便伸手拿出上方的氧氣面罩。我把面罩罩在臉上,吸了幾口似曾相似、帶有金屬味的氧氣,我的胸腔溫度便降低了幾度。
尼可轉向我,比了一個讚。他的眼睛看起來比平常大、眼神比平常野。我把裝備的胸帶放鬆了幾零點幾英吋。後背詭異的癢痛感令人難以忍受,所以我盡量專注在呼吸上。
一萬一千英呎。
此時飛機忽然劇烈震動了起來,我們的屁股全都飛離了座椅,然後又再猛地掉回座椅上。接下來還有幾次餘波,我們笑一笑就過去了,然後氣流就穩定了下來。我腦中快速閃過剛入軍校第一次搭小飛機的情景。亂流把我們往上拋,有的學生大聲尖叫、有的人哭了。還有幾個人把嘔吐袋裝得滿滿的。但我沒有。
我笑了。
高度、飛行有些特性非常吸引我。也許是因為我爸是空軍飛行員。小的時候,我總是會抬頭看看是否能在天上看到爸爸的飛機。也有可能是因為爸爸請假在家時,讀了萊特兄弟和女飛行員艾蜜莉雅.埃爾哈特(Amelia Earhart)的故事給我聽。
或是根本是因為基因。
尼可是對的。我是個怪胎,一直以來都是個怪胎。
我喜歡當怪胎。
感覺距離起飛已經過了好幾個小時機身才終於往前傾,飛行員終於達到指定高度,可以拉平機頭了。
一萬五千英呎。引擎的噪音平靜了下來,現在是快樂的嗡嗡聲。
法蘭茲打開機門。我感覺好像本來有人摀著我的耳朵,然後忽然把手拿開。強風灌入,大聲呼嘯著。一秒之內,狹小機艙內原有的溫度就這樣全被吸了出去。我便迫不及待地用顫抖著的雙手拿掉氧氣面罩和機內對講機。我不需要這些東西了。幾分鐘之後我們便會以極限速度比賽衝回厚重的大氣層中。
法蘭茲進行第三次配備檢查,幫我把身上的背帶整理好。我的視線沒有離開機門外。跳傘的人一個接著一個消失。接著是海莉,她深吸了一口大氣便跳下去了。尼可給了我一個燦爛的微笑,比劃了個十字架,踏出機艙。
機上只剩下我和法蘭茲。我走到艙內長凳的盡頭。馬上我就到了門邊,望向外面,空無一物。美麗的天空在世界的盡頭渲成一片白。
「菜鳥,準備好了?」法蘭茲在咆哮著的風中大聲喊。
我豎起大拇指,給他一個我的招牌蠢蛋笑容。我深呼吸。只剩我和一望無際的湛藍天空了。
我來了。
「三……二……一……」我一躍而下。
20180116_2 Tyler
自由落體的過程中,我的五臟六腑翻攪著,身體也感覺快被撕裂。我在空中打滾,忽然看見小小的紅色飛機在我上方翱翔,但是一陣天旋地轉之後就掉出視線外了。風像一道水流一樣打在我的臉上,腎上腺素隨著我的尖叫聲飆升。
此時我照著之前受的訓練立刻把四肢伸展開來,於是我的身體就這樣穩定了下來。我向下看著距離我一萬英里處的雲層,雲層上方空無一物。除了已經展開的降落傘之外,沒想到我竟然也可以看見其他還在自由落體中的跳傘員,散布在空中成為一個個小點。有一支打開的降落傘消失在蓬鬆雪白的雲層中。重力加速度把我的身體向下拉,自由落體的起初的震動感慢慢消失。我越掉越快,腎上腺素卻讓我越來越興奮。
「耶~~~!」我大叫。但是我的聲音在自己能聽見以前很快就被拋在遙遠處了。我身上的每一個細胞都在顫動著。空氣非常冰冷,但我吸入的每一口氣都讓我真實地感覺到自己活著。
我動脈中的血液以全速竄流,此時我忽然出現了一個瘋狂的衝動,想要揮動雙臂。
但是後背一陣劇烈的痙攣馬上扼殺了這股衝動。
我的體內、我背後的隆起處,好像有什麼東西準備要爬出來。這畫面閃過腦海的同時,一股深層的恐懼感席捲而來。這種痛楚蒙蔽了我的視線。
我在空中往下墜,但是卻無法擺脫幽閉恐懼感。我的雙臂好似被綁在身體上了。我得掙脫!
我向後看,此時卻聽見了一陣撕裂聲,不會錯。有爪子深入我的胸腔,想要把我撕成兩半,把我舉向天空,向兩側撥開。一陣慌亂中,我便把減速降落傘從傘包上扯下來。但傘沒有開。這麼用力一扯副傘好像有點幫助,因為我身體一側被拉力往上帶,但是我的身體還是沒有打直,也沒有穩定下來,我開始失控旋轉。
我下墜經過其他傘員時,他們全都在尖叫。尼可哭喊著我的名字,海莉發出驚恐的叫聲。世界從我身旁閃過,我帶著痛苦和恐懼大叫著。
那時,我知道自己要死了。旋轉著的天空白大於藍。有東西扯著我的身體,就像要把我的手臂從身上扭下來一樣。我試著轉頭看看究竟是個什麼東西。
我的身體又轉了一圈,我看見一個黑色的影子撲來,又猛然消失。
怪的是,我可以***斜體字型感受斜體字型***到它在動,感覺就像是我的肩胛骨中有個旋轉壓力點。我的身體又再一次隨著氣流旋轉,黑影又出現了,這次我看仔細了。血濺了出來。一片粗糙的什麼揮動著,上面有深色的斑點,這形狀似曾相似。
是翅膀。
這翅膀好像會讀心術,它又動了起來。
靠,是翅膀。是個翅膀!
從我背上長出的翅膀!
我努力想要讓身體停止旋轉,我想看看另一側的肩膀,但是太痛了,我無法轉頭。我哭了。
成千的小點點扎著我的臉和雙手。是雲。
我的家人會親眼看著我墜地身亡。
不!
我喘著大氣,用力閉上雙眼對抗令我頭昏的天旋地轉,試著集中注意力。
但還沒結束。我可以感覺到另一隻翅膀蜷在我的左後背。我想像著翅膀移動、彎曲──然後它便揮動了起來。疼痛更加劇烈了,不過現在的痛像是做了一百下伏地挺身的健康痛。這隻翅膀被傘包困住了,傘包的袋子像巨人手指一樣扣著翅膀。我因為疼痛和使力叫出了聲音,膀臂便快速抽動。我用盡吃奶的力氣向兩側使勁推,壓力使我的眼睛和耳膜都鼓了起來,我覺得自己快要爆炸了。
我左側的身體出現劇烈的灼痛感,感覺巨人的手好像出了點力。我再次用力推,左翼便衝破了跳傘服,從背帶的手臂空隙中穿了出來。一股強大的警報解除感貫穿我的全身。在這短暫片刻中,一切好似都沒有問題,直到強風打上我的新翅膀,把它們向後扭。我痛得大哭,但打在翅膀上的強風卻也減緩了身體旋轉的速度。
***斜體字型靠斜體字型***──原來身體打轉是因為右翅使我身體失去平衡,擾亂了空氣動力。但現在我有一對翅膀,出現了一線希望。
如果無法順利掌控翅膀,我便必死無疑。降落傘現在整個纏在我腿上,完全沒有作用。我展開雙手,想像新生成的翅膀模仿著我手臂的動作。
翅膀竟也真的照做了。
約與雙臂同長的翅膀因為還不夠強壯,已經又累又疼痛。我的頸背因劇烈疼動哀嚎著。翅膀的初試啼聲有點狼狽,稱不上飛,只能勉強算是微微滑行。我一邊下墜一邊試圖保持雙翅展開的狀態,我覺得自己兩隻手臂下方好像綁著兩塊大木板,而我則是在洶湧的水流中努力要壓住這兩塊板子。
我整個人成了人體降落傘,不過不太好使。但說到底,當個活體降落傘總比當隻死鳥好。
這一切僅發生在短短幾秒之中,而我的求生時間還更短。樹木、大樓、硬邦邦的馬路馬上就要來了。草地上布滿降落傘的橫屍。我看到有人在跑,有人跑掉、有人跑向我。下墜的速度變慢了,但還不夠慢。
離地數百英呎時,空氣變得溫暖,濃度也升高了。我看見降落區邊緣有一大叢矮木。我發出了一個使勁的聲音,試圖想要靠近樹叢,我努力舉起左翼、把右翼放低。我成功了,這下可以靠邊降落了。
我的雙腿拖過樹叢的枝葉,枝葉勾在降落傘上,幫助我減速。下一個心跳之前我就撞上地面了。我雙腿彎曲,身體側面著地。其中一隻翅膀折在我的身體下方,很痛;另一隻則落在我的肩膀前方。
全身都好痛。
完全的靜止狀態僅有片刻,我慢慢、痛苦地翻了個身讓肚子朝下。翅膀──我自己的翅膀──受傷的一端從草地上拖過。我隱約發現翅膀的淺褐色其實就是我的髮色。我後背的肌肉顫抖著。深呼吸之後,我爬起來,雙手雙膝著地。地面好似在我下方搖晃著。我的視線好像已經定在近焦,仔細盯著被壓爛的葉片還有小土塊的細節瞧。小昆蟲紛紛逃出我的陰影。
我感覺很渙散。
我緩緩撐起自己的身子,身上還纏著繩子和傘布。我的心跳極快,但不至於喘不過氣。背痛已經慢慢緩解,現在身上只剩下撞擊落地造成的疼痛感。我從剪不斷、理還亂的帶子、繩子還有傘布中爬出來,搖搖晃晃地直起身子,踉蹌向前走。
「泰勒!不要動!」
我跌入父親的懷中。
「謝天謝地,我的兒子。哪裡痛?怎麼搞的……?」
爸爸攙扶我坐下,用他總是能安撫我的冷靜口吻向我說話。他總是知道該怎麼做。頭昏腦脹的我只能無助地看著他。我的喉嚨鎖住了。我一直很努力想要達到他的標準,想要變得跟他一樣優秀,不想愧為羅伯˙歐文上校的兒子,但是我這次卻差點把自己搞死,還變成了一隻大怪鳥,把大家給嚇壞了!
爸爸幫我解開傘包的背帶。要卸下這裝備可不容易。
「我替你檢查檢查。」我倒抽了一口涼氣。我可以感覺到爸爸在檢查背部的時候用手順開我的羽毛。「天啊!泰勒!怎麼回事?」
接著他輕輕地把我的護目鏡移到安全帽上方。爸爸難掩臉上震驚的表情。這是這輩子我第一次覺得爸爸可能要哭了。
「泰勒!你的眼睛怎麼了?」忽然間一大群人圍住了我們。
有人用攝影機對準我,簡直像是拿槍管指著我一樣,我下意識地舉起手自我防衛。
爸爸跳起來,開始像在軍隊裡一樣發號施令。我試著直起身來,幾處的肌肉不自覺地使了力,於是我的翅膀收到背後,回到原本的隆起位置,被破裂的跳傘服微微扯傷。這個動作引起了這一小群人的注意,在他們的驚呼聲中,我又縮回去了。
世界又開始旋轉了起來。我一個絆倒跌到了地上。我見到的最後一幕是架在我肩上的運動攝影機直直地對著我的臉。
我昏了過去。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伊卡洛斯之翼:凌空而生的圖書 |
 |
伊卡洛斯之翼-凌空而生1 作者:Jessica Pawley 出版社:威向文化 出版日期:2020-07-20 語言:繁體中文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09 |
恐怖\驚悚小說 |
電子書 |
$ 209 |
科幻/奇幻 |
$ 236 |
西洋驚悚/恐怖小說 |
$ 269 |
文學 |
$ 299 |
大眾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伊卡洛斯之翼:凌空而生
我的過去
我的現在
我的未來
全都毀於一旦
我,到底是誰?
17歲的少年泰勒,聰明年輕,長相英俊,他立志成為戰鬥機飛行員。他的人生已有藍圖,一切都依著計畫進行。
但一切計畫就在他生平第一次單人跳傘時戛然而止了。就在半空中,泰勒經歷了一場可怕的變形,而這一切都被錄了下來。泰勒瞬間成了爆紅的網路名人!每個人都想要得到他的一部份,甚至連邪惡的進化公司以及一個名為天使信徒的宗教狂熱團體都想捉到他。
影片傳遍全世界的同時,也讓泰勒認識了其他和自己相同的人。出於本能,他們聚在一起組成了新的種族「空隊」。這支前所未見的特異種族,想要生存下去,唯有一條路──展翼高飛!
本書特色
如果... ...你突然長了翅膀?
如果... ...無法明白?
如果... ...你不是唯一一個?
作者簡介:
作者(大家都稱她傑斯),滿28歲時已有英文和媒體的大學學位,和優等英文碩士學位。她的論文研究是關於網路社群、互動電子書對閱讀習慣的影響。她在求學過程中也開始投入寫作,期間總共寫了9本小說和6張短篇小說。其中的幾部小說她自己利用網路發行,她的作品在英文電子書平台Wattpad發行後已經點閱累積超過100萬次! 除此之外,受到粉絲熱愛,這部作品已被改編成繪圖、粉絲自創小說和許多分支的粉絲網路群。
紐西蘭出版社Eunoia Publishing 和 Steam Press在2016年找傑斯合作,出版這套小說。2017年9月23號在紐西蘭正式出版,有製片公司在評估改編成為電影。
章節試閱
「泰勒,你真是個怪咖。」
我檢查著我的腕式高度計,沒理會尼可。一千英呎。我提高音量唱著。「血腥、血腥,殘暴的死法。」
尼可用指關節輕敲我的頭盔,我的耳機再度傳來他模糊的聲音。「嘿!泰勒的地球之歌──首次獨跳的最佳主題曲。」
我把麥克風壓近嘴邊,這樣才能好好大唱副歌。「血腥、血腥,殘暴的死法。他將不再~一躍而下。」
「小怪胎,你長大的速度未免太快、你的歌聲未免太爛。」
「我的歌聲可能很爛,但至少我聽的音樂很有品味,你他媽這個──」
耳機傳來了另一人的聲音。「各位,專業,好嗎?不要用對講機閒聊。」
我...
我檢查著我的腕式高度計,沒理會尼可。一千英呎。我提高音量唱著。「血腥、血腥,殘暴的死法。」
尼可用指關節輕敲我的頭盔,我的耳機再度傳來他模糊的聲音。「嘿!泰勒的地球之歌──首次獨跳的最佳主題曲。」
我把麥克風壓近嘴邊,這樣才能好好大唱副歌。「血腥、血腥,殘暴的死法。他將不再~一躍而下。」
「小怪胎,你長大的速度未免太快、你的歌聲未免太爛。」
「我的歌聲可能很爛,但至少我聽的音樂很有品味,你他媽這個──」
耳機傳來了另一人的聲音。「各位,專業,好嗎?不要用對講機閒聊。」
我...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