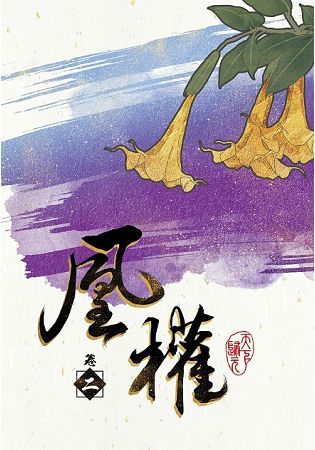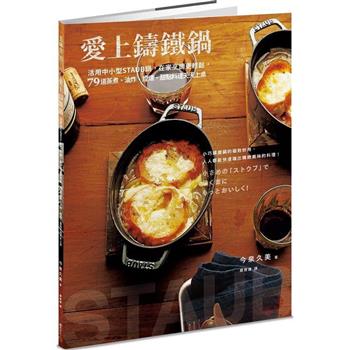第五十九章 給我賠禮
瀟灑決斷數字詩,一詩出而滿堂驚。
華宮眉踉蹌退後,手扶著几案,怔怔良久,眼淚斷線般滾下來。
寧弈把玩著手中的酒杯,唇角笑意薄如落花。
不如拋一片痴心,不如拋一片痴心。
這絕頂慧黠女子,竟用這樣的方式,拒絕了他。
只是,這麼一拒絕,卻也令他窺見了她深沉渺遠內心裡,一些不願為他看見的心思。
有一種女子,如域外蓬萊,遠在高天山海之外,想要走近,先得穿過重重迷霧。
亂花漸欲迷人眼,然而只要他始終在高處,何畏浮雲遮眼?
他笑著,舉杯,遙遙對鳳知微一敬。
鳳知微挑挑眉,遙遙對上首一禮,含笑歸座,一句話也不肯多說了。
眾人驚異佩服的目光跟隨著她,想不到這出身曖昧的鳳氏女,竟然多年來明珠蒙塵,如今一朝拂拭,塵盡光生,竟比那些頻頻參加詩會博得好大名聲的世家之女要強上不知多少倍!
這才想起鳳知微那個飽受非議特立獨行的母親,秋府大小姐秋明纓,當年也是馳名帝京的女中人傑,號稱文武雙絕,詩書琴棋俱佳,只是後來帶兵上陣拜為女帥,武功戰績太過耀眼掩蓋了華美文采,倒讓人忘記了她也曾輕衣緩帶,臨亭賦詩。
不用問,鳳小姐一直跟隨母親過活,如此出眾才華,定然來自母親日夜教導。
「不愧是當年火鳳女帥之後。」若有所思凝望她半晌,天盛帝終於緩緩開口,「家學淵源,名不虛傳。」
這句「家學淵源」,和以往那句深含諷刺的「家學淵源」,絕對不可同日而語,一旦出自天盛帝之口,代表的是一種態度。
眾人立即心領神會。
「火鳳女帥文武雙絕,當年便已名聞帝京,鳳小姐不愧名門之後……」
「想當年女帥英風俠彩,令人神往……」
「不見女帥久矣,想必風華更勝當年……」
鳳知微手按桌案,面帶謙虛微笑,平靜傾聽,半邊臉沉在宮燈的淡紅光影裡,無人看見她臉上神情。
無人發現她眼中晶亮微閃,水光盈動。
娘。
多年前春日宴,妳也曾臨屏賦詩,一詩出而滿殿驚。
妳也曾含笑簪花穿宮入殿,載了那一身萬人榮光。
妳也曾金殿之上面對挑釁,一杯酒當殿擲出,杯酒盡而篇章出。
如今我重現妳當年慷慨傲然風華,鬥酒詩百篇,笑傲帝王前。
終換來帝王緬懷往事一番感歎。
有他這句,從此後再無人可以欺妳,再無人可以拿那當年舊事羞辱於妳。
她晶亮著眼神,想要再喝一杯酒,讓那溫醇辛辣之味,沖去此刻心中熱潮洶湧,卻摸不到酒杯──酒杯已經被她給做戲擲出。
一杯滿滿的酒突然遞到她面前,赫連錚賊兮兮在她耳邊笑,「喂,一杯酒而已,妳不要感動得想哭。」
鳳知微轉過臉,眼神內晶瑩已去,目光溫潤,含笑看著赫連錚,「謝謝。」
赫連錚看著她的笑容微微怔了一瞬,隨即又恢復了平日的散漫豪氣,胸膛一拍,「小姨就是我的心我的肝我的命根子寶貝兒,別說一杯酒,就是妳要我不娶另外九個老婆我也認了!」
什麼九個老婆?鳳知微怔了一怔,才反應過來他又繞回去了,白了他一眼,笑道,「放心,小姨既然是你的心你的肝,肯定會為寶貝侄子的十個老婆操心的,一個都不能少。」
赫連錚笑而不答,給自己斟酒,只是那杯酒,遲遲擱在唇邊,不飲。
因為選妃未能得償所願,小姐們情緒都有些低落,常貴妃見著,在天盛帝耳邊低語幾句,天盛帝眼睛一亮,隨即笑道:「朕就知道妳最有心。」
「陛下誇臣妾,臣妾這次卻不敢受。」常貴妃笑道,「這可是魏王的孝心,臣妾也是沒見過的。」
她拍了拍掌,四面突起樂聲。
樂聲突如其來,音調華麗古怪,帶幾分清遠飄渺,又帶幾分詭異跌宕,隱隱含著奇異的鼓動節奏,聽著人的心似緊似鬆,砰砰的跳起來。
四面卻不見奏樂之人,只覺得那節奏忽遠忽近,跳脫放縱,一收一放間,似要將人的脈中血都擠出來一般,激得人脈動怦然,一些嬌弱的大家小姐,不知不覺已經紅暈上臉。
僅是樂聲便已先聲奪人,天盛帝一改一直漫不經心的神態,丟了杯子,微微直了身。
四面的宮燈的紅光突然暗了暗,暈紅光芒一閃。
紅光一閃,夜風徐來,殿前蓮花池上,忽有人自一朵碩大蓮花上飛舞而起!
披妖紅金帛,舞衣帶當風,靈蛇髻芙蓉面,雙眉繚繞如妖,眉心間一點金色波羅花,灼灼如相思。
她抱一柄奇形嬌小金色琵琶似的樂器,纖指起錚錚之聲,似近似遠奇異樂聲裡,輕薄嬌軟雨後蓮花間,人在花上步姿蹁躚,忽亂得亭亭蓮葉翻覆搖動,忽撥得濯濯碧水清波微濺,纖腰柔指,如絲綢般翻來疊去,軟至不可思議,諸般動作也就更加妖嬈魅惑,明明是端莊飛天之舞,竟也給她跳出幾分冶豔來,那冶豔寓於端莊之中,若隱若現,反而比豔舞更動人心魄。
座中女子,人人臉色嬌紅,座中男子,人人呼吸緊迫。
天盛帝努力自持,仍舊控制不了呼吸急促,只覺得那女子遠遠舞來,明明容顏不清,但那一顰一笑,容華極盛,便彷若只對自己一人。
獻上這舞娘的二皇子立即湊趣的上前來,笑道:「父皇,這是來自西涼的舞娘,自幼以蠻荒密林之地的奇特藥草洗身伐髓,不食煙火之食,薰陶得體軟如綿氣息清新,又善花上之舞,和我中原風韻大異,您看如何?」
「好!」天盛帝忍不住大贊一聲,隨即發覺失態,趕緊正正臉色,道,「正當戰事,理當節儉用度,不得靡費歌舞,這要傳到前方,也太不像話了。」
「父皇,娘娘五十整壽,若連歌舞都無,也太委屈娘娘。」二皇子笑道,「何況這女子舞的也是我朝戰舞『陽關烈』啊。」
「這是『陽關烈』?」天盛帝愕然,仔細傾身看了看,才喃喃道,「戰舞能舞成這樣?真是奇葩啊……」
二皇子露出喜悅神色。
常貴妃神情就有些複雜,幾分高興幾分無奈,年老色衰的妃子,要想維持住自己在宮中地位,能做的,也就是獻美於皇了。
一舞畢,那女子飛下蓮花曼步而來,衣袂飄舉,妖紅金帛長長搖曳於身後,姿態風華,令眾家以氣質高華自居的小姐羞愧得無臉見人。
她在階下盈盈拜了,聲音並不是鶯聲嚦嚦的嬌脆,微帶低啞,反而更加引人綺思,令人想起紅羅帳鴛鴦被,想起所有粉豔的溫軟的物事,而她下拜時微微傾下的頸和胸,是天下所有男子夢寐以求的嚮往。
這女子所有風情,都是端莊與妖豔共存,因其特別,反而更加極盡誘惑之能事。
天盛帝眉間閃耀著喜悅的光,常貴妃十分有眼色,立即命人賞了這舞娘,安排她在自己宮中休憩,那女子抱著琵琶盈盈而去時,猶自不忘回眸一瞥天盛帝,眼神嬌媚,看得天盛帝險些把持不住追出去。
座下皇子們看著那女子離去,眼神複雜,只有寧弈,雖然一開始對那舞娘的美貌和妖豔表示了極大的興趣,此刻反而淡定下來,隱在暗紅的燈光後慢慢飲酒。
鳳知微望著他,心想他明明舊傷發作,酒卻喝得極多,是興之所至,還是……心緒不穩?
又想這獻姬一事,怎麼會由二皇子出面?這是五皇子的娘的壽辰啊。
她心中有隱隱不安,按住了一直喝酒的赫連錚。
座上,天盛帝心緒極好,越看常貴妃越順眼,笑道:「上次想起要給妳寫個壽字,臨到頭來卻忙忘記了,今日便當堂補給妳,如何?」
常貴妃目光一亮,壽辰有皇帝親筆寫壽字,是莫大的恩榮,而對於後宮,更有一番特別意義──天盛帝只給一個女人寫過壽字,就是早薨的常皇后,三十歲壽辰時,天盛帝為她寫了個斗方。
如今天盛帝一旦給她寫了這個壽字,其中意義,自然非同凡響。
她因此在壽辰前夕多次暗示過想要一個壽字,天盛帝都不置可否,如今總算這舞娘投了他所好,開了金口。
喜不自勝的常貴妃,急忙命人送上筆墨,筆墨紙硯是現成的,先前下發的還有多餘,當即送上來。
天盛帝就在案上援筆濡墨,筆走龍蛇,一個鬥大的壽字頃刻便成。
暗淡紅燈燈光下,墨蹟濡滿,字字凸出。
「雄健灑脫,鸞翔鳳翥!」常貴妃連聲贊好。
常貴妃帶著的那兩隻筆猴,向來是看見筆墨就歡喜,聞得墨香,從筆筒裡鑽出來,吱吱叫著去捧那斗方。
天盛帝大笑著,撒開手。
金光一閃!
兩隻筆猴觸到那斗方,突然狂躁,厲聲一嘶電射而出,直撲天盛帝面門!
近在咫尺,勢如閃電,天盛帝正撒開手歡暢大笑,侍衛還離得遠,常貴妃驚得忘記動作,哪裡還救得及?
「咻!」
又是一道金光,自階下飛射而上,後發而先至,角度極佳的先後撞飛兩隻筆猴,撞得那兩個小東西吱吱在地下打了個滾,自趕來的侍衛腿縫中一鑽不見。
階下,寧弈身子前傾,臉色蒼白,手中金杯已無。
驚魂初定的天盛帝,望了他一眼,勉強鎮定著啞聲道:「弈兒,去查──」
一句未完,他突然晃了晃,倒了下去。
手背上,兩道烏黑的抓痕。
==
一場皇家富盛榮華宴,以皇帝被刺收場。
誰也沒想到變起頃刻,誰也沒想到那兩隻可愛的天天隨侍常貴妃身側的筆猴,竟然會在壽宴之上爆發。
壽星轉眼變災星,常貴妃脫去簪環哭哭啼啼,整日跪在天盛帝寢宮前自陳冤情,卻沒人有空理她──天盛帝身中奇毒,昏迷未醒。
她要辯白也很難辨清楚,那兩隻筆猴朝夕隨在她身側,卻攜帶奇毒,她沒嫌疑誰有嫌疑?
然而此時問題的關鍵其實已經不是查清嫌疑了──皇帝一倒,所有人不可避免的想到,萬一這毒治不好,聖駕西歸,身後這至尊之位,誰坐?
這真是個讓人想起來就忍不住血脈僨張的命題。
騷動,嚴重的騷動。
京中的消息還在封鎖,西平道的長寧王卻已經派人前來京城,說是王爺給陛下和皇子問安,準備明年聖駕南巡的物事採買,並表達了王爺對帝京和皇帝的思念──很明顯長寧王已經得了消息,這是來試探了,一旦皇帝駕崩,這思念之情一定會到達頂峰,長寧王十有八九會難以壓抑蓬勃的思念,並用豐滿的大軍和鐵蹄來帝京表達的。
二皇子原本管著虎威大營一部分營務,聽說最近頻頻召集將領們開會。
七皇子派的幾位閣臣和尚書,提議在國家無主的狀態下,由閣老指定親王監國,至於人選──那批人表示,哪位王爺都可以嘛,但是當此非常之時,亂像將顯,國家急需賢明厚德之人安撫四方。
賢明厚德名聲在外的,自然是七皇子。
聽說宮中也莫名其妙的死了幾位妃子。
一片鬧哄哄中,原本最該有動作的寧弈,反而全無動靜,只做著自己該做的事──天盛帝昏迷前曾說過,此事交他查辦,他也就真的煞有介事的主持查辦此事,對外界的風雨流言蠢蠢欲動,似乎毫無感覺。
「這事裡有很大問題。」鳳知微在自己的魏府裡,對她家衣衣道,「兩個可能,第一,寧弈幹的,第二,皇帝自己幹的。」
顧少爺看鳳知微再次擺出了分析朝政的架勢,很有眼色的慢吞吞擺出了一袋小胡桃,抓出一個大的,再抓出一個小的。
鳳知微很自然的接過去剝,剝開小的那個,道:「你還記得那天皇子們一起在我府中喝酒的那次嗎,當時五皇子就把筆猴拿出來顯擺,我記得那時筆猴毛色金燦燦的,這次看的時候,卻發現黯淡了很多,宮裡不會缺吃的,所以絕不會是營養不夠,我懷疑問題不在那墨上,當時筆墨大家都用了,沒有異常,問題就應該在那猴子上,但是接觸過那猴子的人太多了,這根本就查無可查。」
「寧弈。」顧少爺把剝好的胡桃接過去吃了,也不知道說的是凶手是寧弈還是他要吃胡桃寧弈。
「或者就是天盛帝。」鳳知微剝開那個大的,「他想藉這個事,看看眾家兒子的心地,這也可以從寧弈目前的動作看出點端倪來,別人都蠢蠢欲動,他還在做戲,做給誰看?誰還能看見?不就是天盛帝?不過話又說回來,我絕不相信天盛帝那麼自私的人,會捨得使苦肉計來試探兒子,他有更好的辦法可以試探,何必苦了自己?那麼,寧弈又是在做在誰看?」
「如果是寧弈動手,他好不容易將天盛帝弄倒,卻白白放過這個機會按兵不動,那又是為什麼?」鳳知微百思不得其解,無意識的將胡桃送進自己嘴裡。
一隻手突然伸過來,一把掐住她的下巴,奪過那只已經送進嘴一半的胡桃,丟進了自己的嘴裡。
鳳知微滿腦子的陰謀詭計推演唰一下飛到九霄雲外,目瞪口呆的望著那個還沾著她口水的胡桃進了顧少爺的嘴。
「我的。」顧少爺滿意的道。
也不知道指的到底是什麼。
鳳知微:「……」
半晌她壓下滿臉的紅暈,拍拍顧少爺,苦口婆心的道:「少爺,我跟你說,這樣子是不對的,不乾淨。」
「妳不乾淨?」顧少爺問。
鳳知微:「……」
「我不乾淨?」顧少爺再問。
天底下沒有比你更乾淨的!我天天給你洗內衣我知道!鳳知微含淚:「……」
「胡桃不乾淨?」顧少爺這回語氣嚴肅了,這個問題比前兩個更要緊。
鳳知微深呼吸:「……」
「那哪裡不乾淨?」直線思維的顧少爺難得的茫然了。
「這樣子。」鳳知微氣若遊絲的還在試圖解釋,「從嘴裡搶出來不乾淨……」
顧少爺突然湊過來。
他一向避人三尺之外,從不主動靠近人,這是他第一次湊近人,鳳知微被驚得忘記動作,就看見雪白的輕紗微風拂動,輕紗後那張若隱若現的臉越來越近越來越近,隱約間眼前若有光華突生,鳳知微唰一下閉上眼。
隨即覺得一隻有胡桃香的微涼手指,輕輕摸上了自己的唇。
手指動作很輕,似帶著幾分猶疑,先是輕輕一觸,又細細撫了撫,似乎被指下光滑柔軟所驚,於是又摸了摸。
鳳知微身子一顫趕緊偏頭讓開,睜開眼看見顧少爺已經回到原位,偏著頭,看著剛剛摸過她唇的手指,似乎在找上面的灰。
鳳知微啼笑皆非,正想轉移他對於「乾淨」這個問題的注意力,不想那廝沒有最驚悚只有更驚悚,看完了手上沒有灰,又將那摸過她唇的手指,去摸自己的唇。
手指雪白,沾唇輕輕,紅唇如火,如玉下頷。
那一個指在唇邊的姿勢,微微偏頭帶幾分迷惑的神情,散發著甜蜜而純的氣息,天然誘惑。
鳳知微唰一下站起來,再不好意思看那手指一眼,飛奔而出。
決定了!
她這輩子再也不吃胡桃!
==
那日從宮中回去後,秋夫人很快就給鳳夫人母子調換了院子,在宴席上大出風頭的鳳知微也開始接到各種請柬,要不是現在正是多事之秋,各府沒什麼心思辦各種茶會詩會,鳳知微的邀請會堆滿屋子。
帝京第一才女已經換人做,新任第一才女卻不再涉足任何社交場合──她病了。
何止是病,鳳知微還想著要把鳳知微給「病死」。
魏知這個身分如果想繼續下去,鳳知微就不能再招人眼目,那日宮宴被寧弈設計,誤打誤撞出了風頭,原非她本意,再不韜光養晦,難免惹出禍端。
先病一陣子,不見外客,再以養病為名「出京」,把鳳知微這個身分合理的抹出人們視線再說。
稱病之前,她去了鳳夫人的院子,轉告了陳嬤嬤的話。
「我知道了。」坐在暗處的鳳夫人,臉上的神情被飛揚的塵光模糊得不清,只點了點頭。
鳳知微卻從那語氣裡聽出幾分疲憊和蒼涼。
「妳做得很好。」鳳夫人抬頭望她,嘴角一抹笑意,「宮宴上的事,我聽說了。」
鳳知微輕咳一聲,竟然有點不知道怎麼回答,這許多年來娘很少誇讚她,她是個嚴厲的母親,從她記事開始,她便被不停的逼著學很多東西,不僅有經史子集詩詞歌賦,還有天文算數地理兵法之類的實用學說,甚至還會搬出前朝厚厚史書,和她「以史為鑒」,看歷朝將相當政得失。
娘沒教她的,是女紅裁剪之類的女子最該學的東西,她曾以為娘不會,然而在披甲上陣之前,娘也是堂堂秋府的大小姐,這樣的高門巨戶家的小姐,怎麼可能沒學過這些?
此刻乍然聽到娘的誇讚,她臉上微微綻出薄紅,心裡流轉著小小的喜悅。
「只是……妳不該這樣。」鳳夫人話風急轉直下,她愕然望著母親,鳳夫人站起身,憂傷的望著皇城方向,「我很早就和妳說過,切勿好高騖遠,切勿喜好賣弄,切勿爭風鬥狠……如今妳出去一趟,竟然都忘記了……」
鳳知微退後一步,張口結舌的望著鳳夫人──她怎麼可以這樣說她!
她何曾好高騖遠,何曾喜好賣弄,何曾爭風鬥狠,何曾──輕薄如此?
不過是心中一個小小願望,從聽見多年前火鳳女帥英風豪烈事蹟後便湧動起的一個小小願望,她希望能通過自己,讓被迫墮於塵埃的那個明烈女子再次昂起頭來,讓她因為女兒的驕傲和出眾,再次獲得世人承認。
她想給她掙回已經流失的尊重和榮光,就算不能重回人上,也最起碼能獲得世人平等看待。
原來,娘是這麼想的嗎?
原來她無論做什麼,在娘的眼裡,都是輕狂的嗎?
心一寸寸的沉,墜到月光的波心裡,漾出無限的涼……總是這樣,總是這樣,她僅有的熱血丹心只捧給那個人,卻每次都被棄若敝屣。
眼光一時不知該落在何處,她習慣性的垂下,一眼看見鳳夫人擱在椅上的汗巾。
松香色的汗巾,繡著精緻的大鵬展翅,還沒完工,一看就是給鳳皓的。
「呵呵……」鳳知微微帶譏諷的笑起來,真是的,傷心什麼呢,說到底還是自己傻,怨不得別人的。
「知道了。」她攏攏袖子,不再迴避眼光,深深注目鳳夫人半晌,「您放心,沒下次了。」
說完她跨出門去,再不回首。
一室暗淡的光影如水光動盪,被她毫不猶豫的拋在身後,那般浮漾的微光裡,她沒有聽見身後也如水光一般清淡的,一聲歎息。
==
鳳知微「出天花」,萃芳齋驅散傭僕閉門謝客,魏知整整衣冠,照舊活躍在天盛朝廷舞臺上。
局勢內裡暗潮洶湧,官員們一撥撥的見人串聯,各大王爺府邸車水馬龍,本該在貴妃壽宴後便回江淮道的五皇子,以需要伺候皇帝湯藥為名賴著不走,他是皇帝被刺案的嫌疑人,卻沒有好好的閉府聽勘──事實上現在也沒有人來勘他,太子薨,皇帝病,皇后早逝,常貴妃待罪,楚王拒絕主持政務,從內到外,無人可以主事,誰想主事別人也不依,內閣按下這頭翹起那頭,大學士們天天往皇帝寢宮跑,嘴角起的泡,一個比一個大。
而原先由五皇子主持的工部,再三向內閣遞帖子,指責戶部故意延緩京中九城城門修葺工程工銀發放,戶部則反唇相譏工部未曾做好通杭運河的工程,導致今年夏天南方大水沖毀堤岸,運送錢糧稅銀的官船無法通行,延誤了戶部回銀,戶工兩部吵得不可開交,連帶著扯出了工部尚書的侄子和南方大戶承辦漕運其中有貓膩,據說還打死了人卻又逍遙法外,扯著扯著扯上了刑部枉法縱凶,刑部不甘示弱,拋出當年的北疆於鄴糧庫以黴糧冒充新糧送往戰場導致兵敗的舊案,聲稱掌握了什麼什麼新證據──滾雪球似的,六部吵成了一堆。
「陛下再不醒,事情就大發了。」胡大學士在一次入宮回來後,憂心忡忡對鳳知微歎息。
「老相宜擇木而棲矣,卻不知誰家的樹比較結實些?」鳳知微開玩笑。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胡大學士捋捋老鼠鬍子,斜瞄她一眼,一搖三晃的走了。
鳳知微含笑看他遠去,心想楚王派最近也很有些騷動的,比如姚大首輔就有些心神不定,倒是辛子硯和胡聖山,一副安之若素樣子,辛子硯乾脆搬到修纂處去住,一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模樣,倒把青溟書院都交了給她。
那就靜觀其變吧,鳳知微也就外甥打燈籠──照舊,每日帶著她的顧大人去上班。
青溟書院目前還獨立於風波之外,自有其超然之態,自然也有人試圖拉攏,比如工部尚書就以品書賞鑒為名,給鳳知微送了好幾次珍貴典籍,鳳知微拿來翻翻,客客氣氣送回去,來回幾次,人家也就不送了。
鳳知微倒是有幾分疑惑,她供職內閣和書院,和六部沒有交情,這位工部尚書突然大獻殷勤,有點發人深省,但是誰都知道,現在的六部是渾水,碰不得,有這個拉扯的功夫,不如和顧衣衣剝剝胡桃,和赫連世子喝喝酒。
赫連錚現在不爬牆了,現在直接拎著酒來拜訪司業大人,他終於摸清了他家小姨的唯一缺點──貪杯也,於是今天「大漠醉」,明天「千谷醇」,後天「江淮春」,都是極品的令鳳知微無法抗拒的好酒,把他小姨和小姨的衣衣喝得每天眉開眼笑心花怒放。
赫連錚原先也眉開眼笑心花怒放,漸漸的臉便苦了──小姨又騙人!小姨的酒量根本就不是兩壺──她千杯不醉!
於是打著主意想灌醉小姨亂倫一次的赫連世子,無數次興高采烈的來,偃旗息鼓的去……
心情不好自然要找人發洩,最佳出氣包就是他小姨的弟弟他的親愛的內弟,於是可憐的鳳皓,在每次赫連錚和鳳知微喝酒時,被不斷使喚「溫酒去!」、「拿個汗巾來!」、「背我回去!」
鳳皓一向是沒公子命卻有公子派頭,嬌寵慣了的,哪裡吃得了這個苦,然而奇怪的是,雖然他的臉色臭比茅坑,但是居然乖乖忍了下來,和他當初一板磚拍倒國公爺的煞氣不可同日而語,鳳知微冷眼看著,心中倒有幾分疑惑。
她還有個疑惑一直放在心裡,終於有次在和眾人一起喝酒時,問姚揚宇,當初怎麼認識鳳皓的。
那批公子哥兒早給鳳知微和顧南衣整服氣了,現在鳳知微叫他們汪汪他們絕對不哼哼,姚揚宇姚公子聽見鳳知微問這個,斜著醉眼拍著他家司業大人的肩笑,「咱們哪裡看得上那小子?有次和楚王殿下在外面玩,碰見這小子探頭探腦,咱們要趕,殿下心情倒好,留下了,說他怪可憐見的,不妨帶著玩玩,讓他見識下帝京榮華也好,可惜這小子沒錢,兄弟們倒說幫他墊的,殿下卻又不許,說只有借錢賭的,哪有借錢嫖的?秋府家大業大,隨便拿出什麼來都夠用了……後來這小子不知怎的便不見了,現在又冒出來……我是看不上眼這小子,真不知道哪裡投了殿下的眼了……」
又是寧弈!
鳳知微一瞬間想到了秋府初見,想到了五姨娘萃芳齋床下的金鎖片,想到了鳳皓不斷的和娘要錢和那批公子哥兒的結交……其中似乎都隱約有寧弈的影子,隱在幕後,卻無處不在。
他是想要知道什麼嗎?
鳳皓身上,能有什麼令他感興趣的祕密?
還有這幾天,鳳皓雖然被赫連錚使喚來使喚去,但臉上有隱隱掩不住的興奮之色,又搞出了什麼事?
鳳知微酒杯擱在唇邊,遲遲不飲,看似神情意興遄飛,其實酒杯裡浮蕩的全是心事。
心事還沒喝乾,惡客已至。
「大人!」一個主事帶著一批人飛奔而來,神色倉皇,「刑部和九城衙門來了人,說書院窩藏重犯,要拿我們前去刑部衙門!」
「反了他!」姚揚宇今天又不管赫連錚的臉色,跑來蹭酒喝,年輕氣盛的姚公子聽見這話,爆竹似的蹦起來就捋袖子,「敢來青溟書院拿人?天盛建國到現在,還沒出過這麼荒唐的事兒!我去打發了!」
他氣勢洶洶帶了一批人就要走。
「慢著!」
這個人的話姚揚宇不敢不聽,回身怒道:「司業大人,我知道不得鬧事,但是沒道理欺上頭來還不反擊吧?」
「什麼事還沒搞清楚,急什麼呢?」鳳知微輕衣緩帶立在風中,還拿著一杯酒,笑吟吟道,「總得給人家說話的機會。」
遙遙指了指大門的方向,她道:「開門,不要讓人家堵在門口站累了,讓人進來說話。」
「司業!」姚揚宇急道,「刑部那批衙役和九城衙門那批狗腿子,最是禍害──」
「讓人進來。」鳳知微一個眼神過去,姚揚宇一顫住口,眼前清風拂過,鳳知微已經步伐輕快的從他身邊過去,拋下的語聲淡淡。
「既然天盛建國以來,青溟書院就沒出過荒唐的事兒,那麼在我手裡,一樣不會。」
鳳知微人已走開,姚揚宇還呆呆的站著,有點迷惑的問赫連錚:「為什麼我就覺得,司業大人每句話,都那麼的無比正確呢?」
「那當然。」赫連錚豪情萬丈張開雙臂擁抱天空,「我小姨……哦不我家司業,最凶猛!像密林裡潛伏的赤眼鷹,陰毒的狠辣,溫柔的凶猛!」
他樂顛顛的追著鳳知微去了,留下姚揚宇繼續發呆。
「……這是稱讚嗎?」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凰權(卷二)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凰權(卷二)
贏得皇帝的賞識,
得了世子未婚妻的名銜,
更占了風流楚王寧弈的心,
由妓院平步至第一書院的鳳知微,
可謂少年得志,春風得意。
但世人豈知她內心這苦呀──
皇族算計,世家鬥爭,
彷彿這些還不夠她累似的,
楚王明裡暗裡的惡意設計,
加上顧南衣不定時的石破天驚,
鳳知微咬牙,
普天之下,唯楚王與顧小呆難養也!
還沒能過上多少平靜日子,
鳳知微受任由楚王隨同至南海整肅海寇。
盤根錯節的氏族勢力,還未清除,
兩人竟已路遇埋伏,九死一生,
難道這南海一行,
即將成為鳳知微的不歸路!?
作者簡介:
天下歸元,女,水瓶座,生於山溫水軟江南,一生鍾情文字變幻之美,摯愛性靈本我之真,遂以博大細膩行文風格,打造風采各異紅顏傳奇,筆下江山改盡,美人不老,有情人時時,陌上同歸。代表作《扶搖皇后》、《帝凰》、《燕傾天下》、《凰權》。
TOP
章節試閱
第五十九章 給我賠禮
瀟灑決斷數字詩,一詩出而滿堂驚。
華宮眉踉蹌退後,手扶著几案,怔怔良久,眼淚斷線般滾下來。
寧弈把玩著手中的酒杯,唇角笑意薄如落花。
不如拋一片痴心,不如拋一片痴心。
這絕頂慧黠女子,竟用這樣的方式,拒絕了他。
只是,這麼一拒絕,卻也令他窺見了她深沉渺遠內心裡,一些不願為他看見的心思。
有一種女子,如域外蓬萊,遠在高天山海之外,想要走近,先得穿過重重迷霧。
亂花漸欲迷人眼,然而只要他始終在高處,何畏浮雲遮眼?
他笑著,舉杯,遙遙對鳳知微一敬。
鳳知微挑挑眉,遙遙對上首一禮,...
瀟灑決斷數字詩,一詩出而滿堂驚。
華宮眉踉蹌退後,手扶著几案,怔怔良久,眼淚斷線般滾下來。
寧弈把玩著手中的酒杯,唇角笑意薄如落花。
不如拋一片痴心,不如拋一片痴心。
這絕頂慧黠女子,竟用這樣的方式,拒絕了他。
只是,這麼一拒絕,卻也令他窺見了她深沉渺遠內心裡,一些不願為他看見的心思。
有一種女子,如域外蓬萊,遠在高天山海之外,想要走近,先得穿過重重迷霧。
亂花漸欲迷人眼,然而只要他始終在高處,何畏浮雲遮眼?
他笑著,舉杯,遙遙對鳳知微一敬。
鳳知微挑挑眉,遙遙對上首一禮,...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天下歸元
- 出版社: 米國度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07-18 ISBN/ISSN:978986967014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48頁
- 商品尺寸:長:210mm \ 寬:150mm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