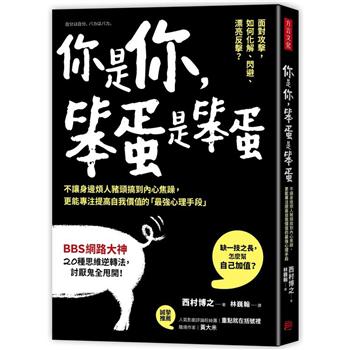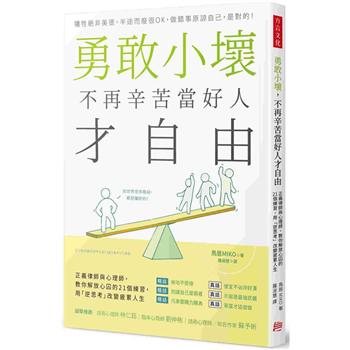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2 項符合
我的蟻人父親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圖書名稱:我的蟻人父親
** 傷害難免,包容有時 家,一輩子的成長痛**
●同名作品榮獲【第十一屆林榮三文學獎.散文獎三獎】
●蟻人的孩子們如何描述自己的父親?
●無法輕忽的臺灣九零年代成長紀事,21世紀家庭書寫最深刻的一頁。
●內附16頁回憶重疊之全彩寫真
螞蟻能拖行比自己重一千四百倍的物品,也能舉起比自己重五十二倍的東西,是全世界力氣最大的昆蟲之一。
「父親指著二十多層的大廈說:我蓋這棟的時候,你小學剛畢業……」
「父親是喜歡小東西的;父親曾是三十年的版模工人;父親也曾好賭成性但至終為了家庭收手;父親退休了;父親是知道我的同志身分的。父親是沉默的。」
失了分寸的愛,傷人最深。
青年作家謝凱特走過必然的成長痛,透過細膩觀察,解析親情、友誼與愛情中的索討、給予及矛盾,重新理解愛與被愛的各式可能。他以平易近人的文字,打造出一間微觀世界的娃娃屋,妥善安置在人生長河中所遭逢的角色:與他交換化妝心得的媽媽、帶著些微距離感的哥哥、因為當兵跳傘而罹患重度憂鬱症的大伯、暗戀過的女同學與男同學、罵人是gay實際上也是同志的同學L、擔任兄弟間傳話筒的髮型設計師、前任與現任戀人們,當然還有如螞蟻般撐起一座城市與一個家的父親......
以文字停格美好遺憾,溫柔再現愛的副作用,讓傷害與愛並存相擁。一本無法輕忽的臺灣九零年代成長紀事。
「時光會輪迴,以一種看不見的形式重新安排父母子女間的關係。當父親工作時,我安心念書;當他退休時,我忙於工作,在他豢養的家中宇宙頻頻缺席。」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