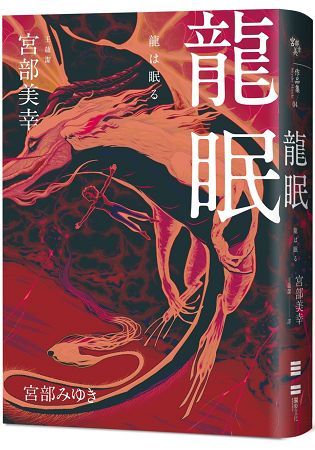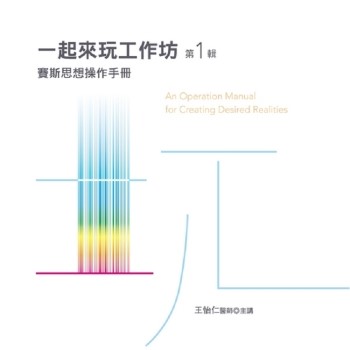他卻為了擁有額外的能力,而痛不欲生──
我想知道若這世上真有超能力,那會是何種能力,又會帶來怎麼樣的喜怒哀樂?本作可以說是我創作的原點/宮部美幸
【得獎紀錄】
1991年第105屆直木獎入圍作
1992年第45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
【故事大綱】
每個人的體內都有一條龍,那是一條外型極為不可思議,蘊藏著無窮力量,沉睡的龍。當這條龍甦醒時,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禱。
暴風雨襲擊的夜晚,雜誌記者高坂昭吾在回東京的路上,讓一名全身濕透的少年稻村慎司搭了便車。途中兩人遇上一樁幼童跌落下水道的意外。始終散發著一股不可思議氣質的慎司,竟告訴高坂他是超能力者,他看見了這樁意外的真凶。高坂雖然對此感到不可置信,卻也按著慎司提供的線索找到了後者口中的真凶,只是事情發展卻不如慎司想像,真相並未大白。
然而這場慘劇,不過是一切的開端……
慎司的能力是真是假?
高坂在意外後不斷收到的恐嚇信件寄件者又是何人?
一場看不見的決鬥即將開始。
【名家推薦】
閱讀宮部,每每會給讀者帶來「溫柔」與「療癒」的感受。然而我想宮部的此份溫柔,並非只是為了療癒我們的心,而更是希望我們在理解社會的殘酷後,能更溫柔地去對待他人──特別是那些「少數者」。他們或許在身體機能、能力與性向偏好上與我們不同,但這並不構成妨礙他們掌握自己人生的理由,不是嗎?
──路那(推理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