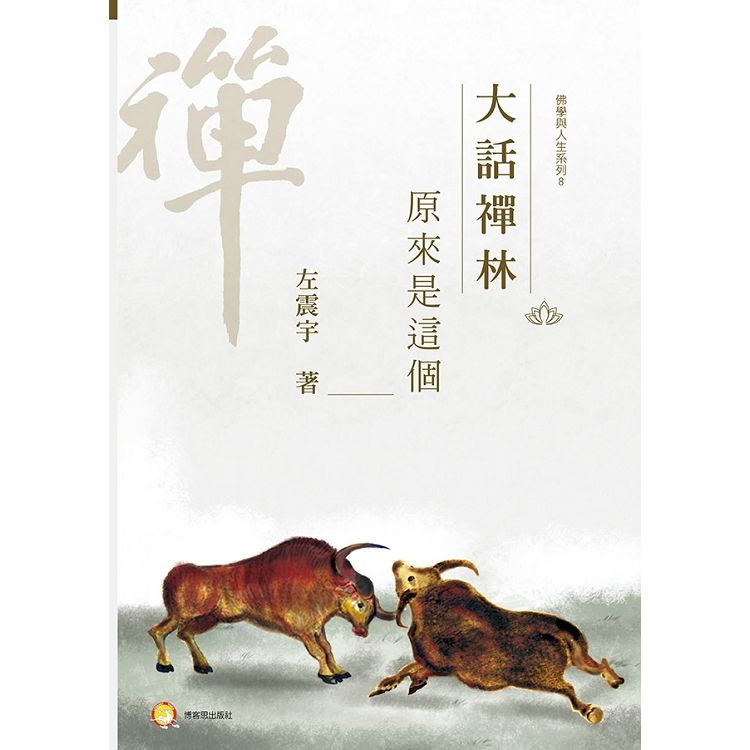禪的世界總是讓人感受到撲朔迷離、不可置信、充滿矛盾,比偵探情節更加難以推理,常使人不知如何下手。不過,若找到了源頭、關鍵,就能迎刃而解,豁然開朗。也能透徹禪師們千變萬化的機竅,其實是萬變不離其宗。
禪宗從達摩祖師面壁九年後,思索出一種適合中土修佛之士的法門,他到中土後觀看這一方所譯出的佛經,他表示與他所傳的法較為接近的是《楞伽經》,因此從二祖開始,主要講述的經典首要為此經,迨四祖之時,金剛經雖已被譯出,但當時世人認為此經為不了義經,所以尚未受到重視,隨著研究者增多,才發覺此經有著甚深涵義,最後成為大乘佛教具有殊勝地位的經典,禪宗四祖講經說法時,除了以楞伽經外也兼講金剛經,至五祖時,金剛經已成為傳法主要經典了。
禪宗在中國發展過程中,一開始並沒有自己的道場,大都是依附在其他教派中(律宗),過著出家人的生活與儀軌,直至百丈懷海首倡「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百丈清規後,禪宗才開始有了自己的叢林道場。
禪宗傳法及開示學人的方法也不同於其他教派,一般認為在於「頓」「漸」及「祖師禪」「如來禪」之分別。另外認為不依經典而修證,也是其特色,也因此,當時受其它教派所批判,挑戰南方頓禪的著名人物德山宣鑑,他背著自己的金剛經注疏,欲往南方去挑戰及所經歷的奇特之事。
禪宗公案本是某一祖師開示弟子的言行,後來被收錄成書,著名的有《碧岩錄》、 《從容錄》、《無門關》、《正法眼藏》、《景德傳燈錄》、《天聖廣燈錄》、《建中靖國續燈錄》、《聯燈會要》、《嘉泰普燈錄》、《人天眼目》、《指月錄》、《續指月錄》等最為著名。
禪以見性為主,公案是種種破迷入悟的事件或手法,禪師不拘形式,應機施教,有時態度幽默,有時動作粗暴,這些生龍活虎般的行止,無非是為了幫學人抽釘拔楔。各種光怪陸離的手法正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都是單刀直入,大破大立。正如風穴禪師所說:「大用現前,莫拘小節。」
禪宗在六祖之後璀璨輝煌一段時間,剛開始時,禪師多以溫和平實之語句開示學人,學人也都能直下領受,但之後因修學之士,師法前朝而著於識中,禪師為斷識見,只得應機而變法,從即心即佛,轉而非心非佛,從無相,轉為無相非相,無相非相就無有相耶?從無到雙遣於無,無無難道就無嗎?是故,禪師們只能止於言,息於行,或用喝或用棒,或無情來說法,設機關,立疑句,無非是為了警醒愚迷,但也折煞禪師們,要想應對得住輪刀上陣的學人們,沒有過人的機峰是無法見招拆招的。故而,禪宗在短暫的顯揚之後,少有禪師能應對習染已深的學人,算是技窮了吧?畢竟有如石頭、巖頭、投子之師,能立峻峰讓學人挑戰的已然不多。禪宗因而消沈但未隕沒,千年多來依然是有志之士,嚮往追尋的道路。
拙筆從高中開始,便對公案喜好,但其莫幻高深的故事,總苦思不得其解,縱然看了許多大德之注,也覺有如隔靴搔癢。讀研究所時,有門課儒家思想,課中分組報告,拙筆代表做荀子思想介紹,在尋思荀孟之間之時,忽然有省—孟子的人性本善。當下並無如同古之大德般,不可遏止的雀躍、流淌胸中之慨然。但之後讀普門品知菩薩三昧,閱公案則有撥雲見日之效。因今時之日,已不知何聖可以印可,故不知是否同古德一般?
寫此公案一書,也深怕萬一注破了,會如同香嚴上樹所示。尋思許久,但問「自己」,無妨!若只是知見之言,也能助人另闢蹊徑。引用版本多所不同,有人問我,為何說的有些跟經典上寫的不同?我反問之:「經是誰說的?」回:「佛所說的」問:「誰寫成典的?」回:「佛弟子們。」問:「誰譯的?」回:「譯師譯成的。」問:「所以是佛弟子及譯經師們的知見所書寫的,我們何必在人家的知見上,去窺測佛意。」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大話禪林:原來是這個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37 |
生活佛法 |
$ 255 |
宗教命理 |
$ 270 |
中文書 |
$ 270 |
生活佛法 |
$ 270 |
禪修 |
$ 270 |
佛教 |
$ 270 |
Social Sciences |
$ 270 |
宗教 |
$ 270 |
宗教命理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大話禪林:原來是這個
《大話禪林-原來是這個》
研究禪宗公案,若能契入核心,則能在一團迷霧中理出其意旨,歷覽諸大德之作,皆只能譯其文猜其意,不明古德言銓。本書將公案分十點為目,所釋之言,讀者可比對己心,是否合於情,順於理?若覺謬誤,敬請大話視之。
通察諸案,便能體會到,諸禪師幽默或粗暴之言行,皆是煞費苦心的在開示學人。本書公案內容參照不同版本,選用合適於本文闡述之辭句,附錄白話翻譯,盡量以意譯而不直譯為主。
商品特色
《大話禪林-原來是這個》─博客思出版──看得懂的公案
禪宗旨在「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由初祖達摩傳至六祖惠能,始分南北二宗,南頓北漸,禪宗以「見性成佛」為目標,那麼究竟如何達到?
歷代祖師留下的公案言簡意賅,現代人礙於不懂當時的用語與無法通達見性的關鍵,往往看公案如入五里霧中,無法了達義趣,讓一乘見性法門埋沉經藏之中,著實可惜。《大話禪林-原來是這個》作者數十年專研禪宗公案,將見解體會分述各章,期與學者一起進入禪宗深奧的一乘佛法殿堂。
作者簡介:
左震字
學歷:私立中原大學電子工程系學士、私立玄奘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畢業論文以質性研究為主,涉獵於儒家、佛教、道教及一貫道思想及教義。
曾任職於新竹市科學園區,生產磁記憶產品公司,擔任產品分析主管,目前已退休。
推薦序
禪的世界總是讓人感受到撲朔迷離、不可置信、充滿矛盾,比偵探情節更加難以推理,常使人不知如何下手。不過,若找到了源頭、關鍵,就能迎刃而解,豁然開朗。也能透徹禪師們千變萬化的機竅,其實是萬變不離其宗。
禪宗從達摩祖師面壁九年後,思索出一種適合中土修佛之士的法門,他到中土後觀看這一方所譯出的佛經,他表示與他所傳的法較為接近的是《楞伽經》,因此從二祖開始,主要講述的經典首要為此經,迨四祖之時,金剛經雖已被譯出,但當時世人認為此經為不了義經,所以尚未受到重視,隨著研究者增多,才發覺此經有著甚深涵義,最後成...
禪宗從達摩祖師面壁九年後,思索出一種適合中土修佛之士的法門,他到中土後觀看這一方所譯出的佛經,他表示與他所傳的法較為接近的是《楞伽經》,因此從二祖開始,主要講述的經典首要為此經,迨四祖之時,金剛經雖已被譯出,但當時世人認為此經為不了義經,所以尚未受到重視,隨著研究者增多,才發覺此經有著甚深涵義,最後成...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前言 0四
第一篇 公案探究 一0
一 不可說 一一
二 如來禪與祖師禪 一四
三 自性作用 一七
四 道在日常 三四
五 污染不得 四六
六 事來則應,事去則淨 五四
七 回到那處 五九
八 以心印心 六七
九 大機大用 七九
十 其它公案 八五
第二篇 應機方式 一0五
一 聖問凡答 一0六
二 參話頭 一一八
三 破三關 一二0
四 臨濟禪 一二八
五 洞山五位說 一三八
結語 一五0
附錄:公案白話文...
第一篇 公案探究 一0
一 不可說 一一
二 如來禪與祖師禪 一四
三 自性作用 一七
四 道在日常 三四
五 污染不得 四六
六 事來則應,事去則淨 五四
七 回到那處 五九
八 以心印心 六七
九 大機大用 七九
十 其它公案 八五
第二篇 應機方式 一0五
一 聖問凡答 一0六
二 參話頭 一一八
三 破三關 一二0
四 臨濟禪 一二八
五 洞山五位說 一三八
結語 一五0
附錄:公案白話文...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