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未設防
寧波與大浹江口相距四十里,是浙江省的第二大郡,也是浙江提督衙門的駐節地。天黑前,第一批潰兵逃回寧波,一陣喧譁和叫嚷後,守城兵丁開了城門,清軍戰敗的消息不脛而走,寧波像地震似的動盪起來。
余步雲和鎮海營的潰兵是最後撤回的,亥時二刻才進城。城裡的大街小巷燈籠遊移,人影幢幢,到處都是潰兵的嘶喊聲和狺狺的狗叫聲。居民們徬徨不安、猶豫不定,不知道該逃走還是該留下,當地縉紳和百姓烏烏壓壓地聚在提督衙門和知府衙門的大門口,打聽官軍是棄還是守。
余步雲在大照壁前翻身下馬,置眾人的詢問於不顧,徑直進入衙門。親兵們立刻在門外築起一道人牆,防止紳民百姓擅自闖入,紳民們卻久久不散,圍著親兵們不停地打聽,聲聲詢問密如雨點。
「英夷攻佔鎮海,是真的嗎?」
「欽差大臣投水自盡,是真的嗎?」
「逆夷會不會攻打寧波?」
「余大人不會置百姓於不顧吧?」
先前余步雲便命令親兵們以安定民心為第一要務,因此他們全都緘口不語,或以「無可奉告」來應付。
官邸裡燈火通明。余家的小女兒春梅即將出嫁,女婿是寧波知府鄧廷彩的三兒子鄧蘭波。院裡擺著親家送來的禮品籃,閨房的窗上貼著剪花喜字,伙房的水缸裡浸著剛宰殺的豬,缸蓋上放著一柄殺豬刀,那刀彎曲得像蘭花葉子,長長一撇。去了毛的豬頭歪在一旁,兩隻眼睛瞇成一條窄縫,嘴巴張得很大,一副嬉皮笑臉的模樣。余家老小十幾口人是去年從福建遷居寧波的,他們被街上的人喊馬嘶聲弄得驚魂不定,提著燈籠在院子裡候著。
余步雲一手提頭盔一手按劍,擰著腳進了後院,他的戰袍掛了一個三角口子,皮靴上的馬刺只剩一只,腦門上全是油汗,臉色疲憊憔悴,肅殺得令人生畏。他戎馬一生勝多敗少,家裡人從沒見他這麼狼狽,透出一股不祥之感,不禁圍過來問長問短。
「阿爹,出事了?」
「阿爹,鎮海敗了?」
「英夷要打寧波,是嗎?」
如夫人林氏從水缸裡舀了水,端過一只銅臉盆,「老爺,洗洗臉,我給你燒洗腳水。」
小女兒春梅拿過一面鏡子,小心翼翼遞上,「爹,您像是從灶膛裡鑽出來的灶王爺。」
余步雲在戰場上是錚錚鐵漢,回到家裡是溫柔丈夫。他解去牛皮甲,用布巾擦了臉,接過鏡子照了照,十幾年前的英雄氣概已經蕩然無存,鏡子裡呈現出一副後背微駝、面目憔悴的敗象。他猛然蹦出一句話,「此頭顱,何人斷?」
春梅陡然變色,一把奪過鏡子,「爹,孩兒要出嫁,您卻講這種不吉利的話。」但她沒抓穩,鏡子掉在地上,啪的一聲碎了。
如夫人林氏信佛,趕緊雙手合十呢喃念道:「阿彌陀佛,歲歲(碎碎)平安。」
余步雲慘澹一笑,「你們想聽吉利話,聽到的偏偏是惡讖!」
春梅一驚,像受了天大的委屈,嗚嗚咽咽地哭起來。
一個僕人進來稟報:「老爺,鄧老爺來了。」寧波知府鄧廷彩是來瞭解戰況的。
余步雲說了聲:「請。」
鄧廷彩是四川崇州人,五十多歲,留著八字一點式鬍鬚,臉上透著焦灼。他一腳踏進門檻,語氣急促,講一口地道的四川話,「余宮保,街上人喊狗叫亂哄哄的,都說鎮海敗了,是嗎?」
一個時辰前,江寧協的弁兵們簇擁著自盡未遂的裕謙退到寧波,官兵們又叫又吼,驚動全城。鄧廷彩聽說鎮海兵敗,但想再確認一遍。
余步雲點了點頭,「打了一天,鎮海縣、招寶山和金雞山全丟了。」
春梅在一旁聽聞,不由得再次抽泣起來。
余步雲吩咐:「梅兒,我和鄧大人談公務,妳和家人先出去。」
春梅扭著腰身出了屋,但沒離開,趴在門縫邊上悄悄聽。
余步雲恨恨地道:「裕謙這個人哪,峻急勇猛,浮躁衝動,莽夫逞能,不自量力。他不知彼、不知己、不知兵,卻主戰,這樣的人只會誤軍誤國誤皇上,讓兵丁白白送死,讓百姓白白遭殃。」
鄧廷彩說:「余宮保,那個蒙古人投水自盡,但沒死。」
余步雲面露詫異,「沒死?」
鄧廷彩確信地點頭,「豐伸泰用門板把他抬回寧波,我摸了他的脈,還活著,但昏迷不醒。」
《大清律》有「守備不設,失陷城寨者,斬監候」的科條。舟山和鎮海丟了,裕謙要是活著,難逃斬監候的厄運;他要是死了,反而會成為以身殉國的英雄,受到封妻蔭子的褒獎。但是現在他不死不活,卻管不了事,萬一英軍攻打寧波,失陷城寨的責任就得由余步雲承擔。鄧廷彩身為寧波知府,同樣在責難逃,因此他最擔心的,就是英軍攻打寧波。
春梅在門外,依稀聽見他們在談論如何守城。余步雲在鎮海與逆夷當面對仗,敗得灰頭土臉,鬥志全喪,「自從英夷犯順以來,所攻之處,無不摧破。去年舟山和虎門失陷,是因為失防。今年,廈門、舟山和鎮海準備充足,調用精銳之師,花費大量財力和物力,防守極嚴,但英夷依然勢如破竹。他們的炮火器械精巧猛烈,為我國所不能及。」
鄧廷彩壓低音量說:「寧波城裡流傳一則謠言:當無帆之舟(火輪船)駛入大浹江時,天下就會易手,一個西方白女人將要取代北方來的滿洲皇帝。這則流言傳得有鼻子有眼,繪聲繪色。」
余步雲有點詫異,這麼荒誕不經的傳言能夠流傳,是因為民智不開,還是因為有人蠱惑?是因為人心幽微,還是因為上蒼給了預兆?他撚著鬍鬚若有所思,「自古以來有多少王朝更迭,鮮卑人、蒙古人、滿洲人、漢人都當過皇帝,老百姓逆來順受,誰當皇帝給誰納糧。仗打到這個地步,恐怕是民心生變,兵心生變了。」
「寧波能不能守住?」
「難。我派陳志剛去找夷酋,探問他們有何干求。」
「哦,這可是違旨,萬一皇上知道了,後果不堪設想!」
余步雲無奈,「自古以來,所有戰爭都是邊打邊談,沒有只打不談的。皇上要是責怪下來,我只能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余步雲和鄧廷彩的話音時高時低,時而憤怒,時而歎息,時而激烈,時而舒緩。過了好久,春梅才聽見鄧廷彩問:「孩子們的婚事怎麼辦?」
「兵荒馬亂的,只能改期。」
女人出嫁是終身大事,卻被意外的兵燹攪黃了,春梅想哭,但不敢,捂著嘴,蹲下身子抽泣。
余步雲聽見抽泣聲,拉開門,見春梅在抹淚,林氏和全家老小靜靜地站在天井裡,不由得一愣神。
林氏預感到要天崩地裂,她用手帕擦著眼淚,「老爺,你千萬要保重,一家老小都指望著你呢。」
余步雲扶起女兒,環視著家人。五十年前,這位堂堂正正的太子太保才十幾歲,是呼嘯於村道鎮口的孩子王,爭強鬥勇打群架,連性命都能潑出去。從當兵之日起,他就把殞命沙場視為野草枯死在冬天般自然。憑著這股子衝勁,他在戰場上所向披靡。
然而現在,他是一隻老掉牙的金錢豹,沒了爭強鬥狠的精氣神,變得兒女情長,英雄氣短,「你們放心,我不會死,就是死,也得有可死之道。勝敗乃兵家常事,大清朝天寬地闊,進可攻,退可守,迴旋的餘地很大。你們現在回屋去,馬上收拾隨身衣物,準備乾糧,明天一早我派人送你們離開寧波。」
林氏問:「去哪兒?」
余步雲撫摸著女兒的肩膀,聲音緩慢淒涼,「我和鄧大人議過了,女兒雖然還沒過門,余、鄧兩家也是兒女親家。我和鄧大人職責在身,留守寧波,你們與鄧大人的家眷一起走,去四川崇州。敵情如火,切勿遊移!」
不是窮途末路,余步雲不會講這種話,全家人不由得潸然淚下。
裕謙曾經鐵言錚錚地要守住大浹江口,寧波居民信以為真,誤以為金雞山和招寶山是牢不可破的天塹,此時他們才大夢初醒,所謂天塹不過是一道破籬笆,一捅即穿。寧波城轟然大亂,人們紛紛收拾細軟,天一亮,車馬舟楫就被有錢人雇用一空,六座城門的門洞大開,車如龍,船如梭,人如蟻,馬如蜂,居民們扶老攜幼離城出走,到處都能聽到男人的咒罵聲和女人的哭泣聲。
余步雲準備收拾殘兵固守城垣,派出一隊遊哨出城十里,偵察敵軍的動向,另外派親兵四處傳令,命令退入寧波的各路將領到提督衙門開會,包括從江蘇和安徽來的客軍將領。
但是,客軍將領不聽他的命令。豐伸泰帶著三百多江寧協的潰兵來到東渡門,準備出城,其中有兩個兵丁用擔架抬著裕謙,他遇救後一直昏迷不醒。把守城門的兵丁接到命令,要城裡所有將領去提督衙門會議,因而拉緊木柵,不讓出城。
豐伸泰厲聲喝道:「打開木柵,我們要出城!」
當值兵目見他頭戴纓槍大帽,身穿二品補服,軍旗上有斗大的「豐」字,衣花上有「江寧協」字樣,知道他是豐伸泰,「啟稟豐大人,余宮保有令,所有退入城中的將弁都得去提督署會議,共議守城事宜。」
豐伸泰跳下馬,「我們江寧協歸兩江總督裕謙大人管轄,不歸余宮保管轄。」
兵目眨了眨眼,「裕大人殉節了,余宮保是本城最高長官。小人傳余宮保的命令,請大人別讓小人為難。」
豐伸泰眉毛一挑,口氣又粗又橫,「誰說裕大人殉節了?裕大人活得好好的!」他一招手,兩個兵丁抬過擔架,擔架上蓋著壽字花紋錦面被子,一張死灰似的臉露在被子外面。
兵目過來細看,裕謙似乎睡著又似乎死去。他不敢掀開被子探究,抬頭掃視四周的弁兵。裕謙的親兵們舉著官銜牌,上面有「欽差大臣」、「兩江總督」、「兵部尚書」、「右督御史」等字樣。
豐伸泰等得不耐煩了,厲聲喝道:「我們奉裕大人之命去杭州,你敢攔阻嗎?」
堂堂二品武官橫眉怒目,還有三百多整裝待發的江寧弁兵,一個小小兵目就是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攔阻,他後退一步,「打開木柵,送裕大人出城!」
幾個守兵嘩啦一聲拉開木柵。兵目喝了一聲:「跪!」守兵們便像牽線木偶似的,齊刷刷單膝跪地,向裕謙行禮。
豐伸泰翻身上馬,一招手,「走!」三百多江寧兵簇擁著擔架,腳步雜遝地出了城門。
豐伸泰抬著裕謙逃離危城的消息很快傳開,處州鎮和衢州鎮的敗兵們群起效尤,余步雲居然拿他們一點兒辦法都沒有,因為裕謙有令,他無權管轄外省客軍。
客軍的逃離打亂了他的部署。余步雲仔細詢問守門兵目裕謙究竟是死是活,兵目說,裕謙可能死了,即使活著,也活不了多久。余步雲的肚腸立即轉動起來,依照有關章程,當總督和巡撫不在位時,提督可以單獨上奏折。余步雲想起裕謙攻擊他的毒言惡語,難免義憤填膺,給朝廷寫了一份奏折,報告寧波的守禦情況:
……從前在城兵額不足四千,除分防各汛調派軍營外,僅只七百餘名……勢難再令守陴。自裕謙……由鎮海退入寧波,是日戊時,即率江寧將弁豐伸泰等兵丁數百名,星夜退走余姚、紹興。所有衢、處二鎮官兵,藉以護送為名,概不入郡守城。以致全郡驚惶,逃避擁擠,自相踐踏,哭聲遍野……浙江全省處處吃緊,現在無兵可調。奴才唯有竭盡心力,督率文武,多方設守……
這份奏折無須經過裕謙審閱,飽含著余步雲對裕謙的深重積怨。「率」者一變,真相扭曲——不是豐伸泰「率」兵奪門而走,而是裕謙「率」豐伸泰等兵丁星夜逃離。如此一來,殺身成仁的裕謙成了率兵逃跑的罪魁!此外,余步雲奏報外省客軍拒不守城,藉故逃離,不僅推卸了自己的責任,更使裕謙罪上加罪。
但是,他畢竟不是玩弄文字的高手,此番借機宣洩私恨,把一腔酸水噴到裕謙身上,卻沒有考慮會有什麼嚴重後果。
他剛派人把奏折送往驛站,鄧廷彩就神色張惶地邁進提督衙署,「余宮保,大事不好!據探哨稟報,英軍沿著大浹江朝寧波殺來!」
余步雲臉色陡變,他以為英軍會在鎮海休整兩天,沒想到他們乘勝追擊,馬不停蹄殺向寧波!他背著雙手,踱著步子,「英軍離寧波有多遠?」
鄧廷彩回答:「據探哨稟報,還有十里。」
寧波的城牆上原本安有一百零二位火炮,為了防禦海口,裕謙把八十二位火炮調往鎮海,致使寧波成為防禦中的薄弱環節。外省客軍聞風喪膽,滑腳溜號,留下的浙江營兵只有千餘人,處處風聲鶴唳,人人心驚膽顫。軍心灰敗到如此田地,讓他們嬰城固守就像派老鼠防貓。余步雲一咬牙,下達了棄城的命令,「傳令各營各汛,整隊集合,開赴上虞!」
余步雲率軍撤走,鄧廷彩更不敢獨守空城,他肚腸一轉二曲三迴旋,近死不如遠死!便急急惶惶地趕回知府衙門,倉促召集幾十個衙役和一百多弓兵,尾隨著余步雲逃離寧波。
外省客軍和本省敗兵不戰而退的消息立即傳遍全城,正午時分,全城的縉紳和保長們不約而同來到寧波商會商議對策。商會位於靈橋門內的慶餘閣,它是全城商人捐資修建的商人公所。
總商陸心蘭坐在中央,此人五十餘歲,穿一件棕色萬字紋府綢長袍,戴一頂嵌玉小帽,手捧一根二尺長的玉嘴水煙袋。他是盛德堂大藥房的東家,也是本城名列前茅的大財東。
寧波商會由成衣行、海鮮行、船運行、醫藥行、米糧行、鐵工行、木工行等二十多個行幫組成,每個行幫各有行主。行主們正亂亂哄哄地說話。
一個姓張的行主道:「陸老爺,小民小戶拎包就能逃跑,在座諸位是有恆產的,前腳逃走,遊痞無賴後腳就會破門而入,把店鋪洗劫一空。」
另一個李姓行主說:「陸老爺,咱們商家年年繳納稅賦捐資助軍,他娘的夷人還沒打到城門口,當兵吃糧的跑得比兔子還快。咱們得想辦法自保呀。」
第三個開口的行主姓趙,「陸老爺,前兩天我去雪竇寺求籤問卜。寺裡的大和尚說當無帆之船從大浹江開到三江口時,就要改朝換代,城頭變換大王旗,西方的白女人要取代東方的滿洲皇帝。這是天命。小小商民,誰當皇上,給誰納稅。眼下這個亂局,保全性命和家園要緊。」
「陸老爺啊,官府棄民命於不管,我們必須想法子自救,否則就會全城遭殃啊!」
「郡城要是沒人管,就會賊盜叢生。」
「陸老爺,您老德高望重,就挑頭擔起拯救全城的重任吧!」
陸心蘭深深吸了一口煙,把水煙袋往桌上一蹾,「各位縉紳和保長信任我,要我臨危主事,我也只好挑這個頭。現在城裡亂哄哄的,咱們商會沒兵沒馬,只有一個水火會(民間消防隊)和一個更夫會(守夜保安隊),養著六七十號會丁和更夫。梁仁!」
梁仁是水火會的領班,兼管更夫,他應聲答道:「在!」
陸心蘭吩咐:「眼下只能把會丁和更夫當義勇使用,維持全城秩序。你立即集合全體會丁分守六座城門,另叫更夫們馬上巡街,嚴防遊痞無賴趁火打劫,碰到溜門撬鎖、盜搶店鋪的小偷無賴,立即敲鑼報警喊人捉拿。」
「我這就去辦理。」
陸心蘭又回頭道:「水火會和更夫會人手少,不足以維護全城秩序。我陸某人拜託各位保長,每保抽丁二十人組隊巡邏,看護好每條街坊,嚴防流氓遊痞借機滋事,哄搶店鋪。」
保長們全都應聲答應。
陸心蘭思考一會兒,「還有一件事。英夷很快就要兵臨城下,我們無力抵抗,請各位行主與我一道去靈橋門,開門迎候。在這個當口,姿態得謙卑一點兒。」
一位劉姓行主有些猶豫,「會不會有人說三道四,罵咱們是漢奸?」
陸心蘭低沉著聲,「那是屁話!眼下要緊的是保境安民,不然的話,全城都得遭殃。」
一番安排後,行主們和保長們依命行事去了。
「復仇神號」和「地獄火河號」鐵甲船在前面探路,木殼火輪船「西索提斯號」、「皇后號」和三條輕型護衛艦跟在後面,沿著蜿蜒的大浹江斗折蛇行,緩緩推進。艦隊沒有航道圖,不得不一邊行駛一邊測量水道,速度極慢。七百多英國步兵背著行囊沿兩岸徒步前進。初秋時節,大浹江兩岸是連片的綠野,濃濃淡淡、漫漫蕩蕩向天邊延展,要是沒有戰爭,這裡是滋潤澄澈又寧靜富饒的地方。
從鎮海到寧波有四十里水路,英軍早晨出發,途中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像是一次野營拉練,下午二時,艦隊抵達三江口。
三江口是大浹江、余姚江和奉化江的匯合點,距離靈橋門只有一里之遙。它雖然在城外,卻是商賈雲集、民殷物富的地方,兩岸的店鋪、倉房、石坊、棧橋鱗次櫛比,此時卻亂哄哄一片。當地商民和船戶們驚惶萬狀,拖兒帶女離家出走。河岸、村道和田埂上到處都是人流,許多人牽衣頓足依依不捨,不時回望著自己的店鋪和家園,想離去,捨不得;想回去,又不敢。
英軍在三江口停下來。難民們頭一次看見奇形怪狀的鐵甲船和外國兵船,頭一次看見金髮藍眼的外國士兵,既驚駭又好奇,少數膽大的難民在遠處停下腳步,猶豫觀望。
郭富和巴加在「復仇神號」上,以手搭棚觀望著灰色的寧波堞牆,城牆上沒有旌旗和鉦鼓,犬牙似的垛口沒有守兵、沒有抬槍。靈橋門的城樓上有五六位鐵炮,但炮口被移開,朝向城裡,拱形的城門大敞。門口站著一百多縉紳,抬著食擔醴酒擎著彩旗,上面寫著「順民」字樣。顯而易見,清軍已經棄城而走,寧波是一座不設防的城市。
距離靈橋門不遠處有一座浮橋,架在十六條木船上,不拆掉它,兵船無法通過。「復仇神號」的艏炮很快便瞄準了浮橋。
巴加詢問:「郭富爵士,炸了它還是拆了它?」炸橋意味著用戰爭手段佔領寧波,一分鐘即可解決問題,拆除它意味著使用和平手段,但要耗費較長時間。
郭富瘦削的臉龐露出一絲惋惜之情,「寧波是一件多麼精美的藝術品!這麼漂亮的城市在歐洲也不多見。既然敵軍逃走了,我們應當以和平方式佔領它。」
巴加不大同意,「郭富爵士,璞鼎查公使的命令非常明確,他要求我軍洗劫寧波,徹底摧垮中國人的抵抗意志。」
郭富看了他一眼,婉言拒絕,「我和璞鼎查公使都在為大英國的海外事業效力,但觀念有差異。我國二百年的殖民史證明了一個真理:輸入劍與火,只會收穫反抗與報復,輸入《聖經》與宗教、寬容與和解,我們才能與佔領區的人民和諧相處。」
巴加對此不以為然,「璞鼎查公使會不高興的。」
郭富卻依舊無動於衷,「我是聖派翠克的信徒,聖派翠克精神的核心是堅忍與慈悲,它不僅開啟了我們愛爾蘭人的心靈,也將開啟中國人的心靈,我們應當對和平居民施以慈悲。」
巴加再次確認,「你想寬恕寧波,是嗎?」
「是的。以和平方式佔領它,我們才有安全感,否則就會暴力四起,人們在殺戮和冤冤相報中不得安寧,勝利將十分遙遠。」
巴加聳聳肩,「我對你的處置方式持保留意見,但看在上帝的份上,暫時寬恕那些可悲可憐的中國百姓吧。不過,你得向璞鼎查公使做出合理的解釋。」
郭富點頭,「我會向他解釋的。」
於是,郭富下達了拆橋的命令。很快地,一隊士兵帶著鉗斧錘鋸上了浮橋,七條兵船和火輪船艏艉相接,靜靜停在三江口。
攻打寧波成了一場武裝遊行,英軍官兵奉命就地休息,他們大大鬆了一口氣,終於有閒心欣賞起周邊的平川沃野和山岡湖塘。初秋時節,湖塘裡有敗荷,河岸旁有衰柳,田疇裡有莊稼,天際線上有如蟻如豆的難民。
陸心蘭等商民站在靈橋門下,小心翼翼地注視著英軍的一舉一動。當他們看到英軍開始拆橋時,決定主動示好,派出幾個水火會的會丁去幫忙。
郭富見狀,叫來了郭士立,要他去靈橋門瞭解中國人的意圖,郭士立是英軍的首席顧問兼翻譯,他的意見對郭富和巴加有重大影響。
不一會兒,郭士立回到「復仇神號」,報告說一批中國商民懇請英軍保護寧波和當地居民。
郭富滿意地點頭,「郭士立牧師,我軍攻打虎門、廈門、舟山和鎮海時,清軍一直在抵抗,這是清軍第一次棄守,這就意味著他們承認自己無能為力了。我期待著中國皇帝按照《致中國宰相書》的要求簽署一份和約。郭士立牧師,請你轉告中國商民,我軍不傷害和平居民,請他們就地安居,軍隊入城後,我將召集他們開一次會。」
一個小時後,浮橋拆除完畢,七條火輪船和兵船緩緩駛至靈橋門下。郭富喝了一聲:「軍樂隊!」
「有!」一個少尉應聲而出。
郭富道:「音樂有安撫人心的作用。奏樂,擺隊入城!」
鼓手們敲響了軍鼓,樂手們奏響了軍樂,一支先遣隊整隊集合,踏著鼓點、喊著號子、甩著正步,耀武揚威地進入寧波城。
不一會兒,靈橋門的城樓上升起一面米字旗,半城百姓都看見了它,它幽幽漫漫地飄著,時捲時舒,像一根刺扎在寧波百姓的心頭。軍樂隊登上城樓,輪番演奏《上帝保衛女王》和《聖派翠克的祭日》,宣揚英國的文治武功和悲天憐人的宗教精神。寧波居民聽不懂,猜不出英軍是在慶祝勝利,還是在自娛自樂。
縉紳和保長們靜靜地接受了變故,他們站在城門樓下面排列成行,等待英軍將領與他們開會。
陸心蘭抑制不住心中的屈辱與悲愴,兩股酸酸的淚水沿著臉頰悄無聲息地流淌,他意識到,他在率領寧波商民們打開城門,在大清與英夷之間的逼仄空間裡騰挪求活,苟安於當前,未來卻兇險萬狀!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鴉片戰爭(全集)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108 |
中文書 |
$ 1109 |
中國歷史 |
$ 1176 |
華文歷史小說 |
$ 1176 |
中國歷史小說 |
$ 1327 |
超值套書 |
$ 1428 |
中國歷史小說 |
$ 1478 |
Social Sciences |
$ 151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鴉片戰爭(全集)
扣除勝者的餘裕,減去敗者的藉口,添加軍者的悲歌,增補商者的無奈,成就這部飽含詩意的民族痛史。
作者簡介:
王曉秦 高級教師。畢業於四川外國語學院,長期在內蒙古師範大學和北京印刷學院進行教學與研究工作。
多年來致力於文史類作品的寫作與研究;精通英文,善於挖掘國外的史料,並與中國史料進行對比研究,成果頗豐。出版過長篇歷史小說《李鴻章大傳》等七本著述和十本譯著(含合著)。
章節試閱
寧波未設防
寧波與大浹江口相距四十里,是浙江省的第二大郡,也是浙江提督衙門的駐節地。天黑前,第一批潰兵逃回寧波,一陣喧譁和叫嚷後,守城兵丁開了城門,清軍戰敗的消息不脛而走,寧波像地震似的動盪起來。
余步雲和鎮海營的潰兵是最後撤回的,亥時二刻才進城。城裡的大街小巷燈籠遊移,人影幢幢,到處都是潰兵的嘶喊聲和狺狺的狗叫聲。居民們徬徨不安、猶豫不定,不知道該逃走還是該留下,當地縉紳和百姓烏烏壓壓地聚在提督衙門和知府衙門的大門口,打聽官軍是棄還是守。
余步雲在大照壁前翻身下馬,置眾人的詢問於不顧,徑直進入...
寧波與大浹江口相距四十里,是浙江省的第二大郡,也是浙江提督衙門的駐節地。天黑前,第一批潰兵逃回寧波,一陣喧譁和叫嚷後,守城兵丁開了城門,清軍戰敗的消息不脛而走,寧波像地震似的動盪起來。
余步雲和鎮海營的潰兵是最後撤回的,亥時二刻才進城。城裡的大街小巷燈籠遊移,人影幢幢,到處都是潰兵的嘶喊聲和狺狺的狗叫聲。居民們徬徨不安、猶豫不定,不知道該逃走還是該留下,當地縉紳和百姓烏烏壓壓地聚在提督衙門和知府衙門的大門口,打聽官軍是棄還是守。
余步雲在大照壁前翻身下馬,置眾人的詢問於不顧,徑直進入...
顯示全部內容
推薦序
推薦序
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有「以詩證史」說,小說是廣義的詩,亦足證史。王曉秦先生這部新著《鴉片戰爭》,即是充滿詩意的歷史小說。他用如椽大筆,繪形寫神,潑墨重彩地勾畫出一幅鴉片戰爭全景圖:虎門禁煙,英酋遠征,突襲舟山,關閘事變,廣州內河戰火,廈門島上烽煙,浙江鏊兵,長江大戰,斡旋媾和,簽字《南京條約》等等。其場景廣闊,情節跌宕起伏,可驚可怖之衝突,可歌可泣之故事,紛至沓來,讓人不忍釋卷。
人物從中英兩國帝王將相,到鴻商巨賈、煙民海盜,乃至販夫走卒,個個刻畫生動,個性鮮活。
在宏大敘事中,作者激情迸射...
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有「以詩證史」說,小說是廣義的詩,亦足證史。王曉秦先生這部新著《鴉片戰爭》,即是充滿詩意的歷史小說。他用如椽大筆,繪形寫神,潑墨重彩地勾畫出一幅鴉片戰爭全景圖:虎門禁煙,英酋遠征,突襲舟山,關閘事變,廣州內河戰火,廈門島上烽煙,浙江鏊兵,長江大戰,斡旋媾和,簽字《南京條約》等等。其場景廣闊,情節跌宕起伏,可驚可怖之衝突,可歌可泣之故事,紛至沓來,讓人不忍釋卷。
人物從中英兩國帝王將相,到鴻商巨賈、煙民海盜,乃至販夫走卒,個個刻畫生動,個性鮮活。
在宏大敘事中,作者激情迸射...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壹 兩總督邂逅相逢
貳 道光皇帝談禁煙
參 樞臣與疆臣
肆 權相回京
伍 紅頂掮客
陸 因義士事件
柒 天字碼頭迎欽差
捌 廣州名士
玖 廣州十三行的官商
拾 欽差大臣嚴訓行商
拾壹 令繳煙諭
拾貳 商步艱難
拾參 英國駐澳門商務監督
拾肆 嚴而不惡
拾伍 夷商繳煙
拾陸 水師提督嚴懲竊賊
拾柒 珠江行
拾捌 虎門—金鎖銅關
拾玖 揚州驛
廿 閒話清福
廿壹 舊部歸來
廿貳 虎門銷煙
廿參 觀風試
廿肆 水至清則無魚
壹 明托家族vs大清帝國
貳 林則徐誤判敵情
參 東方遠征軍
肆 勸捐
伍 ...
貳 道光皇帝談禁煙
參 樞臣與疆臣
肆 權相回京
伍 紅頂掮客
陸 因義士事件
柒 天字碼頭迎欽差
捌 廣州名士
玖 廣州十三行的官商
拾 欽差大臣嚴訓行商
拾壹 令繳煙諭
拾貳 商步艱難
拾參 英國駐澳門商務監督
拾肆 嚴而不惡
拾伍 夷商繳煙
拾陸 水師提督嚴懲竊賊
拾柒 珠江行
拾捌 虎門—金鎖銅關
拾玖 揚州驛
廿 閒話清福
廿壹 舊部歸來
廿貳 虎門銷煙
廿參 觀風試
廿肆 水至清則無魚
壹 明托家族vs大清帝國
貳 林則徐誤判敵情
參 東方遠征軍
肆 勸捐
伍 ...
顯示全部內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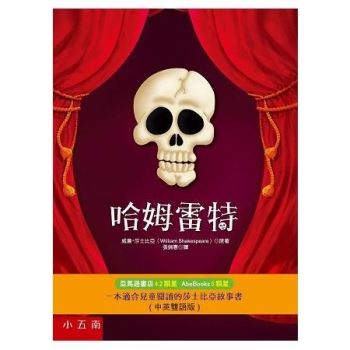






 2025【精選作文範例】國文(作文)[快速上手+歷年試題](記帳士)](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05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