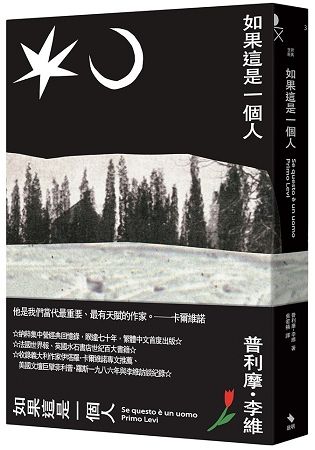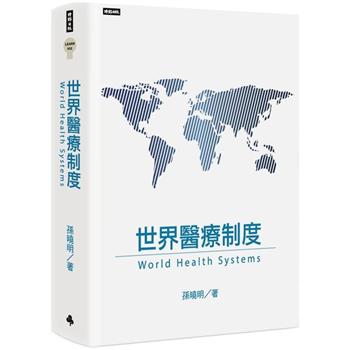義大利作家 普利摩・李維 納粹集中營經典回憶錄
法國世界報、英國水石書店評選為世紀百大必讀經典
伊塔羅・卡爾維諾:「他是我們當代最重要、最有天賦的作家。」✹睽違七十年,繁體中文首度出版
✹收錄義大利國寶級作家卡爾維諾推薦引言
✹收錄美國文壇巨擘菲利普・羅斯1986年與李維訪談紀錄
✹再刷二版:新書封設計+收錄普利摩・李維生平年表
一九四三年,二十四歲的義大利猶太人普利摩・李維受義大利法西斯民兵逮捕,從故鄉杜林被移送至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在集中營裡,德國納粹用系統化的暴力迫害猶太人:先以少量配額的食物使囚犯處於無時無刻飢餓的狀態,再以人類難以負荷的勞動量苦其肉體,最終用權力侵蝕囚犯的尊嚴,使囚犯別無選擇地臣服。
李維用冷靜樸實、卻又入微的筆調,寫下被囚禁於集中營十個月的回憶錄《如果這是一個人》,記錄下時代的暴行,卻也留下了人性堅不可摧最有力的證據。
「我們被密閉的貨車運送至此處;我們看見我們的女人和孩子一去不返;我們淪為奴隸,沉默不語、拖著疲憊的步伐上工收工步行了百次,在淪為無名死者之前,我們的靈魂早已奄奄一息。我們是回不去的了。沒有人可以從這裡出去,沒有人可以帶著烙印在肉體上的印記將這個醜陋的音信傳播至外界,告訴人們,在奧斯維辛,肆無忌憚的人,將人,糟蹋為何物。」
作者簡介:
普利摩•李維 Primo Levi
一九一九年生於義大利杜林的一個傳統猶太家庭,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李維與同伴意外遭法西斯民兵逮捕,為避免被以反法西斯身分槍決,他選擇承認自己的猶太裔身分,雖逃過一劫,但隨即被送往位於佛索利的中轉營。德軍佔領中轉營後,一九四四年二月,李維被送往屬於奧斯維辛集中營之一的布納—莫諾維茨集中營,刺上編號174517,遭囚禁十個月,直至一九四五年一月,蘇俄軍隊解放集中營。當初一同被送往集中營的猶太裔義大利人有六百五十名,最終納粹戰敗後存活的僅有二十餘名,普利摩・李維是其中之一。
一九四七年十月出版《如果這是一個人》,一九五八年收錄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的推薦序後再版,同時普利摩・李維開始創作第二本書《停戰》(La Tregua),於一九六三年出版,記錄他離開奧斯維辛集中營後的返鄉過程,並於一九九七年被改編為電影《劫後餘生》。一九六一年,他成為一家油漆工廠的總經理直到退休,這段期間他仍持續創作許多作品。除了《如果這是一個人》之外,最有名的作品當屬於一九七五年出版的《週期表》(Il sistema periodico),以化學元素為章節名,內容分別對應李維的人生經歷,被英國皇家學會評選為有史以來最好的科學書。
一九八七年,普利摩・李維從三樓的住家墜樓死亡,享壽六十八歲。
譯者簡介:
吳若楠
台大外文系畢業後,先後於義大利波隆那大學(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Bologna)和羅馬智慧大學(Università Roma la Sapienza)的戲劇系攻讀如何將劇本和演員訓練有效應用於外語學習,並取得碩士學位。回台後曾任教於輔大義大利語系,並擔任自由譯者,譯有《死了兩次的男人》、《他人房子裡的燈》、《逃稅者的金庫》等書。
章節試閱
1. 旅途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我被法西斯民兵逮捕。那時我二十四歲,性情魯莽,沒有人生經驗,法西斯政府施行種族隔離政策,四年以來在種族法的荼毒之下,我已習慣活在我那不切實際的個人世界裡,腦袋裡充滿著自以為是的願景與抱負,有著一些稱兄道弟的同性朋友,但幾乎沒有任何異性朋友。我的內在有一種溫和而抽象的叛逆。
對我而言,躲到山裡、貢獻一己之力去幫助那些稍微比我有經驗的朋友,建立一個在「正義與自由」之下的附屬革命團體是項艱難的抉擇。我們缺乏人脈、武器、金錢以及將這一切弄到手的實際經驗;我們缺乏能幹的人手,另一方面,團體裡充斥著等閒之輩,這些人當中有的意圖良善,有的心懷不軌,他們從平地來到此處,有人在尋找一個不存在的部隊組織或武器,也有人僅僅是在尋求保護、一個藏身之處、一個可以取暖的地方,或一雙鞋。
當時,還沒有人教過我一項後來我在集中營裡迅速學會的教條,即人的首要天職,是採取適當的手段實現自己的目標,犯錯者必須付出代價;因此,我不得不將那之後所發生的一切視為天經地義。某個深夜,法西斯民兵出動了三個百人隊,試圖向駐紮在鄰近山谷中,比我們強大和危險得多的另一支革命軍發動突襲,但在幽微的曙光中,他們衝進了我們的藏身之處,我被以可疑分子的身分押送至山谷。
在隨後的審訊中,我選擇坦承自己身為「猶太裔的義大利公民」的處境,因為我認為除此之外,我無法以其他方式解釋,為什麼我會生活在一個連「難民」都視為過度偏僻的地方,當時我心裡的盤算是,假使我坦承自己所從事的政治活動,我將遭受極刑且必死無疑(而後來所發生的一切證明當時的我失算了)。作為一個猶太人,我被送到位於摩德納附近的佛索利(Fossoli),那裡有一座大型的中轉營,原本用來囚禁英國和美國的戰俘,後來也漸漸被拿來收容那些不受甫成立不久的法西斯共和政府所歡迎的各類人物。
一九四四年一月底我剛抵達那裡時,營地裡約有一百五十名猶太裔義大利人,但在短短幾週之內,人數便超過了六百。這些人多半是因為自己不謹慎,或被人告發而舉家遭到法西斯黨或納粹黨逮捕。其他少數人之所以來到此處,有的是因為不堪承受流離失所的辛苦,有的是因為生活無以為繼,也有人是因為想要跟已經被捕的同伴生死與共,甚至有些人是因為「遵守法律」而自首。此外還有上百個被拘留的南斯拉夫軍人,以及其他一些因政治因素而被視為可疑分子的外國人。
照理說,眼見SS的一個小隊親自抵達,就連樂觀分子也應心生懷疑;然而大家仍成功地為這個前所未聞的現象找到了合理的解釋,而不是從中推敲出最顯而易見的後果,從而儘管發生了上述的一切,在SS宣布驅逐令的時候,眾人間仍一陣驚惶不知所以。
二月二十日,德軍仔細地巡視了集中營,最後針對差強人意的廚房服務,以及作為供熱燃料的柴火供給不足等項目,公開地向義大利專員提出了嚴正的抗議;他們甚至宣布不久之後會成立一間Ka-Be。然而,二十一日上午我們得知,隔天營地裡的猶太人將啟程離開。所有人皆然:無一例外。即使是孩子、老人、病人也不例外。至於要去哪裡,沒人知道。為十五日的旅途做準備。每發生一起點名未到,就有十個人要被槍斃。
只有少數過度天真和自欺欺人的人仍執意懷抱希望:我們曾與波蘭籍和克羅埃西亞籍的難民長談,我們知道啟程代表著什麼。
傳統上,人們會為被判處死刑的人舉行一個莊嚴的儀式,意在宣告任何激昂與憤恨就此熄滅,而作為一個正義之舉,這不過是面對社會的一項沉痛義務,如此一來就連劊子手本身都可以對被害者心懷憐憫。因此,人們不對受刑人提供任何外在的關懷,受刑人被允許獨處,此外若他有意願,人們會提供他各種精神上的慰藉,總之設法讓他感覺到圍繞在自己身邊的並非仇恨或迫害,而是必然性與正義,以及伴隨著刑罰而來的寬恕。
但我們並未獲得此種待遇,因為我們人數太多,而時間有限,況且,到頭來,我們究竟應該為了什麼事懺悔、我們又做了什麼應受寬恕的事?因此,義大利專員下令在進行決定性的公布之前,所有的服務必須持續運作;如此一來,廚房繼續供餐,清潔人員一如既往地執行勤務,就連營地裡那座小型學校的教師和教授們都繼續教授晚間的課程,就像平常的每一天一樣。然而,那天晚上,孩子們未被派發任何作業。
然後,夜晚來臨了,大家都知道,那是人類的雙眼不應看見的夜晚,一個逃不過的死劫。所有人都被告知了。沒人,無論是義大利籍或德國籍的警衛,沒人有勇氣前來見證與死亡四目相對的人究竟在做些什麼。
每個人各自以最適合自己的方式向生命告別。有些人祈禱了起來,其他人毫無節制地狂飲,還有一些人放縱在最後一回的激情裡。但人母們徹夜不眠,她們認真地準備旅途所需的食物,幫孩子們洗澡,收拾好行囊,黎明時,鐵絲網上掛滿了孩童的衣物,晾在那兒風乾;母親們也沒有忘記背巾、玩具和枕頭,那些孩子們總是用得上的林林總總的小東西,她們如數家珍。換作是你,你也會這麼做吧?假使明天他們就要對你和你的孩子狠下殺手,你總不會今天就不餵孩子吃東西了吧?
六A棚屋住著老加騰紐、他的妻子和他眾多的兒女、孫子,以及他那些手腳勤快的女婿和兒媳們。他們全家都是木匠,來自於的黎波里,在為數眾多且漫長的旅途之中,他們始終攜帶著做工的家當、平底鍋及手風琴和小提琴,以便在一整天的勞動之後用來彈奏和伴舞,因為他們是歡樂而虔誠的一群人。他們的女人是首先抓緊時間著手為接下來的旅程預做準備的人,她們沉默而俐落,以爭取更多時間用來哀悼;當一切準備就緒,麵餅烤好了,行囊也紮緊了,接著她們會脫下鞋子,鬆開頭髮,將葬禮用的蠟燭排在地上,並根據祖先流傳下來的習俗點亮燭火,接著她們席地而坐,圍成一個圓圈進行哀悼,徹夜祈禱與哭泣。我們成群地佇足於他們門外,這時,這群沒有故土的人的古老傷痛也降臨到我們的靈魂當中,被迫出走者那一世復一世、不帶任何希望的傷痛,對於我們而言是種前所未有的感受。
黎明的到來彷彿是一記背叛;再次升起的太陽彷彿與那些決意殲滅我們的傢伙狼狽為奸。各種感覺在我們的內心裡激盪,在一個無眠的夜晚之後,全心的接納、無從宣洩的反抗、宗教性的臣服、恐懼、絕望匯流成一種不受控制的集體瘋狂。沉思與判斷的時間已經結束,大腦的每個動靜都消融在脫序的騷動中,其中,有關於家園的美好回憶猛地在我們腦海裡升起,如今它們依然如此鮮明,彷彿伸手可及,卻利劍般地帶給我們疼痛。
當時,我們對彼此說了並做了許多事;但有關這一切最好不要留下任何的回憶。
德國人以一種一絲不苟的方式點了名,之後我們被迫適應這種詭異的精確。最後,Wieviel Stück,元帥如此問道;下士立馬敬禮回覆:共六百五十「件」,一切正常;接著便將我們裝載到敞篷巴士裡,運送至卡爾皮火車站。在這裡,我們等待火車和旅途的配給。在這裡,我們第一次遭到毆打:整件事是那麼的陌生和不合邏輯,我們甚至沒有為此感到痛苦,不論是身體還是靈魂。只有一股深沉的震驚:人如何能夠如此不帶憤怒地毆打另一個人?
火車車廂總共是十二個,而我們總共是六百五十人;我所在的車廂裡只有四十五個人,但那是個狹小的車廂。於是,就這樣,在我們的眼前,在我們的腳下,這就是著名的德軍軍運列車,那種沒有返程的列車,也就是我們以往心驚膽跳並帶著幾分不可置信的心情,經常聽人描述過的那種列車。正是如此,一切按部就班:貨車車廂,從外面鎖上,毫無憐憫地將男人、女人、小孩等貨物塞在車廂裡,一趟通往虛無的旅程,列車向下行駛,駛向世界的底部。這一次,車裡裝的是我們。
每個人在他的人生中,或早或晚都會有此發現,即極致的幸福是無法達成的,但很少有人思考過相反的論點:即極致的苦難也是無法達成的。與這兩種極致的狀態相抗衡而使其無法實現的處境,便是人的處境,一種與任何的無限為敵的處境。與其相抗衡的是人對於未來那不完整的認識;而在某些情況下,這被稱作希望,除此之外,則被稱作關於未來的不確定性。與其相對的,是終有一死的確定性,死亡是任何歡樂的終點,也是任何痛苦的終點。與其相抗衡的,是無可避免的物質解救,物質上的解救一方面污染了任何長久的幸福,另一方面也不遺餘力地讓我們不去注意發生在我們身上的那份不幸,支解我們對於那份不幸的感受,讓我們能夠承受它。
旅途中及旅途後,讓我們得以持續漂浮在無底的絕望與空無之上的,正是困厄、毆打、寒冷與飢渴,而非求生意志或一心一意的聽天由命,而世上又有幾人能有此境界,而我們,我們充其量只是一種平凡無奇的人類標本。
車門很快被關上,但列車一直到晚上才啟程。聽到目的地的名稱時,大家都鬆了一口氣。奧斯維辛:對於當時的我們而言,這是個沒有意義的名稱;但它總該對應著這塊土地上的某個地方。
火車行駛得非常緩慢,漫長的停留令人感到煩躁不安。通過小窗,我們看見阿迪傑山谷那蒼白高聳的懸崖,看見了最後幾個義大利城市的名稱。第二天中午我們路過了布倫內羅,所有人都站了起來,但都沒人吭聲。我在心中勾勒著返程的情景,殘忍地想像著那次的過境會有何種不人道的喜悅,車門敞開著,我們看見了頭幾個義大利的地名,但沒有人想要逃跑⋯⋯我環顧四周,心想在這堆可憐的人類灰塵當中有多少人會被命運擊倒。
我所在的車廂的四十五人當中只有四個有幸再次見到家園;這個車廂遠比其他車廂來得幸運。
我們飢寒交迫:每次停車,我們都大聲地要水,不然一捧冰雪也好,但我們的請求很少被聽見;押送我們的士兵會趕走那些試圖接近我們的人。兩位還在哺乳的年輕母親日以繼夜地懇求他們供水。飢餓、疲勞與失眠比較不那麼折騰人,緊繃的神經讓這一切變得不那麼難熬:但夜晚是無止盡的噩夢。
很少人能帶著尊嚴赴死,而辦得到這一點的往往是令你意想不到的人。很少人懂得沉默和尊重其他人的沉默。我們不安穩的睡眠常中斷,因吵雜而無意義的爭執、咒罵或用來回應某些煩人而不可避免的身體接觸的反射性拳打腳踢。這時便會有人點燃黯淡的燭火,照亮俯臥在地的一團陰暗蠕動,那是一種由人類所構成的物質,難以辨識的、流動的、要死不活而痛苦的,三不五時會抽搐一下,接著又立刻被疲勞所湮滅。
通過小窗,我們看見我們所認識和不認識的奧地利城市的名稱,薩爾斯堡、維也納,接著是捷克的城市,最後是波蘭的城市。在第四天的晚上,天氣轉寒:火車穿過無止無盡的黑色松樹林,我們感覺得到車正在爬坡。積雪很深。這想必是一條支線,車站都很小,而且幾乎空無一人。列車停留的時候不再有人嘗試與外界溝通:如今,我們感覺自己已身在「他方」。有一次,列車在一個廣闊的田野裡停留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接著繼續以極其緩慢的速度前進,深夜裡來到一個黑暗無聲的平原後便不再前進。
放眼望去,軌道的兩側是紅白交錯的燈火,一望無際;但感覺不到任何有人類聚落的人聲雜處。在最後的一根蠟燭那吃力的火光之下,不再聽得見任何屬於人的聲音,我們等待著事情的發生。
在整個旅程中,我身旁有一名女子,和我一樣緊緊地被嵌在身體和身體之間。我們彼此已經認識很多年,這個不幸的遭遇同時攫獲了我們,但是我們對彼此所知甚少。那時,在做出決定的時刻,我們彼此說了一些活人之間不會說的事。我們問候了彼此,短暫的問候;我們各自向對方的生命致意。我們不再感到恐懼。
鬆綁的一刻突然來到。車門嘩啦地被打開,黑暗中迴盪著以陌生的語言所發出的號令,德國人發出號令時,那野蠻的咆叫彷彿宣洩著積壓了好幾個世紀的憤怒。我們的眼前出現一條被探照燈照亮的寬闊月台。更遠的地方有一排卡車。接著一切又恢復安靜。有人翻譯道:必須帶著行李下車,並將它們沿著火車放好。頃刻間,一團陰影淹沒了月台,但我們不敢打破那片寂靜,所有人都忙著搬行李,人們尋找著彼此,膽怯地壓低聲音叫喚彼此。
十多個SS站在一旁,帶著漠然的神情,雙腿叉開著站。接著,他們在我們之間移動,並以一種輕柔的聲音,岩石般的表情,迅速地以七零八落的義大利語,一個接著一個,向我們問了起來:「幾歲?健康或生病?」,並根據不同的回覆分別指示我們走往兩個不同的方向。
水族箱一般,夢境一般,一切寂靜無聲。我們原以為會有什麼驚心動魄的事發生:但這些人似乎只是普通的警員。這點令人感到疑惑,卻又令人卸下心防。有人鼓起勇氣詢問有關行李的事,他們回答說:「行李待會兒」;對那些不想與妻子分開的人,他們說:「後來又會一起」;許多母親不願被跟孩子拆散,他們說:「好,好,孩子一起。」自始至終,他們都帶著一種例行公事的平靜;但倫佐向他的女朋友弗蘭西斯卡告別時拖延了太久,他們就隨手朝他的面孔射了一槍,倫佐倒到了地上:那是他們日復一日的例行公事。
十分鐘以內,所有還能勞動的男子便被集合成一組。至於其他人——女人、孩子、老人——有關那時或那之後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就不得而知了:事情純粹而簡單,夜晚吞噬了他們。如今大家都知道,在那次迅速而簡略的篩選中,我們每個人都依照是否為能為「大德意志國」效力而被判別為有用者或無用者;我們知道,與我們搭乘同一班列車的人當中,只有九十六個男人和二十九個女人分別被分配到布納—莫諾維茨集中營(Buna-Monowitz)和比克瑙集中營(Birkenau),而兩天後,其他總數加起來超過五百的人無一倖存。我們還知道,這個用來判定一個人是否還能幹活的薄弱原則並不總是被遵守,那之後,他們往往採取另一種較為簡單的方法,即敞開車廂兩側的門,不再向剛剛抵達的人發出任何的警告或指示。他們隨機決定,從列車某一側的門下車的人進集中營,從另一側下車的,進毒氣室。
艾蜜莉亞就是這樣喪命的,當時她才三歲;因為對於德國人而言,處死猶太人的小孩是一種再明顯不過的歷史必然。艾蜜莉亞是來自米蘭的阿爾多.李維工程師的女兒,她是個充滿好奇心、企圖心、開朗且聰慧的小女孩;旅途中,在擁擠不堪的車廂裡,她的父母會在一只鋅製的小盆裡用溫水幫她洗澡,那是一位不肖的德國技師允許他們從火車的引擎拆下的——那列載著所有人駛向死亡的火車。
就這樣,一瞬間,令人猝不及防地,我們的婦女、我們的父母、我們的孩子就這樣消失了。幾乎沒有人有機會向他們告別。我們隱約瞥見他們的身影隱沒在月台另一端黑壓壓的人影間,接著就什麼都看不到了。
探照燈的光束下浮現了兩組怪異的人馬。他們三人一組、整齊劃一地行走著,笨拙生硬的步伐看起來很詭異,他們垂著頭,手臂僵直。他們頭上戴著一只滑稽可笑的小帽,身上穿著長條紋外套,即使在暗夜裡,而且距離很遠,也看得出骯髒破爛。他們包圍著我們站成一大圈,與我們保持距離,他們不發一語,著手搬運我們的行李,並在空蕩的車廂間進進出出。
我們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這一切顯得瘋狂而難以理解,但有件事我們理解了。這就是在前頭等著我們的轉化,明天我們也將變得如此。
不知怎的,我發現自己被裝載到一輛卡車上,同行的約莫還有三十人。夜裡,卡車全速上路,我們的頭頂上被什麼蓋住了,看不見外面,但可以從一路的顛簸得知這是條蜿蜒崎嶇的道路。他們該不會沒派士兵看守我們?向下一躍?太遲,已經太遲了,我們所有人都已被拋到「底下」了。此外我們便很快地發現我們並非沒人看守:有一個很怪異的守衛。那是一個德國士兵,身上配備有各式武器。一片漆黑裡我們看不見他,但每當顛簸的車輛劇烈搖晃,我們成堆地東倒西歪時,都會感覺身體與硬物接觸。那個人會點亮手電筒,他沒對我們咆哮:「臭小子,你慘了」,反倒非常有禮地用德語或混雜語言——詢問我們是否有錢或手錶可以給他,反正後來就用不到了。這不是一項命令,也不是規章:這顯然只是負責擺渡我們的卡戎私自發起的一項行動。此事在我們的內心激起了憤怒、苦笑以及一種莫名的寬慰感。
1. 旅途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我被法西斯民兵逮捕。那時我二十四歲,性情魯莽,沒有人生經驗,法西斯政府施行種族隔離政策,四年以來在種族法的荼毒之下,我已習慣活在我那不切實際的個人世界裡,腦袋裡充滿著自以為是的願景與抱負,有著一些稱兄道弟的同性朋友,但幾乎沒有任何異性朋友。我的內在有一種溫和而抽象的叛逆。
對我而言,躲到山裡、貢獻一己之力去幫助那些稍微比我有經驗的朋友,建立一個在「正義與自由」之下的附屬革命團體是項艱難的抉擇。我們缺乏人脈、武器、金錢以及將這一切弄到手的實際經驗;我們缺乏能幹的人手...
推薦序
一本關於死亡營的書
普利摩‧李維描述道,有一個於午夜時分再三折騰集中營囚犯的夢——他們夢到自己回家了,試圖將自己所經歷的痛苦告訴親朋好友,卻在一陣荒涼的悲痛中意識到,根本沒有人在聽,沒有人可以理解這一切。我相信,所有試著將自己恐怖經歷付諸文字、寫成回憶錄的倖存者,心中想必也都曾被那股荒涼的悲痛措手不及地佔據。他們倖存了下來,這是種僭越人性底線、任何文字都無法還原的經歷,他們永遠無法將那恐怖經歷如實地傳達給任何人,而那份記憶將繼續迫害他們,無法被理解的煎熬使那股悲痛無限蔓延。
相較於實際發生過的一切,集中營一類的史實,似乎讓任何一本書都顯得蒼白無力。儘管如此,關於這個主題,普利摩‧李維給了我們一本巨著:1948年德希爾瓦初版的《如果這是一個人》,這本書不僅是一份強而有力的見證,其字裡行間更展現了真切的敘事力量,這將在人們心中留下不可抹滅的記憶,成為有關二戰的文學著作中,最美麗的文學作品。
普利摩‧李維於一九四四年初,隨著佛索利集中營的義大利猶太人分隊一起被運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這本書正是從佛索利中轉營出發開始(見第一章老加騰紐的故事),在這幕,我們馬上感受到一個世紀以來四處漂泊的民族那聽天由命的沉重,而這樣的沉重貫穿全書。他們啟程、抵達奧斯維辛,接著又是令人感到椎心刺骨的一幕:男人們和他們的女人、小孩被拆散,從此再無音訊。接著便是集中營的生活。李維不止於讓事實說話,亦評論事實,但從未提高音調,也不曾刻意採取冷靜的語調。他只是精準而平靜地研究:一個泯滅人性的實驗裡,置身其中的人,究竟能保有幾分人性。
Null-Achtzen,018,這位與李維一起勞動的伙伴,彷彿行屍走肉般不再有任何反應,絲毫不予抵抗地邁向死亡。集中營裡多數人向此類人看齊:這類人進入了一個泯滅精神、物質,最終必然以毒氣室收場的緩慢過程。真正的標竿者是特權人士(Prominenten):「懂得門道」的人,這種人找到給自己天天加飯的方法,不多也不少,就剛好弄到確保自己不被淘汰的分量,他成功取得了一個位置,一個能夠支配他人,並利用他人苦難而生的位置,這種人,將所有精力都用在一個基本而至高無上的目的上:存活。
李維為我們呈現的人物具有完整靈魂,是真實且具體的人:工程師阿爾弗雷德L.,他在受苦的集中營囚犯中,繼續維持原本社交生活中所擁有的主導地位;讓人覺得荒謬的埃利亞斯,彷彿在集中營這塊泥濘土地中出生,根本無法想像他身為自由人的模樣;以及令人不寒而慄的潘維茨博士,是日耳曼科學狂熱主義的化身。李維描繪的某些場景為我們還原了具體的氛圍與世界:每天早晨伴隨著被強迫勞動的囚犯上工的伴奏,鬼魅般地象徵一種幾何式的瘋狂;狹窄臥鋪裡無數個折騰的夜晚,同床伙伴的腳緊挨著你的臉;篩選要移送誰到毒氣室的恐怖場景;以及絞刑臺那一幕,當置身於屈服與虛無的地獄裡,仍然找到勇氣密謀起義的人,他從刑架上發出了呼吼——Kamaraden, ich bin der Letzte!
「同志們,我是最後一個了!」
伊塔羅・卡爾維諾
一九四八年五月六日,刊載於義大利《團結報》
一本關於死亡營的書
普利摩‧李維描述道,有一個於午夜時分再三折騰集中營囚犯的夢——他們夢到自己回家了,試圖將自己所經歷的痛苦告訴親朋好友,卻在一陣荒涼的悲痛中意識到,根本沒有人在聽,沒有人可以理解這一切。我相信,所有試著將自己恐怖經歷付諸文字、寫成回憶錄的倖存者,心中想必也都曾被那股荒涼的悲痛措手不及地佔據。他們倖存了下來,這是種僭越人性底線、任何文字都無法還原的經歷,他們永遠無法將那恐怖經歷如實地傳達給任何人,而那份記憶將繼續迫害他們,無法被理解的煎熬使那股悲痛無限蔓延。
相較於實際發生過的一切...
作者序
前言
我很幸運,直到一九四四年才被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那時基於勞動力日益短缺,德國政府已決定延長待宰囚犯的平均壽命,囚犯的生活條件獲得顯著的改善,並暫時中止肆意殺害囚犯。
因此,關於納粹種種令人髮指的暴行,這本書並不會提供更多相關細節,如今有關集中營這個主題的種種已為普世讀者所知。這本書的宗旨不在於揭發某些尚不為世人所知的罪行,而在於提供更多資料,讓我們能冷靜地研究人性的某些面向。個人也好,整個民族也好,許多人往往認定或不知不覺地抱持著以下信念,認為「非我族類就是敵人」。在大多數的案例裡,這種信念像一種潛伏的感染般沉睡於人性深處,只會偶爾猛然發作,而非根植於一種有意識的思想體系。但一旦發生此種情形,當潛在的教條成為一個大前提,並以三段論演繹,位於思路盡頭的,便是集中營。集中營是人類一絲不苟地將某種世界觀發揮得淋漓盡致的後果:只要這個世界觀繼續存在,其後果便會對我們構成威脅。我們必須將集中營的歷史理解為一種警示危險的不祥預兆。
我意識到這本書有種結構上的缺陷,也希望各位能夠諒解這一點。具體上雖然並非如此,但作為一種意圖與構思,早在我被囚禁在集中營的那些日子裡這本書便已誕生。在獲救之前和之後,一種向「他人」傾訴自身的經歷,讓「他人」也能感同身受的需求便佔據了我們,那是股緊迫而強烈的衝動,與人類其他的基本需求不相上下:這本書的書寫便是為了滿足此種需求;主要是為了一種內在的救贖。因此本書顯得有點零碎。章節的排序不按照邏輯,而是對應著內心的緊迫性。連貫和整合的工作是事後按照計畫完成的。
我想我毋須多此一舉地強調,書中所描述的一切並非出於杜撰或虛構。
普利摩‧李維
前言
我很幸運,直到一九四四年才被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那時基於勞動力日益短缺,德國政府已決定延長待宰囚犯的平均壽命,囚犯的生活條件獲得顯著的改善,並暫時中止肆意殺害囚犯。
因此,關於納粹種種令人髮指的暴行,這本書並不會提供更多相關細節,如今有關集中營這個主題的種種已為普世讀者所知。這本書的宗旨不在於揭發某些尚不為世人所知的罪行,而在於提供更多資料,讓我們能冷靜地研究人性的某些面向。個人也好,整個民族也好,許多人往往認定或不知不覺地抱持著以下信念,認為「非我族類就是敵人」。在大多數的案例裡,這種信...
目錄
推薦序:一本關於死亡營的書——伊塔羅・卡爾維諾
如果這是一個人Se questo è un uomo
前言
1. 旅途
2. 在底下
3. 入門
4. Ka-Be
5. 我們的夜晚
6. 勞動
7. 美好的一天
8. 善惡的此岸
9. 滅頂與生還
10. 化學考試
11. 尤里西斯之歌
12. 夏天裡的事
13. 一九四四年十月
14. 克饒斯
15. Die drei Leute vom Labor
16. 最後一人
17. 十天的故事
附錄一:與普利摩.李維的對話——菲利普.羅斯
附錄二:普利摩・李維生平年表
推薦序:一本關於死亡營的書——伊塔羅・卡爾維諾
如果這是一個人Se questo è un uomo
前言
1. 旅途
2. 在底下
3. 入門
4. Ka-Be
5. 我們的夜晚
6. 勞動
7. 美好的一天
8. 善惡的此岸
9. 滅頂與生還
10. 化學考試
11. 尤里西斯之歌
12. 夏天裡的事
13. 一九四四年十月
14. 克饒斯
15. Die drei Leute vom Labor
16. 最後一人
17. 十天的故事
附錄一:與普利摩.李維的對話——菲利普.羅斯
附錄二:普利摩・李維生平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