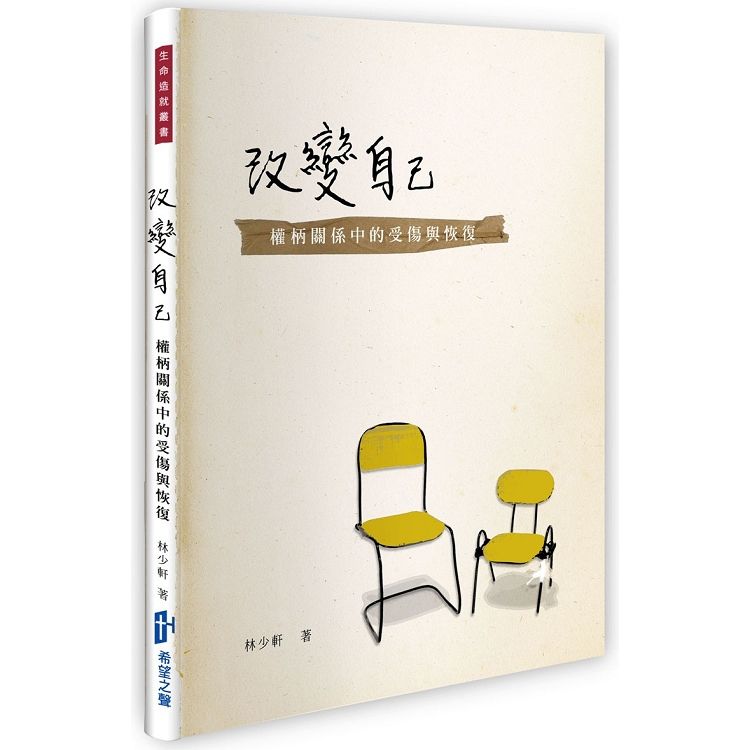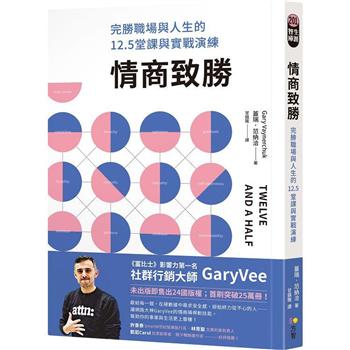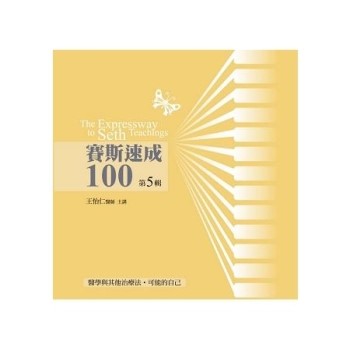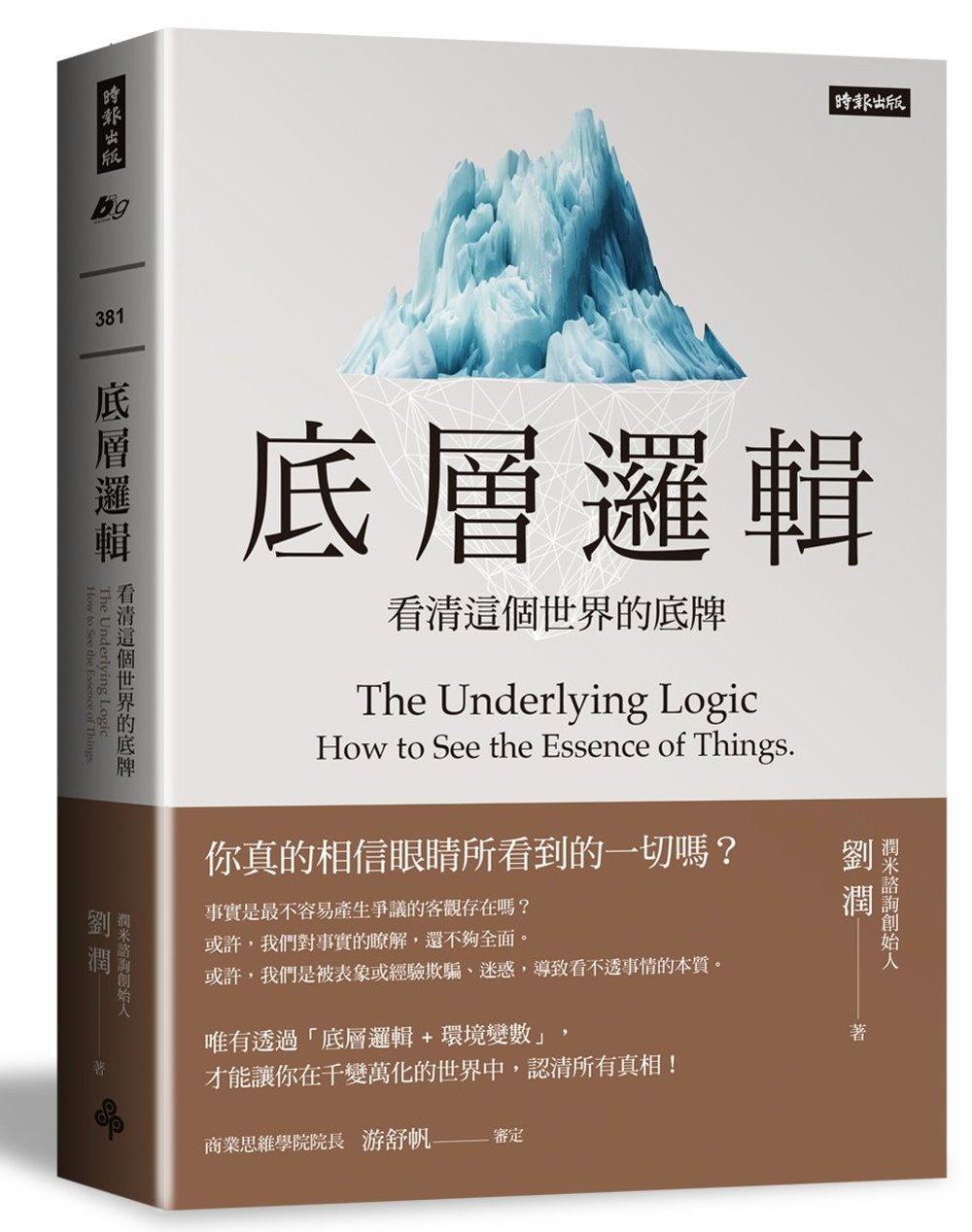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改變自己:權柄關係中的受傷與恢復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5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1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140 |
人際關係 |
$ 176 |
中文書 |
$ 176 |
基督宗教 |
$ 180 |
其他 |
$ 180 |
宗教 |
$ 200 |
宗教命理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圖書名稱:改變自己:權柄關係中的受傷與恢復
內容簡介
這本書的成書過程是上帝醫治我與我自己反思的旅程,也是改變的開始。意識到自己與權柄間的衝突與傷害是如此深刻地在影響著我,於是抱持著想要寫下個人經歷與看法的心情,我從「病人視角」出發寫下了「在權柄關係中受傷」的心路歷程。然而,因著這段過程也讓我發現「如果沒有平安的內心便無法創造平安的世界」,若把想改變環境的精力集中於「改變自己」,環境就比較可能因為我們的改變而產生新契機,所以,如果想要轉化世界,可能最容易開始的第一步就是轉化自己吧!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林少軒
作者林少軒在學生時期活躍於學生自治圈,曾經擔任臺灣師範大學學生會長、臺灣師範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教育部學生自治暨公民教育實踐政策諮詢小組召集人,參與大專校院學生自治組織評鑑設計、負責數屆全國學生自治研討會規劃與籌備,著有「踏入學生自治的世界」一書並獲選為大專優秀青年。
認識耶穌之後開始在教會服事,參與牧養與輔導工作,之後接觸了內在醫治的課程、培訓與服事。本書出版時,作者是美國雷汀伯特利教會──毫無隱藏事工臺灣地區代表,負責婚姻與親密關係的事工,他勇於突破、真誠、真實、知性的特質以及對社會環境的關懷,使他的文章經常引發人的感觸、思考與回響。
林少軒
作者林少軒在學生時期活躍於學生自治圈,曾經擔任臺灣師範大學學生會長、臺灣師範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教育部學生自治暨公民教育實踐政策諮詢小組召集人,參與大專校院學生自治組織評鑑設計、負責數屆全國學生自治研討會規劃與籌備,著有「踏入學生自治的世界」一書並獲選為大專優秀青年。
認識耶穌之後開始在教會服事,參與牧養與輔導工作,之後接觸了內在醫治的課程、培訓與服事。本書出版時,作者是美國雷汀伯特利教會──毫無隱藏事工臺灣地區代表,負責婚姻與親密關係的事工,他勇於突破、真誠、真實、知性的特質以及對社會環境的關懷,使他的文章經常引發人的感觸、思考與回響。
目錄
推薦序
自序
第一章 摔碎的椅子與劃破的臉孔
第二章 我的成長經歷
第三章 認識權柄
第四章控告與不饒恕
第五章知識、自由與順服
第六章一再重複
第七章需要做出改變
第八章 醫治與更新之路
附錄 面對衝突的步驟
自序
第一章 摔碎的椅子與劃破的臉孔
第二章 我的成長經歷
第三章 認識權柄
第四章控告與不饒恕
第五章知識、自由與順服
第六章一再重複
第七章需要做出改變
第八章 醫治與更新之路
附錄 面對衝突的步驟
序
自序
國中以前的我雖然開始懂得反思卻仍然懵懂,主要精力都花在玩樂、做白日夢、應付課業、躲避老師與父母的棍子,只要今天上學沒考試也沒挨打,對我而言那就是幸福。高中時期因為參與扶輪社一年的交換學生計畫而去了德國,回來之後變得更有自己的想法,開始加入學校班聯會、擔任學權組組長,展開了我與學校「對話」的旅程。大學時期擔任學校的學生會長、成為當時教育部訓委會的諮詢委員以及臺灣師範大學的校長遴選委員,一路上為學生爭取權益、代表學生參與大學自治,後來還寫了《踏入學生自治的世界》這本書。人生幾乎有一半的時間都投入在學生自治工作,是什麼樣的原因讓我有如此動力、願意花費這麼多的精力投入在公共事務裡呢──是因為世界大同的理想?還是許多難以忘懷的傷害?事後想想,應該兩者皆是!二零一四年,台灣爆發太陽花學運,青年與社運團體佔領立法院並且試圖攻佔行政院。凱達格蘭大道上數十萬人遊行結束後,抗議者有組織地在青島東路上搭起棚架輪流上台發言準備長期抗戰,群眾則是零散地在街道上或坐或站,多數人的神情看來相當疲憊,當我走過那裡看見這些情景,內心突然有一股極深的悲痛湧上心頭,而我決定相信耶穌也是在那一年。
上帝造訪我的生命是個非常特別的機遇──祂是如此真實、令人難以抗拒。於是在經過百般掙扎後,我成為基督徒開始了穩定的教會生活,然而在教會裡卻有許多讓我感到不適應的文化,記得第一次參加教會主日時,最讓我驚訝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沒有人舉手問問題」──難道大家都聽懂了嗎?對於牧師在台上的講道內容,大家都沒有別的想法嗎?
現在回想,若沒有上帝的恩典,我想我大概無法熬過那段適應教會文化的日子。在教會文化裡非常強調「某一種順服」的概念,有時候甚至會讓人有一種「如果自己和牧師的想法不同,就是一種錯誤」的感覺,特別若又公開地表達自己的想法,這似乎就是所謂的悖逆,於是我開始感受到在教會「某些強調順服權柄的文化」下,似乎會讓因威權而受傷的人難以從傷害中得著恢復(我就是其中的一例),但是聖經說:「愛裡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因為懼怕裡含著刑罰,懼怕的人在愛裡未得完全」(約翰一書四:18)。聖經中也記載了亞伯拉罕、摩西分別與上帝的互動──在面對全能的上帝時,他們既全然順服也敢於說出自己的想法,最奇妙的是上帝還同意了他們的看法。所以我想,也許上帝眼裡的「順服」是與我當時在教會中所感受到的是有些不同的;同樣的,若沒有上帝的恩典,我也不會看見自己在成為權柄時的樣子──信主以前,我不太認為自己的領導風格有什麼問題,然而在信主之後,我才發現自己的領導風格真是慘不忍睹!作為一位基督徒領袖,本該在領導過程中展現上帝的形象、成為如同耶穌般的僕人領袖,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境下,我急躁易怒的性格卻正好與上帝慈愛的特質相反。坦白說,每次在情緒失控後我都很痛苦,因為我不想這樣卻又做不到,於是便開始思考:我到底怎麼了?又該如何成為一位符合上帝心意的領袖?
這本書的成書過程是上帝醫治我與我自己反思的旅程。在信主不久之後,我開始意識到自己與昔日權柄間的衝突與傷害是如此深刻地在影響著我自己,然而也在尋求協助的過程裡,我發現基督教信仰中關於「權柄」的教導多數都是在傳達「順服權柄」的方法,比較少提到「從權柄傷害中得著醫治」的處方,於是當我和許多基督徒朋友談到出版計畫時,有很多人很興奮、期待教會界能有探討這樣主題的書;有一些人則是覺得我在挑戰一個敏感的議題或者認為由牧者來撰寫會比較適宜。我無意要挑起任何波瀾,只是抱持著想要寫下個人經歷與看法的心情,然而同時也真心認為關於「在權柄關係中受傷」的這個主題或許的確需要有一本從「病人視角」出發的著作。
國中以前的我雖然開始懂得反思卻仍然懵懂,主要精力都花在玩樂、做白日夢、應付課業、躲避老師與父母的棍子,只要今天上學沒考試也沒挨打,對我而言那就是幸福。高中時期因為參與扶輪社一年的交換學生計畫而去了德國,回來之後變得更有自己的想法,開始加入學校班聯會、擔任學權組組長,展開了我與學校「對話」的旅程。大學時期擔任學校的學生會長、成為當時教育部訓委會的諮詢委員以及臺灣師範大學的校長遴選委員,一路上為學生爭取權益、代表學生參與大學自治,後來還寫了《踏入學生自治的世界》這本書。人生幾乎有一半的時間都投入在學生自治工作,是什麼樣的原因讓我有如此動力、願意花費這麼多的精力投入在公共事務裡呢──是因為世界大同的理想?還是許多難以忘懷的傷害?事後想想,應該兩者皆是!二零一四年,台灣爆發太陽花學運,青年與社運團體佔領立法院並且試圖攻佔行政院。凱達格蘭大道上數十萬人遊行結束後,抗議者有組織地在青島東路上搭起棚架輪流上台發言準備長期抗戰,群眾則是零散地在街道上或坐或站,多數人的神情看來相當疲憊,當我走過那裡看見這些情景,內心突然有一股極深的悲痛湧上心頭,而我決定相信耶穌也是在那一年。
上帝造訪我的生命是個非常特別的機遇──祂是如此真實、令人難以抗拒。於是在經過百般掙扎後,我成為基督徒開始了穩定的教會生活,然而在教會裡卻有許多讓我感到不適應的文化,記得第一次參加教會主日時,最讓我驚訝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沒有人舉手問問題」──難道大家都聽懂了嗎?對於牧師在台上的講道內容,大家都沒有別的想法嗎?
現在回想,若沒有上帝的恩典,我想我大概無法熬過那段適應教會文化的日子。在教會文化裡非常強調「某一種順服」的概念,有時候甚至會讓人有一種「如果自己和牧師的想法不同,就是一種錯誤」的感覺,特別若又公開地表達自己的想法,這似乎就是所謂的悖逆,於是我開始感受到在教會「某些強調順服權柄的文化」下,似乎會讓因威權而受傷的人難以從傷害中得著恢復(我就是其中的一例),但是聖經說:「愛裡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因為懼怕裡含著刑罰,懼怕的人在愛裡未得完全」(約翰一書四:18)。聖經中也記載了亞伯拉罕、摩西分別與上帝的互動──在面對全能的上帝時,他們既全然順服也敢於說出自己的想法,最奇妙的是上帝還同意了他們的看法。所以我想,也許上帝眼裡的「順服」是與我當時在教會中所感受到的是有些不同的;同樣的,若沒有上帝的恩典,我也不會看見自己在成為權柄時的樣子──信主以前,我不太認為自己的領導風格有什麼問題,然而在信主之後,我才發現自己的領導風格真是慘不忍睹!作為一位基督徒領袖,本該在領導過程中展現上帝的形象、成為如同耶穌般的僕人領袖,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境下,我急躁易怒的性格卻正好與上帝慈愛的特質相反。坦白說,每次在情緒失控後我都很痛苦,因為我不想這樣卻又做不到,於是便開始思考:我到底怎麼了?又該如何成為一位符合上帝心意的領袖?
這本書的成書過程是上帝醫治我與我自己反思的旅程。在信主不久之後,我開始意識到自己與昔日權柄間的衝突與傷害是如此深刻地在影響著我自己,然而也在尋求協助的過程裡,我發現基督教信仰中關於「權柄」的教導多數都是在傳達「順服權柄」的方法,比較少提到「從權柄傷害中得著醫治」的處方,於是當我和許多基督徒朋友談到出版計畫時,有很多人很興奮、期待教會界能有探討這樣主題的書;有一些人則是覺得我在挑戰一個敏感的議題或者認為由牧者來撰寫會比較適宜。我無意要挑起任何波瀾,只是抱持著想要寫下個人經歷與看法的心情,然而同時也真心認為關於「在權柄關係中受傷」的這個主題或許的確需要有一本從「病人視角」出發的著作。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