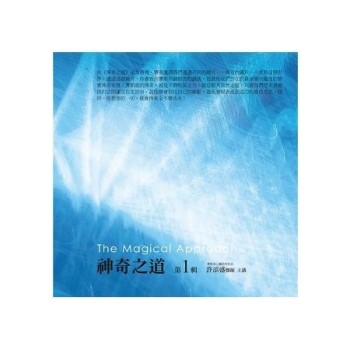離開河
我在淡水河邊生活
已有十幾年的時間
我走過的每一段河岸
每一次輝煌的晚霞
都以詩的方式
改變了河的樣貌
朝前望去
前方已經沒有
看不見的風景
朝後望去
那些陳腐的詩句
有如淤泥
阻礙了河的前進
於是
我將離開
讓未知的一切
重新將我洗滌
我將哭泣
像個不願出生的嬰孩
我將歡笑
彷彿曾經快樂
我將死去
彷彿曾經活過
且完成了一道曲折
蜿蜒的河
已然寂滅的星光
仍在孕育著生命
我的河
儘管是你如此地
波光閃耀
我將離開
我
不是我自誇
我可是蚊子界手搖杯銷售排行No.1
是狗狗最愛追逐與耍狠的對象
是在餐館裡點菜之後
總是被忽略的隱形人
目前的人生似乎
只為了貓咪而活
決心此後不再出門旅行
雖說是為了貓但其實
是根本沒有錢
喝很多水
好像只為了提供足夠的
汗水與淚水
喜歡孤獨與無聊
唯有在這兩種狀態時
才能正常地呼吸
沒有宗教信仰
相信人生即苦
活得愈久苦得愈多
但是只要一朵雲
就能讓我相信全世界
每次看到滿月我就認定
這是世上最美的事物
然而當上弦月懸掛在樹稍
旁邊且綴飾著一顆燦亮的星
我便輕易地放棄了
對滿月的尊崇
我已經很久
沒有看到流星了
我且離開了我最愛的河
在我的夢裡經常出現
毛色斑斕的猛獸
遼闊的海洋
大翅鯨和彩虹
落點
有時難免會感覺到
自己是落在了
錯誤的那一邊
是從小時候在廟會中走失
牽起別人的手叫爸爸
那時開始的嗎?
或者和好友一起
進入一座謎樣的深山裡
就再也沒有走出來了?
又或者是在婚禮上
那枚象徵性的戒指
落地的瞬間?
原來的世界
轉往另一個方向
飛馳而去
唯獨我毫不知情
仍在這陌生的國度裡
拖著別人的病體
生下了不明所以的孩子
為了永遠回不去的故鄉
一次又一次
從夢中驚醒
舊人與新居
一個舊人
捨棄舊有的一切
來到新的城市
新的居所
他能變成一個
全新的人嗎?
而這個以陽光聞名的城市
迎接他
以連月的豪雨
以不間斷的閃電與雷鳴
還有從客廳直達廚房的一次
盛大的淹水
於是他理解了
這終究是一個
陳舊的世界
大雨嚎啕
居民深陷泥沼
曾經以為的自由意志
其實都不是自主的選擇
於是他學會了
如何清理發霉的家具
當酒精擦拭而過
那些可恨的菌絲
便隨之蒸發
接著用漂白水澈底滅絕
彷彿那些黴菌就是
他累世的罪
於是他學會了
將滿地泡爛的紙箱
擠去水分之後
再慢慢地撕碎打包
變成不可回收的垃圾
起初以為的苦
逐漸發展成一種
除舊布新的儀式
到最後
那濃郁的氣味
竟讓他笑了出來
他感覺自己彷彿正在料理著
一鍋味噌湯
湯頭還挺鮮美的呢
大概是柴魚口味的吧
那天深夜
當他從勞務中抬起頭
一個結論忽然
來到眼前:
原來新和舊根本
沒有分別
就好像這首新寫成的詩
其實早已存在
這是波赫士說的
終點也是起點
則是艾略特
至於他則依然是
一臉茫然
順從地來到了
此時此地
因為看不清生命
和一首詩的結尾
而同時感到
喜悅與憂傷
這裡
終於
來到這裡
我渴望許久的
獨居的所在
一座帶有庭院和
星芒狀窗花的
墳墓
冷清、寂靜
每天只有極短暫的時間
陽光斜斜探入
點亮了一小塊磨石子地板
各色卵石在光影中復活
彷彿有魚鱗閃耀
水聲喧嘩
我偽裝自己
仍然活著
和鄰居打招呼
準時倒垃圾
為植物澆水
直到它們死去
我偽裝自己
尚未死去
在貓咪的嘔吐物和肛門腺之間
在蚊子飽脹泛紅的身軀之內
我得不時地發出聲響
寫下定時定量的懺悔
我拔除雜草
移開亂石
抹拭塵埃
為這些徒勞之舉
找到陡峭的階梯和
美麗的雕花扶手
還有那片
向下墜落的
星空
每天、每天
為我帶回睡眠
且覆蓋我以柔軟的
雜草、亂石
塵埃、燐火
音樂
在白天與黑夜
交界的地方
把光收起來
把顏色收起來
風裡不再有
誰的凝望
世界回到黑暗
的懷中
幾個音符
敲擊著
這廣袤無邊的
棺廓
飄搖的思緒
流動的血液
空氣的粒子
都悄悄地
更改了結構
而後從星空
的邊緣
傳來回聲
越過了玫瑰
貓眼和
獵戶座
哭與笑
尚未被分開的
那個回聲
來處和去向
還沒有差別的
那個回聲
那是我們在
媽媽的肚子裡
曾經的提問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0.018秒-隱匿詩集的圖書 |
| |
0.018秒-隱匿詩集 出版日期:2021-08-20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77 |
Books |
電子書 |
$ 315 |
詩 |
$ 315 |
中文書 |
$ 315 |
文學作品 |
$ 315 |
現代詩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0.018秒-隱匿詩集
臺灣詩人隱匿的詩集。
根據《摩訶僧祇律》,一日一夜有30個「須臾」,1.2萬個「彈指」,24萬個「瞬間」,480萬個「剎那」,由此推知「一剎那」是0.018秒……每一首詩的生發就在那0.018秒之間,只是詩人困在有限的肉身和文字的迷障中,註定必須為了那一剎那,而服一輩子的勞役。
在那些偷來的時光之中,我成為現在的帝皇與詩的臣僕,而當這些詩作逐漸累積,我便開始為它們打造一個合適的容器:以極為笨拙的手法,耗費漫長的時間,反覆思索與修改,將這些詩作排列組合,調整版面與行距,甚至為〈這裡〉添加了另一首影子般的詩〈那裡〉,最後再加上插圖與封面,終至,成為一本詩集。
我想像著,我在刑期之間完成的這些書,即是我的墓碑,這該是多麼美。而我在意或說著迷的,從來不是歷史定位,而是寫詩的時刻,我在宇宙間的定位。
作者簡介:
隱匿
寫詩、貓奴。
著有詩集:《自由肉體》、《怎麼可能》、《冤獄》、《足夠的理由》、《永無止境的現在》、《0.018秒》。
有河book玻璃詩集:《沒有時間足夠遠》、《兩次的河》。
散文集:《河貓》、《十年有河》 、《貓隱書店》。
法譯詩選集:《美的邊緣》。
即將出版:散文集《病從所願》。
章節試閱
離開河
我在淡水河邊生活
已有十幾年的時間
我走過的每一段河岸
每一次輝煌的晚霞
都以詩的方式
改變了河的樣貌
朝前望去
前方已經沒有
看不見的風景
朝後望去
那些陳腐的詩句
有如淤泥
阻礙了河的前進
於是
我將離開
讓未知的一切
重新將我洗滌
我將哭泣
像個不願出生的嬰孩
我將歡笑
彷彿曾經快樂
我將死去
彷彿曾經活過
且完成了一道曲折
蜿蜒的河
已然寂滅的星光
仍在孕育著生命
我的河
儘管是你如此地
波光閃耀
我將離開
我
不是我自誇
我可是蚊子界手搖杯銷售排行No.1
是狗狗最愛追逐與耍狠的對象
是在餐館裡點菜之後
總是...
我在淡水河邊生活
已有十幾年的時間
我走過的每一段河岸
每一次輝煌的晚霞
都以詩的方式
改變了河的樣貌
朝前望去
前方已經沒有
看不見的風景
朝後望去
那些陳腐的詩句
有如淤泥
阻礙了河的前進
於是
我將離開
讓未知的一切
重新將我洗滌
我將哭泣
像個不願出生的嬰孩
我將歡笑
彷彿曾經快樂
我將死去
彷彿曾經活過
且完成了一道曲折
蜿蜒的河
已然寂滅的星光
仍在孕育著生命
我的河
儘管是你如此地
波光閃耀
我將離開
我
不是我自誇
我可是蚊子界手搖杯銷售排行No.1
是狗狗最愛追逐與耍狠的對象
是在餐館裡點菜之後
總是...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自序】
序
隱匿
一剎那與一輩子
我十五歲開始寫詩。當時的國文老師帶領全班同學登上集集大山,我在山頂上的竹林前面,遇見了一大片映照著夕陽的、遼闊無邊的雲海……在那種令世界秩序崩潰的、壓倒性的美之前,我頭一次發現:尋常的語言和文字完全失去了作用。下山後好一段時間,我思索著這不可言說之物究竟是什麼?然後,幾個字句浮現,我開始寫詩。
畢業後進入職場,我還是斷續地寫著,只是始終不得要領,下筆如有千金重,詩的產量也很少。一直到我30歲,在某次車...
序
隱匿
一剎那與一輩子
我十五歲開始寫詩。當時的國文老師帶領全班同學登上集集大山,我在山頂上的竹林前面,遇見了一大片映照著夕陽的、遼闊無邊的雲海……在那種令世界秩序崩潰的、壓倒性的美之前,我頭一次發現:尋常的語言和文字完全失去了作用。下山後好一段時間,我思索著這不可言說之物究竟是什麼?然後,幾個字句浮現,我開始寫詩。
畢業後進入職場,我還是斷續地寫著,只是始終不得要領,下筆如有千金重,詩的產量也很少。一直到我30歲,在某次車...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 一剎那與一輩子
離開和抵達
離開河
我 們
我
落點
舊人與新居
這裡
那裡
祕徑
靜下來的時候
音樂
光的密碼
被吃掉的日子
黃金的舞蹈
阿西西的玫瑰
春天的故事
秋天寫給春天
給落選者的祝福
文學獎評審
詩人五衰
詩殭屍頌
老人的回收事業
老年的詩
三點座標
隱匿疫情
屋內的人
拿槍的人
熱血與冷血
惡鄰
人造雲
特殊的月亮
月亮本來
由來
媽媽的話
我以為最美的
路痴的導航系統
歌頌有瑕疵的水果
薛西弗斯問號
富人的一分鐘
沉重的雞蛋
愛的條件
天國近了
水仙
過慮
自主健康管理
居家隔離
愛在瘟疫
病從所願
此刻的構成
...
離開和抵達
離開河
我 們
我
落點
舊人與新居
這裡
那裡
祕徑
靜下來的時候
音樂
光的密碼
被吃掉的日子
黃金的舞蹈
阿西西的玫瑰
春天的故事
秋天寫給春天
給落選者的祝福
文學獎評審
詩人五衰
詩殭屍頌
老人的回收事業
老年的詩
三點座標
隱匿疫情
屋內的人
拿槍的人
熱血與冷血
惡鄰
人造雲
特殊的月亮
月亮本來
由來
媽媽的話
我以為最美的
路痴的導航系統
歌頌有瑕疵的水果
薛西弗斯問號
富人的一分鐘
沉重的雞蛋
愛的條件
天國近了
水仙
過慮
自主健康管理
居家隔離
愛在瘟疫
病從所願
此刻的構成
...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