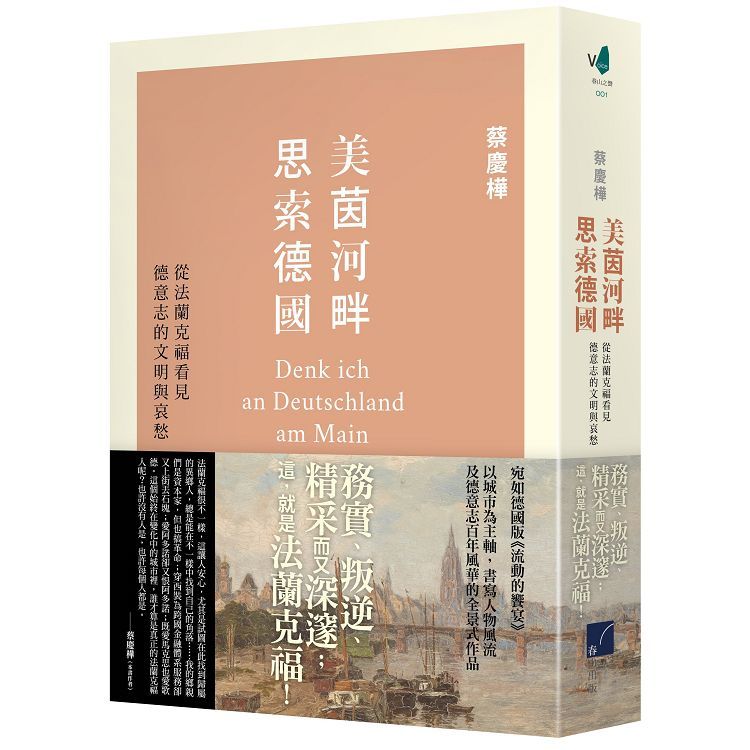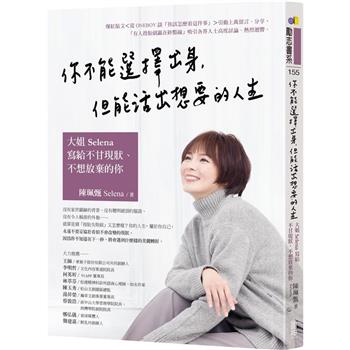六八學運之城
當我還在法蘭克福工作的時候,認識一位在法蘭克福度過六〇年代的朋友。在一次聊天中我提起,正計劃寫一本關於法蘭克福的書,其中有一篇要談學運。他很高興地說,是的,談這座城市不能不談起那個年代的學運,並從家裡拿了張剪報給我看,那是一九六八年,學生們手牽著手上街抗議。他說:你看到了嗎,我就走在第一排。
有意思的是,他本身是法學博士,談起世界各國挑戰政治秩序的運動時,總認為改革甚至革命,不管訴求多麼正當,還是得確定民主憲政的體制不被動搖。但在一九六八年時的他所加入的學運,其實是全面質疑戰後西德體制正當性的。那個年代,對於許多法蘭克福的大學生來說,是生命中難以忘記的一部分。每個人都無畏地走上街頭,覺得這個國家因為自己的行動,正在往更好的地方去。對他們來說,不再能把未來寄托給正在當權的上一代,因為這些人在第三帝國的十二年期間是臣服於獨裁之下的子民,到了共和國時期又未能對下一代交代當時的歷史真相,不提責任,想當成一切都不曾發生。可是對青年人們來說,一切都曾真實的發生,而且,不正確的事情還在繼續發生中。例如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的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對勞動階級的剝削、高等教育的僵固與無批判性、西德在越戰與冷戰中與美國的合謀。
這個反叛的學生世代,剛好在思想上也遇到了理論革命的六〇年代。戰後二十年保守主義並沒有讓德國變得更好,自由主義又僅是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共犯,可是學生們又無法全然接受傳統的左派語彙,因為馬恩所使用的階級、無產者、生產關係、歷史唯物論等等分析方式已過時,一百多年來始終不見左派所允諾的革命。於是,學生們不只挑戰上一代的政治立場,也拒絕上一代的理論宏大敘述,各種新的主體、階級等等以往的社會理論概念退位,尋求社會結構之缺口的「後」思潮興起。霍克海默、阿多諾、哈伯瑪斯等法蘭克福的哲學家們提供的批判理論,缺乏革命的力量。學生們學習了老師所教授的反叛精神,但又相信,要改變這個體制,他們必須更激進,甚至更暴力。
把學生推向街頭的事件中,最具決定性的,是警察槍殺學生,以及學運領袖杜區克遭受右派激進者暗殺,這些暴力事件讓學生相信不可能再任由國家權力宰制,必須起而反抗。於是學生們從課堂上走向了街頭,又走回課堂占領高等教育殿堂,想發動一場從下而上的政治、生活與思想革命。所以整個六〇年代末到七〇年代,學運浪潮席捲整個聯邦共和國。所謂的一九六八分子(1968er),也在這麼長的時間裡奪得了發言權,在政治論述、社會哲學思想、左派理論、文藝創作等領域都想像如何改變世界,累積了極為豐富的成果。倘若我們要理解戰後德國歷史,絕對不可能略過一九六八年。(未完待續)
我的家鄉是文學:文學教宗萊西—拉尼茲基
永遠的局外人
說到法蘭克福與文學,有一個名字永遠留在法蘭克福人的記憶裡,但他不是德國人,他選擇了德國與法蘭克福,做為他第二個家鄉,以及第一個精神的原鄉。
馬賽爾.萊西—拉尼茲基(Marcel Reich-Ranicki),戰後主掌《法蘭克福廣訊報》文藝版的波蘭人,他在這個德國極重要的質報上對德國文學的評論,相當程度上左右了戰後德國寫作與出版的方向,其影響力之大,使得他被暱稱為「文學教宗」(Literaturpapst)。《南德日報》(Suddeutsche Zeitung)總編輯凱瑟(Joachim Kaiser)曾在該報文學版這麼描述他:「德國最被廣為閱讀的、最被畏懼的、最受矚目的、因而最被憎恨的文學批評者。」
一九二〇年,萊西—拉尼茲基出生於波蘭的猶太家庭,他的父親是波蘭商人,母親是說德語的波蘭猶太人,因此萊西—拉尼茲基從小生活在多語的環境裡,但他最喜愛的語言還是德語,那是因為德語對他來說是文化語言。受母親影響,他自小喜歡文學,每年八月二十八日母親生日時,他向母親祝壽,母親總是毫無例外地問他:你知道今天還是誰的生日嗎?
他總是毫不遲疑地說出歌德的名字。
小學時,母親帶他回到兩人的原鄉讀書。他在柏林讀小學,直到一九三八年時高中畢業。早熟的他在小學時已經展現了對文學的熱情,他說,在學校裡因為他比同學都更早能夠閱讀並引述文學作品,使得他在同學間並不受歡迎,他成為「局外人」(Außenseiter)──這個身分,幾乎刻劃了他的一生。 高中畢業後他遭納粹驅趕回華沙,被囚禁在猶太人隔離區,因為通曉德語,得以為占領波蘭的納粹軍隊擔任翻譯。當時在小小的華沙舊城區隔離了幾十萬猶太人,後來爆發了反抗行動,萊西—拉尼茲基也參與了那次反抗,失敗被捕。他與太太原將被送入毒氣室,卻在最後一刻逃離華沙。
波蘭被蘇聯解放後,他加入波蘭共產黨,協助波蘭重建。原來他的姓只有萊西,他不得不加上拉尼茲基,因為萊西太過德國化,也太過猶太化。憑藉其雙語能力,他為波蘭政府的情報機關以及外交部工作,最後也成為我的同行,外派到倫敦擔任波蘭的外交官員。但後來他被召回華沙,並被解職,原因是共產黨政府認定他的意識形態立場與黨不相符。在短暫入獄並獲釋後,他不再為政府做事,而全心投入文學。他開始為報刊撰寫德國文學評論,並在出版德國文學的波蘭出版社工作。最後這位立場被懷疑有問題的前外交官,也被政府下令禁止出版任何作品。波蘭已無他所能容身之處,一九五八年,他帶著妻小,去了德國,從此不再回到家鄉。
他先去了漢堡。漢堡向來是德國的媒體重鎮,《明鏡週刊》、《時代週報》(Die Zeit)、《週日世界報》(Welt Am Sonntag)、《北德廣電》(NDR)、《圖片報》(Bild)等大媒體都在這裡,他很快地找到為各媒體撰寫文學評論的工作。後來,當時最好的報紙《法蘭克福廣訊報》文學版主編出缺,他遂於一九七三年來到法蘭克福,直到二〇一三年過世為止。一九九九年,他出版了《我的一生》(Mein Leben),超過五百五十頁的自傳,文筆優雅清晰,寫出他從威瑪共和、納粹德國到聯邦共和國、從華沙到柏林、漢堡、法蘭克福的動盪一生,每一頁都精采。根據出版社於二〇一五年的資料,這本自傳的銷售數字是不可思議的紀錄:超出一百二十萬冊(其中也包括我買的兩本,第一本在臺灣,但是來德國後,我實在太喜愛這本書,不得不再買一本)。
對文學的愛
在自傳裡,他回憶如何開始其早熟的對文學的熱愛。那是一九三二年底,十二歲的小男孩得了一張戲票,得以進到真正的戲院──不是兒童戲院──去看席勒的戲劇《威廉.泰爾》(Wilhelm Tell)。他說,那個晚上開啟了他對德國文學永遠不變的愛。
在納粹掌權時,他在納粹的首都柏林讀書。在德文課上這個愛著文學的少年表現優異,除了「極佳」沒有拿過別的成績。但高中畢業會考時,他卻只得了「佳」,後來校長偷偷告訴他,閱卷委員們並未考慮給他「極佳」,因為那「不適合」──意思是,對一個猶太人學生來說不適合。在一九三八年的氣氛下,可以理解老師們的顧慮。 當時已經有許多德國的猶太人準備逃亡到國外。與萊西—拉尼茲基同住在柏林的叔叔,有位朋友是化學家,少年常常去他家看書。在逃亡前夕,這位長輩跟他說,你來我家吧,帶一個小行李箱,我帶不走書,你就搬回去吧。萊西—拉尼茲基拉了一只大行李箱,欣喜若狂地裝滿了里爾克等知名作家的全集。他向化學家道謝,化學家告訴他:「你根本不需要向我道謝。這些書我不是送你的,我事實上只是借給你這些書,就像這些年的時間對您來說也是借來的。我的年輕朋友啊,就連您,最終也免不了被驅離此處的命運。而這許多的書呢?最後您也得留下它們,如同我現在一樣。」 化學家是對的,兩年後,萊西—拉尼茲基終究要歸還他借來的時間。他被解送回華沙的猶太人隔離區,離開柏林前他只能匆匆地抓了幾本書放進行李,這些書中的絕大部分,他沒能夠帶走,還給了時代的無情。(未完待續)
| FindBook |
有 12 項符合
美茵河畔思索德國:從法蘭克福看見德意志的文明與哀愁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美茵河畔思索德國:從法蘭克福看見德意志的文明與哀愁
★☆以城市為主軸,書寫人物風流及德意志百年風華的全景式作品★☆
務實、叛逆、精采而又深邃;這,就是法蘭克福!
「法蘭克福很不一樣,這讓人安心,尤其是試圖在此找到歸屬的異鄉人,總是能在不一樣中找到自己的角落……我的鄉親們是資本家,但也搞革命;穿西裝為跨國金融體系服務卻又上街丟石塊;愛阿多諾卻又恨阿多諾;既愛馬克思也愛歌德。這個始終在變化中的城市裡,誰才算是真正的法蘭克福人呢?也許沒有人是,也許每個人都是。」
──蔡慶樺(本書作者)
相較於大家所熟知的德國大城柏林與慕尼黑;法蘭克福除了機場、書展與法蘭克福學派外,似乎缺乏讓人辨識的關鍵字。然而,法蘭克福不僅是六八革命年代的反叛首都,它所走過的歷史與不斷綻放的風流人物,不但累積了自身的厚度、也凝煉出德意志近現代的文明與蒼涼。
這裡是商業與金融的城市。由於位居貿易之路要津,自古人們就在法蘭克福進行交易,也發展出完整的法律體系與同業公會;至今,多個重要商展仍在此舉行,歐洲央行與全球各大銀行亦在此駐點。
這裡是自由與市民、正義與反抗的城市。法蘭克福在神聖羅馬帝國時期就被封為自由城,直屬於皇帝,使法蘭克福人很早就發展出蓬勃的市民社會。而六〇年代的學運與革命世代狂潮、二戰後對納粹罪刑的最大規模起訴,以及左派恐怖組織赤軍連,皆以此處為主戰場,向上一代陳腐的價值觀提出挑戰也責問自身,深刻影響了戰後聯邦共和國的樣貌。
這裡是文學、哲學、社會學、科學與各種天才薈萃的城市。德國大文豪歌德在此誕生;全球最大的書展在此舉行;霍克海默與阿多諾在此成為青年學子的精神導師及日後反叛的對象;哲學家哈伯瑪斯在此完成多數著作,並引領法蘭克福學派走向全世界;阿茲海默醫生在此確認失智是一種病症……法蘭克福以其厚實的文化力量與研發實力,不但影響德國與歐洲,更成為全世界學術與文化的重鎮。
務實、叛逆、精采而又深邃;這,就是法蘭克福。
作者蔡慶樺曾任駐外交部法蘭克福辦事處祕書,已然將法蘭克福視為家鄉,他結合 自身政治哲學的背景、廣博閱讀及實際的生命經驗,帶領讀者從這座城市的肌理凝視德意志的重要命題,思索法蘭克福為什麼是法蘭克福,德國又為什麼是德國。
▌本書特色
#以一座城市做為書寫的主題,內容不但擴及人物、歷史、思想、政治、文化與哲學,且不只是歷年的文章集結,而是有清楚的主題意識、精準分層,寫出法蘭克福的不同面向。如此「全景式」的作品在國內外書市中相對罕見。
#作者本身的書寫與閱讀深廣兼具,能以散文筆法講述哲學概念,敘述之餘更能深刻地進行理論討論、甚至批判,在目前的青壯派作家中獨具風格,是很受歡迎的作家。
#本書宛如德國版本的「流動的饗宴」,諸多人物與歷史事件,以法蘭克福為舞臺相遇、激盪,演繹出這座城市的獨特魅力,及其低調卻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作者簡介:
蔡慶樺
一個有德意志靈魂的臺南人,政大政治學系博士。讀的是德國政治思想,但對德國文化、語言、政治、文學、社會議題都很著迷。曾派駐法蘭克福辦事處,現任職外交部。二〇一八年獲得由香港外國記者會、香港記者協會及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聯合主辦之《人權新聞獎》文字及印刷組評論優異獎。
章節試閱
六八學運之城
當我還在法蘭克福工作的時候,認識一位在法蘭克福度過六〇年代的朋友。在一次聊天中我提起,正計劃寫一本關於法蘭克福的書,其中有一篇要談學運。他很高興地說,是的,談這座城市不能不談起那個年代的學運,並從家裡拿了張剪報給我看,那是一九六八年,學生們手牽著手上街抗議。他說:你看到了嗎,我就走在第一排。
有意思的是,他本身是法學博士,談起世界各國挑戰政治秩序的運動時,總認為改革甚至革命,不管訴求多麼正當,還是得確定民主憲政的體制不被動搖。但在一九六八年時的他所加入的學運,其實是全面質疑戰後西德體...
當我還在法蘭克福工作的時候,認識一位在法蘭克福度過六〇年代的朋友。在一次聊天中我提起,正計劃寫一本關於法蘭克福的書,其中有一篇要談學運。他很高興地說,是的,談這座城市不能不談起那個年代的學運,並從家裡拿了張剪報給我看,那是一九六八年,學生們手牽著手上街抗議。他說:你看到了嗎,我就走在第一排。
有意思的是,他本身是法學博士,談起世界各國挑戰政治秩序的運動時,總認為改革甚至革命,不管訴求多麼正當,還是得確定民主憲政的體制不被動搖。但在一九六八年時的他所加入的學運,其實是全面質疑戰後西德體...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曲】當我在美茵河畔想起德國
文學之城
狂飆天才的誕生:歌德
歌德給當代德國的遺產——不可抹滅的德意志特質
我的家鄉是文學:文學教宗萊西—拉尼茲基
文學四重奏——帶著愛意又有點刻薄地讀書
大學之城
法蘭克福大學的光輝與黑暗
遲來五十六年的博士論文口試
德國大學的歷史自省
哲學與政治——大學焚書
社會學之城
阿多諾與班雅明——最後一個天才與被寵壞的孩子
聯邦共和國的黑格爾:哈伯瑪斯
從未過去的過去——「史家之爭」與納粹德國的罪責問題
哈伯瑪斯是納粹嗎?
六八學運之城
革命之城,革...
文學之城
狂飆天才的誕生:歌德
歌德給當代德國的遺產——不可抹滅的德意志特質
我的家鄉是文學:文學教宗萊西—拉尼茲基
文學四重奏——帶著愛意又有點刻薄地讀書
大學之城
法蘭克福大學的光輝與黑暗
遲來五十六年的博士論文口試
德國大學的歷史自省
哲學與政治——大學焚書
社會學之城
阿多諾與班雅明——最後一個天才與被寵壞的孩子
聯邦共和國的黑格爾:哈伯瑪斯
從未過去的過去——「史家之爭」與納粹德國的罪責問題
哈伯瑪斯是納粹嗎?
六八學運之城
革命之城,革...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