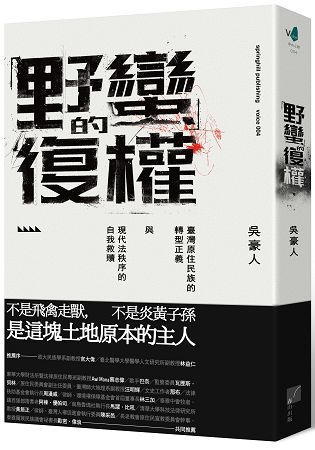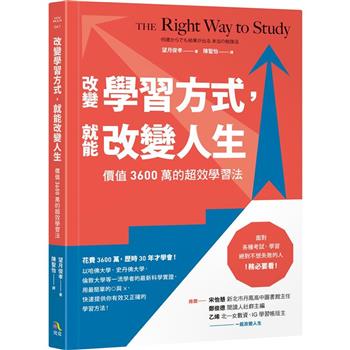自從殖民者踏上這塊土地,現代國家的法秩序如何綑綁臺灣原住民族的種種權利?怎麼做才能真正解套?
二○一七年原住民歌手巴奈等人在總統府周邊紮營抗爭數百天,抗議行政院原民會提出的傳統領域劃定辦法將「私有地」排除在原住民傳統領域之外的做法,大聲喊出「沒有人是局外人」。
這項爭議的核心究竟是什麼?臺灣原住民族歷經數任總統道歉、宣示尊重其人權與文化,二○○五年也通過《原住民族基本法》,但當政者即便想要解決,就真的能夠解決得了嗎?
原住民族的生存與文化發展,最大關鍵在於土地。原住民土地在過去被強奪騙取的事實雖然早已無可否認,但在現代國家的市民法架構之下,若要積極回復原住民族被剝奪許久的權利,將會碰上這種法秩序對於個人私有財產權的無上堅持,以及必須能夠進行市場交易的物權預設,從而與原住民傳統的(但更具永續性質的)集體所有權概念產生根本上的矛盾。
長期關注原住民議題的法律學者吳豪人,從哥倫布以來殖民者如何透過法律剝奪世界各地原住民的土地與權利開始,對照日本北海道阿依努族與台灣原住民族爭取權利的訴訟與立法鬥爭史,檢視、分析原住民族在殖民主義與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法秩序的雙重桎梏之下,難以真正復權的根本癥結,並提出他的解決方案。
【共同推薦】
Awi Mona蔡志偉/東華大學財法所暨法律原住民專班副教授
巴奈/歌手
瓦歷斯.貝林/監察委員
汪明輝/原住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臺灣師大地理系副教授
那布/文史工作者
周漢威/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執行長
林三加/律師,環境權保障基金會首屆董事長
阿棟.優帕司/泰雅中會牧者,鎮西堡部落耆老
馬躍.比吼/南島魯瑪社執行長
黃居正/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
陳采邑/律師,臺灣人權促進會執行委員
歐密.偉浪/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原住民宣教委員會幹事,泰雅爾族民族議會秘書長
作者簡介:
吳豪人
一九六四年生於臺北。日本國立京都大學法學博士,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專任教授,研究領域為基礎法學與人權思想。除發表多篇學術論文外,編有《大正十三年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豫審記錄》(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出版),著有《殖民地的法學者:「現代」樂園的漫遊者群像》(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最常說的一句話是:「我不懂實定法。」天生自由人,遭際冷硬派。非自願型人權工作者。滴酒不沾,痛恨西裝,不會打領帶,會打撐人結。不喜奔競,避官如避禍。曾口占二句以明志:「我是佛門鴦堀子,不學人間富貴禪。」近年開闢專欄「白目豆沙包」,自愚愚人,禍不遠矣。
章節試閱
(摘自第一章)
原住民「飛禽走獸=地上物」論的時代
從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開始「理蕃」,百餘年來臺灣原住民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遭受到外來者以暴力排除其權利參與的歷史。這些外來者的暴力,有的非常赤裸裸,有的則非常狡詐閃爍,不容易辨識。日本殖民初期,對於原住民在法律上地位的認定,就屬於前者。
日治時代,對於清朝主權未及處的原住民族──「生蕃」是否為日本臣民,有無法律人格的問題,曾透過所謂「法理」的討論,達成「將生蕃視為地上物」的共識。總督府殖民官僚安井勝次〈生蕃在國法上的地位〉一文可謂箇中代表。
安井認為,在解決「生蕃」是否為日本「臣民」之前,首先須確定他們是否為清國臣民。因為日本領有臺灣,乃國際法上繼承清帝國之主權而來。牡丹社事件清國的卸責之詞:「臺灣山地不屬於清國版圖,難以派兵究辦」,其中所說的「山地」,其實指的是「生蕃居住之地」。而生蕃乃「化外之民」,非清國臣民,其理甚明。此後,清國改弦更張,積極開拓,因此各國均承認清國主權及於臺灣全島。只是清國法令現實上無法行之於「生蕃」耳。日本繼承清國對臺灣全島及其附屬島嶼之主權,則臺島原「清國臣民」,均可依日本法律取得日本臣民之地位。但對於非清國臣民之生蕃,則不知如何處理。因此只有透過「教化」手段,使生蕃「開化」至熟蕃程度之後,再制定特別法賦予其國籍。明治三十八年(一九○五年)制定戶口調查規則時,仍將生蕃除外,可知此時的生蕃仍非日本臣民。
若非清國臣民,又非日本臣民,則屬於「自然人」之生蕃究竟有無法人格呢?對於不服從日本政令的生蕃,日本人在一籌莫展之際,只好將之視為「飛禽走獸」:
(法)人格除非受法律保護,否則不能享有任何權利。亦即人格須由法律認定,始可享有。故以生蕃為「自然人」之理由視為其具有(法)人格者,可謂不知(法)人格意義之見解。生蕃若有人格,其行動不應超乎法律允許之範圍,亦即須遵守法律。故雖有生物上之自我,但若其行動超越法律允許之範圍,則與飛禽走獸無異。
安井接著引用清治時期清國不視「生蕃」為人類的諸多證據,如:
所異於禽獸者幾希矣(《諸羅縣志》)
此輩雖有人形,全無人理(《東征集》)
鳥語鬼形,殆非人類(《問俗錄》)
如果生蕃不是「人」,沒有法人格,那麼「生蕃棲息」之領域自然屬於國有。這個掠奪原住民傳統土地的「合法」行為,可謂日本繼受西歐法學之後,學以致用的顛峰之作。因此安井更解釋,明治三十三年律令第七號禁止「非蕃人」「以任何名義占有、使用土地做為其他權利之目的」,並非保障生蕃之土地所有權(飛禽走獸如何能擁有所有權?),其目的唯在保障「國有土地」不受侵權耳。
「蕃人」事實上雖占有使用土地,日本殖民地政府也無可如何,但是至少可以否定他們具有法人格,因此這些蕃人再經多少年也無法取得土地之權利。而生蕃既然在國法(即國內法)上「與野獸無異」,那麼要討伐之、剿滅之,亦或教化之,均屬國家之權利。
雖然日本五十年之統治,持續進行剿滅與教化雙管齊下的「理蕃政策」,但從日治初期到末期,「將生蕃視為地上物」始終是日本殖民者看待原住民最重要的指導綱領。相對的,日本人雖大規模進行「蕃族慣習調查研究」,卻始終不曾承認原住民傳統規範的「文明性」,因此原住民不但始終不適用日本法律,而且其傳統法規範也不斷受到破壞。
將原住民定位為無法律可適用(也就是排除其權利參與)的「飛禽走獸」,從最根本處加以否定,不但是日本繼受西歐法學之後,學以致用的顛峰之作,可謂深得哥倫布以來殖民主義的法乳;同時,更是最赤裸裸的暴力行為。妙就妙在這種赤裸裸的暴力,竟然無人進行舉發。日本殖民政府是確信犯,當然不會自我指控;而同為被殖民者的漢人,顯然也不是因為才剛落入棄民處境,無暇仗義執言。事實上漢人對於日本殖民政府「將原住民視為飛禽走獸」根本就是心有戚戚焉。從清治時代起,「將原住民視為飛禽走獸」早就是臺灣漢人的主流論述了。
原住民做為「學術踏腳石」的時代
臺灣總督府曾在明治時期與昭和時期,兩度對原住民進行大規模的人類學調查。雖然本質上都是為了方便推動殖民統治,但此二者性質並不盡相同。
較晚的昭和時期所做的《高砂族調查書》(全六卷),掌握了原住民人口動態的詳細調查,配合國家總動員原則,開始更進一步想要「改造」原住民,使之成為皇民的一部分,因此可謂「將原住民視為地上物」的忠實繼承者。不過較早的明治時期舊慣調查會所完成的《蕃族調查報告書》(全八卷)與《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全八卷),卻有不同的目的。
舊慣調查的領導人岡松參太郎的德國恩師柯勒(Josef Kohler),對於《臺灣舊慣制度調查一斑》未曾調查臺灣原住民法制,表示大失所望。柯勒認為,臺灣漢人的法制度,和當時歐洲人已經知曉的「中國法」大同小異,激不起歐洲學界太大的興趣。
對於柯勒的失望,岡松想必非常在意,因此才會有日後的「蕃族」慣習調查事業。
實際上,柯勒關心的,也集中於「未開」的原住民法律。他甚至不曾深究「臺灣漢人的法律」與「中國法」有什麼異同之處。
然而,有趣的也就在此。原本對日本殖民者而言,為了成功推展其殖民政策。當務之急必然是調查研究占絕對多數的漢人法律,而非僅占人口比例二%的原住民法。但柯勒卻著急地只想瞭解原住民法。他這樣直接的反應,固然是他自信對於所謂的「中國法」已有一定的瞭解;可是未嘗不能說,像柯勒這樣的學者,滿足於個人知識上的好奇,遠比落實殖民政策來得重要多了。這才是人種法學,或比較法學的原始精神──可以追溯到雅各.格林(Jacob Grimm)知識重於實用的治學態度。而這樣的態度也影響了岡松,成為他日後出版《臺灣蕃族慣習研究》的直接動機。
原住民的傳統規範,首次受到「學術」的青睞,大概起因於此。日後,臺北帝國大學的人類學者們,或甚至於是法學者(如增田福太郎)雖然也進行大規模的人類學研究,但是不脫上述兩次調查的路線。也就是說,假如不是純學究趣味(dilettantism),就是為了殖民統治。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學者,認真思索原住民傳統規範的現代價值,以及應如何保留、保障或改良。人類學本來就與殖民主義是一體的,但在臺灣則居然形成一個學術傳統—哪怕到了如今,恐怕都還有不少「人類學家」把原住民視為「研究的客體」,不曾設身處地,以主體視之,何況戰前了。山路勝彥甚至以馬淵東一為例,指出這群偉大的殖民地人類學家,把他們能自由自在研究臺灣原住民的「快樂」,視為一種無人能管束的「梁山泊」。其將原住民視為自己學術踏腳石的心態,昭然若揭矣。
逆流:中華民國如何看待原住民的傳統法律
前文提及日本人是「法匪」,但「法匪」並非全然負面的字彙。筆者願意不厭其煩地再次指出:
法匪行政,簡潔地說,便是公權力做任何事──哪怕是惡事──時都必須依「法」。至於依的法是否惡法,乃次要考量。依法行政依的若是惡法,法曹及官僚們即成「法匪」。因此言及法匪不能只從「匪」的部分做批判,這與納粹掌權下的法曹們,依「法」屠殺猶太人很類似,基本上即屬於漢娜.鄂蘭(Hanna Arendt)所謂的「惡之陳腐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就戰前風靡一時的「惡法亦法、法就是法」的法實證主義觀點而言,法匪也屬於法律「現代性」中重要的一環,因此無可責難。
可是戰後接下日本殖民棒子的中華民國流亡政權,就法史學的意義而言,卻不是「法匪」,而只是匪。因為此一政權甚至可以凍結憲法達三十八年之久,其惡之陳腐平庸性,遠過於日本帝國。本書並無意願詳細檢討國民黨統治下的原住民政策,在此筆者只打算提出幾點補充說明。
中華民國基本上完全繼承日本帝國統治臺灣的負面遺產,也就是繼承異族殖民者否定法律=權利的統治型態。而且,他們同時也是大清帝國法律所代表的中華法系思想的正牌繼承人──因為將他們驅逐出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至少在當時自詡最進步的馬克思信徒,才不吃那一套。(當然,如今倒是成了中華法系的正統繼承人了。)因此中華民國對於「法即權利」理念更為疏遠,倒不如使用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手法對付原住民,更為得心應手。雖然中華民國並沒有視原住民為飛禽走獸,反而「賦予」其法律人格,視為臣民,不,「國民」的一分子,可是卻引發了更大的禍害。因為中華民國更積極地把臺灣原住民納入「炎黃子孫」的一部分,所以也更不留情地破壞原住民的民族認同與傳統文化。「傳統規範」云云,則彷彿「地上物」,不足論矣。然而,在加速同化的過程中,中華民國又繼承了日本法匪苦心孤詣謅出來的,對原住民傳統土地掠奪之正當性。
一九四五年之後,國民黨政府──通稱「國府」的另一個外來政權──來到臺灣。此「國府」在現代法上的素養遠遠不及前一個殖民政權,但是對於使用文藻華麗而內涵空洞的修辭,則顯然高明得使日本人亦不得不「避此『府』出一頭地」矣。最典型的國府式修辭,首推「山地同胞」一詞的發明。從此,臺灣原住民就從「飛禽走獸」升格為「炎黃子孫」,從無法律人格者升格為「中華民國國民」矣。
張松在《臺灣山地行政要論》中說道:「山地同胞在清代以前,稱為『番』……,臺灣光復後改為山地人民,敬稱為山地同胞。」又說:「我國各省處在深山的落後地區同胞,也同樣是中華民族,他是和我們祖宗沒有進化以前的形態一樣。」「山地同胞的祖先係閩浙東渡來臺的越族,而越族亦為今日閩浙蘇廣同胞的祖先,平地山胞係由閩廣後期移住來臺,同為中華民族一分子。」
這一段妙文可說是原住民「炎黃子孫」說的最佳注腳。
「國府」何以如此重視原住民的同胞身分呢?官方說法向來是「基於憲法保護邊疆地區民族之規定」、「基於三民主義之政治理想」。這些濟弱扶傾為名,沙文主義為實的「清詞麗句」,批判者甚夥,如今原不足一哂。說來說去還是蔣介石最坦白:「臺灣和山地同胞要想得到經濟平等、生活自由和文化教育的提高,必須加入反共抗俄的行列中。」「同胞」的代價如此之高,當時的原住民如果能有選擇權,想來不如仍舊「飛禽走獸」也未可知。
「山地同胞/炎黃子孫」說,是國民黨政府精心杜撰的騙局。雖然這個騙局比起日本人的「飛禽走獸」說,明顯地在智性推論上遜色數籌。不過不以知識量而以信口開河取勝,原本就是「國府」治國的特色。重點在於,這種修辭比「飛禽走獸」「溫暖」而且義正辭嚴,更能夠掩飾其行將加諸原住民的各種暴力宰制的行為。只要看一看原住民部落的投票行為至今不變,即可知此種隱性暴力想要得到社會確認,是如何困難了。
(摘自第一章)
原住民「飛禽走獸=地上物」論的時代
從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開始「理蕃」,百餘年來臺灣原住民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遭受到外來者以暴力排除其權利參與的歷史。這些外來者的暴力,有的非常赤裸裸,有的則非常狡詐閃爍,不容易辨識。日本殖民初期,對於原住民在法律上地位的認定,就屬於前者。
日治時代,對於清朝主權未及處的原住民族──「生蕃」是否為日本臣民,有無法律人格的問題,曾透過所謂「法理」的討論,達成「將生蕃視為地上物」的共識。總督府殖民官僚安井勝次〈生蕃在國法上的地位〉一文可謂箇中代表。
安...
目錄
推薦序:他們不是別人,他們就是我們/官大偉DayaDakasi(政大民族學系副教授,泰雅族)
推薦序:「高貴野蠻人」的復返?/林益仁(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
楔子
序言
第一章 臺灣原住民是如何失去土地的?
第二章 日本原住民族的復權之路:從文化權切入的訴訟策略
第三章 帝國的「普通法」與殖民地的「習慣」
第四章 土地所有權的辯證法
第五章 「野蠻」的復權:台灣修復式正義與轉型正義實踐的困境與脫困之道
終章 原住民族在法律思想史中的定位
補論 原住民欺負原住民?──西拉雅族正名訴訟的省思
附錄第三屆模擬憲法法庭:模憲字第四號、第五號判決部分協同意見書
書目
推薦序:他們不是別人,他們就是我們/官大偉DayaDakasi(政大民族學系副教授,泰雅族)
推薦序:「高貴野蠻人」的復返?/林益仁(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
楔子
序言
第一章 臺灣原住民是如何失去土地的?
第二章 日本原住民族的復權之路:從文化權切入的訴訟策略
第三章 帝國的「普通法」與殖民地的「習慣」
第四章 土地所有權的辯證法
第五章 「野蠻」的復權:台灣修復式正義與轉型正義實踐的困境與脫困之道
終章 原住民族在法律思想史中的定位
補論 原住民欺負原住民?──西拉雅族正名訴訟的省思
附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