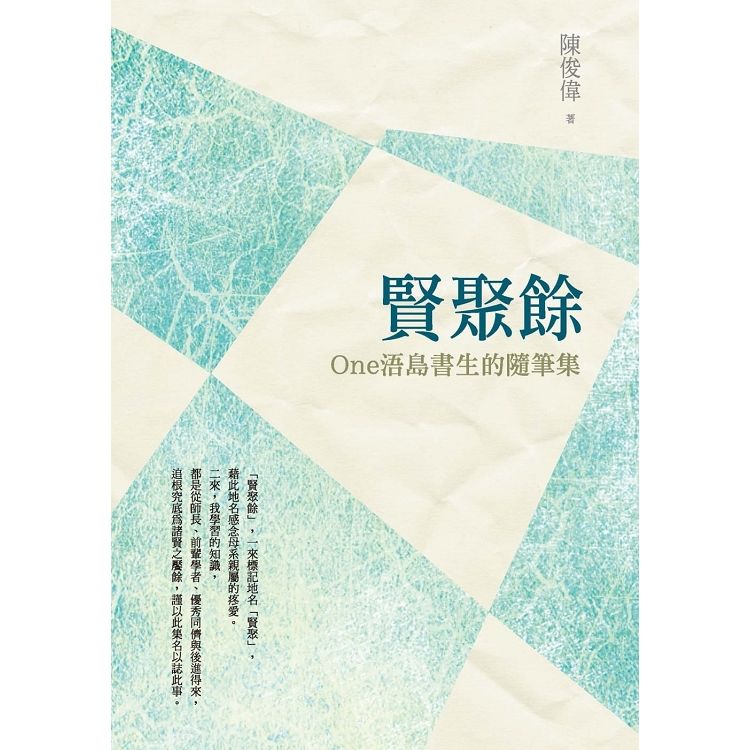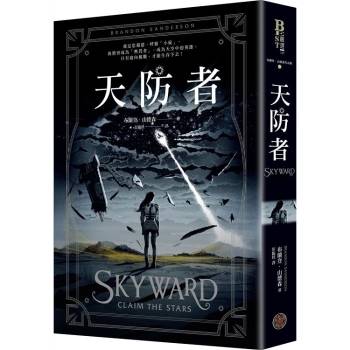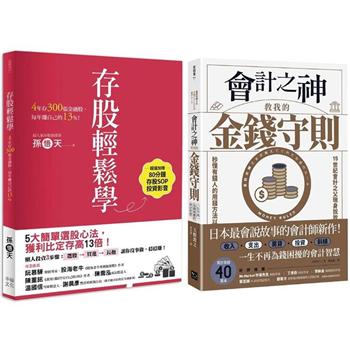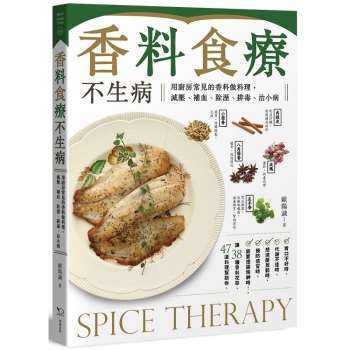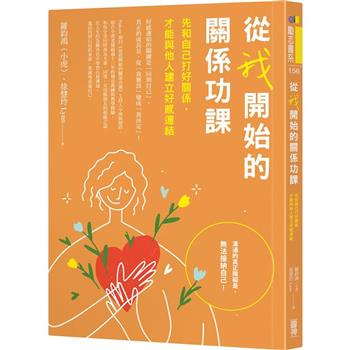這本著作輯錄筆者於博士修業中期,至於替代役服勤的數年,寫下的一些隨筆文字,年紀大約是30-33歲之間。本書沒有明確的主題,共通點大抵是帶有些知識推廣的性質。內容包含著關於電影、書籍的簡單評介,還有些生活、時事所感,也包含一些較有學術性的文章。……主標題「賢聚餘」,一來標記地名「賢聚」,藉此地名感念母系親屬的疼愛。二來,我學習的知識,都是從師長、前輩學者、優秀同儕與後進得來,追根究底為諸賢之饜餘,謹以此集名以誌此事。
這是一本隨筆散文集,內容包含時事、影視、三國史籍、鄉土內容等等,主軸是知識推廣,也參雜幾篇作者的無病呻吟。……期待所有自發學習的一切,最終都能替自己爭取到更多的時間。中國古代的讀書人總是存在一個情結,想要成為「通人」,這個理想就算是於資訊還沒有爆炸的時代,也是辦不到的。可是於主要專業之外,培養自己對其他知識「略懂」一點,不僅豐富生命,也讓視野、心胸更為開放。本世紀接下來三十年,預期幾個關鍵字:5G,反脆弱(anti-fragility),新時代(New age),(技術、經濟)奇點,心腦諧振。這本著作拼貼了一些知識,加上一些作者的感情與閱歷,主要是筆者想要紀錄人生歷程。如果讀者從中找到共鳴,即使是兩、三句而已,也是作者的莫大福氣了。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賢聚餘:One浯島書生的隨筆集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賢聚餘:One浯島書生的隨筆集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陳俊偉
1986年金門縣出生,射手座。
學歷:國立金門高中、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現華文文學系)學士、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現中國語文系)碩士、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研究範圍:三國學、史傳文學
興趣:閱讀、知識推廣、日文
學會:斐陶斐榮譽學會會員、華語文教學學會終身會員
履歷:國立東華大學《奇萊論衡》主編、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編輯委員
除了出版學術專著《敘述觀點與歷史建構:兩晉史家的「三國」前期想像》(秀威),正式學術單篇論文目前已經發表十餘篇,包含《漢學研究》、《東華漢學》等核心期刊。另又有多篇知識推廣的文章,主要發表於「托海爾:地方與經驗研究室」、《國文天地》。假使客觀條件允許,希望在接續的兩年內出版博士學位論文,以及不限期內再出一本隨筆。
陳俊偉
1986年金門縣出生,射手座。
學歷:國立金門高中、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現華文文學系)學士、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現中國語文系)碩士、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研究範圍:三國學、史傳文學
興趣:閱讀、知識推廣、日文
學會:斐陶斐榮譽學會會員、華語文教學學會終身會員
履歷:國立東華大學《奇萊論衡》主編、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編輯委員
除了出版學術專著《敘述觀點與歷史建構:兩晉史家的「三國」前期想像》(秀威),正式學術單篇論文目前已經發表十餘篇,包含《漢學研究》、《東華漢學》等核心期刊。另又有多篇知識推廣的文章,主要發表於「托海爾:地方與經驗研究室」、《國文天地》。假使客觀條件允許,希望在接續的兩年內出版博士學位論文,以及不限期內再出一本隨筆。
目錄
自序
謝誌與歉誌
【時事隨筆】
論「三國」、講「葉問」:揚棄「正統」的意識型態綁定與社會進步的前瞻
經濟/趨勢讀物的他山之石:論《反脆弱》(2013年)與台灣漢學學界之研究生養成
諸葛亮的隱憂
Cosplay阿難與國語課本的難題
怎樣成功的抱腿、組團
秦漢帝國,是個無止境的夢魘?
如果讓我開一門通識課:「中國古典文學的經濟概論」
來一篇王安石的〈傷仲永〉
【影視隨筆】
意外?抑或本意:《超時空要愛》中的關公
香港電影《超時空要愛》(1998年)的關公
《三國之見龍卸甲》的悲劇英雄與「卸甲」
老闆轉大人:電影、小說《侏儸紀公園》的哈蒙德
《明日邊界》的戲謔死亡
歸來已非當初:活屍題材電影中的「前」女友
【學術隨筆】
清代尚鎔《三國志辨微》、《三國志辨微續》述評
清代黃恩彤《三國書法》評述
清代張廉《季漢書辨異》評述
【鄉土隨筆】
卓環國小的六隻小貓
東門行
卓環國小的貓咪,要學習網路購書
卓環國小排演「紫微斗數」的日子
從小到東華大學的碩士班
作者學術、散文列表
謝誌與歉誌
【時事隨筆】
論「三國」、講「葉問」:揚棄「正統」的意識型態綁定與社會進步的前瞻
經濟/趨勢讀物的他山之石:論《反脆弱》(2013年)與台灣漢學學界之研究生養成
諸葛亮的隱憂
Cosplay阿難與國語課本的難題
怎樣成功的抱腿、組團
秦漢帝國,是個無止境的夢魘?
如果讓我開一門通識課:「中國古典文學的經濟概論」
來一篇王安石的〈傷仲永〉
【影視隨筆】
意外?抑或本意:《超時空要愛》中的關公
香港電影《超時空要愛》(1998年)的關公
《三國之見龍卸甲》的悲劇英雄與「卸甲」
老闆轉大人:電影、小說《侏儸紀公園》的哈蒙德
《明日邊界》的戲謔死亡
歸來已非當初:活屍題材電影中的「前」女友
【學術隨筆】
清代尚鎔《三國志辨微》、《三國志辨微續》述評
清代黃恩彤《三國書法》評述
清代張廉《季漢書辨異》評述
【鄉土隨筆】
卓環國小的六隻小貓
東門行
卓環國小的貓咪,要學習網路購書
卓環國小排演「紫微斗數」的日子
從小到東華大學的碩士班
作者學術、散文列表
序
序
感謝科技發達、物質文明進步,讓沒有文曲、文昌坐命的筆者才能有機會出版這本著作。
這是一本隨筆散文集,內容包含時事、影視、三國史籍、鄉土內容等等,主軸是知識推廣,也參雜幾篇作者的無病呻吟。《閒散的藝術與科學》(2016年)的一篇序文指出:「台灣高中生的平均素質肯定在歐美之上,可是台灣大學生學習動機之薄弱,卻和程度完全不成正比,這令很多外國教師感到驚訝不已。很多人出社會後,就對知識不感興趣了。」或許回到學習的初衷,才能有一份知識的從容。
何況,涉獵知識正是增加自己未來可以使用的時間,《贏在拖延術》(2016年)這本著作有一段話語特別精彩:「我明白特定的時間投資或許會花費今天的時間,亦即犧牲我暫時性滿足部分急事的能力,但那些時間投資可以為我的人生製造多一點餘裕,對我的明天會有正面影響。有些事我今天做了,可以讓明天更好。有些選擇我現在做了,可以為稍後製造更多空間。就是這樣一個想法,讓我長久以來第一次覺得,事情有機會出現轉變。頓時,我開始覺得自在,更加心平氣和。最後,我有了一線希望。我可以把今天的時間花在改善明天生活的事情。」期待所有自發學習的一切,最終都能替自己爭取到更多的時間。
中國古代的讀書人總是存在一個情結,想要成為「通人」,這個理想就算是於資訊還沒有爆炸的時代,也是辦不到的。可是於主要專業之外,培養自己對其他知識「略懂」一點,不僅豐富生命,也讓視野、心胸更為開放。本世紀接下來三十年,預期幾個關鍵字:5G,反脆弱(anti-fragility),新時代(New age),(技術、經濟)奇點,心腦諧振。
這本著作拼貼了一些知識,加上一些作者的感情與閱歷,主要是筆者想要紀錄人生歷程。如果讀者從中找到共鳴,即使是兩、三句而已,也是作者的莫大福氣了。
感謝科技發達、物質文明進步,讓沒有文曲、文昌坐命的筆者才能有機會出版這本著作。
這是一本隨筆散文集,內容包含時事、影視、三國史籍、鄉土內容等等,主軸是知識推廣,也參雜幾篇作者的無病呻吟。《閒散的藝術與科學》(2016年)的一篇序文指出:「台灣高中生的平均素質肯定在歐美之上,可是台灣大學生學習動機之薄弱,卻和程度完全不成正比,這令很多外國教師感到驚訝不已。很多人出社會後,就對知識不感興趣了。」或許回到學習的初衷,才能有一份知識的從容。
何況,涉獵知識正是增加自己未來可以使用的時間,《贏在拖延術》(2016年)這本著作有一段話語特別精彩:「我明白特定的時間投資或許會花費今天的時間,亦即犧牲我暫時性滿足部分急事的能力,但那些時間投資可以為我的人生製造多一點餘裕,對我的明天會有正面影響。有些事我今天做了,可以讓明天更好。有些選擇我現在做了,可以為稍後製造更多空間。就是這樣一個想法,讓我長久以來第一次覺得,事情有機會出現轉變。頓時,我開始覺得自在,更加心平氣和。最後,我有了一線希望。我可以把今天的時間花在改善明天生活的事情。」期待所有自發學習的一切,最終都能替自己爭取到更多的時間。
中國古代的讀書人總是存在一個情結,想要成為「通人」,這個理想就算是於資訊還沒有爆炸的時代,也是辦不到的。可是於主要專業之外,培養自己對其他知識「略懂」一點,不僅豐富生命,也讓視野、心胸更為開放。本世紀接下來三十年,預期幾個關鍵字:5G,反脆弱(anti-fragility),新時代(New age),(技術、經濟)奇點,心腦諧振。
這本著作拼貼了一些知識,加上一些作者的感情與閱歷,主要是筆者想要紀錄人生歷程。如果讀者從中找到共鳴,即使是兩、三句而已,也是作者的莫大福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