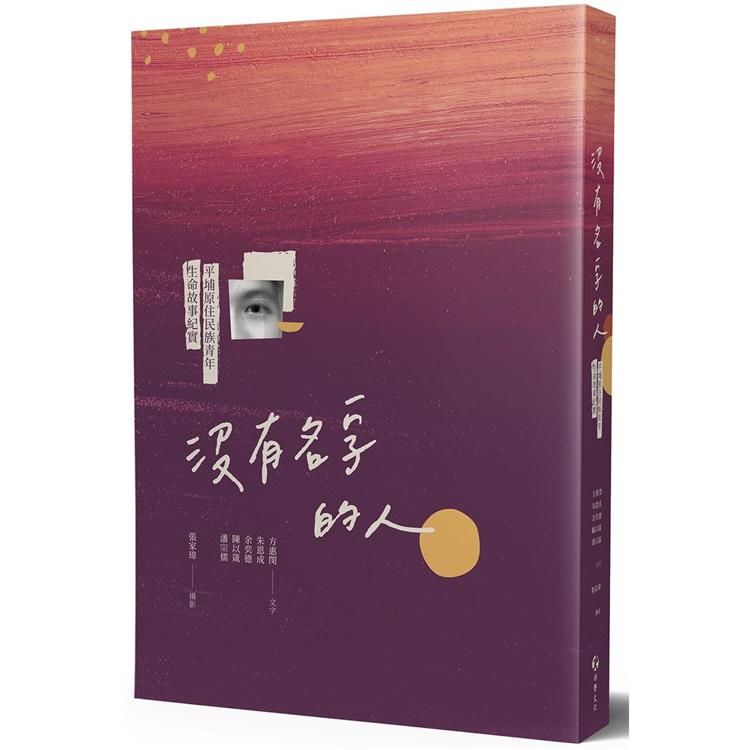故事從島嶼之南的屏東縣滿州鄉開始——
一個原漢混雜、族群界線曖昧難辨的平地原住民鄉。
五位平埔原住民青年從此踏上一段尋找被奪去的名字的旅程……。這是一群被時代噤聲的族群,連名字都是統治政權所賜予的。從清領時期的「熟番」、日治時期的「熟蕃」、「平埔族」,到了國民政府時期,連名字最終都失去了,僅在歷史資料中留下簡短的「漢化殆盡」,一筆帶過族群數百年的興衰命運。似乎族群的賡續與亡佚,可以任由國家機器來裁奪,無須來龍去脈的交代,一切宛如不證自明。
然而,過去並不會憑空消失,平埔族群曾在島嶼的山林、平原馳騁,有著屬於他們的愛恨惡慾;現在依舊真實存在,即便不曾大聲說出自己已被污名的名字,但在島嶼的四方一隅,仍試圖唱著自己的歌、跳自己的舞,傳頌著自己的名,即便是這麼的靜默無聲。
「沒有名字的人」書寫團隊透過自身的書寫與採訪,希望拼湊出台灣當代平埔族群的真實樣貌。被採訪的對象包括二十位平埔族群的青年,他們的身分跳脫非「原」即「漢」,非「生」即「熟」的二元框架,以混血的姿態——包括族群的、語言的、信仰的、認同的,混雜存在。在面對如此雜揉的身分處境,這群青年或是感到困擾、徬徨,或是特別有想法而不斷思考,進而積極追尋或選擇逃避這樣的身分。可是當他們想大聲說出自己的名,現行的族群政策卻又再次給他們迎頭一擊。
根據現行的《原住民身分法》,原住民身分的取得是國民政府依據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的註記做的認定,而不是以血統、認同、文化等標的來檢驗山地/平地原住民的身分。然而,現在卻以文化存續的程度,限縮了平埔族群回復身分的權利空間……。
族群的邊界與框架是權力者認定的,彷彿當我說是「某某族」時,就必須講甚麼語言、穿著什麼衣服、吃甚麼食物、唱甚麼歌、拜甚麼神,否則就無法承認我的存在。但現實的族群樣貌卻是複雜的、移動的、混血的,唯有正視平埔族群部落鑲嵌於資本主義社會的事實,肯認族人真實的生活處境與經驗,進而重新審視族群的定義,才能讓被奪去名字的人,可以重新找回自己的名字,而不再是沒有名字的人。
作者簡介:
方惠閔
1989年生。台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畢業,現任職於台中教育大學原住民族教育及文化研究中心。
朱恩成(Awui)
1992年生。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畢業。
余奕德
1990年生。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畢業,返鄉的freelancer,一直在作地形模型。
陳以箴
1991年生。成功大學工業設計學系畢業,現就讀於台灣大學人類學系碩士班。
潘宗儒
1992年生。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畢業,現任職於屏東縣牡丹鄉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
【攝影者簡介】
張家瑋
1991年生。作品多與階級、教育等社會議題相關,現職自由接案攝影師、《報導者》特約攝影記者、One-Forty特約攝影師。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專文推薦】
「沒有名字的人」的生命故事的內容,也許可以簡化為:如果你是一個意識自己擁有平埔原住民族群身分的青年,你會遭遇什麼?……這些故事是「從前從前」,卻也是「從今以後」的事。必須知道自己的祖先、找回因為他人而被忘卻的語言、家庭的遷移足跡、文化或隱或顯的歸路與線索……我是誰,我在哪裡?主體總是透過敘述而成立,敘述自身是回應「我是誰」、承諾「我可以是誰」,重新錨定自我在記憶與現世的位置,也給了不熟悉台灣當代平埔族群議題讀者的參照與補課。——馬翊航(《幼獅文藝》主編)
……《沒有名字的人》所欲帶給讀者的重要視野:意識到自己的平埔族群身分,不代表就必須否定掉人們原先的其他認同,也不是要大家就開始都「返鄉」做同樣的文化復振工作。對他們來說,追尋自我所欲抵達的終點,並非是要再一次地劃出清楚的族群邊界,也不是要大家安安穩穩地,再把自己塞進到一個分類之中。當文化本來就是不斷處於流動混雜的形成過程,最重要的是,每個人都不會再因為自己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而感到侷限與促狹。——賴奕諭(菲律賓原住民族研究者,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人類系博士生)
《沒有名字的人》分享了致力於尋根的平埔族群青年在尋找族群認同過程中的困難、挫折與不放棄。這些沉重又帶著勵志的故事,除了提醒著有名字的人要懂得珍惜,更呼籲著整體台灣社會應正視平埔族群的權益,其所面臨的文化流失與沒有名字的掙扎是受到歷史殖民創傷與社會變遷衝擊所導致。如今陸續有平埔族群之族人投入於正名與文化復振,並竭盡所能地走訪調查,試圖勾勒其族群之樣貌,如若平埔族群的歷史能被更多人認識,相信台灣社會能以更正面、更有溫度的態度與觀點看待平埔族群正名……。——Ciwang Teyra(太魯閣族人,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推薦《沒有名字的人》,不僅因為它記錄了每個想找到名字的起心動念,更書寫了找到族群脈絡後,平埔青年們如何面對不同族群互動下的歷史結果、如何回家的心路歷程——找尋台灣的過去與未來,相較於依循手肘上的橫線,這群青年的故事將更為真實。——方克舟(Mata.Taiwan創辦人)
名人推薦:【專文推薦】
「沒有名字的人」的生命故事的內容,也許可以簡化為:如果你是一個意識自己擁有平埔原住民族群身分的青年,你會遭遇什麼?……這些故事是「從前從前」,卻也是「從今以後」的事。必須知道自己的祖先、找回因為他人而被忘卻的語言、家庭的遷移足跡、文化或隱或顯的歸路與線索……我是誰,我在哪裡?主體總是透過敘述而成立,敘述自身是回應「我是誰」、承諾「我可以是誰」,重新錨定自我在記憶與現世的位置,也給了不熟悉台灣當代平埔族群議題讀者的參照與補課。——馬翊航(《幼獅文藝》主編)
……《沒有名字的...
章節試閱
沒有名字的人/潘宗儒
認同的追尋
一家四口在盆地邊緣搬遷過好幾次,我在台北生活成長。中學以前,我一直以為自己是個漢人(而且是身為一個完全不會意識到原/漢差別的漢人),父親是屏東內埔客家人,起初以為母親是閩南人,閩南語、炷香、祖先牌位、觀音、紙錢……,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
十二歲的時候改從母姓,我有了官方的原住民身分1。那時候,「原住民」三個字對我來說好虛無,是一個遙不可及的、沒有概念的三個字。那個時候,同學友人會問我:你會不會說族語?不會。會不會打獵?不會。會不會喝小米酒?不會。甚至會問說會不會騎山豬?這些無謂的山林想像,顯得有點荒謬。我的腦海是一片空白,原初的社會已經離我多遙遠了,遠到我已經想像不出來,甚至已經沒有記憶,不僅僅失去身體的能力,也已失去言語的能力。我也不可能再回到經歷過幾個世代、政權更替的那個過去了。
高中的時候,偶然讀到了莫那能的詩〈恢復我們的姓名〉2,他不斷地問:
我們還剩下什麼?
是在平地顛沛流離的足跡嗎?
我們還剩下什麼?
在懸崖猶豫不定的壯志嗎?
在我身上一點「原味」都沒有,經過時代與強權的沖刷,與漢人沒有差異,被同化的命運,我的祖先他們是如何選擇生活的方式,到現在的我們連一點文化的影子都沒有,就像一個漢人一樣,從語言、文化到行為都一模一樣。當我在批評國家福利殖民的思維的同時,我也還得感謝國家的福利政策,使我的父母有一個契機,想讓我擁有官方原住民族的身分,如此我也才有機會喚醒我的族群意識。若我從來未曾經歷過升學優待制度帶來的標籤與質疑、族群認同的矛盾,我大概如同大多數人一樣,過著毫無感知的生活。
十九歲的時候,我來到台灣大學這個地方,自由學習的殿堂。學長姐照著新生名單,打了電話給我,告知有原聲帶社這個社團,邀請我參與活動。會參與的原因,講慷慨激昂一點就是,血液裡隱隱約約的召喚;或者可以很現實地說,有那麼一絲絲覺得來了原住民的社團,那些社會福利跟加分好像會正當一點。
起初我就只是坐在一旁,很安靜,心理的「他們」與「我」有著很強烈的界線,自己那個完全沒有「原味」的自卑感作祟。真正覺得自己好像可以說出來我是原住民,也才是這兩、三年的事情而已。在那之前類似「躲在櫃子裡」的難受,比起同志的身分,不能說更痛苦,但卻是更漫長而模糊地作痛著,也並非污名附加在你身上,而是難以認同自己,就連那些負面的記憶你都未曾擁有,唯一擁有的即是加分與福利政策。
藉由參與原聲帶社年祭,我第一次有機會投身在文化實踐的場域,儘管大一的時候是初鹿卑南族、大二是三地村排灣族、大三是德高阿美。原聲帶社帶給我的文化衝擊,也就是我稀薄的部落經驗、文化經驗,開始構築我對族群的認同。過去的族人並不會有族別、泛原住民族的認同,而是從自身部落開始擴展認同,僅會先認為自己是屬於哪一個部落的。但是在我身上,我是從泛原住民族認同開始建構起來的,至於官方身分的排灣族,我還沒有那麼深刻,更遑論我的部落在哪裡是什麼。記得我大一年祭成年禮唯一說的一句話:「我要找回屬於我自己的那一部分。」
模糊的族群邊界
如果有一天
我們拒絕在歷史裡流浪
藉由一位同是滿州的學長,我才知道「斯卡羅」的故事。三百多年前,卑南族知本社人南遷瑯嶠(恆春一帶),曾與原居於此地的排灣族(如蚊蟀社)發生衝突,由於擁有龐大勢力且擅下咒,當地諸族墾民皆紛紛臣服,以「斯卡羅(乘轎者)」稱呼這一支外族。斯卡羅漸漸成為當地統治階層,並與當地排灣族人通婚,逐漸排灣化,後代認同也漸為排灣族。往後,瑯嶠阿美族人部分回流至台東,影響馬卡道及漢族移居斯卡羅頭目家系的地盤,混居、通婚、共同耕作,斯卡羅族權勢逐漸式微,加上日本統治時代將恆春地區平地化,斯卡羅族及所轄的排灣族、阿美族,一律改稱「熟蕃」。在清代漢化、日本皇民化,與國民政府不當的山地政策之下,造成部落文化流失殆盡,人們喪失原有的認同感,世代的文化傳承戛然中斷,族群意識也沉沒在歷史的洪荒之中。
從出生到現在,漢族在我血液裡未曾消逝,加上排灣化的卑南族的認知,卑南、排灣好像都沾上了某種心理認定。在恆春一帶的族群複雜程度,似乎馬卡道、阿美族也成了可能,姓氏同一的「潘」,排灣姓「潘」、平埔也是,恆春阿美亦是。曾經有平埔前輩對著我說,那你有沒有可能是馬卡道的?你的臉孔很相似。從前總是有太多的人認為我不像原住民,排灣喔,不像啊,心裡總是有些失落,後來開始有人會認為我像是馬卡道,不管是臉孔、膚色上的親近,還是文化流失上的親近,後來自己也認為這些官方劃定族群邊界與身分別不是很重要,早先時代的學者亦曾有卑南、排灣、魯凱劃為同一族與否的討論,何況那是殖民者下的分類。可以顯見族群之間是有邊緣模糊的地帶,不管是在血緣上或者文化上,重要的核心還是我認為:「我是誰?」
我們的姓名
在身分證的表格裡沉沒了
未竟的戶口調查,似乎得要指認一條血脈,心裡才有一個錨,向下挖掘與深根,生命是否會不再飄蕩?從日治戶籍裡,寫的是「熟」,是「蚊蟀社」,我可能是排灣化的卑南族,或根本是排灣族,也或許是阿美、是馬卡道,更無疑的是客家、是漢,然而在這多重的認同間,我必須做出選擇。做一個生活在「大漢」之中的「小番」3,我們除了看見原住民族在結構之中的脆弱性,更應該看見其復原力及韌性,原住民族不只是救助的依賴者,不是安於被殖民地位的弱者。放回文化裡的價值、重拾原住民族的世界觀,原住民族傳統具有解決社會問題的知識與能力,更需要被看見。我永遠選擇站在高牆的對立面,它或許不是蛋殼的脆弱,而是雞蛋裡的靈魂,更可能是一抹鹽巴的味道、一把泥土的氣息4。
沒有名字的人
參與原住民事務雖然還沒有多久,但也不是一、兩天的事情,常常都會有人問我:你的族名是什麼?當我說沒有的時候,總是帶著一點遺憾與慚愧的心情。有的時候還會被勸導,取一個吧,去找吧,要有自己的名字比較好。我總是默默地聽,因為我是知道的,我巴不得趕快換身分證,換臉書的名字,換掉所有。名字不只是稱呼的方式,它標示了族群身分的認同,也等同於大聲地宣示了族群文化與權利。
先說說我的漢名吧。剛開始有意識到原住民族與主流社會文化衝突的歷史時,我很厭惡這個名字,厭惡這個姓和名。中學的時候,我不喜歡「潘」這個姓,因為「番」,我們被教導「番」是歧視性的用詞,所以我不喜歡「潘」這個——殖民政府強加的——姓氏。我也不喜歡我的名,宗儒,就彷彿認祖歸宗只能有儒教那般的霸道。但現在「潘」這個承襲母親的姓,卻是我唯一與原住民族連結的姓氏,這三個字之中唯一隱約的線索,而「宗儒」是祖父精心挑選的也無可厚非。
之前也取過兩個排灣族的名字,但我不想要使用,因為我覺得那不是我真正的名字。那兩個名字對我來說沒有記憶、沒有情感,命名者甚至跟我沒有關係、不認識我,我也不想要隨便地把名字拿來使用,我想找到真正屬於我的名字。
我問過我的母親,我想要有一個族名,她竟然說就隨便取山豬或飛鼠就好了,我沒有生氣,但我也沒有說話。不是這樣的,不是這樣的,我心裡一直這樣想著,母親對傳統文化的斷裂與無知,也就代表了滿州現在漢化的狀態。跟其他原住民青年談話時他們總是說,與父母問及原住民事情的時候,那個關係好像拉近了,但是之於我卻是越離越遠。
我清楚記得一位滿州永靖的青年跟我說的話,他說如果這樣,我寧可當漢人,原住民的身分我寧可不要。我能夠深深地體會到那樣的感受。但是你甘願嗎?我不甘願,我不甘願歷史就這樣被殖民者消磨,我不甘願自己輕易地選擇身為大漢——這條阻力最小的道路。我也記得另一位原住民青年在一次凱達格蘭大道上的遊行曾問我「tima su ngadan」5,我說「我沒有族名」,「抱歉」他說。那個抱歉我一直記得,到現在都還記得。
或許也是因為這樣,這個名字和沒有名字的狀態,會一直讓我記取那被抹去的過程,也希望別人能夠記得有人「沒有名字」。
註 1 :根據《原住民身分法》第四條第二款:「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者,取得原住民身分。」而台灣以從父姓為主,造成漢父原母所生之子女,須由改為傳統姓名或改從母姓始得原住民族身分,而原父漢母則並不用經過改姓或改傳統名的程序,顯見台灣的法律制度的從父制。
註 2 :文中三段引詩皆出自排灣族詩人莫那能詩作〈恢復我們的姓名〉。
註 3 :典出自舞鶴的《餘生》:「無聊時晃來看看我們小番怎樣生活在你們大漢之中」。
註 4 :原民圈常流傳一些像是:唱歌要有鹽巴,意思是唱歌要有味道,要有老人家的味道;也常常說要有土味,那是對土地的情感,對山林、對文化的嚮往。
註 5 :排灣語,「你叫什麼名字」之意。
沒有名字的人/潘宗儒
認同的追尋
一家四口在盆地邊緣搬遷過好幾次,我在台北生活成長。中學以前,我一直以為自己是個漢人(而且是身為一個完全不會意識到原/漢差別的漢人),父親是屏東內埔客家人,起初以為母親是閩南人,閩南語、炷香、祖先牌位、觀音、紙錢……,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
十二歲的時候改從母姓,我有了官方的原住民身分1。那時候,「原住民」三個字對我來說好虛無,是一個遙不可及的、沒有概念的三個字。那個時候,同學友人會問我:你會不會說族語?不會。會不會打獵?不會。會不會喝小米酒?不會。甚至會問說會...
作者序
楔子
我們是一群來自不同族群,也有著不同的生命經驗的平埔原住民族青年,在追索認同的路上、探求族群命脈的過程之中相遇,進而共同組成了書寫團隊,這當中包括了五位寫作者與一位攝影師。本書的成形,是我們從二○一四到二○一七年間刊登在《沒有名字的人》粉絲專頁上的單篇故事集結而來。首先,我們五位的自述,是促使我們集結並行動的骨幹,故成為書中的第一部;接著,由我們採訪、編輯而成的二十位青年敘事,最為面貌豐富的血肉,經過重新排序、分組和整理後,成為本書的第二部;而在至今成書歷時的五年中,隨著平埔族群正名運動的推進,外在的政治面貌沿革多變,加以我們幾位寫作者面臨的生涯變動,再再使我們重新思考爭取族群身分的內在矛盾,我們將這些自省剖開,成為有些沉重的第三部,希望邀請讀者與我們一同窺探台灣各原住民族的膠著和希望所在。
我們試著以「沒有名字的人」這個概念,提出平埔族群在歷來殖民國家治理下被埋沒、被奪去名字與身分的處境,也試著以此作為標的,幫助我們指出那眾多仍未現身的無名之人。我們意識到,與其孤獨地獨自迷惘,不如將那些未知的、消失的、痛苦的、無奈的、無力的、徬徨的一切,以我們所能(或僅能)掌握的現代技術與工具,將其凝鍊成為一股新的力量去衝破這道生命的難關。於是我們決定起身以集體之姿,踏上田埂、穿越林徑、渡過海岸、走上街頭,朝著沒有名字的人們而去,與他們一同邁步前行。
楔子
我們是一群來自不同族群,也有著不同的生命經驗的平埔原住民族青年,在追索認同的路上、探求族群命脈的過程之中相遇,進而共同組成了書寫團隊,這當中包括了五位寫作者與一位攝影師。本書的成形,是我們從二○一四到二○一七年間刊登在《沒有名字的人》粉絲專頁上的單篇故事集結而來。首先,我們五位的自述,是促使我們集結並行動的骨幹,故成為書中的第一部;接著,由我們採訪、編輯而成的二十位青年敘事,最為面貌豐富的血肉,經過重新排序、分組和整理後,成為本書的第二部;而在至今成書歷時的五年中,隨著平埔族群正名運動的推...
目錄
【推薦序】補修、修補,然後住在自己裡 馬翊航(《幼獅文藝》主編)
【推薦序】成為不再被認同困住的人 賴奕諭(菲律賓原住民族研究者,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人類系博士生)
【推薦序】正名,延續族群生存與認同的積極性作為 Ciwang Teyra(太魯閣族人,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推薦序】找回自己的名字,尋得回家的路 方克舟(Mata.Taiwan創辦人)
楔子
第一部 恆春半島的魔幻舞台
01 沒有名字的人:潘宗儒
02 「ima ka aku?」關於我是誰?:Awui Kaisan
03 你是原住民嗎?:余奕德
04 偏要固執地記著:陳以箴
05 吐出那口沉重的氣:方惠閔
第二部 群像故事:二十段旅程
01老祖娘娘的壽宴:丁肇義
02 生熟聯姻:潘婕瑀
03 歸來,如何?:潘宗緯
04 被屠殺的記憶:潘啟新
05 認同不是單選題:潘佳佐
06 最在地的異國臉孔:張俊偉
07 不想再被消失:Tuwaq Masud 杜佤克.瑪蘇筮
08 觀看的實踐:Uki Bauki 潘昱帆
09 以凱達格蘭為名的路:潘彥廷
10 背著祖靈的重量:Bauke Dai’i 潘正浩
11 一輩子的賽跑:Kaisanan Ahuan 王商益
12 拉起一個圓:潘軒豪
13 以身為度:潘寶鳳
14 聽見道卡斯的聲音:劉秋雲
15 甦醒的語言:萬盈綠
16 追隨西拉雅獵人的腳步:Takalomay Kacaw 買啟文
17 回到這片河谷:潘麒宇
18 通靈少年:尤威仁
19 出走,是為了回家:Karai Akatuang 段柏瑜
20 混血調酒:李建霖
第三部 最最遙遠的路
後記
後記之前
潘宗儒
方惠閔
余奕德
張家瑋
陳以箴
參考文獻
【推薦序】補修、修補,然後住在自己裡 馬翊航(《幼獅文藝》主編)
【推薦序】成為不再被認同困住的人 賴奕諭(菲律賓原住民族研究者,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人類系博士生)
【推薦序】正名,延續族群生存與認同的積極性作為 Ciwang Teyra(太魯閣族人,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推薦序】找回自己的名字,尋得回家的路 方克舟(Mata.Taiwan創辦人)
楔子
第一部 恆春半島的魔幻舞台
01 沒有名字的人:潘宗儒
02 「ima ka aku?」關於我是誰?:Awui Kaisan
03 你是原住民嗎?:余奕德
04 偏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