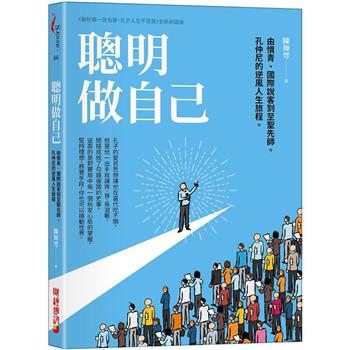兩人下車以後竄入森林,地勢一步一步越來越高。道路位在谷底,周圍長滿古老長青樹,樹冠加上濃霧遮蔽了月光與極光,珮彤最多只能看見二十呎內的景物。
她輕觸戴斯蒙肩膀,指了指手裡的手電筒,示意該不該開燈。
他搖頭表示不要,握緊手槍、扛著步槍,另一手向後牽住珮彤,領她穿過一片幽暗。
太靜了。完全聽不到小動物移動聲響或鳥類鳴囀,珮彤不慎踩碎一截殘枝,斷裂聲在全然的死寂中顯得格外刺耳。
戴斯蒙停住腳步。
「抱歉。」珮彤低語。
他觀察樹林有什麼反應或動靜。
什麼也沒有。
「距離還有多遠?」
珮彤開手機確認。「三十碼,正前方。」
戴斯蒙舉著手槍,緩緩接近。
最後十碼,珮彤屏著氣息,感覺大霧從四面八方壓了過來。
手機發出嗶嗶聲,跳出訊息視窗:到達迷宮入口。
戴斯蒙接過手電筒,打開後在周圍掃了掃。光線撕開濃霧,他忽然停下來。
珮彤也看見了,腦中的第一個反應是:會爆炸。
戴斯蒙朝地上的小金屬盒靠近。「退後,」他低聲吩咐:「或許有陷阱。」
珮彤退到十碼之外的一棵樹後觀望情況。戴斯蒙亮出直刃軍用刀,以鋸齒刀刃砍下旁邊的樹枝,稍微削乾淨後當作棍子,撥開了盒蓋。
沒有任何奇怪反應。她鬆了口氣。
戴斯蒙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彎腰自盒內取出一張紙片,然後呼了口氣。
「是另一組GPS座標。」他解釋。
「在哪兒?」珮彤問。
戴斯蒙取出手機,輸入座標。「還是昔德蘭,距離這裡二、三十哩吧,可以開車過去。」
搜集螢幕忽然跳出提示,是迷宮實境的訊息:
發現入口:1
她拿給戴斯蒙看。
「跟我之前在達達阿布開啟軟體的時候一樣。」
他接過手機、按下訊息,螢幕顯示出一幅地圖,這次位置是在澳洲南部靠近海岸的鄉間。戴斯蒙將其放大,珮彤從側邊瞧見綠色與褐色組成的地貌。比例調到最大時,兩人都愣住,因為那是他們十五年前一起去過的地方—戴斯蒙兒時的老家。廢墟上已長出青草,但仍能看見地基焦痕。乍看之下與當年毫無分別,但珮彤心想不知道衛星影像是何時拍攝,難以判斷目前當地的情況。也許那裡就像昔德蘭一樣藏了什麼。
「有什麼想法?」她問。
戴斯蒙瞥了手機一眼,再看看寫了座標的紙條。「先調查完這邊,再決定要不要去澳洲。」
「需要通知艾芙莉嗎?」
「先不用。等我們確認完再說。」
戴斯蒙走入感應範圍時,樹頂那臺動態感應監視器開啟了。鏡頭彼端的那人清醒過來,專注的面孔顯然十分焦躁。時間不多了。
戴斯蒙與珮彤繼續摸黑出發。雖然霧氣依舊濃重,但已有散開的跡象,車子逆風而行,彷彿穿過巨大風口。深入昔德蘭荒野之後,道路左彎右拐,崎嶇不已。
距離目的地五百碼時,出現了一條泥巴岔路。戴斯蒙從手機導航確認它通向新座標,於是關閉了車頭燈,從背包掏出夜視鏡偵察。
又向前三百碼之後,他熄了火。「我們走過去。」
兩人沿著泥巴路行走,路面切入森林,軌跡看不出規律,盡頭的林間空地上有座小屋。沒有任何生命跡象,窗內黑暗、煙囪冷寂,石頭外牆與木屋頂上滿布灰色、青色和紫色的苔蘚。屋齡看上去歷史悠久,說不定自中世紀便無人聞問至今。
陰暗中,戴斯蒙朝珮彤做了個示意:妳留下。
他沒等珮彤回應,直接將車鑰匙塞過去,自己提著步槍走近了小屋。
珮彤看著戴斯蒙從小屋右側繞過去,緊張得忘了呼吸。十秒、二十秒過去,裡頭突然射出亮光。
前門打開,戴斯蒙走出來對她招手。
她走到門廊階梯。「快進來看。」戴斯蒙說。
珮彤跨進門後,完全目瞪口呆。
牆上貼滿了軟木板,到處釘上圖片、文章、筆記。某些詞彙引起珮彤注意:昇華生技、輝騰基因、基石量子、具現遊戲,還有戴斯蒙和康納的照片。
手寫字跡內容也有幾句話很醒目:
隱日—人,組織,還是計畫名稱?什麼東西用得到那麼龐大的能量?
第三世界是實驗場地?
有一部分剪報來自八○年代。
顯而易見,曾經有人以此為據點,對季蒂昂調查了一段時間,而且最近才剛離開,因為廚房水槽內的盤子上還有食物殘渣,中島上面也擺著一臺闔上的筆記型電腦。
「有電源。」戴斯蒙打開小型暖氣,珮彤覺得舒服多了。「屋子後面有太陽能發電場,我猜屋頂後側應該也有,不過完全沒連接外部電網。」
一面牆下有三個檔案櫃。珮彤正想打開時,戴斯蒙叫著:「這裡。」
他站在客廳,腳底地板踏了踏。「有沒有聽見?」
珮彤搖頭。這是幹嘛?
戴斯蒙抓了壁爐旁邊的火鉗,朝地面一插,當作扳手撬開了木地板。底下居然藏了個保險櫃,門是旋轉式密碼鎖。他趕快將周邊木板都撬開,直到整個保險櫃露出,然後伸手試著開鎖。
珮彤過去跟著蹲下。「你知道密碼?」
「可能吧。」他喃喃著。
不過戴斯蒙扣住把手拉了拉卻拉不開。
「你剛才用的密碼是?」
「歐威爾的保險箱密碼。」
珮彤聽了會意過來:戴斯蒙懷疑是自己布的局,房子裡的研究就是他本人留下的。
他轉頭看著珮彤。「有其他主意嗎?」
方才在森林找到金屬盒的時候,珮彤就覺得不對勁。既然兩個座標相距不遠,幕後黑手為什麼要刻意分成兩次,而不是直接將人引導到小屋?「試試看前一個座標,可能是提示。」
戴斯蒙點頭。「唔,沒錯。大概是避免有人意外闖入,閒雜人等不會知道密碼。」
他用金屬盒所在位置當作密碼,果然立刻開啟了櫃門。
拉開以後找到一疊紙張。最上面那張有一行筆跡:
「季蒂昂的歧途」
戴斯蒙翻開,下面是一份手札,兩人並肩坐下閱讀起來。
若有人看到這個,代表事態邁入最惡劣境地,世界即將被顛覆。我們面對的敵人比任何國家的政府或軍隊都來得更強大。
但我深信仍有希望阻止他們。想要成功,必須先瞭解對方的起源、歷史,以及真正的動機。以下就是答案,也是我所能給予最有威力、唯一的武器。
首先請明白季蒂昂最初是個心存善念、理念崇高的組織。雖然有其儀式與信仰,但成員並不承認神祇,追隨的是科學。他們相信,藉由科學能夠回答最深奧的問題,其中包括所謂大哉問:
人類為何存在?
季蒂昂集團窮究心力尋找答案,過程中卻誤入歧途。一九四五年七月某日,在新墨西哥州發生的事件永遠改變了季蒂昂集團,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我父親親眼見證,故事轉述在後。底下大半是我自己的經歷與觀點,希望足以引導你找出阻止季蒂昂的手段。動作要快。
—威廉
「威廉,」珮彤開口:「沒有姓氏。你有印象嗎?」
「沒有。」戴斯蒙往下翻閱掃視。「但看起來應該是我的同夥,或者線人之類。」
「嗯。接下來怎麼辦?要通知艾芙莉了嗎?」
「不要。」他立刻說:「繼續調查,讀完這些東西,搜索這棟小屋。」
兩人在客廳舊沙發坐下,室外氣溫才攝氏四、五度,裡面卻感覺更冷,小暖爐的熱力不足。她瞥了壁爐一眼,擔心讓煙囪冒煙是不必要的風險,所以拿起沙發上一條薄被蓋在自己和戴斯蒙身上,彼此的體溫慢慢地暖和了被子下的小天地。
戴斯蒙望向她,她知道兩人心裡浮現同樣的往事:十五年前,他們在帕羅奧圖也曾這樣度過寒冬。然而此刻有著人事已非的唏噓,但珮彤無法耽溺在昔日的美好裡,只能趕快翻開手札細讀。
**
我父親叫作勞勃.摩爾。他是個科學家,而且很可能身處在科學史上最重要的時間地點,也就是科學結束戰爭、改變世界的那瞬間。
一九四五年七月那天,他只睡了一小時,卻換上最體面的服飾,開車穿過沙漠,抵達了測試場。門口警衛要求他下車,對他做了很徹底的搜身。
基地裡面氣氛緊繃。控制站內的專案主任瀕臨崩潰,萊斯利.格羅夫斯將軍出面將人帶走,他們站在灰暗天色和紛飛雨水下交談。將軍不斷安撫他,一切都依照計畫(注)進行。
接近五點半,倒數計時開始。那幾秒鐘是勞勃人生最漫長的時間。
團隊替裝置取了暱稱,就叫作「小玩意」(Gadget)。小玩意是一流科學家通力合作,投入五年心血的結晶,事件當下安裝於一百呎高的鐵塔頂端,四面八方盡是荒漠,學者在將近六哩外的控制站等候。就算相隔如此遙遠,勞勃還是帶上了焊接眼鏡,隔著護目鏡片注視鐵塔方向。
然而讀秒歸零前其實只見一片黑暗。
最初,一陣白光驟然閃耀,持續幾秒以後熱浪撲來,全面籠罩世界。牆壁似的強光消褪後,他隱約看見巨大火柱快速朝天空升竄。
爆炸雲隨著高溫直衝一萬七千呎,多數科學家原本以為絕對做不到。爆炸過後幾分鐘,雲氣甚至能夠觸及三萬五千英呎的副平流層。
引爆過後四十秒,衝擊波來到了科學家控制站,緊接著一陣巨響在沙丘迴蕩數秒,乍聽彷彿暴風雨席捲,一百哩外也能聽見,強光可見距離幾乎有兩倍之遠。
支撐炸彈的鐵塔一瞬間熔化,地面留下直徑達半哩的大坑。離爆炸地點一千五百呎外,原本設置於混凝土上寬約四吋、高約十六呎的鐵管,被高溫氣化得連灰也不剩。控制站裡鴉雀無聲,事前各種憂慮同樣化為烏有,在場者心中只有驚畏與茫然。
大家像是驚醒般東張西望,不知所措。片刻後有些人彼此握手祝賀,其他人或笑或哭,但每個人都相信世界會因此轉變。
第一顆原子彈在此引爆。他們曾經希望那也會是最後一顆。
回到新墨西哥州首府洛斯阿拉莫斯市,有人舉起酒杯說:「迎接原子時代的黎明。」
許多成員曾擔心試爆失敗,結果是多數人欣慰,少數人恐懼。
「三位一體」試爆計畫結束以後,勞勃初次開口:「的確是個嶄新的時代,我們給了人類前所未有的東西—毀滅自己的工具。」
沒人回應,他繼續說下去:「距離狂人搶這玩意兒去利用的那一天還遠嗎?五年,十年,一百年?我開始懷疑人類還剩下幾個世代,會在我們兒子還是孫子那一輩滅絕?」
散會後,勞勃的上司跟著他進入辦公室,默默關上門。他一直尊敬且信任這位前輩,對方這樣的態度自然讓他更在意。
「你剛才那番話是認真的?」
「每個字都很認真。我們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
主管好好端詳了他。「勞勃,謹言慎行,我們身邊有些人,不像表面上那麼單純。」
過不到一個月,美國朝廣島丟下了原子彈。
再過三天,輪到長崎。死亡人數從十二萬九千人攀升到二十四萬六千人。
勞勃心裡擠壓的許多情緒終於壓垮了他。遲遲不見他返回工作崗位,主管親自前去他家中拜訪。
「你早就知情?」勞勃問。
「不知道細節,只知道會靠炸彈結束戰爭。」
「那些人都是我們殺死的。」
「不這麼做,戰火還要綿延很多年。」
勞勃搖頭。「明明可以在東京郊外投彈給天皇和居民看見就好。之後再灑下傳單,要日本人投降或推翻政府,他們會照辦的。」
「煽動敵國政變有太多混亂和未知數。更何況東京早就被炸得很慘,那邊的人見識過大風大浪,原子彈在郊區爆炸,已經嚇阻不了任何人。三月那時候才兩天,就有十六平方英里土地被美軍化為焦土。」
「你想說什麼?」
「我要說的就是,無論你是什麼態度,決策並非你下的,根本沒必要有罪惡感。這是戰爭,你只是做好本分。」
「或許吧。但我無法麻木不仁地看待一切。當初原子彈計畫滿足了我內心空虛,我以為自己找到了目標和信念。直到目睹那種人間煉獄,我才知道自己有多蠢。如今覆水難收,人類滅亡只是時間長短問題。」
主管靜靜坐著好一會兒,才又開口:「如果我說,世界上有一群像我們這樣的科學家、知識份子,來自世界各地,而且與你一樣認為人類已經危及自己的存續呢?如果我說,這群人已經開始下一個曼哈頓計畫,但研究的技術是在未來某一天能夠保住人類?如果我說,誰開發的裝置就由誰控管,而那群人心裡沒有小我只有大我,不受民族、宗教、金錢左右?」
「如……如果真的有這樣一個團體存在,我很想和他們多多交流。」
幾個月之後,兩人去了倫敦,對當地景況極其詫異。大轟炸導致市區許多地帶遭到夷平,其他地方則淪為廢墟。不過德軍的猛攻沒有擊潰英國人,他們已經開始重建社會。
子夜一點,一輛汽車載他們前往一間私人俱樂部。兩人登上華麗階梯,走進大廳,一排排座位前面有個講臺,背景高高懸掛著三個標語:「真理、倫理、物理」。與會者魚貫而入,引頸盼望,勞勃粗估至少有六十人到場。
那一夜,講者說的話,永遠改變了勞勃的生命。
|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大滅絕二部曲(限量作者親筆簽名版):密碼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6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大滅絕二部曲(限量作者親筆簽名版):密碼
★美國亞馬遜百大名家、暢銷科幻系列「亞特蘭提斯進化三部曲」作者,又一醫療科幻驚悚奇作!
★橫掃美亞三大科幻排行榜冠軍,作品總銷量突破 4,000,000 冊!
★作品翻譯成24種語言發行全球,近3000位讀者星級好評!
各界驚豔推薦:
生物人類學教授 王道還|瑞典皇家理工學院物理系博士 余海峯|
名人書房主持人 詹慶齡|馬偕紀念醫院兒科住院醫師 戴裕霖|
作家 譚劍
英國衛報大讚:本書之精湛出彩,有如閱讀暢銷大師丹.布朗與麥可.克萊頓的傑作!
台灣讀者心聲:當我翻開這本書,我也被感染了不停讀下去的病毒……
類伊波拉之X1曼德拉病毒橫行世界,
14天內高達61億人感染,1800萬人死亡,
幕後黑手不達目的絕不罷休,
最終目標竟是入侵每一個人身上的基因密碼!
魔鏡計畫肆虐全球,致病率高達99.9%
人類抵抗惡的距離竟只剩下0.1%的可能?
珮彤與戴斯蒙在神祕女子艾芙莉的營救之下,
驚險逃出了「季蒂昂」組織以及那位全身有火焰傷疤的謎般男子──康納.麥克廉的掌心;
只是艾芙莉也帶來了更多謎團,她的動機諱莫如深,
一舉一動都讓珮彤與戴斯蒙不敢掉以輕心。
戴斯蒙在被囚期間從康納口中確知,魔鏡計畫完成的三要素元件:基石、昇華、具現,
而他就是掌握「具現」的人,也是「季蒂昂」的一員,
為了阻止集團首腦們的瘋狂陰謀,竟是他自己運用「昇華」技術讓自己失憶!
艾芙莉、佩彤兩人跟著戴斯蒙留在「迷宮實鏡」app裡給自己的線索,沿途躲避各種追擊,
一步步追尋、解謎「具現」的所在,分秒必爭要搶在敵手之前取得先機。
然而此時此刻必須同心協力的三人卻也各懷心事:
戴斯蒙漸漸想起自己與佩彤、康納糾纏不清的過去;
艾芙莉身懷密令,效忠對象不明;
而佩彤除了想盡辦法要跟上他們,找出解除大瘟疫的可能,
更發現自己開始了感染前期的發燒症狀……
魔鏡計畫投放恐怖病毒攻擊,掠奪無辜生命,試圖取得絕對權力,
卻口口聲稱是為了終極至善而行惡之事?
*****
《大滅絕首部曲:感染》各界驚豔讚賞:
本書之精湛出彩,有如閱讀暢銷大師丹.布朗與麥可.克萊頓的傑作!──英國衛報
李鐸刻畫塑造人物的功力總是凌駕於周遊科幻驚悚情節之上!──出版人周刊
疫病、恐慌、陰謀、人性揉合入巨大恢弘的敘事架構,猶能遊刃有餘緊扣命題抽絲剝繭,是作者科幻驚悚之作的再進化版。──名人書房主持人、資深新聞主播,詹慶齡
一翻開這本書,我就被感染了。除了我熟悉的非洲、病毒、醫療,這本書更融合了科技、人性、與末日。多次想逃離書中的血腥災難,卻不自覺被陰謀背後的驚奇吸引,無法不沉浸這本科幻懸疑小說。──馬偕紀念醫院兒科醫師,戴裕霖
台灣讀者熱烈討論絕佳好評:
《大滅絕首部曲:感染》在緊張時刻終止,讓人對於後續的發展充滿想像空間,失去記憶的戴斯蒙儼然是個關鍵人物,是扣人心弦的情節中僅存的一線希望。──小建
本書帶給我們一個驚悚卻很實際的政治寓言:疾病可以被完美控制,當然也能做為武器。體系的崩壞只是一瞬間的事,建立卻需要很長的時間。──黯泉
字裡行間的畫面就像是一部電影,充滿高潮迭起,也令我相當期待在《大滅絕首部曲:感染》之後的系列作!當然,在閱讀此書的同時,也必須對全世界的公衛人員致上最崇高的敬意。──天才雷普妮小姐
當我翻開這本書的時候,我也被感染了......現實、現代化、栩栩如生的畫面浮現在腦海卻被那驚奇無比的劇情所吸引,讓人想不停一探究竟。──千雪
馬克吐溫說:現實的人生往往比小說離奇,因為現實人生不必顧及可能性。這本小說的誕生,或許代表著人們最原始的生存焦慮,在這個人類不斷的開拓未知的環境之時,逐漸地把古老病毒一一的釋放的年代,或許,可以一讀此書去思索人類自身的命運。──Murphy
大滅絕檔案三部曲──
大滅絕首部曲.感染
大滅絕二部曲.密碼
大滅絕三部曲.未來(2019年7 月上市)
作者簡介:
傑瑞.李鐸A. G. Riddle
曾經花費十年時間開創、經營網路公司,爾後決定投入小說創作,這也是他夢寐以求的志業。李鐸成長於北卡羅萊納州的小鎮,之後進入北卡羅萊納大學Chapel Hill分校就讀,他在那兒和一位自小結識的友人創辦了第一間公司。目前居住佛羅里達州的帕克蘭,非常樂意收到讀者對自己作品的回饋。
他的處女作「亞特蘭提斯進化三部曲」上市後取得了驚人的成績,在美國銷量超過200萬冊,被翻譯成24種語言,並即將拍攝電影。他曾一度位列美國亞馬遜科幻類圖書作家榜第二名,僅次於喬治.馬丁。
著有:「亞特蘭提斯進化三部曲」、「大滅絕檔案三部曲」
官網:http://www.agriddle.com/
相關著作:《大滅絕首部曲:感染》《亞特蘭提斯.新世界(亞特蘭提斯進化終部曲)》《亞特蘭提斯.瘟疫(亞特蘭提斯進化二部曲)》《亞特蘭提斯.基因(亞特蘭提斯進化首部曲)》
譯者簡介:
陳岳辰
師大翻譯研究所畢業,現任專業口筆譯者、大學兼任講師,並參與多款軟體及遊戲中文化專案。譯作有:《死亡之門》、《御劍士傳奇》、《非理性時代:天使微積分》、《非理性時代:渾沌帝國》、《非理性時代:上帝之影》、《無名之書》、《我無罪》、《無罪的罪人》、《原罪》、《把他們關起來,然後呢?》、《誘惑者的日記》、《破碎帝國三部曲》等書。
章節試閱
兩人下車以後竄入森林,地勢一步一步越來越高。道路位在谷底,周圍長滿古老長青樹,樹冠加上濃霧遮蔽了月光與極光,珮彤最多只能看見二十呎內的景物。
她輕觸戴斯蒙肩膀,指了指手裡的手電筒,示意該不該開燈。
他搖頭表示不要,握緊手槍、扛著步槍,另一手向後牽住珮彤,領她穿過一片幽暗。
太靜了。完全聽不到小動物移動聲響或鳥類鳴囀,珮彤不慎踩碎一截殘枝,斷裂聲在全然的死寂中顯得格外刺耳。
戴斯蒙停住腳步。
「抱歉。」珮彤低語。
他觀察樹林有什麼反應或動靜。
什麼也沒有。
「距離還有多遠?」
珮彤開手機確認。「三...
她輕觸戴斯蒙肩膀,指了指手裡的手電筒,示意該不該開燈。
他搖頭表示不要,握緊手槍、扛著步槍,另一手向後牽住珮彤,領她穿過一片幽暗。
太靜了。完全聽不到小動物移動聲響或鳥類鳴囀,珮彤不慎踩碎一截殘枝,斷裂聲在全然的死寂中顯得格外刺耳。
戴斯蒙停住腳步。
「抱歉。」珮彤低語。
他觀察樹林有什麼反應或動靜。
什麼也沒有。
「距離還有多遠?」
珮彤開手機確認。「三...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台灣版獨家作者序】
親愛的讀者們:
臺灣版在我心裡一直有個特別地位,雖然現在自己的作品已經翻譯為二十多種語言、在三十個國家發行,但最初的起點就是臺灣。
五年前,臺灣出版社奇幻基地買下《亞特蘭提斯.基因》(我的處女作)翻譯版權,是第一個賞識我作品的海外出版社,隨後其他國家才有人跟進。《亞特蘭提斯.基因》在奇幻基地的推廣下,也獲得了很大迴響,所以我非常高興能夠繼續在臺灣推出作品,包括各位手中這本新書。
目前我已出版的七本作品裡,《大滅絕首部曲:感染》有十分特殊的意義。我耗費兩年時間收集素材,完成它...
親愛的讀者們:
臺灣版在我心裡一直有個特別地位,雖然現在自己的作品已經翻譯為二十多種語言、在三十個國家發行,但最初的起點就是臺灣。
五年前,臺灣出版社奇幻基地買下《亞特蘭提斯.基因》(我的處女作)翻譯版權,是第一個賞識我作品的海外出版社,隨後其他國家才有人跟進。《亞特蘭提斯.基因》在奇幻基地的推廣下,也獲得了很大迴響,所以我非常高興能夠繼續在臺灣推出作品,包括各位手中這本新書。
目前我已出版的七本作品裡,《大滅絕首部曲:感染》有十分特殊的意義。我耗費兩年時間收集素材,完成它...
顯示全部內容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 |||
|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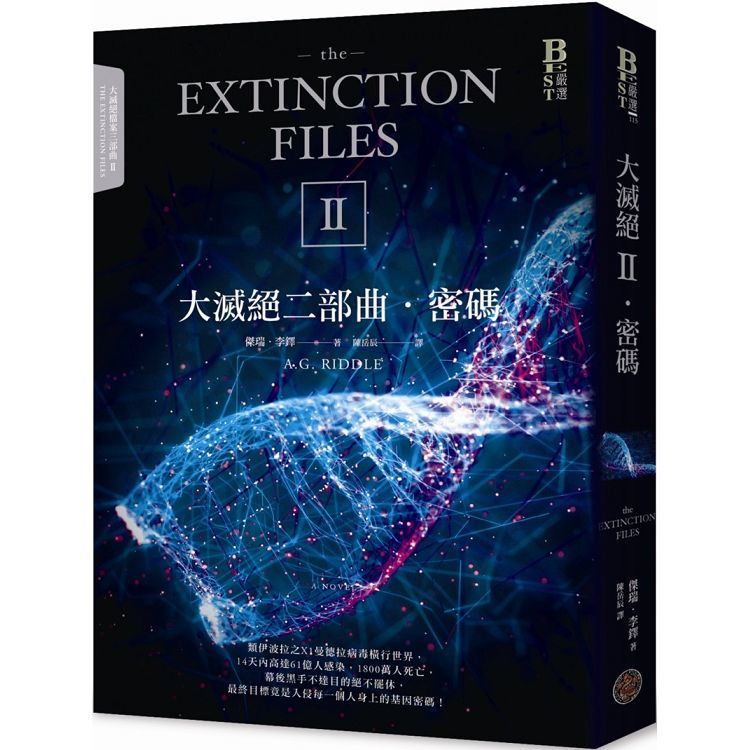
 2019/06/02
2019/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