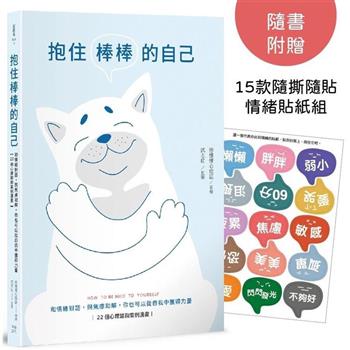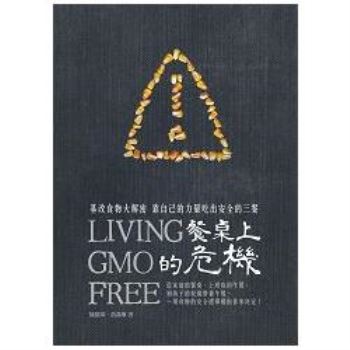第一章生命旅程中的「存有」困境
我在哪裡?我是誰?
我怎麼會在這兒?
這個叫「世界」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我是怎麼來到這世界上的?
為什麼沒有人先問過我的意思?
如果我是被迫參加演出的,
導演在哪兒?我要見他。
——齊克果
生命旅程的實相
我們的本質就像夢的本質一樣,我們短促的一生不過是一場睡眠。
——莎士比亞
齊克果提出:「我們從來不曾擁有自由」。從存在主義哲學的角度看,這一觀點無疑是正確的。因為,我們的「存在」帶著一種被遺棄感:我們不能選擇什麼時候來到這個世界上,不能選擇出生的人種、國籍和家庭,不能選擇長相和智商。當這些都不能選擇的時候,某種程度上,我們也不能選擇未來的生活與最終的命運。換句話說,我們是「被迫」來到這個世界上的。
存在主義心理學家科克J.施奈德經常向人們提出如下比喻:
如果我告訴你,你將要進行一次「偉大的冒險」,你將要為這次冒險而得到所有的裝備——食物、帳篷、衣服,那你會怎麼想呢?
如果我進一步告訴你,你將在這次旅行中體驗到宇宙令人恐怖和驚異之處,一路上將要遇到一大批各式各樣的存在物(beings)——人類的和非人類的,每天你都會有機會對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感到驚異、受其觸動和產生遐想,那你又會怎麼想呢?
而最後,也是真正關鍵的:如果我告訴你,你要花費大約八十年的時間來完成這次旅行,在大約80年之後,要進行一次更令人著迷的和更不可思議的旅行,那你又會怎麼想呢?
如果把這三個比喻代入我們自己的人生,難免使人產生毛骨悚然之感,但這是生命旅程中無法逃避的「存有」困境。《薛西弗斯神話》曾對這種人生困境進行了深刻的描寫:
薛西弗斯是科林斯的建立者和國王。他甚至一度綁架了死神,讓世間沒有了死亡。最後,薛西弗斯觸犯了眾神,諸神為了懲罰薛西弗斯,便要求他把一塊巨石推上山頂,而由於那巨石太重了,每每未上山頂就又滾下山去,前功盡棄,於是他就不斷重複、永無止境地做這件事——諸神認為再也沒有比進行這種無效無望的勞動更為嚴厲的懲罰了。薛西弗斯的生命就在這樣一件無效又無望的勞作當中慢慢消耗殆盡。
齊克果對人類的「存有」困境也提出了相似的論述:
無論一代人可能從另一代人身上學到什麼,從根本上說,沒有哪一代人可以真正地從其先輩那裡學到什麼……因此,沒有哪一代人從另一代人那裡學會如何去愛,沒有哪一代人是從其他點上開始而不是從頭開始,沒有哪一代人比他前一代的人所被分派的任務更少一些……在這一點上,每一代人都是從原初開始的,他們與所有先前的每一代人所擁有的任務都相同,他們的任務也不會更深入,除非先前的這一代人逃避了屬於他們的任務並哄騙他們自己。
可以看出,從「存在」的角度看,人生不僅是一場終點明確——死亡的冒險旅行,而且是孤獨的旅行,旅途中還要忍受各種責任的限制、人際關係的困擾、疾病的折磨、意義感缺失等痛苦,難以自由地、幸福地享受旅途風景。下面借電影《七宗罪》中「翠茜和沙摩賽關於懷孕的對白」來說明人們對生命旅程中這一實相的深深無奈:
沙摩賽:「我不知道……你是否找對人談。」
翠茜:「我恨這城市。」
沙摩賽:「我曾愛過一個人,我們形同夫妻,然後她懷孕了,那是好久以前的事,我記得那天早上去上班,那天跟平常完全沒兩樣,是我首次獲悉懷孕的事,我突然感到恐懼,頭一次那麼怕,我記得當時心裡想:怎能讓小孩在此出世?在這種爛地方長大?我告訴她我不想要,我用了好幾週時間逐漸勸服她。」
翠茜:「我想生小孩。」
沙摩賽:「我此刻能告訴你的是:我知道……我肯定當初沒下錯決定,但我畢生都在後悔,如果你不想留下孩子,如果你決定拿掉,千萬別告訴他你有孕,但若你選擇生下來,你就要盡力去愛護那小孩,我只能給你這忠告。」
生命旅程中主要的「存有」困境
人僅僅是一棵蘆葦,是自然界中最虛弱無力的蘆葦,但是他卻又是一棵會思考的蘆葦。
——布萊茲.巴斯卡
在哲學和心理學領域,生命旅程中主要的「存有」困境涉及認識自己、死亡、自由與限制、孤獨和無意義等。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整個人類歷史,不管文化、地域和人種方面有多大差異,均圍繞上述「存有」困境展開。
一、認識自己
認識自己,又稱「自我意識」,是人區別於動物的關鍵所在。在中國古代,老子說過,「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佛禪學中也把「我是誰」的問題當作生命的核心問題進行研究、參悟。莊子說,從前自己做夢,夢到自己是一隻翩翩飛舞的大蝴蝶,但究竟是自己做夢化為蝴蝶了呢?還是蝴蝶做夢化為自己了呢?這是不清楚的。馮之浚先生認為,認識自我的困難在於「我」之複雜,每個人身上都有四個「我」:一是公開的我,自己知道,別人也知道的部分;二是隱私的我,自己知道,別人不知道的部分;三是背後的我,自己不知道,別人知道的部分;四是潛在的我,自己不知道,別人也不知道的部分。
古希臘有一句名言就是「認識你自己」。西方神話中著名的斯芬克斯之謎也提示了「認識自己」之困難:
獅身人面獸斯芬克斯每天都在問過往的行人一個問題:「有一種動物,它在早晨的時間四條腿,在中午的時候兩條腿,在晚上的時候三條腿,這個動物是什麼呢?」過往的人答不上來,就被獅身人面獸吃掉了。年輕的伊底帕斯在路過的時候,說出了最終答案:「這個動物就是人。」斯芬克斯大叫了一聲,跑到懸崖邊跳了下去。
伊底帕斯儘管回答出了問題,但由於沒認清「我是誰?」,導致誤殺了生身父親,娶了親生母親為妻,最後只能把自己的眼睛弄瞎來懲罰自己。難怪德國著名詩人歌德提出:「人是一個糊塗的生物;他不知從何處來,往何處去;他對這個世界,而首先是對自己,所知甚少。」蘇格拉底也寫道:
智慧是唯一的善,
無知是唯一的惡,
其他東西都無關緊要,難道這就是最終結果嗎?
認識你自己。
電影《美夢成真》更是尖銳地提出了「認識自己」的重要性:「當一個人既不自知,也不接受自己所做的事,於是要永遠承擔後果。所以,地獄中人並不只是我們平日所想的十惡不赦,罪不可恕的大惡人,還有很多渾渾噩噩,不願接受因果的糊塗人。」
二、死亡
死亡是最顯而易見、最容易理解的「存有」困境。儘管我們現在存在,也不管我們身體多麼健康,總有一天,這種存在會終止。死亡將如期而至,絕無逃脫的可能。這是一個恐怖的實相,引起了人們巨大的恐懼。斯賓諾莎提出:「每一事物都在盡力維持自身的存在。」這種對死亡必然性的意識與繼續生存下去的願望之間的張力,構成了存在的一個核心衝突。
古今中外的哲學家、心理學家、醫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們從來沒有停止過對死亡的探討。例如,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中就深入地論述了生死問題:
生存或毀滅,這是個必答之問題:
是默默的忍受坎苛命運之無情打擊,
還是與深如大海之無涯苦難奮然為敵,並將其克服。
此二抉擇,究竟是哪個較崇高?
死即睡眠,它不過如此!
倘若一眠能了結心靈之苦楚與肉體之百患,
那麼,此結局是可盼的!
死去,睡去……
但在睡眠中可能有夢,啊,這就是個阻礙:
當我們擺脫了此垂死之皮囊,
在死之長眠中會有何夢來臨?
它令我們躊躇,
使我們心甘情願地承受長年之災,
否則誰肯容忍人間之百般折磨,
如暴君之政、驕者之傲、失戀之痛、法章之慢、貪官之侮、或庸民之辱,
假如他能簡單的一刃了之?
還有誰會肯去做牛做馬,終生疲於操勞,
默默的忍受其苦其難,而不遠走高飛,飄於渺茫之境,
倘若他不是因恐懼身後之事而使他猶豫不前?
此境乃無人知曉之邦,自古無返者。
莎士比亞繼續寫道:
誰願意負著這樣的重擔,在煩勞的生命的壓迫下呻吟流汗,倘不是因為懼怕不可知的死後,懼怕那從來不曾有一個旅人回來過的神秘之國,是它迷惑了我們的意志,使我們寧願忍受目前的磨折,不敢向我們所不知道的痛苦飛去?這樣,重重的顧慮使我們全變成了懦夫,決心的赤熱光彩,被審慎的思維蓋上了一層灰色,偉大的事業在這一種考慮之下,也會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動的意義。
電影《美夢成真》中的男主角Chris,在面對自己心愛的小狗死亡的時候,心中萌生了恐懼、不捨的情緒。在自己的完全意識中面對自己的死亡時,Chris更是坦白地承認自己面對死亡時的恐懼,恐懼自己的消失(disappear)。
存在主義心理治療家歐文D.亞隆在他的《直視驕陽》中記載了一位死亡恐懼病人的詩,表達了我們人類對死亡的深深恐懼和無奈:
死亡,四處彌散
它攫取著、推搡著、啃噬著我
無處可逃
我只能
痛苦地尖叫
瘋狂地哀嚎
死亡,在每一天裡若隱若現
我試著留下走過的足跡
興許這會有點用
我竭盡全力做到
全然活在每個當下
但死亡潛伏在黑暗之中
我所追尋的
這令人舒適的保護傘
如同包裹孩子的毛毯
在寂靜的寒夜裡
當恐懼來襲
它們就這樣完全被浸透
那時
將不再有我的存在
不再有一個我
能自然呼吸
能改過自新
能感受甜蜜的悲傷
而這難以忍受的喪失
竟無聲無息的逼近
死亡本來什麼也不是
死亡卻成了一切
三、自由與限制
沙特曾說過,人類是註定要受自由之苦的。亨利克.易卜生提出,自由是「我們最美好的財富」。科梅佳強調說,失去自由的代價要比人們所覺察到的大得多。他聲稱,因為自由是「一種進步的需要和一種生存的需要」。如果我們失去了我們的內在自由,我們就隨之失去自我方向和自主性,而這些正是把人類與機器人和電腦區分開來的特質。羅洛.梅甚至把自由作為心理治療目的:
心理治療的目的是使人獲得自由。盡可能地使人免除症狀,無論是像潰瘍這樣的生理症狀還是像嚴重羞怯這種心理症狀。要盡可能地使人免除成為工作狂的強迫行為,免除他們從兒童早期就習得的習慣性無助行為,或沒完沒了地選擇異性伴侶,而這些異性伴侶會引起持續的不快和持續的懲罰。
電影《逍遙騎士》中的兩個主角為了逃避麻木的生活,逃避看似自由實則處處受阻的現實,逃避虛偽的「衛道士」們敵意的側目,尋找夢想的自由。他們天真快樂地上路,伴隨著輕快的西部音樂,彷彿生命如風般美好而清新,卻被二流的汽車旅館拒之門外,露宿荒野,在夕陽無限美景之餘,一再地看到人類淒慘破敗的景象;他們虔誠地祈禱,以為信念真的可以將沙土變成穀糧,生活真的可以無拘無束地快樂,男女之間真的可以心無芥蒂的單純快樂;他們在遊行狂歡的隊伍後面隨性地張揚,卻被無理地抓進了牢獄;他們以大麻、酒精和迷幻藥來釋放對現實的不解,拯救對生活的希望。然而,主角Waytt反覆地對夥伴Billy說:「我們把一切都搞砸了」(We blew it.)。最後,這些無害而善良的人們被生活中那些所謂「正直」的「君子們」以道德的名義殺害。
電影《楚門的世界》也描寫了追求自由的不容易。楚門想去斐濟時,所感到的是來自工作、母親、妻子、朋友以及從小就被強加的思想(水的恐懼、飛機的不安全)等各方面的壓力。於是,他想追尋夢想的自由一次次被扼殺。最後,在自己的堅持下,他達到了「自由」的狀態,下面是楚門與創造者的對白:
楚門:你是誰?
創造者:我是創造者,創造了一個受萬眾歡迎的電視節目。
楚門:那麼,我是誰?
創造者:你就是那個節目的明星。
楚門:什麼都是假的?
創造者:你是真的,所以才有那麼多人看你……聽我的忠告,外面的世界跟我給你的世界一樣的虛假,一樣的謊言,一樣的欺詐。但在我的世界你什麼也不用怕,我比你更清楚你自己。
楚門:你無法在我的腦子裡裝攝影機。
創造者:你害怕,所以你不能走,楚門不要緊,我明白。我看了你的一生,你出生時我在看你;你學走路時,我在看你;你入學,我在看你;還有你掉第一顆牙齒那一幕。你不能離開,楚門你屬於這裡,跟我一起吧。……回答我,說句話……說話!你上了電視,正在向全世界轉播。
楚門:假如再也碰不到你……祝你早安、午安、晚安……
歐文D.亞隆對「存在」意義上的「自由與限制」困境的論述更為精闢:
有史以來,人類不是一直在渴望自由並為之奮鬥嗎?然而從終極層面來看,自由是與憂懼偶聯在一起的。在存在的意義上,「自由」意味著外部結構的空白。與日常經驗相反的是,人類並不是進入(和離開)一個擁有內在設計、高度結構化的宇宙。實際上,個體對他自己的世界、生活設計、選擇以及行為負有全部責任——也就是說,個體是自己世界的創造者。「自由」在這種含義上,帶有一種可怕的暗示:它意味著在我們所站立的地方並不堅實——什麼都沒有,是空的,無底深淵。
四、孤獨
人是群居的動物,天生害怕孤獨。沙特提出:「孤獨是人類處境的基本特徵,個體需要創造生活中的意義,而又覺察自己孤身置於宇宙,覺察到那種空虛,孤獨感就會在這種衝突之中。」可見,孤獨感是個體內心生活的一種本質。
這種孤獨不同於伴隨著寂寞的人際性孤獨,而是一種根本性孤獨。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獨自一人進入世界,同時也必然獨自一人離開。無論我們之間的關係變得多麼親密,仍然會存在一條無法逾越的鴻溝。這樣就會出現:一方面是我們對自身絕對孤獨的意識,另一方面是對接觸、被保護以及成為更大整體一部分的渴望。這兩方面的張力就構成了存有衝突。正如紅樓夢中的《好了歌》所示: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上都曉神仙好,只有嬌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子孫誰見了?
從生物進化角度看,低分子物質、高分子物質向單細胞生物的進化,成就的就是一種偉大的孤獨。細胞膜的出現,為個體與外界的隔離創造了條件。也就是說,孤獨根植於人類的集體潛意識,從進化的初始就已成定局。F.卡夫卡在《城堡》中對此進行了精彩的描繪:
我知道,與偌大的宇宙相比,我們太微不足道了,我知道我們什麼也不是;在如此浩大的宇宙中,似乎沒有任何東西在某種程度上既能淹沒人又能使人重新獲得信心。那些計算,那些人無法理解的力量,是完全不可抗拒的。那麼,究竟有沒有我們可依賴的東西?我們雖然已陷入幻想的泥潭中,但其中尚有一樣真實的東西,那便是愛。此外什麼都沒有,完全是空。我們跌入了一個巨大的黑暗迷宮,我們怕極了。
莎士比亞在《李爾王》中深入地刻畫了存有孤獨問題。在這部戲的開頭,李爾王需要把女兒柯蒂利亞嫁給某位來自歐洲的王子(顯然是勃艮第公爵),因為她已經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他已經把兩個女兒嫁了出去,而柯蒂利亞是他最後一個,也是最珍愛的女兒,是他的歡樂所在。他不想把她嫁出去。對他來說,失去柯蒂利亞就意味著失去一切,這是他活著的理由。為了破壞這門婚事,他謀劃了一個計策,即愛的測試。結果,他自食其果,國土全分給了大女兒和二女兒,柯蒂利亞沒分到一寸土地而遠嫁他鄉,而另兩個女兒原形畢露,迫害自己,這是何等的孤獨啊!
電影《心的方向》也刻畫了一種深層次的孤獨和掙扎:
六十六歲的華倫.施密特退休後無所事事,只能靠看電視打發時間。他來到曾經就職的公司,希望找到一些過去的影子,卻碰了一鼻子灰。
妻子海倫與他在吵吵鬧鬧中共同生活了四十二年,人到老年,施密特對她越來越厭煩,經常半夜醒來問自己睡在旁邊的人是誰。不久,妻子撒手病逝。當施密特感到孤獨,開始懷念海倫時,他突然發現妻子竟與自己的好友有染,而且一直保留著好友的情書。
女兒珍妮是施密特的最愛,也一直是他的精神安慰。眼看她的婚禮越來越近,施密特驅車趕往丹佛,準備為女兒的婚禮籌備做些什麼。途中打電話給珍妮,卻遭到拒絕。他不得不開著車四處遊蕩,靠尋找曾經生活和學習的地方消磨日子。婚禮臨近,施密特住在親家母家裡,但他看不上親家一家人,更看不上珍妮的未婚夫蘭德爾。於是,施密特希望珍妮能取消這場婚禮,遭到女兒的強烈反對,兩人險些反目為仇。最後,施密特不得不言不由衷地在珍妮的婚禮上講話,並出資讓小倆口外出度蜜月。
施密特決定改變生活,他開著自己的露營車長途跋涉。然而,外在的美景無法平抑內心的痛苦,無法滿足內心的需求,他依然是孤獨、忿怨的。
施密特在電視上看到一檔名為「救救孩子」的公益節目,並每個月捐出二十二美元資助一個名叫恩杜戈的坦尚尼亞六歲男孩。於是,寫信給恩杜戈成了他唯一與外界溝通的方式。他不停地、不求回信地給恩杜戈寫信,講述他的生活以及沒有人想聽的感受。
最後,回到家中的施密特收到了恩杜戈的來信,這個只有六歲的男孩不會寫字,他托修女代筆,還寄了一幅自己的畫給施密特,畫著兩個手牽手的人,一個大,一個小。面對這幅畫,施密特流下了兩行濁淚。
五、無意義
因為我們孤獨地來到世界,我們必須構建自己的世界,我們最終孤獨地離開世界。因此,從存在角度說,生命是無意義的。正如電影《七宗罪》中所說:「人是可笑的傀儡,在破舞臺上起舞,以跳舞、做愛為樂,完全不關心世界,不瞭解自己毫無價值,人並非為此而生。」莎士比亞在《馬克白》中也提出:「人生不過是一個行走的影子,一個在舞臺上比手劃腳的笨拙的可憐人,登場片刻,便在無聲無息中悄然退去,這是一個愚人所講的故事,充滿了喧嘩和騷動,卻一無所指。」
那麼,我們為什麼要活著?我們又應該如何活著呢?如果並不存在為我們預先設計的生命藍圖,我們每個人就必須自己去構建自己生命的意義。正如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中提出:「一個人要是把生活的幸福和目的,只看作吃吃睡睡,他還算是個什麼東西?不過是一頭畜生!上帝創造我們,使我們能夠這樣高談闊論,瞻前顧後,當然要我們利用他賦予我們的這一種能力和靈明的理智,不讓它們白白浪費。」電影《鬥陣俱樂部》描述了主角為了逃避無意義、空虛的痛苦而做的種種努力。下文是電影中泰勒演講的內容,精準地描述了人類「尋找意義與宇宙本身無意義」的存有衝突現狀:
來這裡的人都是聰明的人
只是你們的潛力都被浪費了
只做替人加油,或是端盤子、打領帶的工作
廣告誘惑我們買車子,買衣服
於是拼命工作買我們不需要的狗屎
我們是被歷史遺忘的一代
沒有目的,沒有地位
沒有大戰爭,沒有經濟大恐慌
我們的大戰是是心靈之戰
我們的恐慌只是我們的生活
我們從小看電視
希望有一天會成為
富翁、明星、搖滾巨星
但是,我們不會
那是我們漸漸面對的現實
所以我們非常憤怒
在一個平庸的時代裡
沒有動盪與變革來證明自己的出眾才智
缺乏精神領袖而喪失靈魂皈依的原動力
我們都在麻木地飾演自己的社會角色
忠誠地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
事實上大多數人都無法理解自己奮鬥的目標究竟是什麼
上學,工作,戀愛,結婚,生子,生老病死
一切都按部就班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做自己的旁觀者:用禪的智慧自我療癒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90 |
健康醫療 |
二手書 |
$ 260 |
二手中文書 |
$ 266 |
中文書 |
$ 266 |
心理治療 |
$ 300 |
📌宗教79折起 |
$ 334 |
Psychological & Relationships |
$ 342 |
禪修 |
$ 342 |
醫療保健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做自己的旁觀者:用禪的智慧自我療癒
「人,是向死存有的」-馬丁˙海德格 德國哲學家 當人意識到自己終將一死時,就會深刻反思自己生命的意義。
生命是一場冒險的旅行,如果我們想要「療癒生命」,就必須深入人的「存有」困境。
人在面對「存有」困境時,常把權力、奮進、時尚、合群、疾病等當成藉口,藉此麻痺自己的軀體與心靈的感受,使自己免受直面「存有」困境的痛苦。
本書作者根據多年臨床經驗,對生命旅程中的「存有」困境進行分析及論證
提供讀者看待生命的另一種方向,讓讀者能夠
認識自己
接納死亡
理解自由與限制
擁抱孤獨和無意義
成為自己生命的旁觀者,遠離內心的焦慮和不安,讓心靈獲得真正的平靜。
作者簡介:
包祖曉醫學博士、副主任醫師。現任台州醫院精神科主任。長期從事精神疾病與身心疾病的臨床與基礎研究。擅長運用禪學理念與方法治療各種精神官能症即身心疾病。著有禪修三部曲:
首部曲《與自己和解:包祖曉醫師教你換位思考,重新擁抱自己,找回身心靈的平靜與健康》(大都會文化出版)與《喚醒身體的自癒力:用禪的智慧幫你找回相中的平靜》(大都會文化出版)。
並獲中國教育部、教育部、醫藥衛生科技、國家發明專利等多項獎項。
章節試閱
第一章生命旅程中的「存有」困境
我在哪裡?我是誰?
我怎麼會在這兒?
這個叫「世界」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我是怎麼來到這世界上的?
為什麼沒有人先問過我的意思?
如果我是被迫參加演出的,
導演在哪兒?我要見他。
——齊克果
生命旅程的實相
我們的本質就像夢的本質一樣,我們短促的一生不過是一場睡眠。
——莎士比亞
齊克果提出:「我們從來不曾擁有自由」。從存在主義哲學的角度看,這一觀點無疑是正確的。因為,我們的「存在」帶著一種被遺棄感:我們不能選擇什麼時候來到這個世界上,不能選擇出生的人種、國籍和家庭...
我在哪裡?我是誰?
我怎麼會在這兒?
這個叫「世界」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我是怎麼來到這世界上的?
為什麼沒有人先問過我的意思?
如果我是被迫參加演出的,
導演在哪兒?我要見他。
——齊克果
生命旅程的實相
我們的本質就像夢的本質一樣,我們短促的一生不過是一場睡眠。
——莎士比亞
齊克果提出:「我們從來不曾擁有自由」。從存在主義哲學的角度看,這一觀點無疑是正確的。因為,我們的「存在」帶著一種被遺棄感:我們不能選擇什麼時候來到這個世界上,不能選擇出生的人種、國籍和家庭...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我們生活在一個艱難的時代,本以為科學和技術的進步會帶來安逸、舒適和幸福,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簡單。我們的經濟建立在持續發展和擴張的基礎之上;我們最大限度地開採使用可以獲取的各種資源;我們擁有越來越多的個人財產和可供消費的商品,以及無數可供炫耀的技術成果。但是,我們仍然未能達到那種永久快樂的狀態,而且很可能今後也無法享受到這種幸福和快樂。即使我們在某一天體驗到了快樂和幸福,但就在第二天,我們又會認識到,我們的絕望和自我挫敗感沒有減少的傾向。
生命是一場冒險旅程,無論是專注於出人頭地、拼命地積累物質財...
生命是一場冒險旅程,無論是專注於出人頭地、拼命地積累物質財...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一章 生命旅程中的「存有」困境
生命旅程的實相
生命旅程中主要的「存有」困境
第二章 解決生命「存有」困境的錯誤處理方法
我們是「娛樂至死的生物」嗎
解決「存有」痛苦的錯誤方式
第三章 「存有」痛苦與疾病
誰是健康/正常人呢
「存有」痛苦與心理疾患
「存有」痛苦與軀體疾病
第四章 禪學對生命「存有」困境的認識
人生本苦
「存有」困境是逃避不了的
「我」並不存在
「我」是一種「存有」體驗
第五章 現代心理療愈系統中的禪學智慧
行為主義治療中的禪學智慧
精神分析/分析心理學中的禪學智慧
存在主義...
生命旅程的實相
生命旅程中主要的「存有」困境
第二章 解決生命「存有」困境的錯誤處理方法
我們是「娛樂至死的生物」嗎
解決「存有」痛苦的錯誤方式
第三章 「存有」痛苦與疾病
誰是健康/正常人呢
「存有」痛苦與心理疾患
「存有」痛苦與軀體疾病
第四章 禪學對生命「存有」困境的認識
人生本苦
「存有」困境是逃避不了的
「我」並不存在
「我」是一種「存有」體驗
第五章 現代心理療愈系統中的禪學智慧
行為主義治療中的禪學智慧
精神分析/分析心理學中的禪學智慧
存在主義...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