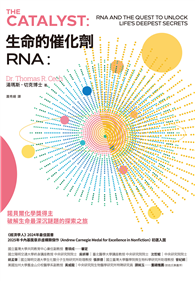恐龍如何學習貓的靈敏?
--九二一新校園重建的關鍵政策
林盛豐/監察委員、前九二一重建推動委員會副執行長
九二一大地震,地方政府包括縣市政府及鄉鎮公所權責範圍內的辦公廳舍及國中小學大量震毀。災區校園全倒者有二九三所,學生人數合計三萬四千人,此次地震若發生在白天上課時間,將會有多少傷亡?長期以來的草率規劃、草率設計、低價搶標、缺乏專業,潛藏了這麼一個可能導致數萬學童喪命的危機。幸運的是,地震來的時候,學生不在教室裡!
產生低品質教室的機制
到底是那些原因導致大量低品質的教室不斷產生?而任何試圖突破的提案,不但馬上被各級行政官僚的反對意見淹沒,甚至以將被檢調起訴為由而堅決反對呢?主要有以下四點原因:
一、人口成長無法預測,教室零星增建。
二、教室興建預算低單價。
三、好建築師不參與公共工程,各校零散新增的教室、預算少、設計費僅數萬元,結果只能草草設計。
四、低價設計,又低價搶標。當時各級政府的行政官僚,都認為公共工程招標,價格標是原則,合理標是例外。各縣市政府常依設計費給付相關規定打八折以示節約,所以設計監造費偏低,工程發包則又以最低價標為之,偷工減料在所難免。
零散成長的校園由設計費極低的建築師草草設計,而營造廠一開始低價搶標,後續必須偷工減料才能有利潤,大量低品質的教室就這樣被製造出來。其實地方政府其他公共設施的生產過程大同小異,包括各種辦公空間、警察局,消防隊的廳舍等等,也在這次地震中大量被震毀。
新校園運動的三大突破
九二一震災之後,重建會與教育部,針對上述公共建築生產流程的嚴重缺失,提出三大對策,以確保重建的新校園,能有最高的設計與施工品質。
三大對策如下:
一、營建管理顧問( PCM)之進用
各級政府之行政人員面對各種建築、營建工程,缺乏規劃、建築設計、遴選建築師、發包、監工的經驗,再多的行政人員開會,也不會做出正確的技術決定,所以PCM之引進絕對是必要的。
二、優良建築師遴選
或許有人認為公共工程都依據採購法公開遴選,選出來的建築師當然是優良建築師。其實採購法的公平、公開精神,還必須用心運用才會有正面效果。首先,建築師的設計條件,包括設計費、監工成本、設計時間是否合理?(沒人敢給予優厚的條件,一定要給最低的條件常常是承辦人員的共識)設計方案是否有理想性?評審是否具有公信力及專業良知?
這次教育部的建築師遴選,提出新校園運動的進步宗旨,確保了合理的設計費,遴聘了一批極為專業的評審委員,終於帶動了國內一流設計好手熱烈參與競圖。
三、採用最有利標
最有利標的精神,是廠商得以最佳方式,達成甲方所提之要求,其方式由乙方提出,而由甲方依先定之遊戲規則判定對甲方最有利者得標。
以往普遍被採用之最低價標,表示甲方最關心的是價格。創意及品質由建築師之設計監造確保,工期則由契約確保。但真實的結果常常是草草設計,所以施工時常需要修正,造價一再追加,工期也延後。這次校園重建對施工及結構安全與限期完工的諸多要求,完全無法冒低價搶標的風險。負責設計新校園的建築師,一致強烈要求以最有利標的方式招標,在諸多前置作業及折衝之後,終於獲得此一突破。
九二一重建委員會的角色
九二一重建委員會在所有重建工作中的角色都是一樣的,就是目標管理,進度控管,以及與各部會和各級政府重建行政之統籌與協調。九二一災後的校園重建讓教育部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國中小學全倒數量龐大,而且又是縣市政府的地方自治工作項目,假使只是政策指導,地方政府則早已超荷。但是若實質介入,教育部的行政、專業人才,卻又無法應付此一局面,
教育部之直接介入執行校園重建,發生雖介入而無法負責之局面(如學校之行政體系,仍要逐級蓋章,學校覺得無權有責,議論紛紛)。教育部提出的三大突破雖然解決不少難題,但是任何突破必有大量的配套作業等待處理。以最有利標為例,對教育部內部及負責PCM之營建署發包業務之同仁而言,均屬第一次承辦之業務,因此承辦人員特別謹慎,公文來往反覆,難以決斷,就產生了大量的工作量。
九二一重建委員會發揮了一個功能,就是以支援教育部新校園運動的理念為前提,儘量壓縮所有相關行政流程的時間,密集開會,解決第一線同仁之溝通、責任分工與責任承擔的問題。關鍵決策人員密集開會,當然解決了不少問題,至少教育部的三大突破,得以不在強大的行政慣性中胎死腹中。這些協商自法律釋疑、責任分工、預算分配、各項前置作業時程管控,各式危機處理,千頭萬緒。
校園重建涉及公共工程委員會對工程項目及預算之核定、採購法之解釋,主計處之預算核撥、兩個PCM,亞新工程顧問及內政部營建署對其PCM工作之範圍認定,及營建署PCM對最有利標之操作,七、八個縣市政府、上百個校長、建築師、營造廠以及建管、土地問題、防災技術問題等等之協商、釐清。其問題之繁雜,如何化繁為簡,是每個參與者的挑戰。重建委員會作為教育部的後盾,全力以赴,扮演了一個協商平台的角色,有效縮短了行政的流程。
校園重建起步晚,卻是重建品質最高的公共建設
教育部推動新校園運動,就像一隻恐龍想要學習一隻貓的靈敏。這一次校園重建,政府與民間均共同參與,好像是一場比賽。
民間如慈濟這樣的組織,其決策流程如下:
決定認養學校→尋找一流建築師→規劃設計→籌款→尋找一流營造廠→發包施工
目標明確,動作迅速,就是要最好的建築師、最好的營造廠、最短的工期。
但是教育部的動作如下:
彙總災校全部資料→公共工程委員會現勘及報核各校災損預算→行政院核定→依採購法遴選PCM→各校彙總所有設計背景資料提出建築計畫→遴選建築師→確認建築設計→遴選營廠→發包→施工
整個流程比起民間協助重建的流程,繁瑣不知多少倍。
政府部門擔心的是各項相關程序是否完備?預算是否浮濫?是否符合採購法等等問題,沒人關心建築師好不好、營造廠好不好、只要「依法」即可。而輿論最在意的工期,卻是政府最無可奈何的,因為無一程序可免。
教育部的動作,涉及所有學校資料的彙總、核定以及三次採購(PCM、建築師與營造廠),三次採購都是新經驗,這麼繁雜的流程,進度晚了民間整整六個月。恐龍無論如何也無法與貓比敏捷,如何讓恐龍瘦身成為貓,是我國行政革新的大課題,整個政府的形象,在這段期問,因此而備受責難。
可喜的是新校園運動的諸多理念與創新作為,在紛紛擾擾後終於以亮麗成果呈現在國人眼前。教育部負責的新校園無論在進步的理念,創意、設計及施工品質,沒有輸給民間認養的校園。而能有這些成績,是因為對三大政策突破的堅持,這些校園就像地震後盛開的花朵,在許多偏遠的地區,給人意外的驚喜。
這些新校園代表大人給災區小孩應有的關愛,代表新一代建築師與教育改革者理念的落實。許多規劃良好的校園空間,因為在規劃過程中的社區的參與,落成後成為社區活動中心,而且也成為新的觀光點。
這一批校園絕對是九二一災後重建中最大量、最具標竿意義的公共建築,而當時參與校園重建的年輕建築師,成立了建改社。建改社對政府的相關立法、政策長期以來積極提出針砭,大幅提升政府營建技術官僚與建築專業的正向溝通。他們長期持續的參與公共工程,關心相關公共政策,是推動台灣建築專業提升的一股重要力量。
尺度院落與大樹場所
--九二一校園後記
王維仁/香港大學建築系教授、王維仁建築研究室主持人
二十年前的九二一校園設計,不但是台灣教育空間改革的重要運動,更代表一個世代的建築師們社會與社區意識的建築思潮,同時也是我個人設計思想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在我參與的光隆、福民與中坑三個小學的設計過程中,除了災後重建的社會與社區語境,更因為災後重建組織單位的人文價值,與校長老師家長們的信任,我們的設計團隊能夠突破學校制式教室與操場排列的一貫模式,對重建的校園共同思考探討了四個重要的建築議題:場所、大樹、尺度、院落。
大樹的場所
學校起始於一個坐在大樹下的人,和圍繞的人分享他得道的理解;他還沒有意識到自己是老師,而他們也不知道自己是學生。
--路易斯.康(Louis Kahn)
路易斯康關於「學校起始於一棵大樹」的名句,是闡述一種未被制度化的知識傳授狀態。大樹成為場所的隱喻,不但是知識傳授的空間背景,也是佛祖菩提樹下得道講經的場景轉化。
記得我們走進災後斷瓦殘壁的中坑小學,第一眼看到四棵蒼天大樹和它們圍合成的校園。至今清楚記得村子裡的小孩騎著單車繞著大樹,一圈又一圈。遠處山坡青綠的檳榔樹林,小孩的嬉戲聲背後,夾雜著夏末無盡的蟬鳴。這樣的場景讓我們覺得,大樹和教室,場地和遠山,應該是我們要保存的永續校園。更寬廣的來看,我們成長過程的學校幾乎都有幾棵大樹,每個人的學校大樹都是他樹下嬉戲或者爬樹的經驗,無論在校門口或操場一角,都成為他們校園場所記憶裡不可分割的場景。
墨西哥建築師巴拉幹(L. Barragan)對建築的場所環境,有過一段現象學式生動的文字描述:
我最早的童年回憶是關於村子附近的農場……,這個村子的供水是由挖空的大圓木以落水管的形式接通,滴水在樹岔構成的支撐結構上,水道橋穿過城市,到達住宅內院,再用石造的大水池來接水。街道上有繫馬的鐵環,覆上苔蘚的挖空圓木,當然:滴水流過全城……,那裡沒有攝影師,我祇是留在記憶裡。
巴拉幹這一段用來詮釋其渾厚地域風格建築的文字,也許可以讓我們對「參與設計」提供另一個註腳,最深層的參與,來自對基地及生活敏銳而深刻的體驗。工作坊與說明會是使用者參與的手段但不是目的,正如「模式語言不能保證達到建築的永恆品質」(Timeless Way of Building)一樣。建築在基地上提供的舞台不只是用來滿足代言人的使用需求,更是未來一代又一代學生的生活場景,我們要的參與是像巴拉幹一樣的投入,一種建築對地點,人與生活的承諾。
當時九二一新校園重建倡導的參與式設計,讓我們和校長老師們建立起一種必須對等的夥伴關係。對我來說這些溝通說明是設計過程必然的一部分,但更重要的,是建築師對場地和人的觀察互動、感受與體驗。在中坑和福民這兩所偏遠山區的小學校,因為有尺度的校園和互動的社區,更因為學校鮮明的場所感,特別是建築倒塌後留下來的大樹和地景,成為更深刻的地景記憶與設計的出發點。
尺度的院落
適當的尺度應該受同時大也是小,是多也是少,是遠也是近,簡單而又複雜,開放而又封閉;並且它永遠會同時是部分也是整體,既統一而且多樣。
--阿多.范艾克(Aldo Van Eyck)
在二十世紀現代主義發展的高峰期,面對無可避免的大尺度城市或學校環境,荷蘭十人組(Team Ten)建築師阿多.范艾克是少數能對當時的簡化功能主義提出批判反省的建築思想家。他的作品包括學校、孤兒院和住宅,都表現出理性主義的思考中流露的人性與親切,在一種清晰的秩序下,展現出各部分構成的多樣性的整體。
范艾克一生的創作與教學都致力發展一種有尺度而人性的現代建築。大尺度的建築如住宅或學校應該可以形成一個系統,利用一個或多個基本模組,組合而成為一個集合的形式,其個別單元的認同感,在這樣的整合中反而得到了強化,小的尺度因為大的整體而彰顯其存在。在這樣的集合形式中,小尺度與大尺度之間交互作用的(gears of reciprocity)就是范艾克所說的系統層級。
面對光隆小學這樣五十個班級的大學校和完整的校地,除了配置一或兩排南北排列的四層教室大樓,我們還能夠如何建立一種系統的、適合小孩成長學習的小尺度單元?從光隆小學開始,四合院尺度和序列的組合系統,逐漸的發展成為我的一種型態設計方法。幾個教室圍合成一個教室尺度的開發院落和一棵共享的大樹,成為我們對未來學校空間的願景。
當我們無可避免的面對大尺度的學校環境,如何做到「或小或大」、「簡單而又複雜」、「開放而又封閉」、「部分也是整體」的系統與環境肌理?我們分析傳統城市建築肌理(Fabric)或者型態(Type)的方法,包括四合院的建築肌理與院落型態,除了幫助我界定與發展基本單元型態,更進而成為一種創造性的設計方法,讓傳統聚落的有機性與生命力,組合成為更大的建築整體。
光隆的院落系統
一般大型中小學的設計,多半是一種以四至六層樓的長條或圍合建築體排列,和戶外場地組合形成的空間形式。我們希望在光隆小學突破這種傳統配置,把集中式的大空地分散成每班級各自擁有的戶外空間與穿廊,以不超過兩層樓高的教室交錯安排,使每一間教室外都屬於一個合院和一棵大樹,一樓的教室外是庭院與大樹的樹幹,二樓則有平台花園與大樹的葉梢,小朋友走出教室就是自己的庭院,大樹,平台,沙坑,穿廊。學校的三個主要的教室區與院落如網絡般的穿插連結。
在光隆國小設計的初期,四周是環境多元住宅與產業混合的社區,我們感覺設計構想不容易由周邊環境入手,必需源自由內部形成的空間邏輯。我們絞盡腦汁想,如何讓一個五十個班級的大學校,每一個班級都擁有自己的小院落,大樹與戶外空間。小學生由教室到中庭再到廣場的空間關係,有如城市由住宅到合院再到廣場的經驗,每個合院教室之間半戶外的穿廊,是雨天的戶外活動空間,而每個合院的鳳凰木或蓮霧,每個平台園圃的蔬菜玉米,也都成為每個院落空間的認同特色。
設計期間也是李安的〈臥虎藏龍〉放映的檔期,俠客們在四合院胡同之間穿梭追逐的視覺滿足,我想像著學校應該有這樣豐富複雜的空間關係,小朋友們能在合院,穿廊與廣場穿梭來往,探索成長,而個個都是「臥虎藏龍」。設計完成十八年之後的一個週末,我再度回到學校,小樹已經長成了大樹,每個院子的樹木菜園不相同,冬天的陽光安靜的穿過一個個院落,教室牆上的繪畫和偶爾出現水桶拖把或課桌椅,暗示了教室、穿廊和院子之間生活學習的場景。我的心情由期待和些微的緊張,到鬆了一口氣後的滿足和開心,我知道這些院子現在到處都是臥虎藏龍了。
我們對建築師有什麼期望?我們不期望的是一棟量體巨大而有壓迫感的建築將孩子與外在世界隔絕開來。正相反的是,我們要一個親切,開放的家,這個有趣而外向的形式和整齊而比例適切的內部安排,會給住在其中的小朋友一個安全而溫暖的家。沒有機會讓孩童在其中迷失的無盡的走廊和門道,取而代之的是連繫各種生活與休閒活動的串聯空間,這樣串聯絲毫不會打斷這個居住社群生活的連續性。縱使這個建築有各種不同的構件部分,其最高層次的建築秩序會將各部分統一起來,使各個構件最終形成一個有生命力的生活整體。
--阿多.范艾克(Aldo Van Eyck)
福民和中坑的大樹
第一次我們拿著福民小學給我們的基地圖,走在瓦礫滿地的校園,建築物沒有了,剩下一棵棵大大小小的樹木。圖紙上密密麻麻的,精確的標明了每一棵大小樹木的位置和學名,是劉總務主任在地震後逐一標記在圖上給建築師用的,謝校長詳細的敘述這幾棵櫻桃樹的年分與開花季節。我深刻的體會到,林區《基地計畫》(Site Planning)的教科書裡對場所、社群、生態與感覺形式的交錯敘述)。這裡的每一個環境物件:升旗台魚池,鞦韆滑梯,還有每一棵樹木物種,和人與事件,都是他們有意義的生活與生態的整體。
我在草圖上無意識的畫著建築物的可能位置時,線條不知不覺的就避開了這一些大大小小的樹木,我們的建築物在平面圖上的曲折不是因為解構或數位,是因為建築物繞樹而行。因為建築物與大樹共舞,我們沒有太多意識的幾何形式沉迷,最後的建築線條變成在樹木之間遊走:穿廊開圓洞給大樹,餐廳開天井給櫻桃樹,廊道的木地板延伸到大王椰樹幹上,小朋友就脫掉鞋子一路從教室走到樹下……不砍去任何一棵樹就成了支配設計最重要的力量。
我們儘量保留了福民和中坑學校的大樹和小樹,不只是因為生態保育,更因為村民們的集體記憶。無論是福民或者中坑,我們不需要景觀建築師的植栽計畫,因為建築空間就是植栽計畫,因為大樹與建築共舞,超越綠化的指標成為建築地景,與地景建築的敘事空間。
保育大樹不只是一種生態意識,和歷史建築一樣,它們是環境記憶與地景場所的必然。之後我們面對校園的建築設計,無論是香港、深圳東莞,或四川江西,只要是校園裡大一些的樹,我都希望成為新建築的一個整體,讓建築以圍合或者退讓的方式保育大樹。業主和施工單位甚至景觀建築師,常會說這些樹價值不高不如換棵好樹。令我困惑的是樹和人一樣哪有必然好壞?長一棵大樹要二十年是多少小孩的等待?
幾乎每個學校在建築之後,都會配合校園的配置植樹綠化。幾十年下來小樹變成大樹,伴隨著小孩的學習成長,大樹成為幾個世代的校園集體記憶,成為校園建築原型不可分割的整體。在中坑和福民的設計中,我們反過來在地震後,以《后建築》的大樹,作為新建築的起點,成為我日後建築設計裡重要信念。
學校的舞台與道具
中坑國小的想法源自對後園中四棵苦楝樹的敘事化的詮釋;福民國小則希望保留山林間的一花一木,讓建築在樹木與環境物件的意義中穿梭。面對地點如此明晰的基地,設計的想法是感知的,現象學式的一體。而面對光隆國小的大尺度與新校的相對疏離,必須用一種空間策略和系統來形塑地點。之後我們香港嶺南大學社區學院、東莞台商學校和香港中文大學的深圳校園,都是透過這樣一種理性的系統,意圖達到一種人本的與可持續的校園空間。
十多年之後我回到當初設計的學校,欣見光隆國小一連串的院落生動如預期,加入了新生活的軌跡。除了小樹變成大樹,平台的花圃變成菜園。過度浪漫的親水池被改成木地板廣場,大樹邊的小盆池因為防蚊填平了,雖然有使用想像的落差,改變卻也讓空間更豐富了。最重要的是串連合院的系統,或者空間的織理關係,持續有力的掌握著場所的架構。中坑國小四棵大樹和繞著大樹踩單車的小孩依舊,而福民國小的想像使用就更真實了:小水池發展成的生態池,逐漸成長的遊戲區與穿廊下,漂流木做成的茶座。
新的使用痕跡持續的豐富建築的生命:我們只是在基地中架上舞台,配置院落與保育大樹,一代又一代的演員才真正要裝置道具,無論是老師、學生或社區,架換布景粉墨登場。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921地動綻開的花蕊的圖書 |
 |
921地動綻開的花蕊 作者:建築改革社 出版社:有方文化 出版日期:2019-09-17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28頁 / 14.8 x 21 x 1.64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52 |
社會工作 |
$ 252 |
中文書 |
$ 272 |
社會人文 |
$ 288 |
社會 |
$ 288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921地動綻開的花蕊
走過20年,從新校園運動到建改社
34位重量級建築師、學者、政府官員、媒體記者……
關於校園、教育、建築、社造與體制最深入完整的再思考
【建築改革社與新校園運動的起點】
他們是建築界最有行動力的一群人,
從建築、跨領域美學、教育議題、文化推廣,從地方到中央政策……
關注的是最困難、最核心、最源頭的事,
「為下一代年輕人」,是永遠不變的核心價值。
921大地震後,教育與建築意外的交集,
不只是校園重建,更是建改社社會參與的起步,
二十年後,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改革仍是永遠的進行式。
【為下一代年輕人,改革是永遠的進行式】
九二一新校園運動的重建過程,凝聚出臺灣校園建築與教育轉折的新起點,這股積極尋求創新與突破的能量,創造出支援教學需要,以使用者學習為根本的核心價值,並持續在教育工作現場傳遞溫度與智慧,跟上全球最新的變局。
PART1 在廢墟中綻放,「新校園運動」的偶然與必然
新校園運動開創的價值,不僅促使校園建築與環境外在形貌的改變,也是一種追求校園內溝通、對話,鼓勵創造和多元價值的轉變,成為全盤翻轉校園空間與教育內容之間,交互辯證新思維的歷史起點。
--范巽綠/教育部政務次長
PART2 改革是永遠的進行式,「新校園運動」的演化和挑戰
在快速變遷的社會中,校園需要有所變與不變。不該變的如歷史資產,校園絕對比其他機構更有責任率先保存;該變的則應勇敢承擔與開放,譬如發揮更積極的社區功能。
--曾旭正/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教授
PART3不只是建築改革,更是社會參與
請回到出發點!珍惜這整體社會力量賦予的時代意義和機會。人民的願望,城市的願景,到底是什麼?那些基本價值必須維繫?不再繼續資本開發的慣性思維!疏散解構,調養生機,以開放精神取代官僚治理。
--趙力行/未完成建築工作室負責人
Part 4建改精神的傳承
陳邁先生不多言詞,但最常講的一句話:「不忍心看到年輕人經歷他同樣的苦。」陳先生引導後繼者把其一生的志業化作為行動,把建築人心繫在一起,影響力前無古人,但他鼓舞後繼要有來者!
--徐岩奇/建築改革社社長
作者簡介:
建築改革社
緣起於921震災後教育部積極進行校園重建工作,由當時的次長范巽綠負責推動,受教育部的新校園理想感召熱烈參與。但面對僵化的法令及招標制度,熱情與能量很快的被非關設計的行政、採購因素磨耗殆盡。隨即自發性的成立了「新校園運動合作社」,研擬改革「建管」、「審議流程」、「招標制度」的方式;時任災後重建副執行長的林盛豐則從公部門施力協助。營建工程採「最有利標」方式,避免低價搶標即為我們當時的推動結果之一,開了類此採購方式的先河。
921後,這群朋友雖然回到了各自的崗位,發現在我們的建築環境裡待改革的事情還有許多;包括執業環境的桎梏、公部門對專業者的藐視心態、建築師公會的運作,以及建築教育及考試制度的偏差作為等,我們都認為是建構美好的執業環境的總體目標下,必須改革的對象。有鑑於上述的認知,我們在921後經過多年的醞釀,於2006年成立了「建築改革社」,2007年向內政部正式登記。第一屆社長為陳邁先生。
章節試閱
恐龍如何學習貓的靈敏?
--九二一新校園重建的關鍵政策
林盛豐/監察委員、前九二一重建推動委員會副執行長
九二一大地震,地方政府包括縣市政府及鄉鎮公所權責範圍內的辦公廳舍及國中小學大量震毀。災區校園全倒者有二九三所,學生人數合計三萬四千人,此次地震若發生在白天上課時間,將會有多少傷亡?長期以來的草率規劃、草率設計、低價搶標、缺乏專業,潛藏了這麼一個可能導致數萬學童喪命的危機。幸運的是,地震來的時候,學生不在教室裡!
產生低品質教室的機制
到底是那些原因導致大量低品質的教室不斷產生?而任何試圖突破...
--九二一新校園重建的關鍵政策
林盛豐/監察委員、前九二一重建推動委員會副執行長
九二一大地震,地方政府包括縣市政府及鄉鎮公所權責範圍內的辦公廳舍及國中小學大量震毀。災區校園全倒者有二九三所,學生人數合計三萬四千人,此次地震若發生在白天上課時間,將會有多少傷亡?長期以來的草率規劃、草率設計、低價搶標、缺乏專業,潛藏了這麼一個可能導致數萬學童喪命的危機。幸運的是,地震來的時候,學生不在教室裡!
產生低品質教室的機制
到底是那些原因導致大量低品質的教室不斷產生?而任何試圖突破...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前言
因九二一而凝聚的奉獻與力量
徐岩奇/建築改革社社長
關於這本書
今年適逢九二一二十週年,建改社出版《九二一地動綻開的花蕊》一書有特別的意義。正在籌劃出書的當下,原本陳邁先生預計要為出書寫序文,但是過程中他在進行化療,不久傳來陳邁先生過世的消息,各界哀痛不已!出書的架構內容也跟著變動,增加用以記錄陳先生與建改社關係與致敬文,其他仍然維持原計畫。本書的編輯區分成四塊:Part1為在廢墟中綻放,「新校園運動」的偶然與必然;Part2為改革是永遠的進行式,「新校園運動」的演化和挑戰;Part3為不只是建築改革,更...
因九二一而凝聚的奉獻與力量
徐岩奇/建築改革社社長
關於這本書
今年適逢九二一二十週年,建改社出版《九二一地動綻開的花蕊》一書有特別的意義。正在籌劃出書的當下,原本陳邁先生預計要為出書寫序文,但是過程中他在進行化療,不久傳來陳邁先生過世的消息,各界哀痛不已!出書的架構內容也跟著變動,增加用以記錄陳先生與建改社關係與致敬文,其他仍然維持原計畫。本書的編輯區分成四塊:Part1為在廢墟中綻放,「新校園運動」的偶然與必然;Part2為改革是永遠的進行式,「新校園運動」的演化和挑戰;Part3為不只是建築改革,更...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曾志朗/廢墟現美景,災難見智慧
序黃榮村/重建校園元年的開啟
序吳思瑤/九二一後,臺灣前進了多少?
序陳柏森/在荊棘中緩步前行,一條充滿使命感的改革之路
前言徐岩奇/因九二一而凝聚的奉獻與力量
PART1 在廢墟中綻放,「新校園運動」的偶然與必然
1.范巽綠/開啟新想像,打造未來世代的多樣化學習空間--「九二一新校園運動」的歷史意義與未來展望
2.林盛豐/恐龍如何學習貓的靈敏?--九二一新校園重建的關鍵政策
3.夏鑄九/廢墟上重新綻放的文化花朵--災後重建的反思與期望
4.王維仁 /尺度院落與大樹場所--九...
序黃榮村/重建校園元年的開啟
序吳思瑤/九二一後,臺灣前進了多少?
序陳柏森/在荊棘中緩步前行,一條充滿使命感的改革之路
前言徐岩奇/因九二一而凝聚的奉獻與力量
PART1 在廢墟中綻放,「新校園運動」的偶然與必然
1.范巽綠/開啟新想像,打造未來世代的多樣化學習空間--「九二一新校園運動」的歷史意義與未來展望
2.林盛豐/恐龍如何學習貓的靈敏?--九二一新校園重建的關鍵政策
3.夏鑄九/廢墟上重新綻放的文化花朵--災後重建的反思與期望
4.王維仁 /尺度院落與大樹場所--九...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