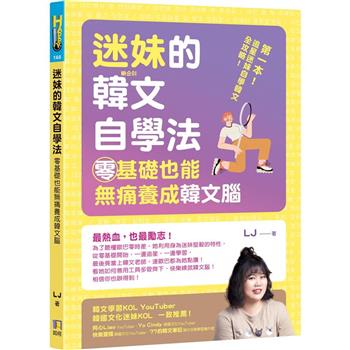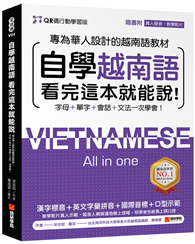推薦序
白心儀的大地孤雛
陳浩/新聞人.媒體顧問
又注意到白心儀的動物報導,是一天在臉書上看到一則長頸鹿流淚的畫面,東非肯亞的國家公園裡,一頭五公尺高的長頸鹿擋在車前求救,畫面上牠的脖子被鋼索勒纏,眼淚直流。
那是一個讓人震驚更不忍的畫面,記者白心儀通報巡邏員,帶著獸醫到處搜尋的巡邏隊,找了一個星期才救到這頭長頸鹿,該則報導經由超級傳播的臉書驚動了國際媒體,長頸鹿被盜獵濫殺的現象也引起世界關切。國際報導特別註明這則新聞的報導者是台灣東森電視台《地球的孤兒》節目主持人。
雖然是偶然捕捉到的畫面與事件,讓台灣的報導與世界連結,但背後卻是一位台灣記者數年不懈對地球瀕危動物的報導努力,她沒有西方動物節目的雄厚資源,卻一人兩槍(兩位攝影夥伴),獨自張羅經費,走南闖北、酷熱極寒:「我們每天早上像苦行軍,揹著裝備,全身爆汗,衣服都可以扭出水來,地獄應該就這麼熱吧!但這個紀錄很快就被打破。南美巴西的潘塔納爾濕地,比哥斯大黎加雨林更熱!平均四十六度,正午飆升至四十八度!我們搭乘無遮蔽的小船,穿梭在濕地流域,每天曝曬超過十二小時追美洲豹,還得忍受馬蠅的圍攻,那才真的是地獄。」
「下一站,我們轉往零下三十度的冰凍森林,溫差高達七十度……白雪覆蓋窩瓦河源頭顛簸難行的棕熊孤兒院。」
剛進電視台我就認識白心儀,除了一雙發亮的眼睛,怯生生嬌滴滴的樣子,我很難想像這些冒險犯難的傳奇動物報導,是她一手完成。其實,電視記者太容易被幹成一種永遠帶著虛假表情的行業,語言輕重失衡,為世事輕描浮誇情緒,很少有人能走出一條內裡帶點硬核的路。白心儀的《地球的孤兒》系列報導引起了我的注意。
《地球的孤兒》是一個優越的電視節目,但電視必須要有畫面,才能說好故事。追求畫面,就必須到現場第一線,拍攝瀕危動物,談何容易?
天涯海角,你必須先抵達,抵達「地獄」之後,你必須先等待。以樹懶來說,牠的每一個動作,是人類放慢十到十五倍的速度。牠一天消耗的熱量只有一百四十卡,超過就會致命,慢是牠的存活方式。研究團隊發現一直慢慢爬下樹排泄的樹懶,記者就得抓著沉重的器材飛奔,趕到現場又得花很長時間拍攝這隻極慢的生物被採集檢體、挑寄生蟲。
半夜接獲大雪山森林樣區有黑熊啟動陷阱的消息,就得集結入山、瘋狂趕路。要跟上研究團隊疾行的腳程,在濕滑陡峭的山區步步搏命,拍攝完黑熊捕捉繫放,黑夜裡再戴著照明頭燈攀岩滾爬著下山,一身是傷。拍攝石虎比拍黑熊還難,接觸到的石虎非死即傷。
拍攝犀牛大象北極熊、巨獺鯨豚美洲豹各種瀕危動物,「鏡頭不能眨眼」,但是鏡頭裡外,筆下都是傷心故事。
她拍冰雪裡的棕熊,看到被遺棄的幼熊「自己少女心大噴發,這是泰迪熊啊,活生生、毛茸茸的,太可愛了。」但是,不能去抱,「幼熊一定要害怕人類,要保持完全野性。棕熊是非常社交的動物,如果牠們和人類太過親近,就不會害怕人類,這將危及牠們的生命。」
棕熊面臨人類大量的捕殺,正從十七個國家滅絕,在俄羅斯境內高速公路兩側,就都是一攤一攤的棕熊標本攤,輕易可以買到整張熊皮、整頭熊。商人甚至允許記者盡量拍攝。獵殺與棲地消失不只威脅著棕熊的生存,也威脅著犀牛、樹懶、長頸鹿、大象等幾乎每一種瀕危動物。
「為了讓犀牛活下來,一定要幫犀牛去角。」這是多麼荒謬而沉痛的悖論!盜獵人圍獵犀牛,「用斧頭砍斷犀牛的脊椎讓牠其癱瘓在地,接著連根拔起犀牛角。屠殺取角的過程,犀牛意識清醒,眼睜睜的看著、感覺著自己的臉面,連皮帶肉,被挖開一個大洞。被凌遲的犀牛通常還能存活一天,然後緩慢地、痛苦地失血而死。」被送到犀牛孤兒院的犀牛寶寶,左眼也幾乎被砍瞎,在圍欄內不停地轉圈圈,害怕焦慮,身心受創。懷「角」其罪,為了保護牠們,只好先為劫後餘生的犀牛「合法去角」!
白心儀走遍世界報導的每座「地球孤兒院」,裡面每一個動物孤兒,都是因為人類的殘酷造成,每一座孤兒院都是傷心處,每一個傷心處都有傷心人,但是傷心人不以傷心為終點,而以勇氣與承擔為起點,救傷圖存,要讓孤兒重新站起來,重新走回去森林荒野棲息地,活著。這些好心人美麗而強悍,犀牛庇護所的女主人公開向盜獵者宣戰,悉心照料一個個受傷的小犀牛;樹懶收容所的褓姆志工,多半是來自世界各國的生物專家、動物專家和獸醫師,他們從鐵絲網上救下小小樹懶,為的是將來讓小生命回到森林,重新野放。冰雪世界裡的帕基特諾夫家族,從獵熊家族變成救熊家族,被封為「棕熊之父」的瓦倫丁已經傳承到了第三代的瓦西里,他拿到了生物學位,森林召喚他的靈魂,要他傳播「把大自然留給下一代」的訊息。
斯里蘭卡工作象收容中心的許多故事都令人動容,最難忘是記者捲起衣袖褲管學習幫大象刷背之後報導了大象與象伕終老一生的故事。一個象伕一輩子就和一頭象一起生活,除非一方先死,絕不輕易離開對方。這故事有許多細節令人難以置信,工作象一生面對沉重的工作,到老不能休,但象伕像老朋友像情人一般懂得大象,他們之間的感情如此深厚,生死以之,如此絕望!
台灣本土的黑熊與石虎,又都是看不到太多的希望,憂鬱自殘的斷掌黑熊,鏡頭捕捉到牠的低吼與眼淚,捕獵的獸鋏使台灣山林變成黑熊的煉獄。石虎的保育更是艱難,但白心儀的鏡頭不只找到了黑熊與石虎,更是緊緊追隨著黑熊媽媽黃美秀與石虎媽媽陳美汀、石虎姊姊林育秀及更多投入心力的志工,翻山越嶺,台灣的本土保育有太多驚心動魄的堅持不懈!
大地孤雛,生靈瀕危。這是一本傷心的真實故事書,也是一個個關於覺醒的故事;有多少殺害的故事,就有更多的黑暗之心,人類的殘酷、自私、無知、自毀家園,沒有盡頭;除非一些屬於極少數的勇敢的人的努力,能被更多人看見、感動、認同、分享,因而喚醒人心。所以,這也是一本愛與修復的書,帶你看見殘肢傷痕,也帶你看見不忍與獻身。
《我在動物孤兒院,看見愛》是一位勇敢而執著的女記者,與她的攝影隊伍,帶來的一個個在絕望中不放棄希望的救傷與保護的故事,也帶我們看到了那些窮盡一切努力的無名英雄。一個電視記者能將她的電視故事,化為一篇一篇飽滿熱情又有豐沛文采的文字,讓讀者在視覺的衝擊下,也能沉吟拳拳文心,在今日新聞界實屬珠玉之作。
世界的孤兒,需要妳!
陳文茜/文茜的世界周報主持人
二十年前,白心儀是TVBS記者,到我家採訪我的狗孩子們。她自己非常喜愛動物,尤其博美犬,一個曾經跟她一起長大的玩伴。採訪時當時我已經四十五歲,還在水深火熱的政治圈,她才二十初頭,剛剛進入電視圈子。
當時的我們都那麼天真,以為世界可以被我們改變的好一點點,只要我們盡一份心力。
第一次採訪我時,我的第一代孩子們正處衰老狀態⋯⋯第二代孩子已隆重登場,平均才一至兩歲,而且全是無法無天、狗各有志的孩子:惟一例外是我收養的一隻秀氣流浪狗,憂鬱的特質,我為他命名:蕭邦。
之後我逃出了政治,但仍陪同李敖大哥登記參選立法委員。登記當天,我特別帶著李大哥送我的「小博美犬:李敖大哥大」助陣,結果那天吾家小犬「大哥大在中選會」一直轉圈圈,表情可愛至極,當然吸睛,搶盡風頭。
不巧那天TVBS派出的記者又是白心儀,她把李敖的參選新聞焦點完全放在我宣布搞笑的總幹事「李敖大哥大」身上,新聞畫面70%全是狗,其他有一點李敖,還有總幹事的媽:陳文茜。
李敖大哥居然頗為介意,我笑他:你這樣一個了不起的歷史人物,怎麼跟一個不到兩公斤的小狗計較呢?他聽完了,瞪我一眼,接著哈哈大笑,請客,吃飯去!
其實那時候的我,早已不再年輕,步入了中年,但説起話來,還是肆無忌彈。青春沒了,心情卻幼稚的很。
又一個十七年過去了,李大哥兩年前走了。
二十年前白心儀到我家採訪的孩子,Baby Buddha 、南禪寺、成吉思汗、Smokey、李敖大哥大,䔥邦、Bakery⋯⋯皆相繼走了。
他們走了,象徵我的中年人生、以及還殘存的少女心,全都走了。
如今我又邁入另一個人生階段,家裡七個孩子,有些時候還在外面例如台大動物醫院認養短尾白,直到她往生。這兩年和王妺,一起照顧Lala。
經歷那麼多孩子的失去、死亡,我告訴心儀:我現在擔心的不是他們又走了,我心情上受不了:而是有一天,我病倒了,不能照顧他們到最後。
我寧可痛的是自己,而不是他們。
我走了,留下他們,沒有了媽媽,沒有了家,一家子兄弟姊妹被拆散各處,重新適應新主人。
那才是我最大的不捨。
這第三批孩子,「當我老了」回家,總是熱鬧非凡,每天都像在開派對,我壓根忘了自己流年逝水,反而可以體會那種老人家「兒孩滿堂」的喜悅。
和過去不同,這一回,我是和著第三批孩子,一起走向生命終點。他們現在的幼稚、活潑,讓我忘了自己的身體狀況及年齡,我毫無恐懼感地和他們一起「再長大」。
等他們老時,我也老了。
但這給了我很大的毅力,逼自己堅強、運動,至少得活到78-80歲。好好照顧他們到最後。
有人崇尚孤獨,也相信孤獨才能找到自我。
我可不!生命稍縱即逝,我是歡樂派,我要和孩子們「牽手」,幸福地一路走到底。
心儀和我一樣喜歡動物,但選擇了不一樣的道路。二○一九年,她以視為終生志業的《地球的孤兒》入圍金鐘獎,卻因故被撤銷入圍資格,我在她臉書寫下:
「心儀,這不是你最黑暗的一天。這是學習自我肯定的一天。
記得那些你們拍攝的地球孤兒,你們是世界上少數與他們相伴相依的朋友。
這才是妳製作節目的意義。
金鐘獎只是一個紀錄,不是全部。
不要氣餒。
你會因此更強大。
為妳鼓掌。
愛,才是永不褪色的紅地毯。
妳已走在其上,請堅持下去,走完它。
世界的孤兒,需要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