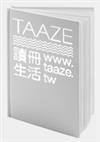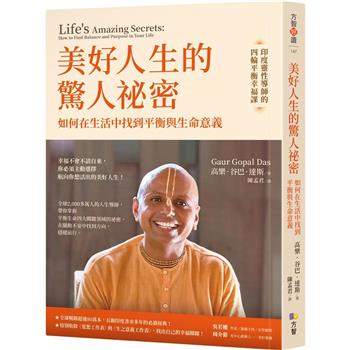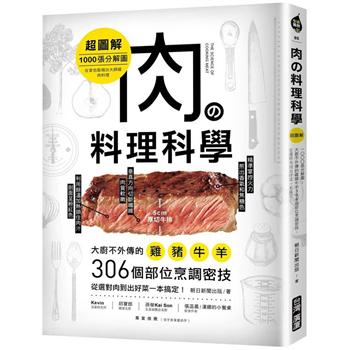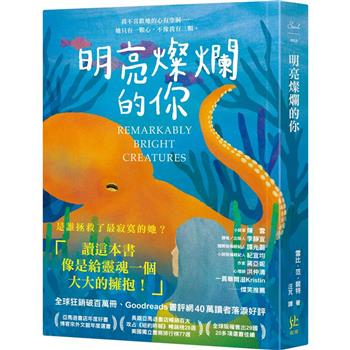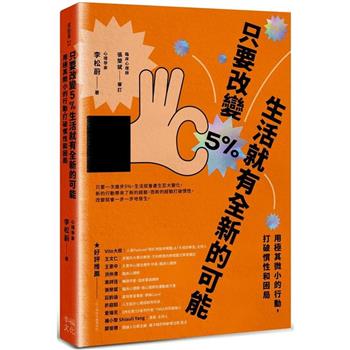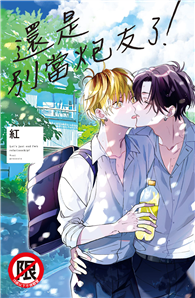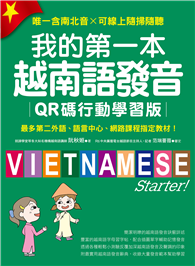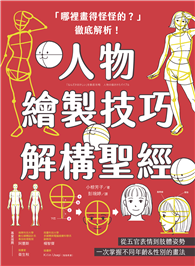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記憶宮殿-揭開史前遺址傳承千年的秘密︰在文字之前,回憶如何被塑造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人們承認口述這個傳統的深奧與複雜,是極晚近的事。考古學家們很早就已發現,新石器時代的英國人,擁有與你我一般的大腦和智力潛能;而現代人類(modern human)存在已有數萬年之久,原住民文化一直以來卻被視為智力低下、未開化。就在不過一百年前,極具影響力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還曾在書中寫道:「我應該選擇被人類學家評為最落後、粗野的野蠻人――澳洲土著,來作為對照的依據。」
但也正是這些「澳洲土著」,讓我見識到他們那套錯綜複雜的資訊系統,以及記憶方法運用的驚人範疇,促使我走上這趟探索的旅程,進而寫成此書。
若我想要主張「史前巨石陣基本上是種用來記憶的方法」,就必須證明無文字文化確實記憶了大量資訊。我所說的記憶,不僅止是記住他們在日常狩獵採集時的所見所聞,也不是像博物館裡豎立的達爾文雕像那樣,只是用來提醒我們想起這個偉大的人,這個古代巨石陣不僅僅是種記憶的提示。
我所要指的是正式的記憶訊息――學習、研究與不斷複誦。這話意思是說,這圓形石陣是用來記憶大量識性資訊的嚴密組織系統的一部分。我逐漸確信,澳洲原民的「歌之路」(songlines)、美洲印第安人的「古道」(trails)、印加人的「塞魁」(ceques),還有許多原民文化所創建的其他「地景」(landscape)通道,都是他們訓練記憶的成果。根據我多年研究,還沒見過哪個原民文化,光靠漫不經心的記憶方式和營火旁的閒聊,就可以保存有關他們環境與文化的知識。
歌之路(songlines)
我第一次有「歌之路」這樣的概念,是在聽澳洲原民談到相關事項時,當時沒料到幾個月後在索爾茲伯里平原上,這個想法會變得更形篤定。藉著唱誦地景歌謠,原民可以找到從一個聖地通往下一個地點的方向,以及沿路的水漥、落腳處,和取得食物、原料的來源。經過鄰近部落領地時,如果下一階段行程是以前沒走過的路線,還可以趁便向人家討教;長老們大多能說鄰近地區的語言,這樣子才能將知識傳播出去。
動物學家蘇‧邱吉爾(Sue Churchill)於公元一九八三年時,為了尋找穴居鬼蝙蝠,曾有利用歌之路來導引方向的特別體驗,她的描述如下:
幾個來自不同團體的不同老人家,開著一台老舊的豐田陸地巡洋艦,一起旅行。我們沒有地圖,要尋找的洞穴多半也已塵封多年,而其中有一個,還必須橫越荒漠的沙丘地,跑一百公里車程才能抵達;洞穴直立的入口很狹小,只要站得稍遠一點,超過三公尺就看不到它。擔任嚮導的老人們根據沙丘的形狀來指引方位,他們時不時會停下腳步吟唱一長串歌謠,以幫助記起沿路的地標。每到一個新地點,他們會「試著」(我們語言有點不通)告訴我們有關鬼蝙蝠的「夢世紀」(dreamtime;為澳洲原住民特有的一種信仰體系)傳說,或指著離洞口不遠處那些排成圓形陣列的石頭,為我們作說明,然後吟唱他們年輕時學會的那些歌謠。
「歌之路」或「夢之途徑」(Dreaming Tracks),指的是穿越在地理景觀間的行走路線;而為數眾多的這些「路徑」,以固定順序連接許多具有重要意義的地點――突岩、源泉、丘陵、山谷、洞穴及水坑等等。吟唱歌之路的時候,是以一長串短詩的形式來進行,藉由所有詩句共同組織構成一幅「唱出來的路線圖」,裡面刻劃出先人曾走過怎樣充滿開創性的旅程,或者有關他們的起源傳說。有些歌謠包含的範圍,可以橫跨數百公里、好幾個部落領地。因為週期性儀式的舉行,確保了這些遺址經常有人到訪、知識能被展示演出、相關連的神聖畫像能得到修繕,並且又更進一步幫助了記憶。
在歐洲人踏上澳洲土地之前,當地曾有超過三百個不同的語言聚落,但不幸地,如今能吟唱部落「歌之路」的長老已所剩無幾。在過去,長老會帶領孩子們去走歌之路,沿途講授故事傳說,吟唱有關遺址的歌謠,並按照在故有澳洲原民環境裡運用的方式,以腦海中的家鄉地圖來訓練教導他們。隨著年歲和所受啟發訓練的增加,傳授故事的內容也會越來越複雜。他們夜裡被帶到神聖地點去進行訓練,一遍又一遍吟唱著具有重大意義的那些路線,直到一字不差為止。
我懂得了吟唱路線圖的概念,也知道輔以圖像與沙畫,將它具象化之後,可以大大加深印象,但我尚未見識到歌之路的力量。它們的作用絕對不僅止於「導航」工具。歌謠的吟唱、儀式的表演,都是在這些路徑上的神聖地點裡進行。純就定義來看,所謂儀式不過是種不斷重複表演的行為而已,但是在那些表演的歌謠和舞蹈裡,還蘊藏著範圍極其廣泛的實用性知識題材(也是我當時正在探索的領域),不僅僅只有那些用來指引方向的路線而已。而引發我好奇的是,這些歌之路的運作方式;它們就像電子記事本,像是這許多知識的目錄表。
在每個地點的儀式表演裡,都蘊含著已轉譯編碼的知識;而這整個神聖地點的作用,就像是在為這裡所收編的知識建立小標題。每一處神聖舊址的生動故事,都會提到神話裡的祖先,談到是他們創造了地理景觀、動物、植物和家園裡的每樣事物;而這地景中每件事物都被命名,都是有所連結的,都有個場域歸屬,都能被辨識。這因襲傳承下來的原民「地景」(landscape),正是一個規模宏大的「記憶空間」(memory space)。
最顯而易見的與神話有關聯的自然景觀,是中澳大利亞的天然巨石――烏魯魯(Uluru;見彩圖1.1),這塊巨岩底部周長將近九公里,上頭有許多裂縫與凹痕,每個都連結了故事;繞行岩石時,會逐一引人回想起那些傳說。「傳統擁有者」阿南古族(Anangu),視烏魯魯為其知識系統「朱庫爾帕(Tjukurpa)」的一部分。根據他們的說明,「朱庫爾帕」一詞具有許多深奧複雜的含意,這系統裡面包含有:人民彼此照顧與守護家園的法規,人類、動物、植物之間的關係,這片大地在過去、現在、未來的自然形貌。對精通阿南古族知識的專家來說,經過多年學習後,那一連串神聖遺址早已爛熟於心,不必實際到現場才能回憶故事;只要憑藉記憶,他們隨時想要瀏覽巨石的哪個部位都行。
人類學家約翰‧布萊德利(John Bradley),與卡奔塔利亞灣的洋尤瓦族人(Yanyuwa)來往長達三十年之久,他所勘測繪製的歌之路,含括範圍已超過八百公里。洋尤瓦族人稱他們的歌之路為「庫基亞」(kujika),認為這是「洋尤瓦人認識事物的方式」,也是他們通往「豐富、複雜而又交錯連結的知識系統」的關鍵之鑰。僅僅其中一首「庫基亞」,布萊德利便記錄了兩百三十多行詩句,當中保存的訊息層層相疊,從啟蒙開始,隨著等級逐漸升高,從中所學得的知識也會越來越複雜。他還描述了長老之間進行討論的方式,他們藉此為所學得的詩句作補充,也為傳說故事加上註解;閱讀有關原民歌謠與故事的文字紀錄時,因為少了這樣的臨場註解,通常幾乎無法採集到什麼資訊。
布萊德利還描述了一種洋尤瓦長老的「歌唱路徑」(singing track),可指引人前往一處露天石礦場;與這條「歌之路」相連結的那些歌謠,又詳細說明了專門的石器技術,當中還包含有一連串地名、人名、風向、季節性活動、物品名稱,以及狩獵、搜尋糧秣、醃製食物、製作器具的正確方法,還有不同群體在國土上的權利。在礦場裡,原民長老傑瑞‧奈恩亞維克哈爾亞(Jerry Ngarn-awakajarra)吟唱了幾首詩歌,詩歌裡以這個地方四處分布的薄石岩,與某種已上百年沒人使用的技術相對應連結。而傑瑞長老上次造訪礦場,已是五十年前的事。
這種利用自然景觀裡的指定地點來形成「記憶空間」的做法,絕非澳洲人所獨有,世界各地的原民文化都會使用這種方式,來遊歷感受自己的家鄉。人類學家基斯‧巴索(Keith Basso),曾談到美洲印第安人如何運用古道,將每件過往的事情和某個特定場所相連結;而這些與場地相連結的知識,在慶典儀式中被改編成戲劇生動表演出來,說故事的方式逐漸變得戲劇化。
巴索還描述了自己曾聆聽一位阿帕契人(Apache)唱誦的經驗,當時他輕聲背誦一連串地名長達十餘分鐘。其中一條已被詳細載入文獻的路徑,是條朝聖必走的荒野小徑,跨越範圍長達數百公里,將屬於普韋布洛語系的一支祖尼部族,與新墨西哥州班德利爾國家紀念區裡的一處場所作了連結。這條朝聖小徑上那些神聖地點的名字,現仍在許多故事中被背誦吟唱著;這些故事描繪出先人遷徙的路線,僅限定接受過入門訓練的人才能加以傳誦。
無論是澳洲文化的歌之路,或是美洲印第安人的荒野小徑,在世界各地被吟唱的大片土地,作用都一樣,都是一套組織化的歌謠系統,是該文化所有知識的整套目錄標題。歌謠與自然景觀之間做了定位連結後,無論是以實地或想像的方式來到景觀裡,人們都可以回想起那些歌謠。而當原民長老唱誦著他們的地名表時,在記憶中就可以看到那些地方的具體影像,同時聯想起和每個地方相關聯的資訊。
傳統原住民藝術的記憶功能
考古學家總是會挖掘出一堆看不出實用意義的,加有綴飾的小型物件。放眼全世界,各地原民文化都在使用類似的物件,他們利用這些繪有抽象裝飾圖案的物品,作為記憶輔助工具。在這裡,我的實驗再度讓我明白,這些簡單的裝置究竟能發揮出多麼大的效用。在嘗試使用這些物品時,自己受到鼓舞的那個心路歷程,就跟之前使用地景與空景作為記憶空間時一樣。最終我得出一個結論:這些繪有抽象圖飾的物件,就是小型的記憶空間。
幾乎所有天然媒介,只要圖像能畫得上去,原民文化就能以某種形式拿來作為記憶空間。目前為止,最為人們所熟知的古文明用來繪圖的平面媒介,是石頭與洞穴。我們知道,澳洲原民會利用塗繪在棲身處與洞穴內的岩石藝術,來描繪他們的神話傳說與歌謠;然後由此,將它們再更進一步轉變成為記憶空間。
這裡出現了一個會有點問題的字眼——「藝術」。就西方的背景來看,衡量藝術的首要標準是美學;但是在無文字文化來說,主要動機則是訓導教誨。我之所以敢做這樣重大的聲明,是因為曾有原民朋友這麼告訴我。我的瓦爾皮瑞族同行——努伽拉伊曾說,傳統原民藝術的目的,始終是為了幫助他們記憶「故鄉」,以及當地的相關傳說與知識。她解釋道,原住民雖然從藝術的美學層面得到了很多樂趣,但那絕不會是他們藝術的主要目的。
在傳統澳洲社會裡,圖案是限定持有資格的;如果是個人想要複製圖案,那麼他必須先接受入門課程,了解圖案所代表的知識。許多藝術作品不僅描繪出創造大地的神話人物與事件,同時也提供了自然地形圖,和利用這地形圖導引方向的方法。原民藝術的作用就像是個小型記憶空間,而圖像元素所代表的那些地點,過去早已被轉譯成密碼,收錄在歌謠裡。
纏繞、扭轉、打結的各種繩線
非常多文化都會利用繩線來輔助記憶。將繩線的花樣與故事搭配在一起,藉由這個動作,以確保故事能依正確順序作鋪陳。如何以簡單的一小截繩線,做出極端複雜精巧的操作變化,然後再拿來說故事?玻利尼西亞、紐西蘭、北美洲、非洲、亞洲與因紐特領地的原住民,全都做了方法示範。
有些時候繩線會綑紮成結,維持固定的樣式。目前最為人所知的結繩工具,是安第斯山脈地區文化用來記錄資訊的「奇普」(khipu,也作quipu)。奇普專家會將一條主繩橫向擺放,然後再直向纏上其他繩線,任其垂直懸掛;我在博物館看過的奇普,有的大約只有十二條垂繩,也有的多達數百條。
一直以來,人們都認為奇普的功能主要只在財務紀錄,直到最近研究人員才體認到奇普是種結構更為複雜的裝置――它是種記憶輔助工具,可用來承載的資訊種類極為廣泛,包括有故事、律法、儀式、歷史,連帶還有人口統計資料、貢品和某種曆書類的東西。奇普卡瑪尤(Quipucamayos),是製作與解讀奇普的專家,他們因此在印加社會中擁有極大影響力。
由於奇普是一種記憶設備,並未使用文字,因此一位「奇普卡瑪尤」或許能解讀自己製作的奇普,但有些資訊,我們認為除非接受原製作者特別指導,否則其他人根本無法破解。這麼一來,這資訊就會掌控在少數受過入門訓練的人手上。印加帝國就算不是全世界,至少也是全美洲最龐大的無文字文化,是什麼賦予印加人這個開創能力?就是奇普,以及在這個裝置上頭的那整套沿著地景通路――塞魁(the ceques)分布的「地點」。
那些出土粗細繩線多半不會被列入考古記錄,但卻極有可能在整個史前時代,人們都在使用它。
作者簡介:
琳恩‧凱利 Lynne Kelly
琳恩‧凱利博士是一名科學作家,也是澳洲拉籌伯大學的榮譽附屬研究員,奉獻大半人生於中等學校教育,教授物理、數學、資訊科技與一般科學等課程。出版過幾本暢銷科學書籍,內容皆與她的研究調查項目有關,諸如超自然現象、鱷魚及蜘蛛等。琳恩最初是以原民動物傳說為博士論文題目,但後來轉而對非讀寫文化記憶的方式產生極大興趣,從此熱衷於研究原民如何能在不使用文字的情況下,記憶鉅量實用資訊。某天,在索爾茲伯里平原上遠觀史前巨石陣,她突然領悟到,自己的新觀點能為世界各地考古遺址,帶來嶄新的觀察角度,從而展開這趟驚奇旅程,以所提史前巨石陣實為一記憶空間的理論主張,廣受各界矚目。最終有了本書的誕生,而這也是她的第十六本著作。
著有:《史前社會的知識與權力》、《蜘蛛:學習如何喜愛它們》、《鱷魚:演化史上最大型的倖存者》、《給無神論者的超自然現象參考指南》等書;合著有:《探索混沌與分形》。
譯者簡介:
張馨方
政大阿語系學士,英國愛丁堡翻譯研究碩士。現為自由譯者,作品包括《恨意、精神分析與羅夏克墨漬測驗》、《脂肪的祕密生命》、《俄羅斯方塊:從誕生、版權之爭到風靡全球的故事》等。
譯作賜教: nurachang@gmail.com
在成為博士生後不過幾週,我在澳洲拉籌伯大學的一門英國語文課程中,即已窺見澳洲原住民先祖們所擁有的知識極其錯綜複雜,而他們也成為我第一個深入研究的文化族群。原民們記憶了巨量有關動...
第1章 原民長老的百科全書記憶庫
原住民的動物知識
原住民的植物知識
表演出來的管制版知識
歌之路(songlines)
記憶空間與古代希臘人
儀式慶典的多樣用途
神話傳說的保存期限
整合的知識系統
第2章 大大小小的「記憶空間」
古代遺址?記憶空間?
記憶的「空景」(skyscapes)
小型的記憶空間
傳統原住民藝術的記憶功能
可攜式物件上的圖案和佩飾
各種各樣的可攜式物件
纏繞、扭轉、打結的各種繩線
成套的非實用物件
神話先人的圖像
神話與科學:普韋布洛的玉米傳說
部族系譜與圖騰
第3章 現代世界的「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