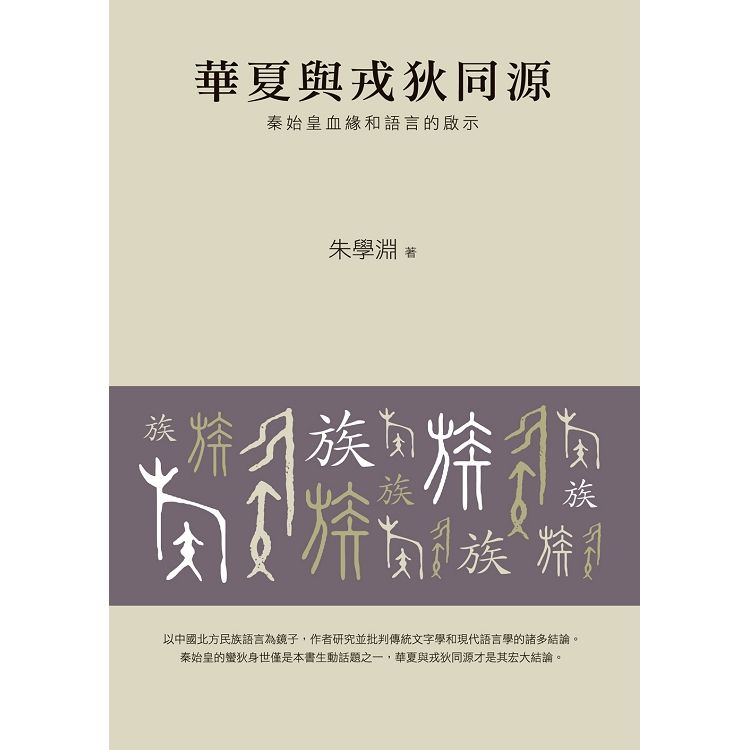▍周策縱:原族──《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序
朱學淵博士把2002年五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他的書《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寄來,說準備在台灣出修訂版,並要我寫一篇序。我早先就讀了他第一篇文章〈Magyar人的遠東祖源〉,他說Magyar(讀「馬扎爾」,即匈牙利),事實上就是中國歷史上的「靺鞨」族。他從「語言、姓氏、歷史故事和人類互相征伐的記載中」,勾畫出了一個「民族」的始末來,旁徵博引,我認為有很大的說服性。後來他又討論了通古斯、鮮卑、匈奴、柔然、吐火羅等許多種族和語言,一共收輯了九篇論文,還有〈附錄〉和〈後記〉,就成了本書。
大家都知道,十九世紀下半期以來,歐洲一些漢學家由於兼識多種語言,而對中亞、遠東諸族的姓氏和源流,多有研考,成績可觀。如斯坦因(Sir Aurel Stein, 1865-1943)、沙畹(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馬伯樂(Henrri Maspero, 1883-1945)等尤為顯著。中國的馮承鈞(1887-1947)翻譯了不少他們的著作。其實是應該全部都譯成中文的。中國學者懂這些語言的太少,像陳垣、陳寅恪都已經去世了,季羨林教授又已年老。將來只能靠年青一代。
學淵這本書遠遠超過前人,對北方各少數民族不但索源,並且窮流,指出亞、歐種族和語言溶合的關係,發前人所未發。尤其難得的是,他本來是學物理學的,能不受傳統人文學科的拘束,獨開生路,真是難能可貴。讀了學淵《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一書之後,不免有許多感想,這裡只能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
第一,中國人「族」的觀念起源很早。至少於三千五百年前甲骨文中的「族」字,就是在「旗」字下標一枝或兩枝「矢」(箭)。丁山解釋得很對,族應該是以家族氏族為本位的軍事組織。這種現像在北方諸族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如《舊唐書.突厥傳下》說的:
「其國分為十部,每部令一人統之,號為十設。每設賜以一箭,故稱為十箭焉。……其後或稱一箭為一部落,大箭頭為大首領。」
這裡的「箭」,本義為「權狀」或「軍令」,後來則轉義為「部落」了。又像滿洲「八旗制度」,將每三百人編為一「牛錄」(滿語niru,義為大箭)。因此「八旗制度」和「十箭制度」,也都在「旗」下集「矢」,是軍事性的氏族組織。「族」與「矢」的這種關係,可以說中原漢族和北方民族是習習相通的。學淵說北方諸族是從中原出走的,這或許是個合理的證據。
箭是人類早期最重要的發明之一;對這個字的研究,自然非常重要。它在匈牙利語中是nyil,芬蘭語中為nuoli,愛沙尼亞語中為nool,竟都與滿語的niru如此相近;而漢語中的相關辭彙「弩」、「砮」等,是否與之相關?也很值得深思。中國古文字研究,重「形」和「義」之解釋,固然有其特殊貢獻,但忽略「語音」的構擬,已經被詬病得很久了。總有一天是要兼走這條路的,而舍比較語言學的方法恐怕不能成功。
第二,關於唐太宗征遼東(高句麗)的戰爭,正史的很多記載並不真實。在學淵的〈Magyar人的遠東祖源〉一文中,他詳細敘述了這場戰爭,但引用的卻多是中國官史的說法。多年前,好像柏克萊加州大學一位美國朋友贈我一文。他根據高句麗方面的記載,說貞觀十九(公元645)年六月安市城(今遼寧海城南)之戰,因高延壽、高惠真率高句麗、靺鞨兵十五萬來救,直抵城東八里,依山佈陣,長四十里,抵抗唐軍。唐太宗親自指揮李世績,長孫無忌、江夏王李道宗(太宗的堂弟)等攻城,然而經過三個月還不能攻下。後來因為太宗中箭,只得在九月班師。
可惜這篇文章一時找不到了,我只能從中國史料來重構一些真相。而中國官方記錄都是一片勝利之聲,實在離真事很遠。據《資治通鑒》說安市之戰時,李道宗命傅伏愛屯兵山頂失職,高句麗兵奪據土山。太宗怒斬伏愛以徇,李道宗「徒跣詣旗下請罪」。太宗說「汝罪當死」,但「特赦汝耳」。據我看,太宗中箭,大約即在此時。而靺鞨兵善射,太宗可能就是中了靺鞨之箭。
《新唐書.黑水靺鞨傳》說:「高惠真等率眾援安市,每戰,靺鞨常居前。帝破安市,執惠真,收靺鞨兵三千餘,悉坑之。」同書〈高麗傳〉所說的「誅靺鞨三千餘人」,當是同一件事。太宗對高句麗軍都很寬恕,獨對靺鞨人仇恨,必非無故。九月班師,《通鑒》說是「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其實都只是藉口。
《通鑒》又說,這年十二月太宗突然患癰疽,「御步輦而行」;「至并州,太子[李治]為上吮癰,扶輦步行者數日。」還有侍中兼民部尚書和禮部尚書劉洎,本是太宗的親信大臣,「及上不豫,洎從內出,色甚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太宗居然用「與人竊議,窺窬萬一,謀執朝政」的罪名,賜他自盡。其實他不過是透露了太宗受箭傷的消息,竟惹來了殺身之禍!
《通鑒》還說,二十年二月,「[太宗]疾未全平,欲專保養,庚午[陽曆三月二十九日],詔軍國機務並委皇太子處決。於是太子間日聽政於東宮,既罷,則入侍藥膳,不離左右。」褚遂良諫太宗多給太子一些閒暇,說明太宗已把責任都交給太子了。二十二年五月,太子率更長史王玄策擊敗天竺(印度),得其方士那邏邇娑婆寐,自言壽二百歲,有不死術。太宗令他「采怪藥異石」,以求「延年之藥」。據我看,太宗是想要治箭瘡。二十三(公元649)年,五月己巳[陽曆七月十日],太宗服丹藥反應崩駕。他死後四天才發喪。當時宣佈他年五十二,實際只有五十歲。
中國後世史家,甚至寫唐史的人都很少留心敵人方面的記載。我只注意到錢穆先生的老師呂思勉在他的《隋唐五代史》裏就懷疑官方的說辭。他說:
「新唐書高麗傳曰:始行,士十萬,馬萬匹,逮還,物故裁千余,馬死什七八。船師七萬,物故亦數百。(通鑒曰:戰士死者幾二千人,馬死者什七八。)此乃諱飾之辭,豈有馬死什七八,而士財[才、僅]喪百一之理?」
當然,他還沒有注意到高句麗方面的記錄,可是有此見解已很不容易了。
第三,關於李唐家族的血緣,前人也有些研究。陳寅恪曾發表兩篇論文,認為唐朝皇室基本出於漢族。日本學者金井之忠發表〈李唐源流出於夷狄考〉一文反駁。陳寅恪又寫了〈三論李唐氏族問題〉來答復。陳說:李唐祖先李熙及妻張氏皆漢族,其子李天賜及妻賈氏亦皆漢族,其子李虎自系漢族,虎妻梁氏固為漢姓,但發現有一例為胡人,乃只好作為可疑了案。陳寅恪是依傳統,以男性血緣為主,所以終於認定李唐為漢族。
依照我從男女平等的看法,張姓本多雜胡姓,李唐皇室早已是混血種。李虎之子李昞本身已可疑,其妻獨孤氏(即匈奴屠各氏,後改劉氏)當是胡族,他們的兒子李淵(高祖)必是漢胡混種,胡血可能在一半以上。李淵的妻子竇氏(太宗之母)乃紇豆陵毅之女,更是鮮卑族胡人,所以唐太宗的胡血,至少有四分之三。太宗的妻子長孫皇后(高宗的母親),是拔拔氏(史亦稱拓拔氏,也就是拓跋氏),高宗身上漢血的成分已很少很少了。
據陳寅恪考定,高宗做太子時,即烝[上淫曰烝]于太宗的「才人」武則天,太宗死後便直接娶了她。為了避免顯得他是直接娶了父親的愛妾,便又偽造武則天先在感業寺為尼,然後才把她娶來的假故事。這雖像掩耳盜鈴,但于胡血甚濃的李唐家族來說,從「父死,妻其後母」的胡俗,又有什麼可驚怪的呢?皇族還可略加追索,至於一般老百姓,當然更是一篇糊塗帳。
中國歷來對姓氏和血緣的研究就不用心,章太炎在〈自述學術次第〉中說:「姓氏之學……所包閎遠,三百年中,何其衰微也!」姚薇元于抗戰前師從陳寅恪,他在1963年出版《北朝胡姓考》,於〈緒言〉中說自己是「以蚊負山」,也不為無故。
第四,這裡還必須指出,太宗的妻子長孫皇后,于貞觀十年六月已卯(陽曆七月二十八日)因病去世,實年僅三十五。她的英年早逝,對唐朝的命運關係重大。身為皇后的她,既好讀書,又反對外戚弄權。她的哥哥長孫無忌與太宗是「布衣交,以佐命為元功,出入臥內,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她向太宗說:「不願私親更據權於朝。漢之呂、霍,可以為誡。」(《新唐書.後傳》)太宗不聽,任無忌為尚書僕射,即宰相之職;她卻勉強要哥哥辭謝了。她一死,無忌就當了權,扶持了外甥李治做太子。親征高麗時,有人建議直取平壤,無忌卻主張先攻安市;結果有太宗的中箭。
後來高宗因常患「風眩」,一切由武則天控制。她把唐朝宗室幾乎殺盡,連太宗的愛女和女婿,和她自己的兒女也遭誅殺。長孫無忌遭貶謫賜自盡,褚遂良則死於貶所。武則天終於篡了天下,做了皇帝。
說來,在玄武門事變中,太宗把同母兄太子建成射死;自己後來也因中箭傷而崩駕,可謂報應不爽。而他讓人把胞兄建成和胞弟元吉的頭割下來示眾,還把他們的十個兒子都殺光。時元吉僅二十三歲,想必他的五個兒子不過幾歲,小孩又有何罪?
趙翼在《廿二史札記》裏說:「是時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視其孫之以反律伏誅,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極矣!」《通鑒》則評得更痛快:「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儀刑 [ 模範 ] 也,後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 [ 摹擬 ],以為口實 [ 藉口 ] 乎!」那幾代皇帝都要靠軍隊平難,方能繼位。太宗雖然是一個歷史上的好皇帝,但他也為本朝後人樹了壞規矩。上述的這些惡果,多少與長孫皇后和魏征的早死有關。魏征死於征遼的兩年前。太宗在戰事失敗後,曾歎曰:「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太宗服丹藥喪命,也是皇室的壞榜樣,趙翼的書中就有〈唐諸帝多餌丹藥〉一條。貞觀二十一年高士廉卒,太宗欲去弔唁,房玄齡諫阻,「以上餌藥石,不宜臨喪。」長孫無忌更一再攔阻。這還不是那印度方士的藥,但可見他早就在服丹藥了。多年後,李藩對唐憲宗(公元 806-820 年在位)說,太宗「服胡僧藥,遂致暴疾不救。」說的才是那印度方士的藥。至於好色和亂倫,更是唐朝皇帝們的家常便飯了。
最後,我想質疑學淵在〈Magyar人的遠東祖源〉的一個說法。他引用馬長壽的結論說「阿伏于是柔然姓氏」。並且推論說:柔然是繼匈奴、鮮卑之後,稱霸漠北的突厥語族部落,公元508年被高車族重創;又據歐洲歷史記載,一枝叫Avars的亞洲部落於568年進入東歐,曾經在匈牙利地區立國,並統治巴爾幹北部地方二百年之久,865年為查理曼帝國所滅。歐洲史家認為Avars是柔然之一部;學淵以為Avars就是匈牙利姓氏Ovars,或「阿伏于」的別字。很可能是在九世紀末,Avars與Magyar人融合,而成為匈牙利民族的一部分。
我原來以為學淵的推測很巧妙;可是一查他在注釋裏引馬長壽的《烏桓與鮮卑》一書中所說的,不是「阿伏于」,而是「阿伏干」。再查馬氏所根據的《魏書.長孫肥傳》附其子長孫翰傳曰:
「蠕蠕大檀入寇雲中,世祖親征之,遣翰率北部諸將尉眷,自參合以北,擊大檀別帥阿伏干於柞山,斬首數千級,獲馬萬餘匹。」
馬氏認為入寇雲中是在公元424年。我查得柞山是在綏遠界內,今屬內蒙。
據陳連慶著《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初版,頁198)說:
《魏書.官氏志》說:「阿伏于氏後改為阿氏。」「于」字系「干」字之誤。《姓纂》七歌、《氏族略》均不誤。《廣韻》七歌誤作「于」。
陳氏又說:
《魏書.高祖紀》云:「延興二(公元472)年二月,蠕蠕犯塞,太上皇(獻文帝拓跋弘)召諸將討之,虜遁走。其別帥阿伏干率千餘落來降。」
為什麼在四十八年之後,阿伏干又來投降北魏?我再查手頭的中華書局標點本,原來陳氏又將「阿大干」錯寫作「阿伏干」了,他們不是一個人。
我以為「阿伏干」讀音,最接近「阿富汗」(Afghan),而阿富汗人多數說的是一種屬於伊朗語言(Iranian language)的普什圖語(Pashtu)。當然阿富汗之名的由來還須查實,1970年版《大英百科全書》說Afghan的名稱是六世紀印度天文學家Varaha-mihira首先提到,當時用的是Avagana。同時期的中國歷史似亦有線索,《魏書.西域傳》記載過「閻浮謁,故高附翕侯,都高附城。」古之「高附」,就是今之喀布爾(Kabul);莫非「閻浮謁」就是阿富汗?此事還望學淵作進一步探索。
我在這篇序裏要強調的有幾點:(一)凡對外、對內關係或戰爭,都應該要比較對方的記錄,平衡判斷。(二)官方的宣傳和記載,不可盡信。(三)偶發事故,像長孫皇后和魏征之死等,往往可有長遠重大的後果,歷史並非有必然定律可循。(四)美國素來以世界諸族熔爐自豪,當然可貴,但還只有三數百年發展;中國卻早有三數千年的民族融合了。語言、血族、文化、文明的和平交流熔會,更可能是將來的趨勢。我看這也是朱學淵博士此書最重要的貢獻。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華夏與戎狄同源--秦始皇血緣和語言的啟示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40 |
二手中文書 |
$ 432 |
中國歷史 |
$ 432 |
社會人文 |
$ 432 |
歷史 |
$ 456 |
中文書 |
$ 456 |
文化研究 |
$ 456 |
Others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華夏與戎狄同源--秦始皇血緣和語言的啟示
★ 物理學博士朱學淵,以其理性科學的研究方法,跨足探討中國民族的語言與身世。
★ 透過語言與發音,大膽假設論證,探究秦始皇的身世起源,挑戰讀者對於中國歷代種族的認識。
秦始皇叫「嬴政」,清雍正帝叫同音的「胤禛」,秦始皇是否也是一個女真人?孔子的父親名「叔良紇」,蒙古人則把「朝鮮」叫做同音的「肅良合」;還有許多古人的名字也與北方民族的族名讀音相關,譬如「虞舜」是「烏孫」,「句踐」是「女真」,「孟軻」是「蒙古」,「墨翟」是「勿吉」等等,上古中原竟像是一個戎狄的世界,北方民族是不是從中原出走的呢?
中國傳統學術重文字輕語言,因此幾千年來步履艱難;歐洲一些漢學家則兼通多種語言,研考東方民族新解紛出。然而,外人治中國史畢竟有條件的限制,中國人治自家史又有傳統的束縛,因此成效都不盡理想。朱學淵博士的專業是理論物理,思維嚴謹,但他不受傳統的拘束,能以比較語言著手,對北方民族索源窮流,還以北方民族為鏡子,對史前中原社會有突破的見解,別開了一面歷史——語言——人類學研究的生動領域。
作者簡介:
▍朱學淵
一九四二年生於廣西桂林,一九六五年畢業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曾經於四川、南京等地任中學教師十餘載,一九七八年入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一九八〇年移學美國,一九八三年獲物理學博士,曾於能源部屬下的實驗室作博士後研究,一九八七年起經商。他以自然科學之學力,有志於人類學和語言學的研究,從中國史料中星星寥寥的語言記載,洞察了許多世界人類的重要線索。
章節試閱
▍周策縱:原族──《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序
朱學淵博士把2002年五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他的書《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寄來,說準備在台灣出修訂版,並要我寫一篇序。我早先就讀了他第一篇文章〈Magyar人的遠東祖源〉,他說Magyar(讀「馬扎爾」,即匈牙利),事實上就是中國歷史上的「靺鞨」族。他從「語言、姓氏、歷史故事和人類互相征伐的記載中」,勾畫出了一個「民族」的始末來,旁徵博引,我認為有很大的說服性。後來他又討論了通古斯、鮮卑、匈奴、柔然、吐火羅等許多種族和語言,一共收輯了九篇論文,還有〈附錄〉和〈後記〉,就成...
朱學淵博士把2002年五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他的書《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寄來,說準備在台灣出修訂版,並要我寫一篇序。我早先就讀了他第一篇文章〈Magyar人的遠東祖源〉,他說Magyar(讀「馬扎爾」,即匈牙利),事實上就是中國歷史上的「靺鞨」族。他從「語言、姓氏、歷史故事和人類互相征伐的記載中」,勾畫出了一個「民族」的始末來,旁徵博引,我認為有很大的說服性。後來他又討論了通古斯、鮮卑、匈奴、柔然、吐火羅等許多種族和語言,一共收輯了九篇論文,還有〈附錄〉和〈後記〉,就成...
顯示全部內容
推薦序
▍小序
本書實為拙著《秦始皇是說蒙古話的女真人》的增訂版,由於《秦》書先後在台灣和中國出版,而本書的內容又已大為擴充,所以我決定採用《華夏與戎狄同源》的書名來點明其人類學研究的宗旨。本書用「秦始皇血緣和語言的啟示」為副題,其實它遠非是一個帝王的身世由來,而是以中國歷史記載中大量的語音線索,來證明中原民族的祖先是與中國北方諸族同源的事實。
謹此也向秀威資訊公司的先生和女士們的耐心工作表示感謝。
▍原版前言
大約十年前,寫了一篇歷史語言的研究文章,是說匈牙利人的祖先是女真民族,它引起了學界的注意;後...
本書實為拙著《秦始皇是說蒙古話的女真人》的增訂版,由於《秦》書先後在台灣和中國出版,而本書的內容又已大為擴充,所以我決定採用《華夏與戎狄同源》的書名來點明其人類學研究的宗旨。本書用「秦始皇血緣和語言的啟示」為副題,其實它遠非是一個帝王的身世由來,而是以中國歷史記載中大量的語音線索,來證明中原民族的祖先是與中國北方諸族同源的事實。
謹此也向秀威資訊公司的先生和女士們的耐心工作表示感謝。
▍原版前言
大約十年前,寫了一篇歷史語言的研究文章,是說匈牙利人的祖先是女真民族,它引起了學界的注意;後...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小序
原版前言
簡體版前言
周策縱:原族─《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序
▍華夏與戎狄同源
一、中國北方諸族研究始末
二、中國北方民族的族名
三、五帝是女真族,黃帝是愛新氏
四、《百家姓》中的北方民族族名
五、中原古代人名的戎狄特徵
六、「通古斯/桃花石」即「九姓」
七、 島夷、氐類、姬姓、子姓,皆是女真
八、「句踐/鬼親」即是女真
九、秦始皇是說蒙古話的女真人
十、以「檮杌」一字,為中華民族尋根
十一、匈奴民族的血緣和語言
十二、匈奴的興起、敗滅和出逃路線
十三、阿梯拉和匈人
十四、突厥民族之由來...
原版前言
簡體版前言
周策縱:原族─《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序
▍華夏與戎狄同源
一、中國北方諸族研究始末
二、中國北方民族的族名
三、五帝是女真族,黃帝是愛新氏
四、《百家姓》中的北方民族族名
五、中原古代人名的戎狄特徵
六、「通古斯/桃花石」即「九姓」
七、 島夷、氐類、姬姓、子姓,皆是女真
八、「句踐/鬼親」即是女真
九、秦始皇是說蒙古話的女真人
十、以「檮杌」一字,為中華民族尋根
十一、匈奴民族的血緣和語言
十二、匈奴的興起、敗滅和出逃路線
十三、阿梯拉和匈人
十四、突厥民族之由來...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