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祖國.同胞
矇矓中醒來時,新高丸在一望無際汪洋大海之中。遙遠的水平線上浮現一輪紅紅的大太陽。一片波光閃爍,藍青海浪濤濤,一群海鳥展翅在天空飛翔,呈現一幅和平安祥的景象。這是大自然美麗的創意、上帝慈悲的期求。可是地球上醜惡的人類為求達到野心的滿足而逞威,在這煦光普照大地的一角落裡,正戰火漫天,違悖人道的姦淫、無情的殺戮、殘忍的擄掠等等,排演著人間最大的罪惡悲劇呢。假如沒有一個萬能的主宰者奇蹟出現,把人類的齷齪慾心滌除淨盡,否則這個世界未來的戰爭是永無止境地繼續發生。將近中午時分,船中發出第一道命令,我們一千個弟兄集合在甲板上排隊,聆聽指揮官的一席訓話。
「……諸君!我們今天成為皇軍的一員,能為天皇陛下捨生效忠是多麼榮幸的事。這是天皇陛下對你們本島人一視同仁的恩澤,願大家要有一死報國的決心……」
指揮官的聲音高傲而昂揚,隊員們個個嚴肅的臉孔,寂然無聲。
「哼!強迫從軍,好一個一視同仁,真是鬼話。」
我齒間覺得癢癢地。這個日人指揮官是陸軍中尉,身子高大、濃眉大眼、鼻樑下生著兩撇八字鬚,冷酷無情形象正象徵著整個殘忍日人的真面目。說話間偶爾撫弄著腰間的軍刀,好像炫耀著他威嚴似地。他續說:
「戰死沙場是帝國男兒的本懷,也是軍人至高的榮譽,為要完成這場聖戰,我們誓為皇國的干城……」
又來一個聖戰……這是日本軍國主義者一套的宣傳口號,這種堂而皇之的美麗謊言,會不知有多少日本青年受騙著了魔似地趕赴戰場,臨死時還撐著最後一口氣高呼「天皇陛下萬歲」呢。厚顏無恥的日本軍閥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竟大肆地狂喚著—為東亞永久和平,這場聖戰非打不可……。如此詭譎狡詐,這樣忝不知恥的東西……我狠狠地掃瞄著指揮官。他更叨叨地一再強調「大和魂」更吭聲誇耀「武士道精神」一番後,略降低嗓門道:
「現在可以明白地告訴你們了。我們這支龐大的隊伍名稱叫做『台灣農業義勇團』,我們的目的地是上海,我們在上海郊外一帶佔領區內,要來開闢一處廣大的軍農場,我們的任務是為前線的將兵提供新鮮的蔬菜,讓他們有足夠的營養糧食,提高他們的戰鬥士氣。我們雖然沒拿起槍桿上前殺敵,但是我們的使命非常重大,我們的一把鋤頭就是槍桿……」
聽了老半天,方得明白一切了。原來我們不是軍夫,不要到前線去運子彈搬糧秣當砲灰,真是謝天謝地,我大大地鬆了口氣。
新高丸緩緩地航行著,到了第三天的中午,大夥兒正在吃飯的時候,船中臨時發出警報,新高丸立即停航了的樣子,傳令兵匆忙跑來大嚷道:
「停止吃飯,全員避入船艙裡。」
究竟發生什麼事?大家都訝然面面相覷。然後一窩蜂跑進艙裡去。我暗忖,這艘運送船沒有兵艦護衛,萬一被敵方探悉受攻擊的話,只有死路一條。為什麼軍部這樣疏忽大意?也許,新高丸滿載的是台籍軍夫,反正日籍軍人沒有幾個,這批死掉了再徵多的是。也許,作戰上的判斷輕視敵方的威力……可是現在已收到警報了。能躲得過這場災厄嗎?
新高丸在茫茫的大海中進不進,退不退,也不拋錠,像失去舵的孤舟般飄泊了一夜,奇怪的在裡頭並沒有半點風吹草動,到了翌日早晨方接到解除警報的電訊,我們的船又啟航了。一股子的悶氣和不安,隨著船首衝浪的聲音一掃而空。我一躍登上甲板上深吸一口海風,這時候真切地體會到「一望無際」「萬里波濤」這些雄壯的字眼給人啟示的力量。自從出娘胎活了二十年,蟄居故鄉癡癡呆呆地虛度歲月,的確,我是井中蛙真不知大海的開闊廣大,自覺可憐又可笑。
經過七日七夜的航程,我們的新高丸終於駛進吳淞港了。停靠在碼頭,一批批下船登陸,我第一步踏上祖國的泥土。噢!祖國喔。我無時無刻嚮往的祖國,我夢裡縈懷的祖國!終於看到您了。剎那間有一股難以言喻的喜悅和自相矛盾的感觸交錯湧上心頭。放眼望去,離碼頭不遠的地方,一尊被炸毀的礮台剩下半截在陽光下黑黑發亮讓人憑吊。那就是聞名的吳淞炮台吧。這一帶沒有看見一個中國老百姓,兵!兵!兵!所有的全是日本士兵,沒有國人的國土,第一眼看見的祖國就是這樣悲戚的現象,不禁心酸了一陣子。
上了軍用大卡車,排成一列長蛇陣向目的地前進,一路上滿目瘡痍,廣披萬里的河山一片蕭條,到處人煙稀疏、田野荒蕪,戰壕、碉堡比比皆是。啊—這就是受難的祖國一幅凄涼圖。
車輛轆轆不知走了多少路程,已經到達了目的地的江灣了。我們的營舍就在轄區內的一個小村莊名叫「夏家塘」。大約三、四十戶的小聚落,弄得面目全非四處殘垣破瓦雜草叢生,大小民房蒙遭砲火的洗禮呈現七零八落,殘骸纍纍,令人不敢卒睹之感。由江灣至大場二鎮之間,一帶平野宛若無人之境,荊草苒苒、茅葦萋萋,顯出荒涼殺伐的景象。也許,這裡的壯丁都為了衛國殺敵上戰場去了。剩下來的婦孺老幼躲避戰火成了難民,不知流落何方。
下車後即時編隊,我屬第一小隊第八班,同班的弟兄都是老同鄉。住進了營舍,這天全員休歇,第二天開始作業。各人拿著大鐮刀向廣漠的荒野進軍。我們這大批的侵略者以新主人的姿態出現,也像拓荒者披荊斬棘,孜孜墾開了一大片土地。一個月後由台灣運來了五十頭耕牛來助陣,「江灣軍農場」於焉形成了。
大陸的初夏北風習習,朝夕還有些微涼意,可是日頭當中的時候,還是酷熱迫人,工作時每每汗流浹背。沒有做過粗活的我來充當莊稼漢的角色,是件很艱苦的差事。不過比起在第一線受砲彈洗禮、和死神搏鬥、不眠不休地搬糧食、搬子彈的軍夫們來算是天大的幸運,而且我這個反叛的小皇民,壓根兒不願為日本天皇陛下效忠,工作不費力,偷偷懶懶地,不知情的弟兄都譏笑我是天生的懶蟲。白天工作,晚上大夥呆在營舍裡頭聊天、下棋,有的玩起撲克牌「打拿破崙」來。這些玩意兒是班裡「小韓信」發明的傑作。「小韓信」的本名叫做莊玉林,他機智且具有小天才,當大伙兒空閒時無所事事,覺得生活枯燥無味,那時候提出棋子教我們消遣的就是他。他撿拾一些磚瓦磨成圓片,上面刻上將、士、象、車、馬、炮字樣,棋子製成後,又在床版上畫個大棋盤讓大夥玩起來。後來為了製作一付撲克牌更費苦心。他拿信箋一張張合糊起來,然後裁成五十四張牌,牌面的圖案畫得精采別緻,牌裡的黑桃、紅心、黑梅、紅磚都且不說,他畫的十八世紀歐洲的國王、皇后、水兵真是維妙維肖,十足發揮他天才的本色。因此我恭送他這個「小韓信」的雅號了。這是引自漢朝名將韓信在軍中設賭振作士氣的故事而來的。莊玉林被叫小韓信笑逐顏開沾沾自得呢。
有一天,友永小隊長帶來了令人興奮的好消息,團本部發令准隊員每逢星期天可以請假外出了。能得去江灣、大場、上海逛逛街了。聽說江灣有酒家,大場的茶館是有名的。上海是國際都市,嫖賭玩樂應有盡有,難怪大夥兒弟兄樂得不可開交,恨不得明天就是星期日,好來擺脫軍中枯燥無味的生活,出去街市遣散無聊、開開眼界。消息發佈後的第一個星期日那天,一大早小隊長室前大排長龍,爭先恐後地請假報名領取一張外出證。江灣、大場可以個人自由行動,但是上海即須團隊有人領班。所以大夥兒弟兄都一窩蜂湧到江灣去了。這個鄰近上海不遠的小鎮江灣—一條彎曲不整的街道,兩旁的人家店舖高矮參差不一,大小房屋傾塌荒廢不堪,偶爾有一、兩家能屹立著,那是稀少的鋼筋水泥造二層樓房。但躲不了戰火的災厄,砲痕纍纍、槍瘡歷歷,足證這裡是上海防衛戰的第一站,曾經發生過何等激烈的戰爭。鎮內處處挖掘了長長的壕溝,佈設碉堡,想起一年前,國軍的健兒們為國家、為生存奮勇抗禦敵人來侵的情形歷歷浮在眼前。這時候,我的思維突然惛惘停頓,感情陷入極度矛盾狀態中。回顧自己身上的日本軍裝,這是一種諷刺,是一種不可原諒的矛盾,心坎裡一股酸澀的無奈感久久不能拂去。
由於日本戰地司令官在佔領區內貼出告示,呼籲善良百姓回來安居樂業,又派出宣撫班到處宣傳,避難流浪四方的住民陸續回到自己的家園來了。幾家破碎不堪的店舖,經主人潦草修整後重新開張,南北貨店、茶肆、理髮鋪等各行各業競相做起生意來。鎮中一家比較完整的水泥建築物早被一個日本浪人佔為私有,略加整頓裝潢後掛出一塊「江灣食堂」的招牌大肆營業。我抱了幾分好奇踏進了這家食堂。寬敞的室內設備非常簡單,長方形的木桌,配以長板凳子,排得整整齊齊。也許是星期天,三排桌都擠得滿滿的,客人清一色的日本士兵,我們農場裡的幾位弟兄也捷足先登混在那裡。使我驚奇的是七、八位中國姑娘輪流地接待著客人。看來年紀很輕,大約十七、八歲左右吧,站在櫃台的會計小姐也是中國女人。她年紀稍長,一對烏溜溜的眼睛甚為迷人。這群服務生一律藍色旗袍,輕妝淡抹沒有半點俗氣,可見是來自鄉下的姑娘。後來聽說,這些姑娘們是被日本浪人老闆強制拉來的。雖然老闆還有一點良心,月支五元的薪金。但誰都很不願意幹這種半妓女生涯。因為這裡的客人統統日本鬼兵,生性殘忍好漁色,一進來就是毛手毛腳、滿口髒話也無人敢去得罪他們,只好笑在嘴裡,苦在心裡,勉強忍耐應付了。幸得憲兵隊有時也派員出來巡邏,雖然飽受輕薄,卻免遭鬼子的強暴就算得不幸中之大幸了。
客人愈來愈多,室內一片嘈雜的嬉笑聲使我無法忍受,把半杯的生啤酒一氣喝完匆匆地走出來。回程走了一段路,倏地想起一件事來。自從踏上祖國的泥土那時候起,都一直想和當地的同胞們多接觸,學習中國話和他們多溝通感情。可是一到營地軍規甚嚴,不許自由行動,沒有機會可來實現我的願望,現在機會有了。要在那鬼食堂嘔氣,倒不如到中國人部落走走,打定主意,步伐自然輕快起來。沿著河邊的小徑不回營舍,朝向大場鎮那邊走十多分鐘路,已至一造小巧的石橋,仔細一看卻刻著「嶺南橋」,斑剝不堪、模糊不清了。曾聽過伙食班長老張說,經過這造橋向南走兩小時就到「八字橋」,離上海閘北不遠,那裡有著宏偉壯麗的「聯義山莊」。所謂山莊者就是墓地,上海人死了,就要購地埋喪,因為這裡沒有公墓,可能全國什麼地方都沒有,這樣落後的社會令人吁嘆不已。上海近郊這門生意一枝獨秀大發利市。
越過石橋,踏著紅色泥土小徑踽踽而行,走了一段路我發現前面有人,一男一女的模樣,好不容易遇到祖國的同胞,碰面時我一定好好跟他打個招呼,這樣想著,加快了步伐向前走去。這時意外的事情發生了,他們一發覺我,好像遇見鬼似地大嚇了一跳,驚惶失措亡命也似地跑入樹林裡去。我非常訝異,這是為什麼呢,等我冷靜思考後得到的結論是,他們以為我是日本軍人。
我們外出時嚴令服裝整齊,整套日本軍裝的我在他們的心目中是兇神惡煞,所以慌忙避之三舍呢。難怪中國同胞謂日本兵曰「東洋鬼子」,日寇在中國大陸如何殘虐霸道由此可想而知。
蜿蜒的小徑兩旁樹木密萃,枝葉蒼蒼遮蓋了天空,好像沒有太陽的地方。我抱著一個似惆悵也像惻隱的心走在陰暗的泥土上。沒有時間的辨別,也不知走了多少路,直至路樹中斷了,終於來到聯義山莊的大門前。強烈的陽光一時使我眩暈,我佇立在陌生的鐵門前。抬頭仰望,高聳的牌樓是經石匠雕琢過的石塊砌成的,兩旁連接著磚牆圍繞四周,佔地非常寬闊,幾乎上百甲之譜了。瞭望莊內有涼亭假山、小河石橋,環境優雅,尚有巍峨廟宇隱約可見,極似觀光勝地一般。
牌樓下面唯一的出入口處鐵門緊閉著,而且下了個大鎖。這個紅漆鐵門已處處落漆生鏽了。也許,無情的戰火波及,這裡的主人疲於奔命,無人看管任其風雨侵蝕的緣故吧。鐵門上懸掛一塊長木板,寫著「日本人小原榮次郎佔領」。多麼絕!我想這是極惡非道的日本浪人精心的傑作吧。
日本軍閥佔領中國的城市鄉鎮,日本浪人竟把這靈魂的安息所「山莊」也給佔領了。日寇的侵略使千千萬萬的生靈塗炭,連無辜的鬼魂都蒙受無限的侵害和困擾,這種無法無天的作為真是令人髮指。
中國人啊,中國人!奮起吧,奮起吧!這麼慘大的國恨家仇無報豈肯干休?
我正在慨嘆呼嘯著,這時對面一家低矮的木造民房裡,傳來沙啞的咳嗽聲。把視線移轉過去,由昏暗的門角裡走出一個人影來。瘦黑的肢軀披著藍色粗布衣,彎腰曲背的矮個子,蓬髮垢面,兩隻低陷的眼眶發出異樣的光芒一直瞪視我。那是充滿了敵意的神情,不由地全身起了慄寒。我聯想起「鐘樓怪人」裡那佝僂來。稍時後,我鼓起勇氣走近老人,十分慇懃地打個招呼。
「老先生您好。」
「……」
佝僂老人本能地倒退了一步,目不轉睛的瞪住我。為要舒解他的敵意,我刻意顯出十分友善的態度裝著笑容。我這番努力沒有奏效,老人仍然無動於衷冷漠漠地。他的眼神籠罩著重重的疑雲,很顯然的存著深刻的憎恨和戒懼。我感到灰心又尷尬。難怪嘛,我這身打扮在他心目中是個可憎的日本兵,是他們不共戴天的可惡敵人。我怔了老半天不知如何是好。
「老先生別怕啊,我不是壞人……」
我恐怕他聽不懂,比手畫腳地。老人仍然三緘其口不吭一聲。我有點急了。
「吔!……不要誤會,我不是東洋鬼子,是……台灣人。」
我索性撿起一支柴枝把台灣人三字寫在地面。老人的臉微動了,他的目光追索著地面的字,終於詑異地顫動唇角輕微地唸出來。
「台……灣……人。」
可是他的發音是「提……喂……菱。」我知道,這是他們的地方鄉音。我忖量著,他已瞭解我是台灣人,並非他們憎惡的日寇,我們可以開懷暢談了。
「是的,我是『提喂菱』,儂明白啦。」
我略鬆口氣移步接近他。但出乎意料之外,令人驚奇的一幕出現了。佝僂老人一瞧我挪動身軀,煞地全身發抖慌忙縮退了幾步,一隻腳已跨過門檻去。
「不要進來……,阿拉家裡沒有姑娘……」
一聲悽叫也似的猛喚令我怔住了半天。
「老先生我……」
「不……不……阿拉啥東西也沒有,阿拉苦來西啊。」
「老先生……我是……」
我進一大步想和他解釋什麼似地。
「儂……儂……若強進來阿拉就殺……」
那是嚴厲的、悲切的,由肚子裡拚力發出來的絕叫聲。
這像無限的怨懟和抗議的哀號,宛若六月雷霹般重重地震撼我心田。
我思索了好久,終於想通了。
—沒有姑娘……沒有啥東西……原來中國老百姓對日本兵的第一印象就是姦淫和搶劫。中國人痛恨日寇的心亦其來有自,這個怫恙難能拂拭了。凡是大漢子民誰能對日寇的殘暴橫行無不痛心蝕骨同仇敵愾呢。我頭一遭由佝僂人的口裡聽到受盡苦難的同胞發自內心無奈的心聲。
從八字橋回來之後,整個一星期日夜戚戚難安。檢討那天的尷尬場面,被路人視如鬼神般敬而遠之,又遭佝僂老人執惡如仇怒責一場。究其原因實在因我身著軍裝呈現日本軍兵的形象所致,語言未能暢通也是最大原因。基於這點認識,我焦急著學習祖國語言,便托老張到上海書店弄來一本「支那語會話」,認真地研習起來。老張是伙食班長,由於身分特殊趁得領取糧秣的機會順便開溜上海逛逛。這天他更帶回一本書名「未死的兵」的小冊子,是日本名作家石川達三的從軍報導文章,內容大膽地暴露日軍在佔領區內許許多多慘無人道的所作所為,閱後真是感慨萬千。戰爭與姦淫是拆不開的最大罪惡,戰勝軍在佔領區內就是暴君,就是一切的主宰者了。在這裡沒有天理、沒有良心,也沒有法律,更沒有道德可言。「反抗」二字早在他們戰勝者的字典裡被抹煞掉,一切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的原則支配下,億萬無辜的百姓們為生存只好認命忍辱偷生,苦度暗無天日的日子了。
|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太陽旗下的小子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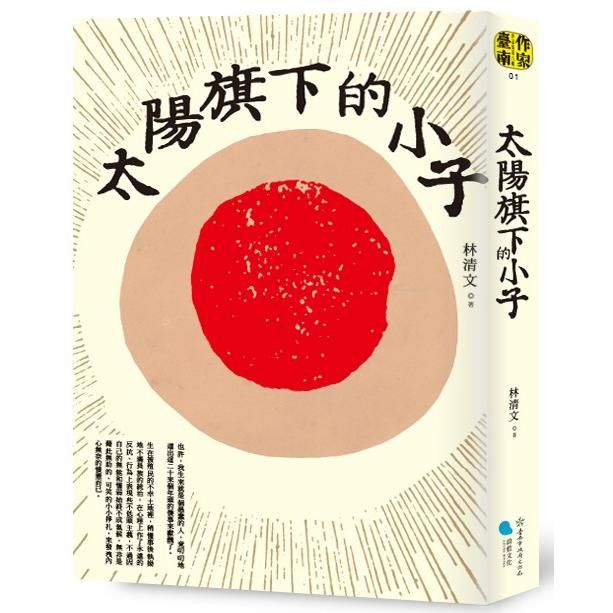 |
太陽旗下的小子 作者:林清文 出版社:蔚藍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9-12-09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太陽旗下的小子
林清文的這本自傳小說,有兩個方面特別值得參考。
首先是真實的人性;其次是歷史的見證。
把一個小學時被日本老師罵「清國奴」、在臺灣「光復」後落魄天涯的理想破滅者真實地袒露讀者眼前。作者對地景的描摹,對社會環境和家國變遷的敘寫,提供了日治時期很好的研究材料。
作者在書中感恩不已的小學五年級的日籍導師田中先生,期許他做一個「有作為的臺灣人」,他是否實現了呢?留給知者識者去評斷吧。
他在文中自稱「一個不倫不類的叛徒」,是否貼切,也留給讀者在字裡行間披索答案了。
「也許,我生來就是個愚蠢的人,竟叨叨地道出這二十來個年頭的傻事來獻醜了。
生在被殖民的不幸土地裡,稍懂事後執拗地不滿異族的統治,在心理上作了永遠的反抗、行為上表現些不低頭主義,不過因自己的無能和懦弱始終不成氣候,無非是藉此無助的、可笑的小小掙扎,來發洩內心無奈的憤懣而已。」——林清文
作者簡介:
林清文(1919-1987)
臺灣臺南佳里興人,鹽分地帶重要文學作家,為「北門七子」中最年輕者。創作文類包括新詩、散文、小說及劇本等。長年參與劇團巡迴演出,其編、導、演之「廖添丁」一劇,風靡全臺。曾獲臺灣新文學特別推崇獎。
章節試閱
第十六章 祖國.同胞
矇矓中醒來時,新高丸在一望無際汪洋大海之中。遙遠的水平線上浮現一輪紅紅的大太陽。一片波光閃爍,藍青海浪濤濤,一群海鳥展翅在天空飛翔,呈現一幅和平安祥的景象。這是大自然美麗的創意、上帝慈悲的期求。可是地球上醜惡的人類為求達到野心的滿足而逞威,在這煦光普照大地的一角落裡,正戰火漫天,違悖人道的姦淫、無情的殺戮、殘忍的擄掠等等,排演著人間最大的罪惡悲劇呢。假如沒有一個萬能的主宰者奇蹟出現,把人類的齷齪慾心滌除淨盡,否則這個世界未來的戰爭是永無止境地繼續發生。將近中午時分,船中發出...
矇矓中醒來時,新高丸在一望無際汪洋大海之中。遙遠的水平線上浮現一輪紅紅的大太陽。一片波光閃爍,藍青海浪濤濤,一群海鳥展翅在天空飛翔,呈現一幅和平安祥的景象。這是大自然美麗的創意、上帝慈悲的期求。可是地球上醜惡的人類為求達到野心的滿足而逞威,在這煦光普照大地的一角落裡,正戰火漫天,違悖人道的姦淫、無情的殺戮、殘忍的擄掠等等,排演著人間最大的罪惡悲劇呢。假如沒有一個萬能的主宰者奇蹟出現,把人類的齷齪慾心滌除淨盡,否則這個世界未來的戰爭是永無止境地繼續發生。將近中午時分,船中發出...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自序】
【主編序】一個不倫不類的叛徒 / 李若鶯
本書內文一九八○年首度在「自立晚報」連載刊出時,標題「愚者自述」,次年刊載結束,經作者多次增刪修改,並易書名為「太陽旗下的小子」,於一九八八年在作者哲嗣林佛兒主持的「林白出版社」出版。不管是「愚者」或是「小子」,都隱微暗示作者寫作這部取材生命經歷的傳記小說的部分心態。諷喻自己在那樣時空背景下反抗高壓體制與異族統治的作為,或者竟只是青春焰火燃燒下的愚行,而個人,終究也只是一株小草,一個不起眼的「小子」。
作者出生於一九一九年,日本據治臺灣已二十四年;...
【主編序】一個不倫不類的叛徒 / 李若鶯
本書內文一九八○年首度在「自立晚報」連載刊出時,標題「愚者自述」,次年刊載結束,經作者多次增刪修改,並易書名為「太陽旗下的小子」,於一九八八年在作者哲嗣林佛兒主持的「林白出版社」出版。不管是「愚者」或是「小子」,都隱微暗示作者寫作這部取材生命經歷的傳記小說的部分心態。諷喻自己在那樣時空背景下反抗高壓體制與異族統治的作為,或者竟只是青春焰火燃燒下的愚行,而個人,終究也只是一株小草,一個不起眼的「小子」。
作者出生於一九一九年,日本據治臺灣已二十四年;...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局長序 臺南繁花盛開 文學盡訴衷曲 文/葉澤山
總序 文學森林的新株 文/李若鶯
主編序 一個不倫不類的叛徒 文/李若鶯
林白版原序一 最頑固,又最可愛的學人 文/林芳年
林白版原序二 我的父親——林清文先生——祭文代序 文/林佛兒
▍第一章 ▍ 生在這裡
▍第二章 ▍ 問題學生
▍第三章 ▍ 田中老師
▍第四章 ▍ 初出茅廬
▍第五章 ▍ 情竇初開
▍第六章 ▍ 瘋狂之夜
▍第七章 ▍ 心猿意馬
▍第八章 ▍ 無聊的日子
▍第九章 ▍邂逅
▍第十章 ▍ 日本婆仔
▍第十一章 ▍ 房東阿姨
▍第十二章 ▍ 淘氣姑娘
...
總序 文學森林的新株 文/李若鶯
主編序 一個不倫不類的叛徒 文/李若鶯
林白版原序一 最頑固,又最可愛的學人 文/林芳年
林白版原序二 我的父親——林清文先生——祭文代序 文/林佛兒
▍第一章 ▍ 生在這裡
▍第二章 ▍ 問題學生
▍第三章 ▍ 田中老師
▍第四章 ▍ 初出茅廬
▍第五章 ▍ 情竇初開
▍第六章 ▍ 瘋狂之夜
▍第七章 ▍ 心猿意馬
▍第八章 ▍ 無聊的日子
▍第九章 ▍邂逅
▍第十章 ▍ 日本婆仔
▍第十一章 ▍ 房東阿姨
▍第十二章 ▍ 淘氣姑娘
...
顯示全部內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