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名稱:與己同在
一位心理學家,在一個特殊的對話情境,記憶脫離了常軌,回到三十年前的時空,因緣際會致使她誠實而幾近毫無保留地呈現自己、挑戰自己,為了追尋真理,也為了寫給想找自己、修復自己、想自我創造、努力要活出自己,卻不時陷入迷茫的外甥女──安。
這書的開始是在臉書的訊息方塊上。作者在紐約這頭快速敲著鍵盤與地球另一端的安對話,原本僅是為了回答當社工的她,人生何去何從的大哉問。
對話的議題一個接一個出現,一個尚未完成下一個已經在等著揭露,最後發現探尋的各種存在議題,譬如:自卑、自由、錢、權力、關係、愛情、原生家庭、人性陰影、創傷因應、自我探索、生涯發展、孤獨、個體化、宗教、靈性發展、死亡、失落悲傷等等,幾乎也是所有人都會持續不斷的經歷、必須面對的共通問題。
三十年前的人生驟變,以及後來無法直視的變調,原以為塵封,而今卻發現從未遠離!在生命劇烈的震盪裡,往事一幕一幕湧現,過去與此刻不斷交錯重疊……
這位心理學家的生命故事,也是芸芸眾生的故事;就好像一首歌,無論是悲傷或歡樂曲調,讓人想聽完就不僅是歌者一個人的歌,而是每個想聽這首歌的人的歌。而這首生命之歌的迴盪,就如安寫給作者的信中所言:
「對我而言,有一個人相信我,願意跟我分享私密的往事,讓我感到自己被人重視、被人信任,我在過程中嚐到了好好被對待、被珍視的滋味,光是這個過程就足以讓我覺得自己很重要,相信自己可以克服困難,有能力去改變。
「讀這本書的過程,像是經歷一次生存實錄,步履維艱,曲折離奇,常常重擊我的心,直至心中深處,可是這個陰暗處往往透著一絲光,讓人看到一些希望與轉機。
「妳以真實的妳喚起我去面對自己的真實,妳用妳的生命故事影響了我的生命,讓我有力量去行動。」
作者簡介
汪淑媛
紐約大學(NYU)發展心理學博士,現任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教學之餘從事寫作,實務帶領心理諮商師、心靈藝術工作者、社工員、教師以及社區大眾讀夢探索潛意識,覺察統整自我,挖掘心靈活水,趨近生命本質,好好存在。著有《夢、覺察、轉化─南勢角讀夢團體現場》、《好好存在》;翻譯《讀夢團體原理與實務技巧》、《佛洛伊德與偽記憶症候群》;最新著作為《與己同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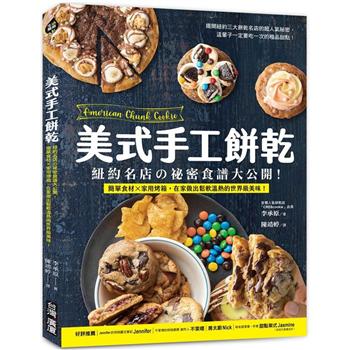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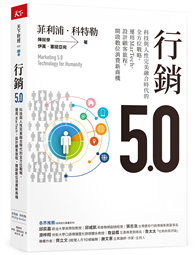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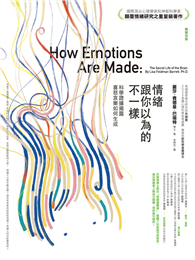


這是一本非常值得大力推薦的書籍。 前陣子生活過得很不順遂,失業讓身心俱疲。內心焦慮不安,過去憂鬱症的症狀又復發。還出現大量掉髮的現象,生活很(盲)然而不知所措。因緣際會之下看到(與己同在)這本書。 (真): 閱讀這本書後,很佩服汪教授巨大的勇氣,能真實地將過去在愛情和工作上的事情,赤裸裸地呈現在大眾面前。漸愧自己還沒有這樣的勇氣表達。看到汪教授過去生活所經歷的考驗和打擊。反觀自己的痛苦,相較之下,自己顯得無病呻吟和可笑至極。 (善): 靜下來看本書的過程,像是在接受心理治療,作者先邀請讀者聽 她說故事,其中有很多悲歡離合的情節,也遇到很多曲折變化。她像慈母般娓娓道來,分享如何克服一道又一道難關。漸漸地撫平我受傷的心靈。作者有難能可貴的人生的智慧,並努力地實踐在生活中。有份擇善固執的大愛和慈悲心腸,想解救芸芸眾生脫離苦海的大志。 (美): 看完這本書,雖然無華麗的場景或優美的詞藻,但這本書字裡行間散發一股(拙美)的氣質。如一幅只用筆墨呈現的長卷水墨畫,雋永深刻,讓人流連忘返。只要你肯靜下心來細心地品味,就能體會到書中那獨特的境界。 作者書寫的語調,彷佛像流浪者,抱著舊吉他,手指撥弄琴弦,簡單的音符和旋律,卻道盡人生的悲歡離合和歲月滄桑。驚嘆一把吉他卻比一個大樂團,更有著難以形容的(穿透力),穿過層層的牆,傳達到我的心靈,引起靈魂的共鳴。 每一章節,如同一張張泛黃的黑白照片,散發往事和回憶的芬芳。雖然沒有鮮豔的色彩,卻讓故事的層次和明暗更豐富,呈現人和人之間獨特的情感。作者有化繁為簡的魔力,吸引我專注地閱讀。 每當我看完一本書,都會閉上眼睛,想像那本書給了我什麼樣的風景: 眼前在黑暗中慢慢浮現的風景是: 作者去爬一座高山,雖然旁人反對,作者仍勇敢地和朋友結伴而行出發。沿途出現不同的風景,作者的物資貧乏,但她們抱著取經的精神去挑戰。剛開始還能邊爬山,邊欣賞沿路的美景。呼吸和以往不同的空氣。 但天公不作美地開始下起雪,四周逐漸變成白茫茫的雪花世界,氣候變得越來越惡劣。作者和同伴勇敢地走下去,冷冽的寒風不斷地吹襲。最後作者必須揹著同伴前行,雖然舉步維艱,眼前看不到願景。但她咬牙苦撐,山路變的崎嶇蜿蜒,稍有不慎,可能會墜入山谷,過程歷經坎坷危難和顛沛流離。 路途中更遇到無法對抗的暴風雪,讓作者萬般不捨地下山,感嘆人生無常。但作者休息後仍然重拾行囊和堅毅的勇氣,再去攀爬那座高山。 也許是(愛)和(宗教)的力量,引領作者走完最艱難的路途,到達山頂。作者抬起頭,仰望著陰鬱的天空,忽然有一道陽光,穿透灰暗的雲層,照在作者滿是風霜的臉上,那道光芒是上天對作者的恩賜。唯獨作者能心領神會,露出了欣慰的微笑,這一幕讓人為之動容。作者經過歲月的沉澱,想將那趟路程和更多人分享。 回想那些年在山上每跨出步伐,就陷入積雪中,要使力地拔出腳,才能再走下一步。作者的身後,留下很漫長而深厚的腳印,雖然融化後了無痕跡,但那些腳印卻在多年後被作者幻化成文字記錄下來,讓那辛勤的瞬間變成永恆。 看完這本書後,發現作者在書中有提到(書寫)的神奇力量,能有療癒的效果。於是準備筆和稿紙,開始練習書寫,規定自己每天要寫相當的量。將內心所有的痛苦,煩悶,焦慮寫出來。發現身心起了很大的變化,可以將內心的負面情緒宣洩出來。 因為忙於寫出每天規定的量,讓自己處於忙碌之中,生活有了重心。不再空於胡思亂想,能避免內心被情緒綁架。身體也變得越來越健康。讓我有勇氣揮別過去,去體驗不同的人生,學習接納不完美的自己、善待自己、愛惜自己。現在能從做喜歡的事情從中體驗快樂。(與己同在)對讀者而言,就像是夜晚天空中一顆明星,在浩瀚的海洋中,指引航向正確的方向。 非常感激 汪教授 和 (與己同在)這本書拯救了我。 誠摯地推薦大家買這一本書好好閱讀,容我用直白的比喻: 作者好比一座發電廠,無私地燃燒自己,發出巨大的正能量。每一位讀著所買的書,彷佛在不同的地方立下一座又一座電線杆。這樣作者才能將源源不絕的正能量傳達到台灣不同的角落,照亮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