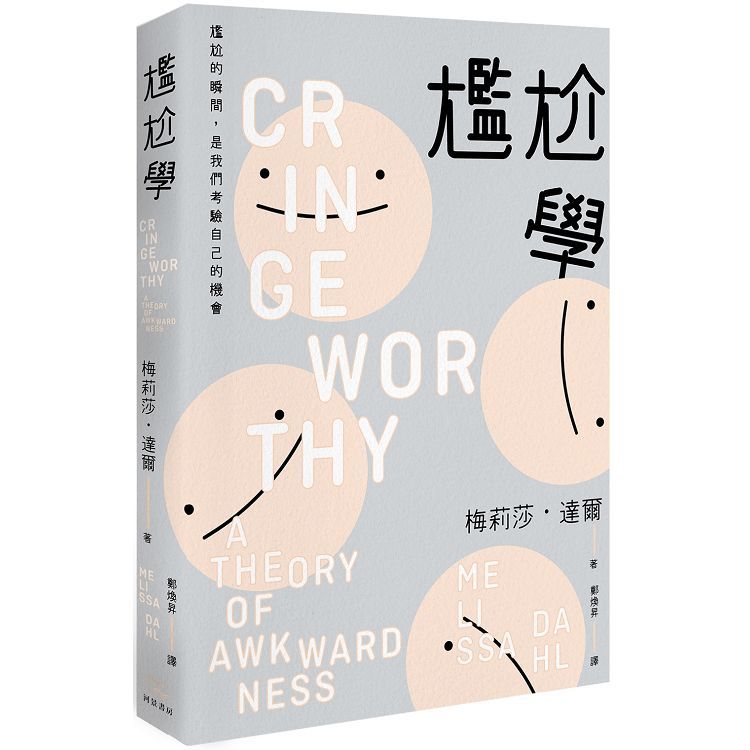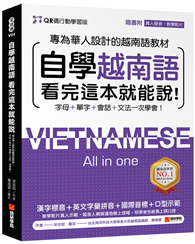圖書名稱:尷尬學
在會議中暢所欲言後你感覺非常棒,但現場每個人卻一語不發……
鄰居說完「哈囉」,而你竟回答「謝謝,我很好」……
突然發現廚房的菜瓜布黏在毛衣上,而你已經走過兩條大馬路……
這些瞬間都會讓人冷汗直流,但你有沒有想過或許這些至為尷尬的時刻,
其實是我們的人生至寶?
梅莉莎‧達爾身為《New York》雜誌旗下「Science of Us」網站的共同創辦人,對尷尬的處境一點也不陌生。
在尷尬了一輩子之後,她的好奇心盯上了「尷尬」:這種人皆有之但沒人多瞧過兩眼的情緒。於是她踏上了對尷尬一探究竟的旅程──結果她發現,尷尬其實可以充實我們的人生:尷尬不必然會讓我們感覺孤單,事實上,但凡所有會讓我們尷尬的人事物,都在提醒著我們彼此間的羈絆。
在本書裡,達爾親炙了人世間最怪誕、最令人視為畏途的尷尬角落。
她鼓起勇氣與陌生人在匆促繁忙的紐約地鐵裡聊天,她咬著手帕用純友誼版Tinder約了網友見面,她拚了老命報名成為即興喜劇課程的學生,她甚至豁出去,把中學日記唸給一群素昧平生的觀眾聆聽!
在體驗這一切後,她懂得了一個道理:尷尬的瞬間,是我們考驗自己的機會。當其他人都在裝酷、裝冷豔的時候,你可以比他們更勇敢,更寬容──也在同時間更不畏尷尬地做自己一點。
作者簡介
梅莉莎‧達爾
以資深編輯一職服務於《New York》雜誌的時尚網站分支《The Cut》,並主跑其中的健康與心理線。2014年,她與人共同創立了《New York》雜誌旗下十分有人氣的社會科普網站〈The Science of Us〉。她的作品曾刊出於Elle雜誌、Parents雜誌與TODAY.com網站等媒體。《尷尬學》是她的處女作,她的推特帳號是@MELISSADAH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