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異鄉人:翻案調查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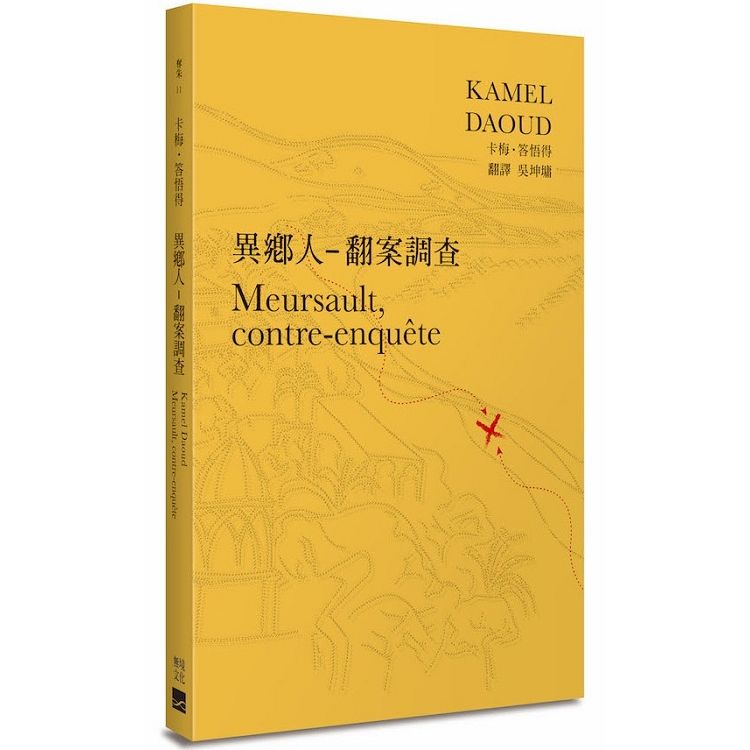 |
異鄉人:翻案調查 作者:卡梅.答悟得 / 譯者:吳坤墉 出版社:無境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9-10-25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本書作者是當今西方世界最重視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以法語寫作的阿爾及利亞作家、記者/時事專欄評論家卡梅•答悟得Kamel Daoud先生。
答悟得專欄評論文章皆同時以多種語言發表在法國(Le Point 週刊)、美國(紐約時報)......等西方及阿拉伯世界重要媒體。2016年獲得Jean-Luc Lagardère年度最佳記者獎,2019年獲得法蘭西研究院頒發的Cino Del Duca 文學成就獎。後者地位崇高,獎金僅次於諾貝爾獎。
本書為七十年來首部在文學的才情與思想的深度都能與文豪哲學家卡繆的傑作《異鄉人》並駕齊驅的作品,榮獲2015年龔固爾首部小說獎。法國世界報權威書評:「從今以後,《異鄉人》與《異鄉人-翻案調查》必須當做上下冊來閱讀。」
入圍2019年Openbook 好書獎。
在西方世界,人們先由卡梅•答悟得榮獲2014年法國龔固爾首部小說獎的名作《異鄉人-翻案調查》(Meursault, contre-enquête )認識到他傑出的文學才情 。進而發現他在阿爾及利亞之法語瓦赫蘭日報Le Quotidien d'Oran 擔任記者與專欄作家,撰寫那些精闢而批判的評論。很快的,其犀利的觀點、精準的文字、毫無畏懼的直言,就受到媒體與知識界持續的注目。現今其專欄評論文章皆同時以多種語言發表在法國(Le Point 週刊)、美國(紐約時報)......等西方及阿拉伯世界之重要媒體。不僅促使西方社會更深入認識阿拉伯世界,反思自身的問題;同時也在阿拉伯開明人士間獲得巨大共鳴。
短短數年,卡梅•答悟得獲得諸多榮耀。較為重要的除了《異鄉人-翻案調查》獲得2015年龔固爾首部小說獎之外,2016年獲得Jean-Luc Lagardère年度最佳記者獎,而2019年更獲得法蘭西研究院頒發的Cino Del Duca 文學成就獎。此獎之珍貴不在於獎金號稱僅次於諾貝爾獎,更在於法蘭西研究院在人文領域的崇高地位。
無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以及法國在台協會將在2019年11月5號至9號聯合邀請卡梅•答悟得Kamel Daoud先生來台舉辦公開講座以及交流活動。
卡梅•答悟得兩本重要著作的中文譯本:《異鄉人-翻案調查》(小說,吳坤墉翻譯)以及《吞吃女人的畫家》(文集,陳文瑤翻譯),均於2019年11月由無境文化在台出版。
作者簡介:
卡梅•答悟得Kamel Daoud
以法語寫作的阿爾及利亞作家,同時是阿爾及利亞之法語瓦赫蘭日報Le Quotidien d'Oran 記者及專欄作家,是當今西方世界最重視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他2014年在法國出版首部小說《異鄉人-翻案調查》,無論在文學的才情與思想的深度都能與文豪哲學家卡繆並駕齊驅,立即享譽文壇,在純文學領域備受注目。而他作為記者/時事評論家,其專欄文章皆同時以多種語言發表在法國(Le Point 週刊)、美國(紐約時報)......等西方及阿拉伯世界之重要媒體。兩種身分與專業同時傑出的表現,讓卡梅•答悟得享譽國際。因為他不僅促使西方社會更深入認識阿拉伯世界,反思自身的問題;同時也在阿拉伯開明人士間獲得巨大共鳴。
短短數年,卡梅•答悟得獲得諸多榮耀。較為重要的除了《異鄉人-翻案調查》獲得2015年龔固爾首部小說獎之外,2016年獲得Jean-Luc Lagardère年度最佳記者獎,而2019年更獲得法蘭西研究院頒發的Cino Del Duca 文學成就獎。此獎之名貴不在其獎金號稱僅次於諾貝爾獎,更在於法蘭西研究院在人文領域的崇高地位。
卡梅•答悟得在台灣出版的作品有《異鄉人-翻案調查》(小說。吳坤墉翻譯。) 以及《吞吃女人的畫家》(散文集。陳文瑤翻譯),都於2019年11月由無境文化出版。
譯者簡介:
吳坤墉
無境文化出版【人文批判系列】總策劃。致力出版具批判性觀點的思潮、藝術或文學類書籍。中法文筆譯工作以人文科學類作品為主。譯作有《倡議一個批判的政治哲學--條條道路》(Miguel Abensour著,無境文化,台北,2010),《死刑犯的最後一天》(雨果著,無境文化,台北,2016)等。
2017年獲法國文化部頒贈藝術與文學騎士勳位。
今天,媽還活著。
她什麼都不講了。但其實,她可說的東西還很多。不像我,一再的加工改造這個故事,現在幾乎都記不起來了。
我是說,這是個超過半世紀以前的故事。事情發生,那時候人們就講了很多。到如今也都還在講。但他們都只提到一個死者,你看這是不是很無恥!那時候,死掉的人,明明就是兩個。沒錯,兩個。為什麼被消失?因為前一位故事講得好,好到能叫人忘掉他的罪行。而另外一個是可憐的文盲,好像天神創造他就只為了來吃顆子彈,然後就歸於塵土;一個連姓名都來不及擁有的無名氏。
我現在就告訴你:另一個死者,被謀殺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