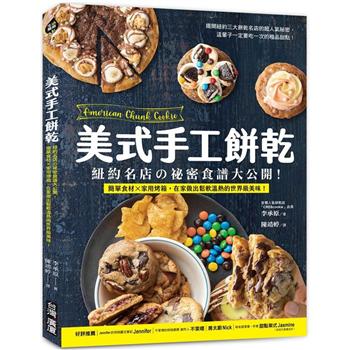康熙五十四年(1715)貴州人周鍾瑄來到臺灣擔任諸羅知縣,次年開始編修的《諸羅縣志》寫道:「夫衣飾侈僭、婚姻論財、豪飲呼盧、好巫信鬼觀劇,全臺之敝俗也。」 當時與民眾生活緊密的看戲活動,就知縣大人看來與賭博、喝酒一樣,也是臺民的「陋習」之一。康熙年間,民眾看的應該不是亂彈戲,可能是較早傳入的七子戲。亂彈戲何時來到臺灣,可以從兩方面來觀察:一是北管音樂傳入的時間,目前臺灣歷史最悠久的北管曲館彰化梨春園成立於嘉慶十六年(1811)。另一個是尋找「官音」演出的時間,現今最早的紀錄是臺南武廟道光十五年(1835)的「武廟禳熒祈安建醮牌記」有:「開演官音班九檯半,佛銀八十二元。」其他如日本人統治臺灣後整理的《臺灣私法》中的規約書、緣簿都在更晚的咸豐、光緒年間。
儘管上述有相關的文獻可以推測,但清代可確切找到名稱的亂彈戲班,有自霧峰林家頂厝林文欽家班而出的「詠霓園」,約成立於光緒十六年(1890)前後,而邱坤良主持的《臺灣地區北管戲曲資料蒐集計畫》(1991)中,最早可追溯到的亂彈班是宜蘭的「江總理班」,這是清朝紅水溝堡鹿埔庄龍目井(在今宜蘭冬山鄉)的總理江錦章(1849-1916)出資雇用伶人所組的戲班。江錦章出身有錢有勢的富農家庭,在光緒十六年(1889)錄用為東勢六堡總理,戲班可能是在他擔任總理後組成的,除供自家人觀賞外,亦由冬瓜山(今冬山)的保正對外負責經營,演出營利,該班的演員有小生憨仔、老生陳河枝、旦角阿福、大花益仔、小丑阿水等,約在1910年代初期解散。江錦章、江錦華兄弟都列名羅東福蘭社的先賢圖,他們與這個宜蘭溪南歷史最悠久的福路派子弟團應有往來。
以「北管」與「官音」為線索,是因為臺灣亂彈戲是以北管音樂做為伴奏的戲曲,音樂稱「北管」,戲曲為「亂彈」,演出使用官話與白話(即方言,通常是閩南語)。名為「北管」,是為與更早傳入的泉州閩南語系「南管」音樂對照,北管的內容包含崑腔、吹腔、梆子腔、皮黃及一些民間小戲、雜曲,兼蓄雅部與花部諸腔音樂,承載戲曲史上各聲腔流變發展的軌跡。臺灣亂彈戲主要含括「西皮」與「福路」 兩大聲腔系統,也稱為「西路(新路)」與「古路」,福路大致屬於亂彈腔系,西皮則以皮黃腔為主,並包含一些吹撥腔的成分。
若以「花部亂彈」的角度來看,臺灣的亂彈腔系劇種應包括亂彈戲、四平戲、京劇(正音)、豫劇等。中國浙江也有許多在地名後加「亂彈」的劇種,如溫州亂彈(今甌劇)、紹興亂彈(今紹劇)等。從臺灣總督府文教局1928年出版的《在臺灣的中國戲劇與臺灣戲劇調查》(《臺灣に於ける支那演劇與臺灣演劇調》),可發現日治時期臺灣亂彈班命名以「陞」(如大榮陞)、「班」(如大破布班)為多,但也有難以歸類,如「豐吉祥」等(不過民間常習稱偏名,如「大榮陞」稱為「阿食仔班」),其下演出的「種類別(劇種)」標記為「亂彈」。1970年代開始有臺灣學者以「北管戲」稱北管音樂伴奏演出的戲曲,但大家知其指的是「亂彈戲」。昔日亂彈班眾多時,以「亂彈戲」、「北管戲」區分為職業與業餘演出,或許是一種習慣,但筆者自1980年代晚期開始接觸的職業戲班,如「新美園」、「亂彈嬌」、「漢陽」,皆加上「北管劇團」定名。為方便行文,並與中國的亂彈聲腔劇種區分,本書以「臺灣亂彈戲」、「北管戲」兩個名詞交互使用,但其指稱的內容相同。
亂彈戲在臺灣的興盛與各地蓬勃發展的北管子弟團密切相關。「子弟團」指的音樂或戲曲業餘參與者──「子弟」合組的團體,他們練習的空間稱為「曲館」。臺灣各地的音樂類社團以北管最多,遂有人將北管子弟演出的亂彈戲稱為「子弟戲」。1970年代本地轉型為工商業社會之前,各地可見的北管子弟團培育了許多懂得「看門道」的觀眾,亂彈班的表演者因而戰戰兢兢,不斷提升表演水準。戶外廟會是北管戲最常出現的演出空間,上演數代表演者持續編修的成果,也散播戲劇文本(dramatic text)的思想內容。相較於亂彈戲傳播時間的綿長,其戲劇文本的研究卻非常有限,主要原因在不管傳承的藝術家是否識字,口耳相傳依舊是教學的主要方式。職業班或子弟團因應需要,可能會將演出內容書寫下來,這些「口語衍生的文本」稱為「總綱」。試圖以文字保存活生生的舞臺表演,天生便有許多侷限:最明顯的是小花長篇的諧趣言語,通常僅以「白話」或「白話不盡」帶過;同一個音樂符號包含不同的唱腔,如果沒有點板難以分辨,得由老師說明才能確定;牌子、鼓介的標記非常精簡,除了特別作為教材者外,通常不會在唱詞旁註明工尺譜,遑論記載身段動作。這或許是呂錘寬說:「當前的北管戲研究,主要為對唱腔的蒐集與整理,並做初步分析,至於劇本、身段方面,幾乎尚無系統且深入的研究」的原因。
北管戲的口語紀錄形式除了總綱外,還有僅記載單一行當唱詞、臺詞的「曲爿」。在沒有影印機、複寫困難的年代,演員在排練的過程中,自然知道與他人接續的順序,不會因為沒有總綱而困擾,甚至他們會覺得自己的部分都不一定學得全,並不需要知道全部的內容。 由於「曲爿」屬於私人學習之用,反倒不如從某些子弟團借出或流出的總綱來得常見。
昔日北管圈大多將總綱視為團體的重要資產,除非彼此有相當的交情或是著眼於互抄互利,通常不會輕易示於外人。近年透過國家文化資料庫、南北管主題音樂知識庫、彰化南北管戲曲館、臺灣戲劇館等蒐集,或相關計畫成果的出版,原本的封閉性雖被打破,但若沒有親身學習,依舊難以掌握實際表演的全貌。屬於歷代集體創作的總綱與「曲爿」多以手抄本形式存在,字跡雖不一定潦草,但常採用簡字、俗字來記錄發音,與一般劇作家作品不同,有時文意不通,又無句讀,常讓讀者備感困難,兼以音樂標注簡略,很難自行辨識學習。缺乏注解、直接數位化的手抄本,或有保存文獻的功能,但對劇種保存功用不大。李殿魁在〈讀戲曲館出版的集樂軒楊夢雄北管抄本〉中提到:「近年來政府花錢將許多老抄本數位化,好像可以保存傳世,但沒有仔細整理、解讀、傳習,只是做了一大堆的白工,徒然浪費公帑,而無可預期的成果。」可謂一針見血。
1991年我從研究羅東福蘭社的歷史、北管總綱與演出,開始與此領域結下不解之緣,關於歷史研究已有相關的書籍發表,然而關於戲劇文本與表演文本的方面,每一主題都各有關卡必須突破:有些是方法學的重新思量與改用,有些是比較資料蒐羅困難,有些是需要轉換俯瞰角度……。如同我曾藉由博士論文研究北管社團從清朝到二十世紀的發展,探尋該樂種與劇種由盛轉衰的原因,筆者也想追尋臺灣亂彈戲在近兩百年裡,是否已因本地社會、風土的影響,產生不同於他處的地方特色?相較於其他劇種,北管戲少有新創劇目的情形令人不解,因觀察到總綱中套語與主題運用頻繁,在研究初期便希望將其結構化整理,作為未來新創劇本的養分。隨著對「傳仔戲」此一課題的鑽研,我逐漸了解亂彈班曾有改編演義故事或借用其他劇種劇目演出「活戲」的情形,而演員之所以具備此等能力,是由於他們已掌握戲劇在自報家門、場景處理、應對方式時一定數量的模組處理。昔日藝人以大量的觀看、演出,累積「腹內」,面對演出機會稀少的當代,若能整理總綱中的組成元素,如套語、主題與敘事結構,並透過演出或老師對總綱中簡略記載部分的說明與示範,新一代的學習者才能事半功倍。
儘管接觸手抄本的時間不短,但終於意識到總綱只是戲先生口述演出的書寫紀錄這件事,是在2009年於保安宮觀賞「漢陽」演出《打登州》之時。過去對《打登州》總綱上三大字「假童科」不求甚解的我,被李阿質老師那段精彩的「程咬金假童」一棒打醒,也讓我留意到將總綱視為「作品」(oeuvre)的不當。
法國的符號學家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在區分文本(texte)與作品時提到:「作品是已完成之物,可以計算,通常占有實質空間(例如在圖書館的書架上占有位置)。文本是方法論的範圍,因此我們無法(至少規律性地)計量文本。」文本的身分不是種複製(reproduction),而是種生產力(productivité)。將北管總綱與已知作者的作品(如關漢卿的作品)一同看待並不恰當,北管總綱裡有不少只寫著「小花便白」、「白話不盡」,或記載簡略的地方,倘若沒有透過表演加以補足,必然會有許多缺漏。亂彈戲因演出環境、表演者、觀眾的交相影響而演變,如同文本一樣不斷變化,透過演出表現其頑強的生命力。
從清代至今,不管從文獻或是田野觀察,我們都可確認臺灣亂彈戲的演出與廟會節慶息息相關,是民眾向神明獻上敬意的供品之一,這項特色也影響北管戲的劇情。有些同源的劇目同時存在福路系統以及與西皮系統相近的京劇中,如北管福路戲《雌雄鞭》、《三官堂》與京劇的《白良關》、《鍘美案》,然而福路劇目以全家團圓作結,京劇則以某人的死亡告終,這可能與宗教演劇與商業劇場的傾向不同有關。
吾生也晚,我認識亂彈戲時,已是它的遲暮之年,但二十多年後,我慶幸自己可以在上個世紀最後的十年開始田野調查與表演者的訪談,有幸遇到幾位出身日治時期亂彈童伶班的演員,還有一些經歷過北管盛景的長者,得以從他們的話語與演出中,尋覓源自「花部」的臺灣亂彈戲在島嶼枝繁葉茂的榮光。這是本書定名為「移地花競豔——臺灣亂彈戲的敘事結構與地方特色」的源頭。而以「敘事結構」與「地方特色」為重點,除了要整理出結構化的套式構成外,還想觀察沿襲中國戲曲敘事傳統的北管戲在情節鋪陳、角色安排與其他劇種的差別,找出因臺灣特殊風土而有的展現。本書將探討下列問題:
一、口耳相傳的地方戲其戲劇文本是如何形成,為何類似劇目會形成不同的結局?
二、手抄本與實際演出之間的差異;地方戲曲如何反映當地特色?
三、以北管戲為例,其套語、主題的套式運用與敘事結構為何?
四、在總綱複製不普及的年代,表演者如何學習?亂彈戲如何拓展劇目?亂彈戲的「活戲」型態為何?
五、不同的世代如何解讀幾乎不變的北管戲?
|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移地花競艷:臺灣亂彈戲的敘事結構與地方特色的圖書 |
 |
移地花競艷:臺灣亂彈戲的敘事結構與地方特色 作者:簡秀珍 出版社: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10-29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移地花競艷:臺灣亂彈戲的敘事結構與地方特色
出自清朝「花部」戲曲的亂彈戲,來到臺灣已超過兩百年,因主要以北管音樂伴奏,半世紀以來也有人稱它為「北管戲」。由於迎神賽會的大量需求,臺灣亂彈戲曾經非常興盛,然而隨著觀眾喜好的轉變,亂彈戲逐漸無法與後起的歌仔戲競爭,1970年代末期,專演亂彈的僅剩「新美園」一團。
本書作者自1990年代以來,進行大量的北管表演者訪談與演出現場的田野調查,透過不同劇種同名劇目的分析比較,找出北管戲與中國同源劇種的異同,從北管總綱的敘事結構與套式運用中,尋找「活戲」演出的結合組件。臺灣亂彈戲的表演內容,呼應著清代漢人移民的群體心態,也反映日治時期民眾面對原住民族、現代化社會的態度,持續傳承並編創新劇,是北管戲曲在當代無法迴避的挑戰。
作者簡介:
簡秀珍
宜蘭羅東人,法國巴黎第七大學遠東研究博士,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音樂學系專任副教授。出版有《開枝散葉根猶在──宜蘭總蘭社的繁華與衰微》(宜蘭:傳藝中心,2015)、《續修臺中縣志文化志.表演藝術》(臺中:臺中縣政府,2010)、《臺灣偶戲走向世界舞臺──班任旅東遊記(與蔡紫珊合著)》(宜蘭:傳藝中心,2007)、《環境、表演與審美──蘭陽地區清代到1960年代的表演活動》(臺北:稻鄉,2005),策劃《憨子弟、瘋亂彈──臺灣北管藝術大展》(傳藝中心,2019-2021)。近年研究重心在:透過臺灣亂彈戲的文本與演出,分析其套式運用、敘事結構和地方特色;研究日治時期臺灣的戲劇活動,並經由日本奇術團天勝一座的跨國展演,勾勒臺灣在東亞表演市場的地位。
作者序
康熙五十四年(1715)貴州人周鍾瑄來到臺灣擔任諸羅知縣,次年開始編修的《諸羅縣志》寫道:「夫衣飾侈僭、婚姻論財、豪飲呼盧、好巫信鬼觀劇,全臺之敝俗也。」 當時與民眾生活緊密的看戲活動,就知縣大人看來與賭博、喝酒一樣,也是臺民的「陋習」之一。康熙年間,民眾看的應該不是亂彈戲,可能是較早傳入的七子戲。亂彈戲何時來到臺灣,可以從兩方面來觀察:一是北管音樂傳入的時間,目前臺灣歷史最悠久的北管曲館彰化梨春園成立於嘉慶十六年(1811)。另一個是尋找「官音」演出的時間,現今最早的紀錄是臺南武廟道光十五年(1835)的...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緒論
一、北管劇目的分類與研究對象的選擇
二、研究取徑與相關研究
壹、戲曲故事的形成與差異——以臺灣亂彈戲《雌雄鞭》與京劇《白良關》為發端
一、前言
二、《雌雄鞭》、《白良關》裡的主要人物
三、《白良關》尉遲恭認子的故事脈絡
四、京劇《白良關》的版本差異
(一)「百本張抄本」版
(二)「故宮珍本叢刊」版與「敦厚堂志」抄本
(三)「繪圖京調十七集光緒中石印本」版
(四)雙紅堂文庫「中華印刷局」版
五、紹興亂彈與北管戲《雌雄鞭》的比較
六、從劇種聲腔關係探尋兩版的差異 ...
一、北管劇目的分類與研究對象的選擇
二、研究取徑與相關研究
壹、戲曲故事的形成與差異——以臺灣亂彈戲《雌雄鞭》與京劇《白良關》為發端
一、前言
二、《雌雄鞭》、《白良關》裡的主要人物
三、《白良關》尉遲恭認子的故事脈絡
四、京劇《白良關》的版本差異
(一)「百本張抄本」版
(二)「故宮珍本叢刊」版與「敦厚堂志」抄本
(三)「繪圖京調十七集光緒中石印本」版
(四)雙紅堂文庫「中華印刷局」版
五、紹興亂彈與北管戲《雌雄鞭》的比較
六、從劇種聲腔關係探尋兩版的差異 ...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