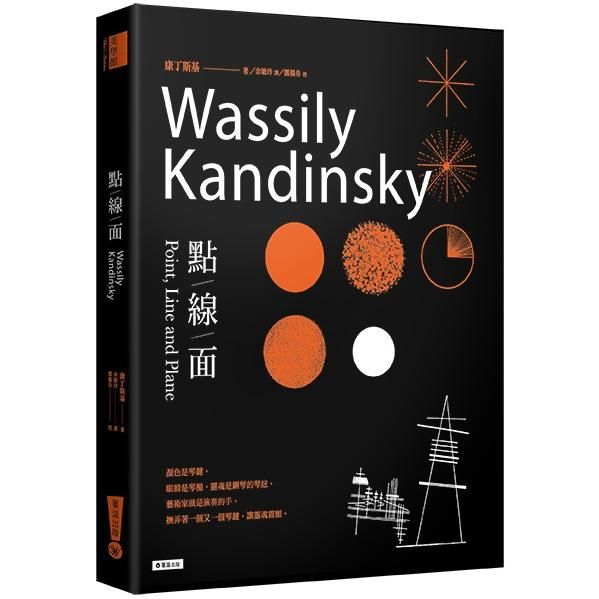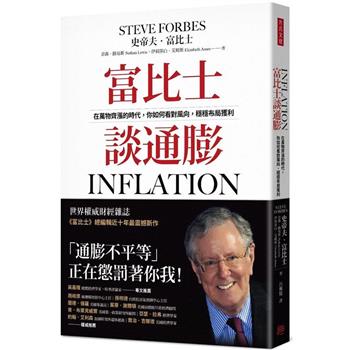導言
內外有別
世間萬象,都可以從其內外兩方面去體驗。內外如何分定,取決於現象自身的特性,隨意不得。
幽坐室內,隔窗望街,窗玻璃隔絕鬧市的嘈雜,街上一切行色,依稀彷彿默劇魅影。窗裡窗外,一時「恍如隔世」。
開門啟戶,走出幽室,觀者置身於外面真實世界,並成為它一分子。五官暫態萌動,體驗亦隨之而來。這邊鬧市喧嘩,不絕於耳,聽到聲調音速各異,抑揚頓挫,此起彼伏;那邊車馬往來,川流不息,看到線條生動,橫豎不一,又看到色彩繽紛,此消彼長。
藝術品有如一面鏡子,映照在我們的意識表面。它們的形象總像是在鏡面之後,當感覺隱退,畫像便逐漸消失,不留痕跡。我們和藝術品之間,有如隔了一堵透明卻堅固的玻璃璧,難以直接溝通,但我們依然可以接收藝術的資訊,調動我們所有的官能去體驗藝術品鮮活的生命力。
藝術分析
對藝術元素逐一精心分析研察,既有其科學價值,亦能架起一座橋樑,通達藝術品內在的生命脈動。
時人普遍認為,「剖析」(dissect)藝術必然為其帶來滅頂之災,這其實是源於對藝術元素的無知,從而不敢面對藝術元素自身的原始力量。
繪畫和其他藝術形式
就分析研究方面而言,相比於其他藝術形式,繪畫處於一種奇怪的地位。譬如建築,因其固有的實用性,必須講求一定程度的科學嚴謹,所以理論分析就勢不可少。而抽象的音樂藝術雖無實際用途(進行曲和舞曲除外),樂理卻也早已有所發展,目前看來雖還未夠完善,至少也在不斷推進。建築和音樂,雖形式迥異,卻都有自身的科學理論基礎,似乎也未見不妥。
相較之下,其他藝術門類的理論研究多少顯得遲緩,似乎總落在藝術本身發展之後。
繪畫理論
繪畫尤其如此。最近數十年,繪畫的發展日新月異,不久前,更是從實用意義中解放出來,不必再為先前諸多既定目的服務。繪畫藝術既已如此發展,對圖畫方法事以理論考察,則勢在必行。沒有嚴格的新理論作為支撐,藝術家也好,公眾也好,若要為藝術尋求新路,恐怕都是妄談。
早期理論
毋庸置疑,繪畫理論並非一直如今日般處於空白狀態。自古以來,初學者或多或少總要學些理論,比如技法、構圖以及其他關於造型元素的基本知識。
一些純技術手段,比如印刷和裝裱等,最近二十年內在德國備受重視,並因此促進了色彩理論的發展。除此之外,留存到今天的早期理論知識少得可憐,雖然它們之間有些內容也許蘊含著某種完備的藝術科學。有意思的是,印象派堅稱藝術應「師自然而不師古人」,在與「學院派」的較量中徹底摧毀了傳統的繪畫理論,同時卻在不自覺之間,又為藝術設置了一方新的理論基石。
康丁斯基的一生
康丁斯基曾經說過:「畫家得忍受骯髒的畫室,未免格調太低。對我來說,我可以穿著晚禮服作畫。」這句話出自現代藝術的主要創始人──康丁斯基口中,的確令人難堪。
看著瓦西利.康丁斯基的照片,很難想像他是一位畫家。因為康丁斯基給人一種嚴謹、不苟言笑的印象,這種成見讓人總是把他當成法官、哲學教授或者是醫生。很難想像他會是一位傑出的藝術家。
其實康丁斯基如果願意的話,他可以成為法官,因為他年輕時專攻法律;我們還可能將他當成是一位哲學家,因為他創作了第一幅抽象水彩畫之後,幾乎同時又寫了《藝術中的精神》這本書。他雖然不是一位醫生,但分析起藝術創作來,却像個外科醫生手持解剖刀一樣的精確。因此,在本世紀前半葉的創造性藝術世界中,康丁斯基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毋庸置疑,他是一位藝術家,也是一位研究人員、理論家和優秀的教師。
康丁斯基是一個俄國人,先入了德國籍,接著又入了法國籍;他為歐洲知識階層所肯定,但在1944年去世時還不被世界其他地方所熟知。藉著他的妻子妮娜.康丁斯基,我們才得以理解他的不凡成就。妮娜在1980年被人謀殺死亡,她極力想讓夫婿的重大成就廣泛的被世人所理解。這個重要的工作,對二十世紀思想的發展極為重要,而且將成為全球藝術創造的基石。康丁斯基之所以如此被世人所推崇與肯定,妮娜居功厥偉。
莫瑙時期和藍騎士
1907年康丁斯基返回慕尼黑。這位藝術家本來就有不少操心的事,再加上他與表妹失敗的婚姻,以及與加布利埃爾.蒙特的戀情等等。之後他和加布利埃爾.蒙特一起定居在慕尼黑,租了一間公寓,離他還不認識的保羅.克利的公寓不遠。
康丁斯基是個嚴謹的人,他總是把自己所有的文件整理得井井有條,我們才得以知道他支付了很高的租金,租了艾因米萊爾大街上有四個房間的屋子,並親自為這間新居設計家具。這些細節並非毫無意義,一則表明康丁斯基的經濟優渥;再則表明了康丁斯基在設計家具時,已經開始在追求各種藝術形式之間的和諧。這種追求藝術形式的和諧,正是威瑪共和(WeimarRepublic)時期,他曾任教的包浩斯(Bauhaus)學院之所以成立的基本理念。
這時他還沒有到達創作「非具象」繪畫的地步。實際上恰恰相反,他和加布利埃爾在巴伐利亞阿爾卑斯山區,創作了許多風景畫。在莫瑙,他也購置了一所房子,和加布利埃爾分手之後,她仍舊住在那裡。人們可能認為,在這麼幽僻的地方居住,這對情人可能過著離群索居的生活,但事實卻不然。他們周圍有一大羣朋友,包括:畫家雅夫楞斯基(Jawlensky)和佛凱(Verkade),舞蹈家薩哈羅夫(Sakharoff)及其他人。
康丁斯基雖然和他們廣泛交流看法,卻沒有被任何人影響。由於康丁斯基使用的純色,人們常過於輕率地把他在莫瑙時期的作品,定義為野獸派的作品,還錯誤地把它們和1905年在德勒斯登形成的「橋派」(DieBrückegroup)聯想在一起。但這些對他都毫無意義,因為不同的地方具有不同的個性,正如象徵主義需要北方的霧靄;野獸派則需要南方強烈的光影一樣。野獸派畫家適應地中海沿岸;「橋派」畫家則對德勒斯登周圍地區特別敏銳。莫瑙位於巴伐利亞州的阿爾卑斯山區,這裡則是另一種氣候、另一種光線、另一種個性。
康丁斯基作品的另一個特色就是眾所周知的:「聲音和顏色之間的對等。」在康丁斯基逗留莫瑙時期,我們可以看到他雖然還沒有達到創作非具象繪畫的地步,可是作品的形式已漸漸失去了實體感,顏色安排得宛如音符,在這些風景畫中產生一種顫動,因而也就有一定程度的音樂性。他在作品中經常運用平行的筆觸,並極力拋開靜態的描寫。畢卡索是個憑藉直覺的畫家,他曾說:「我不刻意尋求,我不期而遇。」康丁斯基是更善於思考的人,作為一位畫家,他的大半生都用於尋求這種創作的直覺。
1909年他和朋友決定再組一個團體,以方便舉辦畫展。就某種程度而言,它是密集團的復活,只不過改個名稱叫「慕尼黑新藝術家協會(NeueKünstlervereinigungMünchen)」,康丁斯基是協會的靈魂人物,新協會的目的就是通過畫展讓新藝術能得到廣泛的理解。該團體的成員全都是康丁斯基的朋友,也都是在思想上願意接受當代藝術,表現各種形式的藝術家聯盟。他們的第二次畫展,邀請參展的畫家包括布拉克、畢卡索、德安、烏拉曼克、盧奧和范.唐根(VanDongen)。這次畫展給法蘭茲.馬克(FranzMarc)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他也加入了康丁斯基的協會。這是二人初次的相會,幾年以後,他們還將共同創立「藍騎士」。
經過了四分之三個世紀,歐洲發生了各種各樣的藝術革命之後,我們很難想像這類協會和畫展會引起什麼樣的非議。當時在巴黎的一次官方畫展開幕之際,有一位學院院士,試圖阻止共和國總統進入印象派畫家所占用的展覽廳,他高呼:「別進去,總統先生!那是法國藝術恥辱開始的地方!」說這話的那位學院派畫家,無疑和批評家路易.沃塞勒(LouisVauxcelles,曾用「野獸的籠子」來形容馬諦斯等人的展覽一樣,都是非常認真的。康丁斯基當時還是俄國評論刊物《阿波羅》的通訊記者,他對這種態度表示惋惜,他以最嚴厲的文字批評慕尼黑竟然會喜歡索然乏味的德國畫家,更勝於喜歡像高更、馬諦斯、梵谷或塞尚之類的藝術家。
慕尼黑對當代藝術展覽報以嘲笑及污辱。評論家漫罵展覽的組織者是瘋子、騙子及奸商。這使法蘭茲.馬克大為憤怒,他決定創辦一份評論刊物,為這種新藝術辯護,它就是後來的「藍騎士」。
新藝術協會成員之間的關係,既不單純也不美妙,顯然康丁斯基太有個性了,最後他不得不辭去協會主席的職務。協會第三次畫展選拔委員會編造了一個藉口,以他的作品《構成D》不符合格式要求,拒絕讓他參展。康丁斯基因此於1911年12月毅然退出該組織,到了第二年,該協會就湮沒無聞了。
1910年是康丁斯基第一幅抽象水彩畫問世之年,1912年出版了《藍騎士年鑒》,還出版了康丁斯基兩年前寫成的重要著作《藝術中的精神》(UberdasGeistigeinderkunst)。但這時,康丁斯基的買主們開始拋棄了他。更糟糕的是,他成了批評家的眼中釘,遭到他們極端粗野的抨擊,德國知識界有許多人急忙地為他辯護,外國畫家和知識分子也不斷地為他辯護,例如:費爾南.雷捷(FernandLéger)、羅勃.德洛內(RobertDelaunay)、格列茲(Gleizes)等人,尤其是阿波里內爾(Apollinaire),他在1913年三月寫道:「康丁斯基在巴黎舉辦畫展時,我經常談到他的作品。我非常高興藉此機會表達我對這位畫家的敬重,在我看來,他的藝術既嚴肅又重要。」當時德國的批評家把這種藝術當作是「極其愚蠢的玩藝兒」而予以摒棄。
在德國藝術界,自相殘殺的傾軋非常殘酷。每一個小集團,都無情地攻擊其他團體。然而康丁斯基絕不會缺乏朋友與合作者的忠誠支持。其中最主要的是法蘭茲.馬克和保羅.克利。克利寫道:「他確實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有一個敏捷、清晰的頭腦……在他身上不乏嚴厲的精神……是他開導了博物館,而不是博物館開導了他,在那裡甚至連最偉大的人,都無法和他爭辯,或者削弱他對精神世界的重要影響。」至於法蘭茲.馬克,則在德國的重要評論《風暴》(DerSturn)上寫道:「我想到他時,總是看到一條寬闊擁擠的大街上,人羣之中有一位智者,不聲不響地走著,那就是他。然而,康丁斯基的繪畫正在遠離那條大街,插入遼闊的藍天……,很快地隱沒於歷代沈寂的黑暗中,不過,不久之後他將如慧星一般燦爛重現……,我總有說不出的感激,竟然再一次有了一位能排山倒海的人,而且他做得何等瀟灑。」
馬可(Macke)也很賞識康丁斯基;之前他認為馬諦斯和畢卡索比康丁斯基偉大,卻在藍騎士第一次畫展之後寫道:「康丁斯基無疑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雖然抽象藝術打動不了馬可,但他卻承認康丁斯基是「一個浪漫派的人、一個夢想家和一個敘述者……」而且「他充滿了無限的活力。」
嚴格來說《藍騎士年鑒》並不具備宣言意義。法蘭茲.馬克把它概括稱為:「我們要創辦一份年鑒,使之成為宣傳我們這個時代,一切有思想價值的喉舌。繪畫、音樂、戲劇等等……其主要宗旨就是借助比較資料,闡明許許多多的事物……我們希望從中獲得有益的、使人振奮的資糧,藉著闡明各種思想,直接對我們的工作有益,使它成為一切夢想的開端。」
今天回過頭來看這份年鑒,就會看到其中有許多我們夢寐以求的東西。它研究當代藝術、音樂和戲劇。插圖五花八門,從原始藝術到塞尚、盧梭和德洛內的作品,還包括:東方藝術、中世紀藝術、甚至包括大眾藝術和兒童繪畫在內。繪畫中各種重要的名字都出現在此,而荀伯格(Schönberg)、伯格(Berg)和韋伯恩(Webern)之類創造力很強的人物,則代表著他們在音樂方面的努力。即使現在我們能理解康丁斯基的選擇是多麼明智,但在當時這卻是一種艱苦的奮鬥。
馬克在年鑒上寫了一篇社論,題為『精神財產』(SpiritualAssets):
「通常賦予『精神』財產的價值,和賦予『物質』財富的價值相差懸殊。例如某個人為國家征服了一個新的殖民地,就會受到所有同胞的推崇和敬重……但是任何人向國家提交一份純精神的新建議時,幾乎可以肯定人們會憤怒、不耐煩地予以拒絕,他本人也會因此而成了被懷疑的對象,人們千方百計想要除掉他;只要被允許,這位奉獻者就會因為他的建言而被活活燒死。」
直到很久以後──在德國直到二十世紀二○年代,在許多其他國家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人們才開始認識到,這個新藝術思想的重要意義與價值。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點線面(全新修訂版)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點線面(全新修訂版)
藝術元素是藝術品的基礎。
藝術科學的基礎研究,首要課題即是藝術元素的分析。
顏色是琴鍵,眼睛是琴槌,靈魂是鋼琴的琴絃。藝術家就是演奏的手,撫弄著一個又一個琴鍵,讓靈魂震顫。
藝術品有如一面鏡子,映照在我們的意識表面。當感覺隱退,畫像也隨之消失。而世間萬象,都可以從內外兩方面去體驗;但內外如何分界,取決於現象自身的特性,隨意不得。
《點.線.面》一書本為包浩斯學校的基礎課程講義,其內容與精神延續著前一本書:《藝術中的精神》,既貫徹抽象藝術的觀點,以具體分析的方法研究抽象視覺元素的特徵,又繼續前書的視覺構成課題,從色彩構成轉到平面構成,探討現代構圖理論的基本原則與觀念。全書自成體系,內容具體,深入淺出,富含美學洞見。是一本藝術學系學生和對插畫有興趣的朋友們必看的案頭書。
作者簡介:
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 1866 - 1944)
俄國人,早年在莫斯科念法律和經濟,並獲教授職;30 歲後赴慕尼黑習畫,且創立了「藍騎士」社團,又在包浩斯學校任教,直至該校被納粹關閉為止;之後,再轉往巴黎,專事抽象繪畫創作。康丁斯基是現代抽象表現主義藝術的實踐和理論先驅,既是藝術家,又是理論家。康丁斯基著有《藝術中的精神》、《點線面》,俱是現代藝術理論的經典文獻。
章節試閱
導言
內外有別
世間萬象,都可以從其內外兩方面去體驗。內外如何分定,取決於現象自身的特性,隨意不得。
幽坐室內,隔窗望街,窗玻璃隔絕鬧市的嘈雜,街上一切行色,依稀彷彿默劇魅影。窗裡窗外,一時「恍如隔世」。
開門啟戶,走出幽室,觀者置身於外面真實世界,並成為它一分子。五官暫態萌動,體驗亦隨之而來。這邊鬧市喧嘩,不絕於耳,聽到聲調音速各異,抑揚頓挫,此起彼伏;那邊車馬往來,川流不息,看到線條生動,橫豎不一,又看到色彩繽紛,此消彼長。
藝術品有如一面鏡子,映照在我們的意識表面。它們的形象總像是在鏡面之...
內外有別
世間萬象,都可以從其內外兩方面去體驗。內外如何分定,取決於現象自身的特性,隨意不得。
幽坐室內,隔窗望街,窗玻璃隔絕鬧市的嘈雜,街上一切行色,依稀彷彿默劇魅影。窗裡窗外,一時「恍如隔世」。
開門啟戶,走出幽室,觀者置身於外面真實世界,並成為它一分子。五官暫態萌動,體驗亦隨之而來。這邊鬧市喧嘩,不絕於耳,聽到聲調音速各異,抑揚頓挫,此起彼伏;那邊車馬往來,川流不息,看到線條生動,橫豎不一,又看到色彩繽紛,此消彼長。
藝術品有如一面鏡子,映照在我們的意識表面。它們的形象總像是在鏡面之...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小書所錄,乃是拙作《藝術中的精神》內容的延續。善始善終,也算有趣。
世界大戰伊始,本人在康斯坦茨(Constance Lake)湖畔的戈爾達奇(Goldach)逗留三月,將素日理論及實踐經驗,一一條分縷析,居然也集腋成裘,蔚為可觀。此後,這些成果塵封十年,未曾理會。今日再作收拾,遂有此書。
寫作本書,初衷乃是要集中探索一門藝術的科學,然而此一問題,殊為複雜,且絕非繪畫乃至藝術範疇自身所能概括。此書若能大略確立一些理論方向,構設一些分析方法,考量一些綜合價值,也就聊以自慰了。
康丁斯基
1923年於威瑪
1926年於狄索
再版...
世界大戰伊始,本人在康斯坦茨(Constance Lake)湖畔的戈爾達奇(Goldach)逗留三月,將素日理論及實踐經驗,一一條分縷析,居然也集腋成裘,蔚為可觀。此後,這些成果塵封十年,未曾理會。今日再作收拾,遂有此書。
寫作本書,初衷乃是要集中探索一門藝術的科學,然而此一問題,殊為複雜,且絕非繪畫乃至藝術範疇自身所能概括。此書若能大略確立一些理論方向,構設一些分析方法,考量一些綜合價值,也就聊以自慰了。
康丁斯基
1923年於威瑪
1926年於狄索
再版...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康丁斯基的一生
前言
自序
再版序
導言
點
線
面
附圖
譯後記
年表
前言
自序
再版序
導言
點
線
面
附圖
譯後記
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