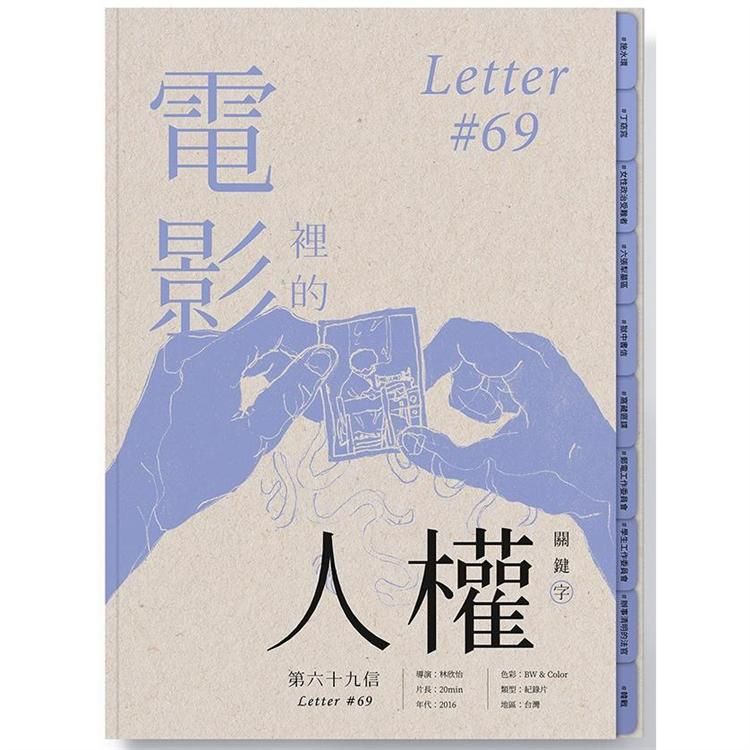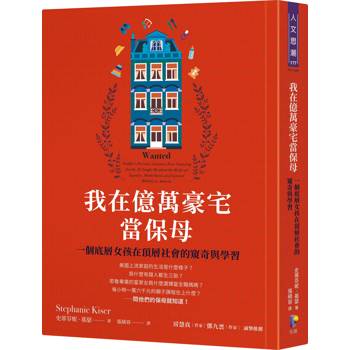六張犁墓區(節錄)
談到白色恐怖,一般人的理解通常到了「馬場町槍決」的這個環節就結束了。這是因為大多數人不認識作為個體的政治犯,他們在沒名沒姓的狀態下,以一種「被殺了」的印象留在社會記憶之中。那麼,遺體去了哪裡?有人處理嗎?
是的,確實有人處理。處理的機構正是當時台北市唯一的殯儀館:極樂殯儀館。1949年開張的極樂殯儀館,是由當時的台北市長游彌堅特邀曾任上海殯儀公會理事長的錢宗範開設。游彌堅為什麼要開設殯儀館呢?因為當時的本省人習慣在家中辦喪事,但逃難來台的外省人因缺乏空間、鄰里關係與覺得總有一天要歸葬故土,需要一個辦理喪事的特定場所。在此需求下,游彌堅以「無償無限期」的方式,把日本人留下來的三板橋葬儀堂與葬儀堂所屬的六張犁公墓共十七公頃交給錢氏。在獨佔市場的情況下,極樂殯儀館的生意可說相當興隆。如胡適、于右任、許世英、賈景德、王寵惠、陳果夫與洪蘭友等知名人士(其中陳果夫,曾是國民黨在中國時期知名的特務頭子),均在這裡走完最後一程。其服務的價格,不消說也相當昂貴。
作為台北市唯一一家專業殯儀館,遭槍決的政治犯遺體交由極樂殯儀館來處理也很合理。從馬場町到極樂殯儀館,於是成了受刑者在死亡後的第一段旅程,亦是政府的標準作業流程。
接下來,就是通知親屬前來領屍了。然而理應負責通知家屬的保安司令部在這方面的作業可說糟糕透頂。許多人根本來不及在領屍期限前知道親友已經被槍斃的消息。家屬中,有人會收到保安司令部的通知,有人卻要每天在火車站前的公布欄上仔細端詳公告,甚至有人是提著菜去探望時,才當場被告知。還有人甚至連通知都沒辦法,因為他們的家人還留在中國,沒有跟著一起到台灣來。
根據日後在此一墓區的統計,總共264名受難者中,本省籍111人,佔了42%,外省籍153人,佔58%。35歲以下的青年世代有195人,受難比例高達74%。女性受難者8人,佔3%;男性256人,佔97%。大部分的受難者集中在1950到1953年間遇難。
至於幸運接獲通知,又來得及前去領屍的受難者家屬,當他們到了極樂殯儀館,想要領回親人屍體返鄉安葬,會發現一個驚人的情況──他們得付錢才能領屍體,這筆「處理費」的金額相當驚人。當時的公務員月薪大約兩百元,然而根據口述歷史,拿回一具屍體,要付四到五百元。這金額對於普通人家來說,已是一筆不小的負擔,而政治犯家庭的經濟狀況,在當時白色恐怖的氣氛下,又比一般家庭更為艱困。因此,有辦法領回親人遺體的家屬,可說少之又少。
這些無人領取的屍體,後來都到哪裡去了呢?極樂殯儀館得做出最後的處分。
當時,台灣還不流行大體捐贈,因此常出現亟需屍體以練習解剖的醫學生半夜到墓地裡偷盜遺體,結果落下一隻手或一隻腳沒拿走的怪聞。由此可見當年缺乏大體的程度。因此,在執行死刑後,無人認領的遺體便有可能交由國防醫學院充作解剖教材使用。解剖完的遺體,由極樂殯儀館火化後放入靈骨塔。沒被解剖的遺體,則由極樂殯儀館葬於六張犁墓區。
當政治犯成為符號之後
讀到這裡,不知道你是否會感到一點「怪怪的」?撇開白色恐怖不談,從槍斃到埋葬,畢竟是公家機關的固定流程,為什麼曾梅蘭(或許毅生)得問了那麼多人,尋找了這麼久,最後在因緣際會之下才得以讓墓區重見天日?
更別提,遭槍決的受難者超過千人,六張犁絕對不是唯一一個政治犯的埋骨之所。然而其他受難者到底葬在哪裡,仍是未解之謎。
明明有那麼多人應該知道的啊?但為什麼他們都不說?
這牽涉到「白色恐怖」最令人感到憤怒的本質:它不分青紅皂白地設下了許多關鍵字,只要與這些關鍵字有所牽連,那麼不管你的目的為何,通通處於危險之中。於是對於一般民眾來說,一個個有血有肉的政治犯與他們的親屬,頓時間成了所有人都避之唯恐不及的關鍵字。他們被變成了社會的禁忌,無人膽敢提及。不僅受難者閉口不談,社會大眾對於談政論治的恐懼亦難以輕易消除。至於有能力談論此事的政治人物呢?願意談的沒有資料,有資料的則不願意談。
在眾人噤口的情況下,歷史逐漸地被遺忘。當社會越趨開放,終於開始討論白色恐怖時,在社會大眾的記憶中,作為符號的政治犯已經取代了作為個人的政治犯──社會更加關心的,比起他們作為個體的遭遇,毋寧在於他們作為遭受迫害的象徵上。因為唯有如此,社會大眾才能安心地討論相關的議題。但符號無法感動人,無法讓我們痛下決心,不再重蹈覆轍。
這就是為什麼《第六十九信》的導演林欣怡要從施水環寫給家人的信件出發。在此之前,我們也許不認識施水環,然而透過她的信件,我們逐漸發現,她是個很普通的女孩子。普通的就像是我們的鄰居、朋友與親人。
這樣一個普通的女孩子,為什麼會被關到監獄裡?又為什麼非得被槍斃呢?你難道不好奇嗎?仔細探究,原來施水環是因為藏匿受到「學生工作委員會案」牽連而遭通緝的弟弟施至成所以被捕。施至成有沒有罪?施水環有沒有罪?如果他們無罪,那麼為何要賠上性命?如果他們有罪,他們的罪又真的重到要殺死兩條生命嗎?
如果僅僅將「政治犯」視為一個整體,我們將難以去理解為何他們的死亡會帶來這麼大的創傷。透過文學,透過影像,它們將個體與象徵結合,帶領我們蜿蜒走過作為「人」的政治犯的一生,透過他們的眼睛,讓我們體會到他們的喜悅與悲傷。於是,透過電影,我們或許終於能碰觸到曾梅蘭與徐慶蘭的痛苦、遺憾與悲傷,以及白色恐怖之所以成為白色恐怖的核心──那是統治者對於可能喪失權力的無邊恐懼,所導致的極致瘋狂。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電影裡的人權關鍵字:第六十九信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4 |
二手中文書 |
$ 174 |
Social Sciences |
$ 187 |
社會人文 |
$ 198 |
中文書 |
$ 198 |
電影評論 |
$ 198 |
電影評論 |
$ 198 |
電影 |
$ 198 |
台灣研究 |
$ 198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電影裡的人權關鍵字:第六十九信
電影是對話的起點,
也是理解人權議題的可能路徑。
◎手工裝訂,一個關鍵字一張插卡
◎每篇提供「教學提示」,重點一目瞭然
《電影裡的人權關鍵字》系列手冊由國家人權博物館與富邦文教基金會共同策劃。以不同類型的電影為文本,爬梳其中觸及的人權議題,整理成關鍵字,進而展現身處此時的台灣,我們如何以電影作為透鏡,觀察這些關鍵字與己身的關係。
在《電影裡的人權關鍵字:第六十九信》一冊中,我們挑選了十個關鍵字:
#施水環、#丁窈窕、#女性政治受難者、#六張犁墓區、#獄中書信、#窩藏匪諜、#郵電工作委員會、#學生工作委員會、#辦事清明的法官、#韓戰
電影《第六十九信》以白色恐怖受難者施水環的書信為引,試圖顯影施水環的最後一封空白家書,是一部透過影像挑戰歷史敘事的實驗之作。這十個關鍵字除了作為施水環遇難前的生命線索,也牽引出其他共同的受難經驗與狀態。「施水環」、「丁窈窕」、「郵電工作委員會」,令我們一窺曾出現在施水環身邊的人與事;「窩藏匪諜」、「獄中書信」、「辦事清明的法官」則在歷史書寫之中揭露無論是在實質(監獄、窩藏處)或抽象空間(戒嚴體制)中,身體囚禁的暴力經驗;「學生工作委員會」、「韓戰」則將國家暴力置入世界政治角力競逐的地緣政治脈絡,理解當時台人的理想與拼搏;而即便「女性政治受難者」與「六張犁墓區」代表生命的消逝,卻不駛向終結。
所有人注視著相同的銀幕,卻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感受。我們期待,電影是對話的起點,也是理解人權議題的可能路徑。
作者簡介:
總編輯/陳俊宏
主編/蔡雨辰
撰文/何友倫、林傳凱、房慧真、馬翊航、路那、溫席昕(按姓氏筆畫排列)
章節試閱
六張犁墓區(節錄)
談到白色恐怖,一般人的理解通常到了「馬場町槍決」的這個環節就結束了。這是因為大多數人不認識作為個體的政治犯,他們在沒名沒姓的狀態下,以一種「被殺了」的印象留在社會記憶之中。那麼,遺體去了哪裡?有人處理嗎?
是的,確實有人處理。處理的機構正是當時台北市唯一的殯儀館:極樂殯儀館。1949年開張的極樂殯儀館,是由當時的台北市長游彌堅特邀曾任上海殯儀公會理事長的錢宗範開設。游彌堅為什麼要開設殯儀館呢?因為當時的本省人習慣在家中辦喪事,但逃難來台的外省人因缺乏空間、鄰里關係與覺得總有一天要...
談到白色恐怖,一般人的理解通常到了「馬場町槍決」的這個環節就結束了。這是因為大多數人不認識作為個體的政治犯,他們在沒名沒姓的狀態下,以一種「被殺了」的印象留在社會記憶之中。那麼,遺體去了哪裡?有人處理嗎?
是的,確實有人處理。處理的機構正是當時台北市唯一的殯儀館:極樂殯儀館。1949年開張的極樂殯儀館,是由當時的台北市長游彌堅特邀曾任上海殯儀公會理事長的錢宗範開設。游彌堅為什麼要開設殯儀館呢?因為當時的本省人習慣在家中辦喪事,但逃難來台的外省人因缺乏空間、鄰里關係與覺得總有一天要...
顯示全部內容
推薦序
導讀
難以成為歷史的人
文/史惟筑
人們死去後成為歷史;雕像死後成為藝術。
──《雕像也會死亡》
有沒有可能人們死去後沒能成為歷史?
如果有,是否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們死去之後,在哪裡?
1953年,法國導演亞倫.雷奈(Alain Resnais)與克里斯.馬克(Chris Marker)接受人類博物館的邀請拍了《雕像也會死亡》(Les statues meurent aussi)這部影片,拍攝動機源自一個看似簡單的提問:「為什麼古希臘與埃及藝術進了羅浮宮,而黑人藝術卻被放進人類博物館?」然而,用來回應這個問題的答案竟卻遭致長達十年的禁演。影片抨擊了法...
難以成為歷史的人
文/史惟筑
人們死去後成為歷史;雕像死後成為藝術。
──《雕像也會死亡》
有沒有可能人們死去後沒能成為歷史?
如果有,是否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們死去之後,在哪裡?
1953年,法國導演亞倫.雷奈(Alain Resnais)與克里斯.馬克(Chris Marker)接受人類博物館的邀請拍了《雕像也會死亡》(Les statues meurent aussi)這部影片,拍攝動機源自一個看似簡單的提問:「為什麼古希臘與埃及藝術進了羅浮宮,而黑人藝術卻被放進人類博物館?」然而,用來回應這個問題的答案竟卻遭致長達十年的禁演。影片抨擊了法...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國家人權博物館 館長
導讀:難以成為歷史的人
1. 施水環
2. 丁窈窕
3. 女性政治受難者
4. 六張犁墓區
5. 獄中書信
6. 窩藏匪諜
7. 郵電工作委員會
8. 學生工作委員會
9. 辦事清明的法官
10. 韓戰
導讀:難以成為歷史的人
1. 施水環
2. 丁窈窕
3. 女性政治受難者
4. 六張犁墓區
5. 獄中書信
6. 窩藏匪諜
7. 郵電工作委員會
8. 學生工作委員會
9. 辦事清明的法官
10. 韓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