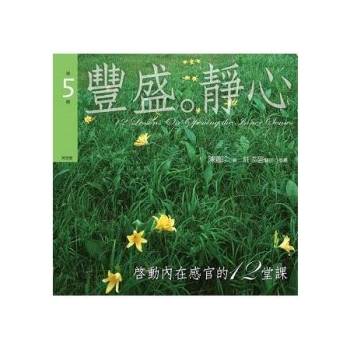《瘋人院之旅》的創傷迴圈
陳怡靜 (原文刊載於新活水網站,以下經過再次編輯)
念書時看過電影《Girl, Interrupted.》(台譯:女生向前走),描述一群精神病院少女們的故事,想成為作家的蘇珊娜記錄下她在療養院裡遇見的一切,瘋狂的朋友莉莎一次次出院又一次次入院。電影有一幕特別讓我印象深刻,莉莎殘酷地揭示了另位女孩黛西家庭生活裡的秘密。隔天,在〈The End of the World〉的歌聲中,少女黛西上吊身亡。
多年過去,每當聽見〈The End of the World〉的旋律,腦海裡冒出的便是那高掛搖晃著的黛西的身體,彷彿記憶裡的鬼魅揮之不去。我總是會想,黛西有個假想完美的生活,但瘋狂的朋友戳破了那個美好的泡泡,強硬地逼她面對真實生活中的殘酷,生命再也無以為繼。電影末尾,蘇珊娜搭計程車離開療養院,她對司機說:「真正瘋狂的,也許是生活。」
最近又想起〈The End of the World〉,是在讀漫畫家Pam Pam《瘋人院之旅》的時候,我一邊看著漫畫,幾乎要哭出來了,裡頭一段主角的獨白是這樣的:「不……他們明明知道,小雞是我的朋友。這些人是瘋子吧?!我應該,當時,就要把他們全部殺死才對……。因為那一天,死掉的……,還有我的心。」場景是灰色的,畫面停在破碎的娃娃人形上:「我曾經那麼健康的心。」
《瘋人院之旅》是漫畫家Pam Pam第一部長篇漫畫,她耗時8個月創作,以虛構的手法,試圖說明真實存在的故事。但這個故事深藏在她內心已經10年了,經過10年的漫畫創作與沈澱,她開始相信自己能以漫畫述說這個故事。漫畫的起手式只是一句話:「整個世界就是你的精神病院。」
Pam Pam說:「有時候,我真的覺得,那些被社會認可的所謂的『正常人』,心理上其實比被貼上有病標籤的人們更加扭曲,甚至,還是造成他人生病的源頭。」15個篇章、336頁的故事從小女孩的舅舅進入精神病院開始,結束在舅舅離開精神病院的時刻。只是經過精神病院的「治療」,舅舅看起來還是舅舅,卻好像也不是舅舅了。
在這段「瘋人院之旅」中,舅舅遇到好多人,有自視甚高的高材生一級棒、善良但也瘋狂的小玉、長髮嬌媚但有秘密的庭庭……奇妙的是,每個病友總有一點我們熟悉的樣貌,每顆傷痕累累的心,都有過去層層疊疊起來的記憶。Pam Pam總是這樣,擅長巧妙以詼諧的故事述說冷酷的事實,在這本書裡,我們讀到的是,童年的創傷是如何影響了一個人。
創作《瘋人院之旅》前,Pam Pam剛讀完《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也帶給Pam Pam動力與基礎知識去完成這本作品,帶出童年創傷的議題。漫畫裡的小女孩看著舅舅一不開心便對家人施暴,小小的她是那樣憤怒難過,但會不會有一天,小女孩在被壓迫的時刻,也自然而然重現那樣的暴力?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童年的傷,心靈也不會忘記。
今年4月初,死刑犯翁仁賢遭槍決,2016年時的除夕夜,他在自家潑汽油縱火、燒死父母等6名親友。翁仁賢行刑後,有網友耙梳資料,拼湊出他悲傷的童年,以及毫無成就感的人生。童年時那個跟愛小動物愛植物的小男孩,究竟為什麼會來到這一天?縱火之前,他想的是什麼?他又遭遇過什麼?
血是什麼時候冷卻的?心是什麼時候傷痕累累的?《瘋人院之旅》沒有打算說教,而是透過一篇又一篇讓人發笑的故事背後,光怪陸離的精神病人們的相處,輕輕淺淺地帶出所謂的瘋子們的內心世界。那些看似正常的人們,真的比較正常嗎?在這現實世界裡,總有暴力回應暴力,總有人帶給他人創傷。那麼,到底,誰才是真正的瘋子呢?
有病喔!不要跟蹤我
從《瘋人院之旅》窺看精神異常者在社會上可能遇到的異樣眼光
——黃大旺(獨立音樂工作者)
「有間療養院很適合你。
別擔心,沒有你想像的這麼可怕。
現在的狀況,在裡面可以休息一下,試試看,也許你會喜歡的。
我來向你的家人講解一下…」
「舅舅」的主治醫師建議自殘成傷的舅舅入院,入院後的舅舅本來還以為自己可以早早出院,姊姊(「我」的媽媽)沒多久就會回來接他。怎知進了療養院,才是一連串惡夢的開端。
作為台灣獨立漫畫圈產量豐富,也以兩性漫畫受到矚目的中堅創作者, Pam Pam先發表了描寫家庭關係的照護漫畫《癌症好朋友》,為台灣的漫畫創作開闢了新的社會題材;這次的力作《瘋人院之旅》更赤裸裸地揭露思覺失調(精神分裂)症患者與「客觀現實」環境的拉鋸,以及當事人在各種不安恐懼下的內心交戰,是少數以近距離描述思覺失調的作品。每一章節之中,舅舅遇到的各種病友與光怪陸離的情境,看在那些鍵盤正義之士眼裡,又會如何呢?剝開一層層冠冕堂皇的理由,不外乎就是找一個機會朝這種(這群)人丟石頭,以捍衛自己的言論正當性。
內在世界的感覺無法以具體而貼切的方式解釋、表現出來,使得不同思覺失調者都會產生不同的異常狀態,然而周圍未必能及時發現,即使是專業鑑定,也難像某診所的醫師一樣,同時讓三四個患者入診間看診,只看一眼就可以知道是什麼問題,開什麼藥。在送醫診治之前,一般家庭陪伴者容易試著用一些緩不濟急的方法處理,當然也只能期待巧合帶來奇蹟。腦部化學物質分泌與電流傳導上出現的不規律現象,至今還沒有找到具體的解釋;在癲癇與妥瑞氏症都已經納入神經醫學的今日,包括思覺失調在內的多種精神疾病,還在不斷增補病理模型。然而技術的進步,還是追不上臨床上看到的各種現象,所以醫師更不可能只看一眼就可以知道是什麼問題。在《瘋人院之旅》的故事時空(1990年前後),則更難發現。
何況即使患者自己有病識感,也未必能像描述自己感冒症狀一樣說清楚。再加上環境因素對發病的影響,會使得判定益發困難。
「希望這間房間有電話
叫姊姊明天就接我回家!」
在療養院裡知道自己可能出不去的舅舅,在如同谷底的黑暗中這樣說著。他當然不會知道自己姊姊(以及家庭)私下的態度。看著媽媽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以及舅舅入院期間的舉動,「我」的心裡也出現了一些可怕的想法,只是反抗的力道通常不被大人當一回事。
「不要以為…我不知道…
你們不停耍我,玩我,嘲笑我…
和過去那些傷害我的人一樣嘛…」
由於病友擁有各自的小宇宙,舅舅在這個微型社會體系裡,仍然被不斷湧上腦海的回憶懲罰,與其他病友間的互動也不順利,連病友有意伸出援手,都要吃舅舅一頓拳打腳踢。通常病友是在不甘願的狀態下被送入療養院,久之對於醫療體系與家庭也不再信任,覺得自己只是被排除的一群。縱使能遵從院內的生活規律,仍有不滿與抵抗的念頭。簡言之,病友不僅在社會遭受到異樣的眼光,在院內也不會得到安寧,只能靠院方的治療。
在故事的最後,舅舅雖然被院方判定可以出院,看起來也「好好的」,作者也沒有提出皆大歡喜的答案。只用凝鍊的構圖提出離舅舅原始想法最接近的想像。這麼簡單的要求,但家庭環境從不給他,還把他往暗處塞,就是那些沒有切身之痛的「他者」想得到最方便的處理方式。
我們只是沒有想像過人生幾個基本平衡點突然少掉一個時,會發生的情形。
我們都是牆上的另一塊磚。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瘋人院之旅 A TRIP TO ASYLUM:整個世界就是你的精神病院的圖書 |
 |
瘋人院之旅 A TRIP TO ASYLUM:整個世界就是你的精神病院 作者:PAM PAM LIU 出版社:慢工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06-18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380 |
二手中文書 |
$ 560 |
社會寫實 |
$ 560 |
中文書 |
$ 560 |
社會 |
$ 560 |
親子共讀 |
$ 560 |
Books |
$ 560 |
Social Sciences |
$ 560 |
Books |
$ 560 |
圖文/插畫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瘋人院之旅 A TRIP TO ASYLUM:整個世界就是你的精神病院
★榮獲2021台北書展大獎小說組首獎★
★入選文策院影視媒合推薦作品★
★幻覺、催眠、解謎,具娛樂性的黑色幽默懸疑劇★
★冷靜而激進地描寫出惡的滋生和轉移★
救贖沒有可能、人人都在落井下石
在一個沒有醫生的療養院內,剛入院的主角不斷經歷各種幻覺,在病友製造的混亂中一步一步看見過去創傷的真相……「裡面」和「外面」失去界線、救贖沒有可能、人人都在落井下石,而暴力的迴圈亦永遠不會停止。
「我是被病態教養出來的,就像我們這個時代的文明人該有的樣子。」
── 杜斯妥也夫斯基 《地下室手記》
娛樂與深度兼備
PAM PAM 再次發揮其擅長的黑色幽默和卡通式的輕快節奏感,讓你哈哈哈地快步向前,再猛然地給你重重一刀,這次的刀捅得比《癌症好朋友》的更深,娛樂與深度在此證實可以兼得。
瘋狂背後的殘酷真實
取材自作者個人及家庭經歷,搜羅數本精神疾病、創傷名作,以虛構手法描繪出瘋狂背後的殘酷真實。
「我並非某天醒來發覺自己瘋了,如果人生這般簡單就好了。」
── 凱‧傑米森《躁鬱之心》
大人請看,小孩且慢!
突破台灣圖像小說史,第一本榮獲小說類獎項的圖像小說,媲美曼布克獎作品《薩賓娜之死》,以慎密的結構拆解社會與家庭的暴力。大人請看,小孩且慢!
各界推薦
「《瘋人院之旅》沒有叫做比較政治正確的《精神病院之旅》,暗示了這本漫畫在面對這個議題時,直白、不美化、不掩飾的作風。」── 林蔚昀(作家、譯者)
「我們只是沒有想像過人生幾個基本平衡點突然少掉一個時,會發生的情形。我們都是牆上的另一塊磚。」── 黃大旺(音樂人)
「血是什麼時候冷卻的?心是什麼時候傷痕累累的?《瘋人院之旅》沒有打算說教,而是透過一篇又一篇讓人發笑的故事背後,光怪陸離的精神病人們的相處,輕輕淺淺地帶出所謂的瘋子們的內心世界。那些看似正常的人們,真的比較正常嗎?在這現實世界裡,總有暴力回應暴力,總有人帶給他人創傷。那麼,到底,誰才是真正的瘋子呢?」── 陳怡靜(自由撰稿人)
作者簡介:
PAM PAM LIU 活躍於插畫、獨立漫畫和獨立音樂圈,也製作動畫。
2009年畢業於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學系,2013年畢業於倫敦中央聖馬丁MA傳達設計學系。自2010年起創立「過去未來多提無用 」自費出版為數不少的漫畫集以及圖文刊物,亦曾參與衛城出版的「社情漫畫」。2018至2019年駐村安古蘭漫畫之家三個月。2021以《瘋人院之旅》榮獲台北書展大獎小說組首獎。
她的創作靈感來自男女關係、音樂、漫畫、電影、小說與微量社會議題。經常將生活的黑暗、恨、失敗轉為狂想式的漫畫,也有像《癌症好朋友》、《我弟小時候》這樣完全紀實的作品。黑色感的幽默令人發笑又發冷!
個人網站http://www.pampamliu.com
推薦序
《瘋人院之旅》的創傷迴圈
陳怡靜 (原文刊載於新活水網站,以下經過再次編輯)
念書時看過電影《Girl, Interrupted.》(台譯:女生向前走),描述一群精神病院少女們的故事,想成為作家的蘇珊娜記錄下她在療養院裡遇見的一切,瘋狂的朋友莉莎一次次出院又一次次入院。電影有一幕特別讓我印象深刻,莉莎殘酷地揭示了另位女孩黛西家庭生活裡的秘密。隔天,在〈The End of the World〉的歌聲中,少女黛西上吊身亡。
多年過去,每當聽見〈The End of the World〉的旋律,腦海裡冒出的便是那高掛搖晃著的黛西的身體,彷彿記憶裡的鬼魅揮...
陳怡靜 (原文刊載於新活水網站,以下經過再次編輯)
念書時看過電影《Girl, Interrupted.》(台譯:女生向前走),描述一群精神病院少女們的故事,想成為作家的蘇珊娜記錄下她在療養院裡遇見的一切,瘋狂的朋友莉莎一次次出院又一次次入院。電影有一幕特別讓我印象深刻,莉莎殘酷地揭示了另位女孩黛西家庭生活裡的秘密。隔天,在〈The End of the World〉的歌聲中,少女黛西上吊身亡。
多年過去,每當聽見〈The End of the World〉的旋律,腦海裡冒出的便是那高掛搖晃著的黛西的身體,彷彿記憶裡的鬼魅揮...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