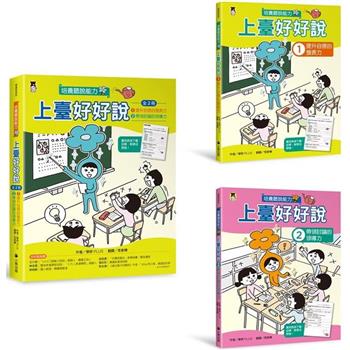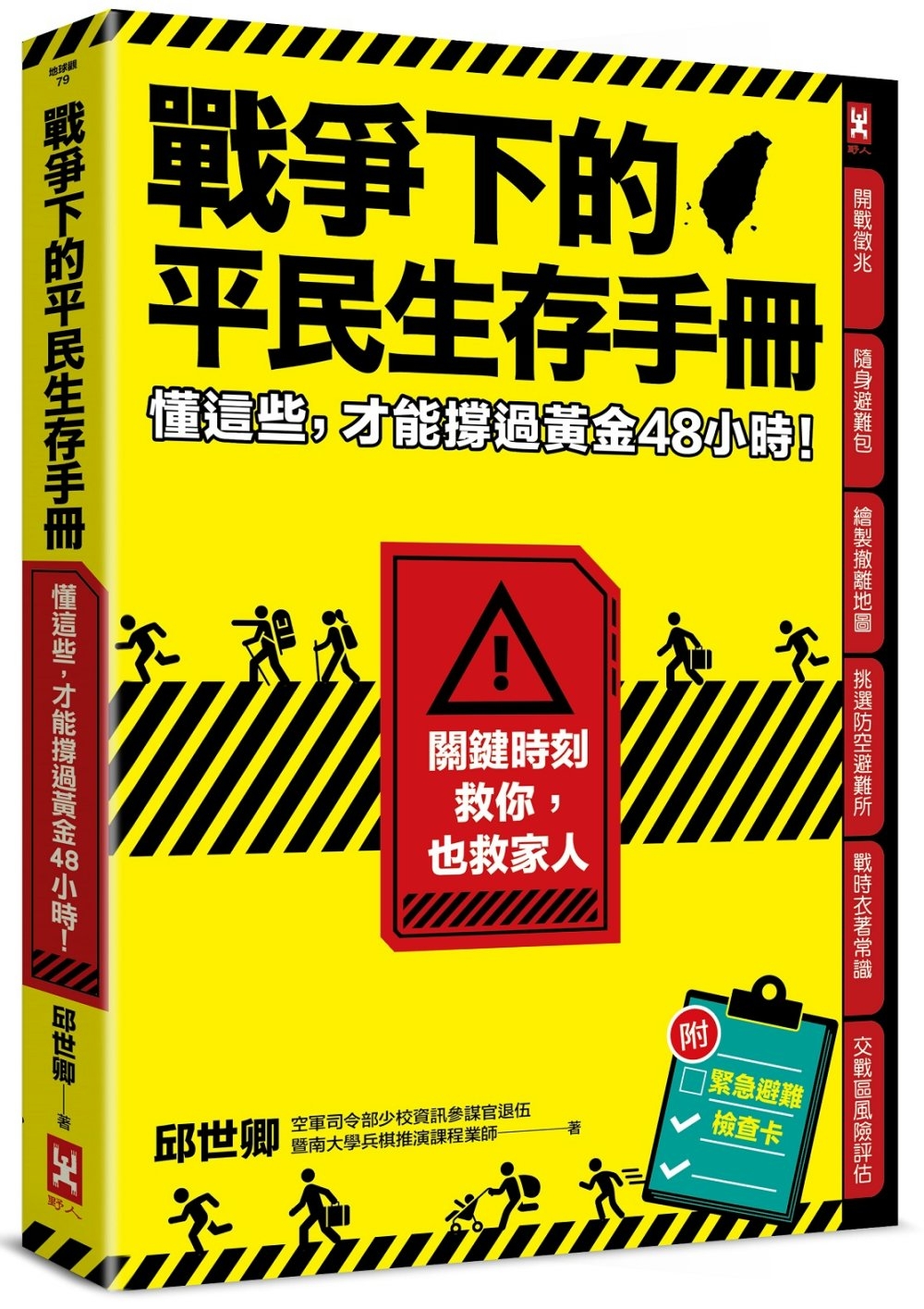第一天平壤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一月
我是二月二十九日生的,我喜歡我的生日。二跟二十九是質數,而二加二十九等於三十一也是質數。質數是天生孤獨的數字,在質數月的質數日出生的我也是孤獨的。另一個喜歡的數字是四,我喜歡每四年舉行一次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也喜歡每四年舉行一次的數學奧林匹亞競賽,還有要踩過四個壘包才能得到一分的棒球,以及棒球隊四號打者。我喜歡的時間是十一點十一分,因為11:11呈現完美的左右對稱,而且加起來的總和等於四。
暗夜殺人命案 留下三個謎團
《紐約每日新聞》二○○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紐約警方二十八日在皇后區的一處住宅,發現一名五十多歲男性中槍身亡,當天凌晨二點左右,鄰居聽到槍聲向警方報案,警方立刻出動抵達現場,發現一名亞裔男子腹部中槍身亡。死者史帝夫・尹,二年前從北韓逃亡來到美國,領導一個名為「自由的朋友們」的人權團體。
鑑識人員表示,案發現場與一般殺人命案不同,死者的臉部疑似有以酒精類的藥品消毒過的痕跡,(P.12)屍體旁邊則用鮮血書寫了複雜且不明的數字和圖形,如下所示:
1 11 21 1211 111221 312211⋯⋯
我是個騙子
警方在案發現場逮捕到一名身分不明的男子,初步研判涉有重嫌,目前正在調查中,但該名男子拒絕做出任何陳述。該名男子約二十多歲,發現時大腿中槍,現已送往醫院治療,沒有生命危險。鑑識人員在該名男子的手上,發現了被害人的血跡,以及與被害人臉部相同的酒精類化學藥品反應。
另一方面,據瞭解被害人曾任職北韓重要機關,逃亡來美後曾向美國情報當局提供北韓方面的重要情報。根據匿名的情報當局相關人士表示,「目前無法確定這起事件是否為單純的命案,我們正著手進行調查,是否為北韓方面因擔心洩露核武相關情報而採取的恐怖襲擊。」
當局目前正對現場留下的謎題般暗號進行解讀,同時也在確認嫌犯的身分及調查犯案動機。
☆☆☆☆☆
數字是1 11 21⋯⋯
圖形是心形、四葉草、鑰匙⋯⋯
還有一句話,「我是個騙子」。
我是騙子嗎?死亡,一個我無法解開的算式⋯⋯
睜開眼睛,我在一個正四方形的房間裡。沒有窗戶,有三面牆還有一面是鐵窗,我躺在正對著鐵窗的床上,右大腿像被什麼刺了似感覺陣陣刺痛,用白色的繃帶層層包裹著。一個陌生男子向我靠近,他說我在命案現場昏迷不醒而遭到逮捕,還說有人死了,是我殺的。是誰死了?真的是我殺的嗎?我想不起來,我為什麼會去那個地方?是誰?為什麼被殺?如果不是我殺的那又是誰殺的⋯⋯
死亡就像是我無法解開的繁瑣算式,未知數x有三個的複合多項式問題,x1是死亡,x2是兇手,x3是我。為求出x1,必須先找出x2,為找出x2就必須知道x3,未知的事全都連結在一起。就像地球繞行著太陽而月亮繞行地球一樣,如果想求出未知數x,就必須把已知的常數帶入算式中,現在已知的,是有人死了而我是兇手。如果x2=x3,而我並非x2的話呢?
我腦中浮現了對x1的印象,死亡就像開關被關掉了一樣,燈光熄滅、四周變得昏暗,曾經閃耀的眼睛闔上、鼻子不再吐出氣息、一分鐘跳動六十次的心臟停止,不再繼續,一切終結,從一變成○。
如果生與死是一與○組成的二進制,2=10、3=11、4=100、5=101、6=110、7=111、8=1000、9=1001、10=1010⋯⋯有與無、存在與消滅、實際與虛幻、我與你、生與死反覆的世界,以最簡單的數字構成最複雜的世界,○不是無、消滅、終結,是讓一成長、完成的「一」的影子。就像死亡是生命的一半,透過死亡才能完成人生。
門打開,一群男人進來了。有高個子男人、矮個子男人、歪鼻子男人、全身像米其林輪胎一樣凹凹凸凸高低不平的男人、額頭兩邊像左右對稱的M字的男人⋯⋯他們帶著有如羅丹雕塑般堅硬線條的臉靠近我,像大聯盟投手藍迪.強森的快速球一樣投擲出一連串的問題。
「姓名?」、「年齡?」、「出生地?」「二月二十七日晚上的行蹤?」、「與死者的關係?」、「殺人動機?」、「行兇的經過?」⋯⋯
一瞬間丟出的不是提問,而是無序,無法接受無秩序的我沒有回答問題,而是放聲喊叫。歪鼻子男人粗魯地捂住我的嘴,他的身高超過一八八公分,正中間看到的是像鈎子一般的鼻子,他用像龍蝦的螯一樣強而有力的手勁,一把抓起我的衣領把我按坐在椅子上。他嘴角歪曲,用不對稱的臉自稱是羅素.班克斯探員,而我正在接受CIA的調查。他說我應該要感到恐懼,因為我不只是殺人犯還是個恐怖分子。
羅素與他的同夥把我⋯⋯準確地說是把我的身體和背包抖了抖,找出了下列的東西。
我的身體——
右手臂上有個不明來歷的龍紋身。
大腿明顯可見一處槍傷。
上半身四處、下半身七處的疤痕,至少四公分以上。
左手無名指有骨折過的痕跡。
我的背包——
七百五十毫升的酒精瓶及棉花。
包括中國、澳門、韓國、哥倫比亞、宏都拉斯、墨西哥、日本、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偽造護照共九本。
中文、粵語、英文、韓文的舊報紙及《新聞週刊》等雜誌中剪下的報導。
用英文及數字寫下意義不明的謎題共十九張。
一本巴掌大小的手冊寫著《關於不可能之事的可能性的航海日誌》。
兩把三角尺、一個三公尺長的捲尺、及一個日本製的舊電子計算機。
羅素把背包倒過來抖動著,五顏六色的卡片紛紛掉落在桌上,我喜歡卡片。不過近看才發現不是卡片,羅素咬著牙,
「偽造護照九本!可以玩紙牌遊戲了。名字也有九個嗎?張家界、菲利普韓、安基慕、佩魯沙.岡薩雷斯、魏全民、松本洋治、詹姆士.甘、賽斯.古特比、穆罕默德.費薩爾⋯⋯到底哪個才是你?你跟這些名字有什麼關係?你最好解釋一下。」
不知道「關係」為何的我沉默了,我並非不知道它字面上的意思:「兩個以上的人、事物、現象相互碰撞發生的交互連結」。所謂「秘密關係」的意義、「拉關係」的雙重意義我都懂。水星和金星的關係、黑洞和星星的關係、函數關係、對稱關係、比例關係⋯⋯等等,但是對於我與不是我的人、我與世界的關係就無法理解,我甚至不知道那種關係是否存在。在我的沉默中,羅素的眉毛不停地蠕動。
「你快點說啊!讓我們知道你不是啞巴。」
雖然羅素希望我感到恐懼,但我一點也不害怕。人們會對不可知的世界和不安的命運感到恐懼,但是我與這個世界無法建立關係。雖然我與他身在同一個空間裡,但我看的卻是另一個空間。羅素用耙子般的手抓住我的衣領拚命地甩,很多東西飛到我身上,耙子般的手、青銅般堅硬的拳頭、光溜溜的鞋尖⋯⋯我像濕掉的毛巾一樣被扭成一團。但羅素想錯了,也許他可以打破、撕裂我的人,但是無法打破、撕裂我的沉默。
像燈被關掉一樣,我眼前所見的景物一個一個熄滅,透過鐵窗望出去的走道變得漆黑,椅子、桌子,像掛在灰牆上的畫一樣融化,看著我的羅素的臉也變得灰暗。就在這時聽到某種聲音,是急促打開鐵窗的聲音,還有一個女人尖銳的聲音。
「住手!這裡是醫院可不是屠宰場啊!」
羅素掐住我脖子的手頓時鬆了下來,原本被堵住的血瞬間往上衝入腦中,我拖著僵硬的腿,勉強把身體抬起一半。羅素回頭吼著:
「沒看到在執行公務嗎?這傢伙是國際刑警組織的通緝犯,而且是殺人犯、恐怖分子。」
「這裡禁止使用暴力,而且這個人是患者,你不只違反規定而且還違法。」
「規定?法?這種情況還講究那些嗎,難道要讓這世界變成殺人犯的天堂嗎?我正在審問極度危險的恐怖分子啊!」
「在這個世界變成殺人犯的天堂之前,你的飯碗會先沒了。」
羅素氣呼呼地把我扔回椅子上,一邊用斧頭般銳利的眼睛盯著那女人,笑著說:
「我就告訴妳幾個這傢伙的有趣事實,他的護照全都是假的,殺人、詐欺詐賭、毒品交易等總共涉及十多起案件,他是被國際刑警組織發出紅色通緝令 的國際罪犯。雖然一直以來,他利用偽造護照,像泥鰍一樣逍遙法外,但現在一切都結束了。不管他開不開口,這輩子註定是要在監獄裡蹲到爛掉了。」羅素的話像毒針一樣亂飛,那女人說道:
「雖然你知道很多,但有一點你不知道。」
「什麼?」
「這名男子患有亞斯伯格症。」
「亞斯伯格症?那是什麼?」
「意思是你無法讓他開口,你再怎麼威嚇都沒有用,因為你的提問他不接受。」
「妳憑什麼根據這樣斷定?」
「亞斯伯格症是在社會化關係和人際關係上有障礙,其行動或所關心的領域受限,常常會重覆同樣的特定行為。他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審問。」
「但是他卻做了一般人想像不到的事啊!犯毒、非法賭博、詐欺、偷渡、還有殺人⋯⋯如果他是智力不足的人,又如何能犯下那些事呢?」
「亞斯伯格症並不代表智力不足,也不是在語言發展上有問題,只是因為他們會使用玄虛或迂迴的語言,因此在一般日常溝通上存在著困難。」
血液開始流動後,我的眼前豁然開朗。她是一個穿著白衣的女子,梳得整整齊齊的金髮,稍微下垂的臉頰,溫和而堅定的微笑,略顯豐腴的身材。她站得筆直,像一塊歷經歲月風化作用的岩石。羅素不耐煩地問:
「妳到底是什麼人?」
「我是病監的責任護理師安琪拉.斯托。如同你一樣,我也正在執行公務,要審問的話請先與我討論過。現在我必須確認患者的狀況,所以請出去,羅素探員。」
羅素愣了一下,只好悻悻然地走出去。安琪拉面無表情地將耳溫槍塞進我的耳朵裡,我靜靜地默唸她剛才說的那個名詞,亞斯伯格、亞斯伯格⋯⋯她在診療單上寫下我的體溫。
37.2。
我喜歡拼圖,因為拼圖必須從複雜中提取簡單,可以一舉解開難關。遇到問題時瞬間的孤獨,以及與問題打交道的漫長時間;在想放棄的誘惑下,我們化解了複雜,理解了不能理解的東西,把苦惱變成喜悅。珠子、摺紙、骰子、魔術方塊、星形、三角形、四邊形、五邊形、同心圓和橢圓、火柴棍、瓢蟲、繩結、曲線和直線......我喜歡拼拼圖,但更喜歡製作拼圖。因為看一個人拼拼圖的方式,就可以知道他是個什麼樣的人。性子急躁的人會很快就放棄;而敏銳的人會先推敲一下答案,然後研究出解開的方法。安琪拉會是哪一種呢?是急性子?還是敏銳的人?我在紙上畫了這樣的圖形:
安琪拉像拔蔥一樣把耳溫槍從我耳朵拔出,悄悄地唸著三十六點五。我的身體與一年的歲月相似,我的身體是三十六點五度,而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發現我畫的圖案,她腦中複雜的電流開始流動,她抓起紙放在板子上拿筆揮動著,放下紙後我看到這個:
答對了!她跟我的思考方式是一樣的。如果我敏銳那她也是敏銳的;如果我說謊那麼她也是說謊的。她說:
「對稱是世界上最美的形態,最美的數字是質數。」
她什麼都沒問,而是將「我」解開了。為了瞭解她而設定的問題,也同時告訴她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是那些隱藏在圖形中的對稱和質數。
心形是最小質數2的對稱圖形;四葉草是質數3的對稱;鑰匙是5的對稱。她從這三個圖形中得知質數的數列,以及對稱的秘密,於是以相同的方式畫出接下來的質數7、11、13的對稱圖形。她追蹤我的想法路徑,同時履行觀察、推論、假設和證明。與我有著相同思考方式的她也是數學天才嗎?或者是個跟我一樣的笨蛋?她說道:
「對稱不管如何操作都不會變,心形就算左右對調還是心形;四葉草就算上下左右對調也還是四葉草。圓就算翻轉掉落仍是個圓,球在三次元空間也不會變。喜歡對稱就像喜歡真相一樣,不管如何操作,真相都是不會改變的。」
這句話聽起來不像是我,而是她自己喜愛對稱的原因。她也跟我一樣喜愛左右對稱的ᗅᗺᗷᗅ合唱團的音樂嗎?想到對稱心情就變好,我也開口了,
「=就像Decalcomanie 一樣,是完成稱稱的符號。不管再怎麼複雜或冗長的算式,只要有了=,兩邊就是對稱了。」
我在紙上,以=相隔畫了一個正三角形。=是我最喜歡的符號,而三角形是我最喜歡的圖形。
1×1=1
11×11=121
111×111=12321
1111×1111=1234321
11111×11111=123454321
111111×111111=12345654321
她看了金字塔圖形又看看我,接著問道:
「你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她的問題和像帶著尖銳魚鈎的羅素不一樣,她很溫柔、圓滑,不像是提問,反而像是掏出自己想說的話的手。我看著美麗的金字塔圖形,一邊想著我是從哪裡來的。
「從哪裡來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在哪裡?要往哪裡去?」
「是吧!也許那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畫的圖形就像是殺人現場的死亡記號。數字遊戲結束了,你說吧!不管你記得什麼都好。」
我再度低頭看我畫的金字塔,如霧一般的記憶中,浮現了一個大型金字塔,那是很久前就離開的柳樹之城,它在那個城市的正中央矗立著,不管在城市的任何地方都看得到。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天國少年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天國少年
李正明 又一鉅著
✽✽✽
漂泊世界的脫北難民∕數學天才∕自閉症少年∕一級國際罪犯
在驚奇的數學奧德賽之旅中尋找愛
在不可理解的人生裡尋找解答
美麗的事物讓我感到幸福,因為在美麗的事物中藏有數字。
數字看似是一個個單獨存在的東西,但其實所有關係都是繫在一起的,數學的世界裡沒有偶然。
世界廣闊,人們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樣多,但沒有一個人是孤獨的,我們所有人都像看不見的蜘蛛網一樣相互連接。
✽✽✽
暗夜的殺人命案,以鮮血留下謎樣的死亡記號,
行使緘默權的嫌疑犯……
二○○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凌晨在紐約一處住宅,發生一起謎樣的殺人命案。死者的臉部疑似有以酒精類的藥品消毒過的痕跡,屍體旁邊則用鮮血書寫了複雜且不明的數字和圖形記號,
1 11 21 1211 111221 312211⋯⋯
我是個騙子
現場逮捕的嫌疑犯,在CIA探員的審問下,持續行使緘默權拒絕陳述。調查進行中,發現該名嫌犯縱橫世界各地,是個涉及毒品交易,曾加入犯罪組織,涉嫌詐欺、詐賭、槍擊案件、非法入境、殺人等十多起案件,被國際刑警組織發出紅色通緝令的一級國際罪犯。
一直行使緘默權的嫌犯,與負責看護他的護理師一同解開數學題,藉由數學進行溝通、心靈交流。他開始一點一滴地向護理師透露祕密裡關於自己與謎樣的死亡記號的線索,一個漂泊世界的難民、自閉症患者、數學天才,同時也是頭號罪犯的人生……
分開的事物終將會再度相遇……
我知道死亡,因為它是我朋友。
作者簡介:
李正明(이정명)
慶北大學韓國語文系畢業,曾任職報社及雜誌社,擔任記者。他以集賢殿大學士連續謀殺事件為題材,於二○○六年創作了描述韓國文字發明史的長篇小說《樹大根深》,開創韓國歷史懸疑小說的先河。二○○七年發表描述韓國史上兩位天才畫師申潤福與金弘道畫作秘密的藝術推理小說《風之畫師》。
李正明的作品節奏明快,充滿熾烈的時代意識,並以具備歷史深度的題材而獲得讀者熱烈迴響,開啓了韓國紀實小說的新篇章。
《風之畫師》於二○○八年拍攝成電視劇,由文瑾瑩、朴新陽主演;《樹大根深》於二○一一年推出電視劇,由韓石圭、張赫、申世景主演,均受到矚目。二○一二年推出的《罪囚645號》,更是在出版前版權便已售出予英、法等五個國家。另著有《千年之後》、《向日葵》、《最後的郊遊》、《恐怖的回憶》等。
譯者簡介:
馮燕珠
新聞系畢業,曾任職記者、公關、企劃。某天毅然辭去工作,隻身赴韓吃泡菜進修,回國後踏入翻譯界,翻劇也翻書。一切得來不易,所以格外珍惜努力經營自己的「譯」界人生。譯有《老婆,今天可能有點辣》、《飛機雲》、《若有來生》等。
工作聯繫:yenchu18@gmail.com
章節試閱
第一天平壤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一月
我是二月二十九日生的,我喜歡我的生日。二跟二十九是質數,而二加二十九等於三十一也是質數。質數是天生孤獨的數字,在質數月的質數日出生的我也是孤獨的。另一個喜歡的數字是四,我喜歡每四年舉行一次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也喜歡每四年舉行一次的數學奧林匹亞競賽,還有要踩過四個壘包才能得到一分的棒球,以及棒球隊四號打者。我喜歡的時間是十一點十一分,因為11:11呈現完美的左右對稱,而且加起來的總和等於四。
暗夜殺人命案 留下三個謎團
《紐約每日新聞》二○○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一月
我是二月二十九日生的,我喜歡我的生日。二跟二十九是質數,而二加二十九等於三十一也是質數。質數是天生孤獨的數字,在質數月的質數日出生的我也是孤獨的。另一個喜歡的數字是四,我喜歡每四年舉行一次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也喜歡每四年舉行一次的數學奧林匹亞競賽,還有要踩過四個壘包才能得到一分的棒球,以及棒球隊四號打者。我喜歡的時間是十一點十一分,因為11:11呈現完美的左右對稱,而且加起來的總和等於四。
暗夜殺人命案 留下三個謎團
《紐約每日新聞》二○○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作者的話
在寫《天國的少年》期間,得到許多人直接和間接的幫助。對於脫北者們即使經歷苦難,也無法奪走他們對生命堅毅的熱情和對自由的執念,我深表敬意。
在執筆的過程中,曾參考已在韓國社會中定居的優秀脫北者們的各種記錄,以及網站上數百件脫北手記及文章,透過那些作品使本書內容更加豐富。雖然無法一一列出所有資料,但其中幾個具有代表性的如:《完全管制區域》(安明哲著)、《教化所之歌》(姜哲煥著)、《隱藏的收容所》(大衛.霍克著)等,我由這些作品獲得有關北韓政治犯收容所的內部情形,以及實際發生的真實情報,...
在寫《天國的少年》期間,得到許多人直接和間接的幫助。對於脫北者們即使經歷苦難,也無法奪走他們對生命堅毅的熱情和對自由的執念,我深表敬意。
在執筆的過程中,曾參考已在韓國社會中定居的優秀脫北者們的各種記錄,以及網站上數百件脫北手記及文章,透過那些作品使本書內容更加豐富。雖然無法一一列出所有資料,但其中幾個具有代表性的如:《完全管制區域》(安明哲著)、《教化所之歌》(姜哲煥著)、《隱藏的收容所》(大衛.霍克著)等,我由這些作品獲得有關北韓政治犯收容所的內部情形,以及實際發生的真實情報,...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一天 平壤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年十一月
第二天 收容所
二○○○年十一月~二○○二年三月
第三天 第一個故事 花燕
二○○二年三月~二○○二年九月
第三天 第二個故事 延吉
二○○二年九月~二○○三年二月
第四天 上海
二○○三年二月~二○○四年五月
第五天 澳門
二○○五年六月~二○○六年二月
第六天 首爾
二○○六年二月~二○○七年八月
第七天 第一個故事 墨西哥
二○○七年八月~二○○七年十一月
第七天 第二個故事 紐約
二○○七年十一月~二○○九年二月
六個月後 伯恩
...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年十一月
第二天 收容所
二○○○年十一月~二○○二年三月
第三天 第一個故事 花燕
二○○二年三月~二○○二年九月
第三天 第二個故事 延吉
二○○二年九月~二○○三年二月
第四天 上海
二○○三年二月~二○○四年五月
第五天 澳門
二○○五年六月~二○○六年二月
第六天 首爾
二○○六年二月~二○○七年八月
第七天 第一個故事 墨西哥
二○○七年八月~二○○七年十一月
第七天 第二個故事 紐約
二○○七年十一月~二○○九年二月
六個月後 伯恩
...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