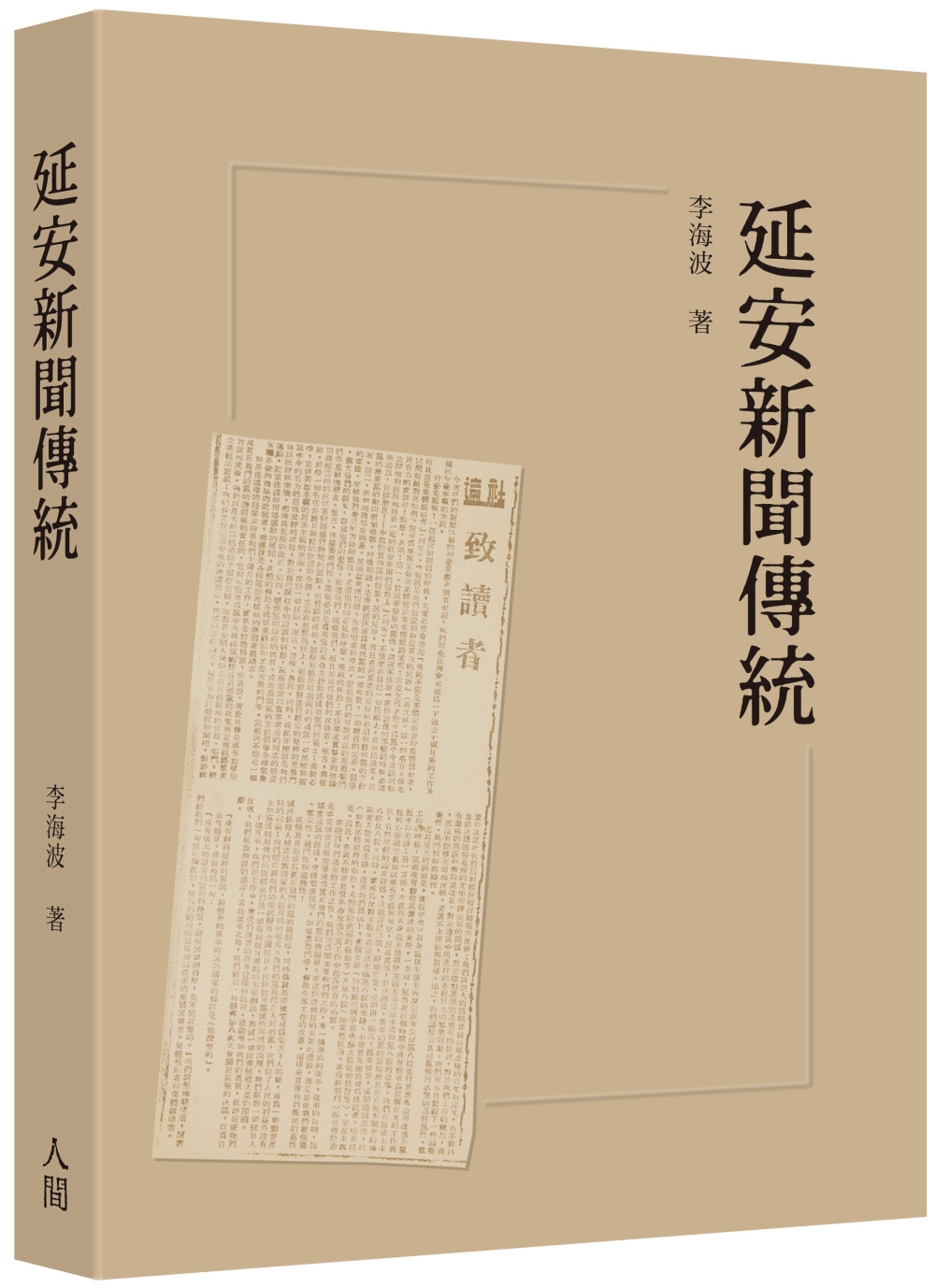中國特色新聞學自延安開始,這是一個基本判斷,因為它與革命黨的使命、執政黨的命運休戚與共。本書描述了延安新聞傳統的來龍去脈,打開了諸多討論的空間。作者把起點放在延安整風和政黨政治革新的敘述框架下,也即「革命史範式」中。雖然「革命史範式」在當下受到諸多質疑和挑戰,但這並不是因為「革命史範式」已經失效,毋寧是對這一範式的把握並沒有真正做到「內在視野」的貫通,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的理解沒有、也不可能真正打開「革命史範式」的活力,這也是本書試圖展開的工作。――呂新雨
延安新聞傳統,構成了一種獨特的現代新聞規範。如果與當代新聞專業主義進行比較分析,可以發現無論在形而上的價值訴求,還是在形而下的操作準則方面,都形成鮮明差異,我概括為「業餘路線」。這裡的「業餘」,並不意味著技術水準的低劣,而是強調一種打破專業化社會分工及其局限的自覺狀態,一方面新聞知識分子與社會民眾、進步政治建立有機聯繫,一方面人民群眾投身新聞傳播事業之中,使之真正成為共有、開放的公共領域。用汪暉的話說,「業餘」不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而是一個倫理性的問題,「一種倫理性的政治」。對於當代的新聞狀況,這無疑提供了一種批判性的思想資源。――李海波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延安新聞傳統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08 |
區域研究 |
$ 396 |
中文書 |
$ 396 |
新聞學 |
$ 396 |
中國歷史 |
$ 396 |
媒體傳播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延安新聞傳統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李海波
江蘇贛榆人,清華大學新聞學博士,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新聞學系主任,華東師範大學亞洲馬克思主義傳播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共新聞史、新聞傳播史論,曾任《體壇週報》、《足球報》編輯和記者,密蘇里大學訪問學者。
李海波
江蘇贛榆人,清華大學新聞學博士,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新聞學系主任,華東師範大學亞洲馬克思主義傳播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共新聞史、新聞傳播史論,曾任《體壇週報》、《足球報》編輯和記者,密蘇里大學訪問學者。
目錄
序 / 呂新雨……009
緒論 重訪延安的特殊歷史時刻……021
第一節 新聞公共性及其當代挑戰……021
第二節 中國新聞學的延安傳統……033
第三節 新聞大眾化:一種整合式視角……041
第一章 範式裂變:整風改版與政黨政治革新……051
第一節 黨性:從辦報方針到觀念作風……056
一、「我們生在新聞的時代」……059
二、黨管報紙與布爾什維克化……080
三、作為動員媒介的文宣事業……094
第二節 群眾性:重構新聞生產的邏輯……099
一、整風改版的群眾性面向……100
二、黨報、列寧主義政黨與群眾政治參與……105
三、新聞業群眾路線的多重蘊涵……113
本章小結……121
第二章 新型記者:有機知識分子的鍛造……125
第一節 「新的報紙」與「新的新聞工作者」……128
第二節 「新型記者」與「有機知識分子」……135
第三節 「有機知識分子」的培育程式……143
一、話語習得:把全黨辦成一個大學校……148
二、理論創新:開中國報界之新紀元……158
三、苦其心志:「一堂必須上的課」……168
四、勞其筋骨:在紡車聲中改造……182
本章小結……194
第三章 通訊員運動:從新聞編輯室走向基層……203
第一節 曲折展開:新聞大眾化運動的興起……206
一、大眾讀物社小試身手……207
二、解放日報社掀動波瀾……214
第二節 細膩革命:群眾運動的動員技術……224
一、宣傳教化:消解新聞專業的壁壘……226
二、組織調控:寫稿是測量黨性的尺度……235
三、典型示範:工農通訊員的光輝例子……244
四、通訊競賽:激發樸素的好勝心……253
本章小結……259
第四章 運動中的通訊員:運作機制與行為邏輯……265
第一節 高度組織化:通訊要素及流程勾勒……267
一、通訊員的人口統計學特徵……268
二、基幹通訊員、通訊幹事、本地通訊員……277
三、採訪寫作與稿件審查發表……284
第二節 行動者:工農幹部、新聞人與政黨……295
一、通訊寫作與工農文化翻身……296
二、你修理了文章,他修理了你……305
三、熱烈的喝彩,艱難的批評……313
第三節 個案:「邊區通訊之光」志丹縣……323
本章小結……331
第五章 「業餘路線」:延安新聞傳統的一種闡釋……341
第一節 做一個「業餘」的記者……341
第二節 黨與黨報:業餘路線的內在理路……347
一、先鋒隊的領導與啟蒙……350
二、群眾路線的信息流動……356
三、黨報的一種「理想類型」……362
第三節 「業餘」的倫理性政治……365
結語……371
後記……377
參考書目……379
緒論 重訪延安的特殊歷史時刻……021
第一節 新聞公共性及其當代挑戰……021
第二節 中國新聞學的延安傳統……033
第三節 新聞大眾化:一種整合式視角……041
第一章 範式裂變:整風改版與政黨政治革新……051
第一節 黨性:從辦報方針到觀念作風……056
一、「我們生在新聞的時代」……059
二、黨管報紙與布爾什維克化……080
三、作為動員媒介的文宣事業……094
第二節 群眾性:重構新聞生產的邏輯……099
一、整風改版的群眾性面向……100
二、黨報、列寧主義政黨與群眾政治參與……105
三、新聞業群眾路線的多重蘊涵……113
本章小結……121
第二章 新型記者:有機知識分子的鍛造……125
第一節 「新的報紙」與「新的新聞工作者」……128
第二節 「新型記者」與「有機知識分子」……135
第三節 「有機知識分子」的培育程式……143
一、話語習得:把全黨辦成一個大學校……148
二、理論創新:開中國報界之新紀元……158
三、苦其心志:「一堂必須上的課」……168
四、勞其筋骨:在紡車聲中改造……182
本章小結……194
第三章 通訊員運動:從新聞編輯室走向基層……203
第一節 曲折展開:新聞大眾化運動的興起……206
一、大眾讀物社小試身手……207
二、解放日報社掀動波瀾……214
第二節 細膩革命:群眾運動的動員技術……224
一、宣傳教化:消解新聞專業的壁壘……226
二、組織調控:寫稿是測量黨性的尺度……235
三、典型示範:工農通訊員的光輝例子……244
四、通訊競賽:激發樸素的好勝心……253
本章小結……259
第四章 運動中的通訊員:運作機制與行為邏輯……265
第一節 高度組織化:通訊要素及流程勾勒……267
一、通訊員的人口統計學特徵……268
二、基幹通訊員、通訊幹事、本地通訊員……277
三、採訪寫作與稿件審查發表……284
第二節 行動者:工農幹部、新聞人與政黨……295
一、通訊寫作與工農文化翻身……296
二、你修理了文章,他修理了你……305
三、熱烈的喝彩,艱難的批評……313
第三節 個案:「邊區通訊之光」志丹縣……323
本章小結……331
第五章 「業餘路線」:延安新聞傳統的一種闡釋……341
第一節 做一個「業餘」的記者……341
第二節 黨與黨報:業餘路線的內在理路……347
一、先鋒隊的領導與啟蒙……350
二、群眾路線的信息流動……356
三、黨報的一種「理想類型」……362
第三節 「業餘」的倫理性政治……365
結語……371
後記……377
參考書目……379
序
序
呂新雨
「延安道路」關乎中國的未來。
1981年,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tavrianos)出版《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他將「第三世界」看成是一系列不平等關係,由一些在經濟上依附並從屬於發達第一世界的國家和地區所組成,該書著重描述了第三世界從殖民主義到新殖民主義的失敗過程。雖然二十世紀第三世界的革命浪潮在全球範圍內湧現,但是一戰之後形成的歐洲列強在二戰後基本維持和延續了殖民帝國的完整,「其中的一個原因在於,除中國之外,第三世界的革命運動本質上都是民主主義性質的」,即資產階級基於民族主義而非社會主義的革命。
斯塔夫里阿諾斯在書中批評一些美國學者把共產黨的成功完全歸之於「中國的民族主義」,在他看來,中共能贏得民眾、戰勝國民黨還在於「他們是社會主義者」。而共產黨人之所以「了解民眾需求」,就因為有「延安道路」――不僅僅是一種戰鬥模式,也是生活方式,體現著人和社會的願望,「並提供了一種基於平等主義價值觀和廣大民眾參與之上的發展模式」,也就是群眾路線。「延安道路」對內以整風形式,要求黨員幹部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對外則積極發動農民參與政治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即以政黨政治的方式推動黨和農民群眾的融合,以構建革命的政治主體。在這一過程中,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基於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主義激情奔赴延安,他們首先面臨的就是自我改造的考驗,以適應新的政黨政治與群眾結合的嚴峻任務。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歷史角色和命運,不同的歷史闡述也在此大分野。在斯塔夫里阿諾斯看來:
中國的未來影響力將會取決於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解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乃至第三世界仍然未能解決的矛盾――精神刺激與物質刺激之間的矛盾、城鄉之間的矛盾、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的矛盾等。單靠國民生產總值的提高並不能解決這些矛盾,美國、蘇聯,以及第三世界的巴西、伊朗和印度尼西亞等國的經驗已經反覆證明了這一點。
這一論述值得在今天的語境中重新審視。
李海波博士的這本《延安新聞傳統》,把當下看成是「重訪延安的特殊歷史時刻」,因為歷史總是以複調的方式展開,這正是歷史的辯證法。我更強調的是「重返」,即今天的執政黨需要回到「延安道路」作為「新長征」的起點,因為「延安道路」致力於解決的問題並沒有終結,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延續,不僅鑒往知來,更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中國共產黨的新聞事業,正是在這個視野中需要「重返」自己的「中國特色新聞學」,即書中所言「中國特色新聞學歸根到底是社會主義新聞學,而不是什麼別的什麼主義新聞學」。
中國特色新聞學自延安開始,這是一個基本判斷,因為它與革命黨的使命、執政黨的命運休戚與共。本書描述了延安新聞傳統的來龍去脈,打開了諸多討論的空間。他把起點放在延安整風和政黨政治革新的敘述框架下,也即「革命史範式」中。雖然「革命史範式」在當下受到諸多質疑和挑戰,但這並不是因為「革命史範式」已經失效,毋寧是對這一範式的把握並沒有真正做到「內在視野」的貫通,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的理解沒有、也不可能真正打開「革命史範式」的活力,這也是本書試圖展開的工作。這其實並不是革命史範式的「新」、「舊」問題,不是用「新革命史範式」去取代舊範式,而是重新勘探回望歷史的立足點,這既需要打通「新」、「舊」,也需要貫穿「內」、「外」,更需要重建立場作為重新出發的起點。
從延安新聞傳統的視角切入,一個突出的尖銳問題是知識分子改造與中國革命的關係。濫觴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傷痕文學,知識分子苦難史的敘述成為主流,這其中黨內知識分子的聲音占了多數。在這一敘述的籠罩下,延安整風被回溯為知識分子受迫害史的開端。但是,如果把這一歷史放在第三世界知識分子的歷史角色與民族國家建構的關係中去看,意味就會完全不同。中國知識分子參加二十世紀革命以來的命運和心靈史,需要放置在第三世界的比較視野中去理解,才能發現問題的癥結及其獨特性。這一癥結需要在世界歷史的視野中進行梳理,也需要放在今天中國與世界的格局中研判。
作為接受啟蒙洗禮的五四之子,中國第一代青年知識分子投身共產主義革命的過程,是從靈魂深處進行的角色轉換,充滿了可歌可泣的艱難困苦、犧牲與自我犧牲,也伴隨著信念的堅守或幻滅,問題只在於如何闡釋知識分子的犧牲。關於「革命吞噬它的兒女」的「反思」與「控訴」,主要是指知識分子階層。知識分子首先需要接受「改造」,這本身就意味著決裂和犧牲,延安整風中知識分子靈魂深處革命即來源於此。這一「幸福」與「痛苦」並存的過程,同樣屬於二十世紀中國革命中無法忽略的思想畫卷,也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思想革命,是為了從無路的地方走出路來。與此同時,「改造」還是政黨組織對「幹部」的剛性需求,是對革命的知識分子主體詢喚的道德訴求。
過往研究多著重於知識分子失去「自我」的過程,革命對於知識分子「大寫的主體」再鍛造過程,則被遮蔽、扭曲和汙名。實際上,沒有這個鍛造過程,就沒有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完成――我們需要在這個第三世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視野下重讀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史以及犧牲史。知識分子「控訴史」敘述的悖論在於,通過知識分子的受難和犧牲否決了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集體信仰本身,從而取消了一代知識分子的歷史意義,其所完成的正是對第一代現代中國革命知識分子的自我否定。這正是被一些知識分子研究稱為「謎一般存在」的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現象:為什麼啟蒙一代的知識分子會自願地集體性接受政黨政治的「洗腦」?其實,這一問題的提出本身,已經是「革命史觀」被遮蔽的後果。它也被概括性地體現在一個悖論性的描述:啟蒙與救亡的關係,即所謂「救亡壓倒啟蒙」。然而救亡本身就是五四運動「啟蒙」的出發點和訴求,正因此,啟蒙一代走向政黨政治,不是別的,而是歷史大勢的體現。
美國學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曾檢討西方左翼社會運動失敗的原因,他發現「任何將個人自由提升到神聖位置的政治運動都有被新自由主義收編的危險」,1968年席捲西方世界的學生運動就被要求更多個人自由的欲望所扭曲:
個人自由的價值和社會正義並不必然相容;追求社會正義預設了社會團結和下述前提:考慮到某些更主要的、為社會平等或環境正義進行的鬥爭,需要壓抑個體的需求和欲望。……新自由主義修辭以其對個性自由的基本強調,有力地將自由至上主義、身分政治、多元主義、自戀的消費主義從想靠奪取國家權力來追求社會正義的社會力量中分離出來。比如,美國左翼長期面臨的棘手麻煩,便是無法一方面確立實現社會正義需要的集體紀律,另一方面又不冒犯政治參與者表達個人自由、徹底的承認與特殊身分的要求。新自由主義不曾創造這些差異,但能輕易利用它們――如果不是煽動的話。
「小資產階級性」與革命的結合,或是小資產階級的勝利,革命的失敗;或是相反。兩者必居其一,無法調和,這是革命的歷史齒輪所決定的。大衛.哈維所評述的西方左翼運動走向前者,中國革命走向後者――這是關於中國知識分子問題論爭中一切分歧的基點,即革命史觀與西方現代性史觀的衝突。正是在這樣的衝突中,「革命吞噬它的兒女」成為對革命的控訴,知識分子改造問題成為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獨特的旋律,迄今尚未定調。
在廓清上述歷史脈絡的前提下,我們才有可能重新打開「延安新聞傳統」的歷史畫卷。本書從1942年《解放日報》改版開啟討論,並非偶然。一方面,黨報改版與整風運動同步展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作為辦報的主體,首先碰到的就是辦報理念的革命――必須轉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軌道上,這是革命本身的訴求,也必然與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結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政黨政治對新聞業的規範甚於文藝,作為黨報的《解放日報》已經被置放在中共政黨組織傳播的歷史位置上――這是一個完全不同於歐美報刊作為資產階級上升階段同步起源的歷史。作為決定政黨組織生存和發展必不可少的信息溝通保障系統,需要鍛造「政黨組織傳播」的理論視野以重新梳理中共黨報理論與實踐的「革命史範式」,如此才能綱舉目張。政黨的自我定位與歷史使命,則是決定其組織傳播特性的關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作為中國特色的黨報理論與實踐的「政黨組織傳播」,應該成為一個新的理論研究範式。
政黨組織傳播體系的建立,首先要求的必然是黨報工作者本身的轉變。從本書的梳理中可以看到,1941年前後黨報知識分子在觀念形態上受到極大震撼。1941年11月,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上,《解放日報》記者發起「提高記者地位和待遇,尊重記者參訪自由」的提案。時任《解放日報》國際部編輯吳冷西回憶當時的情況,「對事對人都從個人的興趣、利益、得失出發,自高自大,有的甚至是相當狂妄,自己寫的稿子別人改一個字都不答應。許多人自由散漫,毫無紀律觀念,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想說什麼就順便說」。從「醉心於辦個『獨立刊物』」到走向群眾組織通訊員、幫助工農幹部寫稿改稿,這樣的轉換無疑是巨大且艱難的,卻正是政黨政治的內在邏輯要求,即成為貫通政黨組織和群眾運動的「有機知識分子」。
沒有這樣大規模的「有機知識分子」的存在,中國革命就不能完成。這也是本書關注「新型記者」與「有機知識分子」的緣由。在這個意義上,延安知識分子改造的歷史過程,呼應了幾乎同一時期在法西斯監獄中艱苦思考政黨、階級、知識分子與國家問題的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葛蘭西(Antonio Gramsci)。他在《獄中札記》中如此論述知識分子與群眾之間的辯證法:
人民群眾如果不在最廣大的意義上把自己組織起來,就不能「區別」自身,就不可能真正獨立;而要是沒有知識分子,也就是說,沒有組織者和領導者,換句話說,沒有由於存在著一個「專門」從概念上和哲學上研究思想的集團,而從理論—實踐的關係中具體地區分出來的理論方面,也就不可能成為有組織的群體。但是,造就知識分子的過程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它充滿著矛盾、前進和倒退、分散和重新集合。
葛蘭西從政黨政治的角度對「有機知識分子」的經典論述,與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大眾文化的論述相映成輝,說明這其實是世界範圍內共產主義運動共同面對的結構性問題。區別僅在於,身陷囹圄的葛蘭西只能從失敗經驗出發進行理論化的分析,毛澤東則在廣袤的中國西北大地上展開了實踐性的探索。從列寧到葛蘭西、毛澤東,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此展開了自己複雜而曲折的歷史邏輯。
知識分子的犧牲是中國革命的一個重要面向,它無法與整個二十世紀中國革命中無數革命者的犧牲相分離。
1936年,早期無政府主義的信仰者巴金翻譯了屠格涅夫的散文〈門檻〉,它立刻成為整整一代五四啟蒙知識分子走向革命的「聖經」:
我看見一所大廈。正面一道窄門大開著,門裡一片陰暗的濃霧。高高的門檻外面站著一個女郎……一個俄羅斯的女郎。
濃霧裡吹著帶雪的風,從那建築的深處透出一股寒氣,同時還有一個緩慢、重濁的聲音問著:「啊,你想跨進這門檻來做什麼?你知道裡面有什麼東西在等著你?」
「我知道。」女郎這樣回答。
「寒冷、飢餓、憎恨、嘲笑、輕視、侮辱、監獄、疾病,甚至於死亡?」
「我知道。」
「跟人們的疏遠,完全的孤獨?」
「我知道,我準備好了。我願意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擊。」
「不僅是你的敵人,就是你的親戚,你的朋友也都要給你這些痛苦、這些打擊?」
「是……就是他們給我這些,我也要忍受。」
「好。你也準備著犧牲嗎?」
「是。」
「這是無名的犧牲,你會滅亡,甚至沒有人……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尊崇地紀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我不要人憐惜。我也不要名聲。」
「你甘心去犯罪?」
姑娘埋下了她的頭。
「我也甘心……去犯罪。」
裡面的聲音停了一會兒。過後又說出這樣的話:
「你知道將來在困苦中你會否認你現在這個信仰,你會以為你是白白地浪費了你的青春?」
「這一層我也知道。我只求你放我進去。」
「進來吧。」
女郎跨進了門檻。一幅厚簾子立刻放下來。
「傻瓜!」有人在後面嘲罵。
「一個聖人!」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傳來了這一聲回答。
這篇具有極大預言性的散文,已經用「傻瓜」和「聖人」界定了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肖像。這也是今天中國知識分子研究的關鍵詞,不過歷史語境卻有了很大的轉換。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語境下,「聖人」和「傻瓜」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只有甘做「傻瓜」才能成就「聖人」。今天,這兩個名詞卻彼此分離。作為「傻瓜」的歷史內容隱匿了,成為不被理解的歷史之謎。「理想」如屠格涅夫所預料的那樣被否認了,只剩下被強加的「苦難」,以及建立在空洞的苦難基礎上的自我神聖感。
如果當年中國的知識分子是認定了一切犧牲而邁入革命的門檻,那麼建立在一個被自己否決的理想上,還有可能獲得「神聖性」嗎?中國的知識分子到底為什麼要承擔革命的十字架,只是為了否定十字架本身嗎?這樣的「神聖性」其實是自我消解的。把知識分子從血與汙的革命中分離出來,恰恰也構成了對整個二十世紀知識分子的否決,這樣的知識分子研究只能陷入了無法自我解脫的悖論中。正是因為二十世紀中國社會歷史性的城鄉分裂,才有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為此前赴後繼。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是二十世紀總體性悲劇的一部分,知識分子的苦難是二十世紀可歌可泣的革命內在組成,因為革命正是由新型知識分子啟蒙和領導的。
1982年,蕭軍再版了書稿《側面—從臨汾到延安》,他在新版前言中寫道:「我們能有今天這局面:祖國獨立了,民族解放了,人民翻身了,以及開始走向一個沒有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的現實大路上,這是來之不易的!歷史上每一寸小小的改革和進步,那全是由若干革命先行者的熱血和頭顱,生命和汗水,辛勤勞動,艱難忍耐……而換得來的。……我為什麼要寫這段旅行記,也就是要對比地觀照一下當時的政治、社會……制度:什麼是應該肯定的,發揚的;什麼是應該改造的,消滅的;也觀照一下『人』,人之中,什麼是應該肯定的,發揚的;什麼是應該否定的、消滅的,這裡並無任何個人的恩、怨、愛、惡……在其間,――一切以人民革命利益為依歸。」
這就是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最後自白。丁玲在生命的最後歲月裡,把重回延安看成晚年一大宿願。1985年4月,她在延安大學講話:沒有延安,就沒有我以後的50年,我是在這塊土地上,由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轉變為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有了延安墊底,我才能戰勝以後的艱難。這次訪問中,丁玲還參觀了清涼山的解放日報社舊址。這時距離她去世已不到一年。
今天,當我們站在歷史的界碑前,重新回顧延安新聞傳統的時候,這會是一個新的「重新集合」的時代嗎?
2020年5月 上海
呂新雨
「延安道路」關乎中國的未來。
1981年,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tavrianos)出版《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他將「第三世界」看成是一系列不平等關係,由一些在經濟上依附並從屬於發達第一世界的國家和地區所組成,該書著重描述了第三世界從殖民主義到新殖民主義的失敗過程。雖然二十世紀第三世界的革命浪潮在全球範圍內湧現,但是一戰之後形成的歐洲列強在二戰後基本維持和延續了殖民帝國的完整,「其中的一個原因在於,除中國之外,第三世界的革命運動本質上都是民主主義性質的」,即資產階級基於民族主義而非社會主義的革命。
斯塔夫里阿諾斯在書中批評一些美國學者把共產黨的成功完全歸之於「中國的民族主義」,在他看來,中共能贏得民眾、戰勝國民黨還在於「他們是社會主義者」。而共產黨人之所以「了解民眾需求」,就因為有「延安道路」――不僅僅是一種戰鬥模式,也是生活方式,體現著人和社會的願望,「並提供了一種基於平等主義價值觀和廣大民眾參與之上的發展模式」,也就是群眾路線。「延安道路」對內以整風形式,要求黨員幹部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對外則積極發動農民參與政治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即以政黨政治的方式推動黨和農民群眾的融合,以構建革命的政治主體。在這一過程中,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基於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主義激情奔赴延安,他們首先面臨的就是自我改造的考驗,以適應新的政黨政治與群眾結合的嚴峻任務。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歷史角色和命運,不同的歷史闡述也在此大分野。在斯塔夫里阿諾斯看來:
中國的未來影響力將會取決於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解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乃至第三世界仍然未能解決的矛盾――精神刺激與物質刺激之間的矛盾、城鄉之間的矛盾、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的矛盾等。單靠國民生產總值的提高並不能解決這些矛盾,美國、蘇聯,以及第三世界的巴西、伊朗和印度尼西亞等國的經驗已經反覆證明了這一點。
這一論述值得在今天的語境中重新審視。
李海波博士的這本《延安新聞傳統》,把當下看成是「重訪延安的特殊歷史時刻」,因為歷史總是以複調的方式展開,這正是歷史的辯證法。我更強調的是「重返」,即今天的執政黨需要回到「延安道路」作為「新長征」的起點,因為「延安道路」致力於解決的問題並沒有終結,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延續,不僅鑒往知來,更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中國共產黨的新聞事業,正是在這個視野中需要「重返」自己的「中國特色新聞學」,即書中所言「中國特色新聞學歸根到底是社會主義新聞學,而不是什麼別的什麼主義新聞學」。
中國特色新聞學自延安開始,這是一個基本判斷,因為它與革命黨的使命、執政黨的命運休戚與共。本書描述了延安新聞傳統的來龍去脈,打開了諸多討論的空間。他把起點放在延安整風和政黨政治革新的敘述框架下,也即「革命史範式」中。雖然「革命史範式」在當下受到諸多質疑和挑戰,但這並不是因為「革命史範式」已經失效,毋寧是對這一範式的把握並沒有真正做到「內在視野」的貫通,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的理解沒有、也不可能真正打開「革命史範式」的活力,這也是本書試圖展開的工作。這其實並不是革命史範式的「新」、「舊」問題,不是用「新革命史範式」去取代舊範式,而是重新勘探回望歷史的立足點,這既需要打通「新」、「舊」,也需要貫穿「內」、「外」,更需要重建立場作為重新出發的起點。
從延安新聞傳統的視角切入,一個突出的尖銳問題是知識分子改造與中國革命的關係。濫觴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傷痕文學,知識分子苦難史的敘述成為主流,這其中黨內知識分子的聲音占了多數。在這一敘述的籠罩下,延安整風被回溯為知識分子受迫害史的開端。但是,如果把這一歷史放在第三世界知識分子的歷史角色與民族國家建構的關係中去看,意味就會完全不同。中國知識分子參加二十世紀革命以來的命運和心靈史,需要放置在第三世界的比較視野中去理解,才能發現問題的癥結及其獨特性。這一癥結需要在世界歷史的視野中進行梳理,也需要放在今天中國與世界的格局中研判。
作為接受啟蒙洗禮的五四之子,中國第一代青年知識分子投身共產主義革命的過程,是從靈魂深處進行的角色轉換,充滿了可歌可泣的艱難困苦、犧牲與自我犧牲,也伴隨著信念的堅守或幻滅,問題只在於如何闡釋知識分子的犧牲。關於「革命吞噬它的兒女」的「反思」與「控訴」,主要是指知識分子階層。知識分子首先需要接受「改造」,這本身就意味著決裂和犧牲,延安整風中知識分子靈魂深處革命即來源於此。這一「幸福」與「痛苦」並存的過程,同樣屬於二十世紀中國革命中無法忽略的思想畫卷,也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思想革命,是為了從無路的地方走出路來。與此同時,「改造」還是政黨組織對「幹部」的剛性需求,是對革命的知識分子主體詢喚的道德訴求。
過往研究多著重於知識分子失去「自我」的過程,革命對於知識分子「大寫的主體」再鍛造過程,則被遮蔽、扭曲和汙名。實際上,沒有這個鍛造過程,就沒有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完成――我們需要在這個第三世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視野下重讀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史以及犧牲史。知識分子「控訴史」敘述的悖論在於,通過知識分子的受難和犧牲否決了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集體信仰本身,從而取消了一代知識分子的歷史意義,其所完成的正是對第一代現代中國革命知識分子的自我否定。這正是被一些知識分子研究稱為「謎一般存在」的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現象:為什麼啟蒙一代的知識分子會自願地集體性接受政黨政治的「洗腦」?其實,這一問題的提出本身,已經是「革命史觀」被遮蔽的後果。它也被概括性地體現在一個悖論性的描述:啟蒙與救亡的關係,即所謂「救亡壓倒啟蒙」。然而救亡本身就是五四運動「啟蒙」的出發點和訴求,正因此,啟蒙一代走向政黨政治,不是別的,而是歷史大勢的體現。
美國學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曾檢討西方左翼社會運動失敗的原因,他發現「任何將個人自由提升到神聖位置的政治運動都有被新自由主義收編的危險」,1968年席捲西方世界的學生運動就被要求更多個人自由的欲望所扭曲:
個人自由的價值和社會正義並不必然相容;追求社會正義預設了社會團結和下述前提:考慮到某些更主要的、為社會平等或環境正義進行的鬥爭,需要壓抑個體的需求和欲望。……新自由主義修辭以其對個性自由的基本強調,有力地將自由至上主義、身分政治、多元主義、自戀的消費主義從想靠奪取國家權力來追求社會正義的社會力量中分離出來。比如,美國左翼長期面臨的棘手麻煩,便是無法一方面確立實現社會正義需要的集體紀律,另一方面又不冒犯政治參與者表達個人自由、徹底的承認與特殊身分的要求。新自由主義不曾創造這些差異,但能輕易利用它們――如果不是煽動的話。
「小資產階級性」與革命的結合,或是小資產階級的勝利,革命的失敗;或是相反。兩者必居其一,無法調和,這是革命的歷史齒輪所決定的。大衛.哈維所評述的西方左翼運動走向前者,中國革命走向後者――這是關於中國知識分子問題論爭中一切分歧的基點,即革命史觀與西方現代性史觀的衝突。正是在這樣的衝突中,「革命吞噬它的兒女」成為對革命的控訴,知識分子改造問題成為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獨特的旋律,迄今尚未定調。
在廓清上述歷史脈絡的前提下,我們才有可能重新打開「延安新聞傳統」的歷史畫卷。本書從1942年《解放日報》改版開啟討論,並非偶然。一方面,黨報改版與整風運動同步展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作為辦報的主體,首先碰到的就是辦報理念的革命――必須轉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軌道上,這是革命本身的訴求,也必然與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結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政黨政治對新聞業的規範甚於文藝,作為黨報的《解放日報》已經被置放在中共政黨組織傳播的歷史位置上――這是一個完全不同於歐美報刊作為資產階級上升階段同步起源的歷史。作為決定政黨組織生存和發展必不可少的信息溝通保障系統,需要鍛造「政黨組織傳播」的理論視野以重新梳理中共黨報理論與實踐的「革命史範式」,如此才能綱舉目張。政黨的自我定位與歷史使命,則是決定其組織傳播特性的關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作為中國特色的黨報理論與實踐的「政黨組織傳播」,應該成為一個新的理論研究範式。
政黨組織傳播體系的建立,首先要求的必然是黨報工作者本身的轉變。從本書的梳理中可以看到,1941年前後黨報知識分子在觀念形態上受到極大震撼。1941年11月,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上,《解放日報》記者發起「提高記者地位和待遇,尊重記者參訪自由」的提案。時任《解放日報》國際部編輯吳冷西回憶當時的情況,「對事對人都從個人的興趣、利益、得失出發,自高自大,有的甚至是相當狂妄,自己寫的稿子別人改一個字都不答應。許多人自由散漫,毫無紀律觀念,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想說什麼就順便說」。從「醉心於辦個『獨立刊物』」到走向群眾組織通訊員、幫助工農幹部寫稿改稿,這樣的轉換無疑是巨大且艱難的,卻正是政黨政治的內在邏輯要求,即成為貫通政黨組織和群眾運動的「有機知識分子」。
沒有這樣大規模的「有機知識分子」的存在,中國革命就不能完成。這也是本書關注「新型記者」與「有機知識分子」的緣由。在這個意義上,延安知識分子改造的歷史過程,呼應了幾乎同一時期在法西斯監獄中艱苦思考政黨、階級、知識分子與國家問題的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葛蘭西(Antonio Gramsci)。他在《獄中札記》中如此論述知識分子與群眾之間的辯證法:
人民群眾如果不在最廣大的意義上把自己組織起來,就不能「區別」自身,就不可能真正獨立;而要是沒有知識分子,也就是說,沒有組織者和領導者,換句話說,沒有由於存在著一個「專門」從概念上和哲學上研究思想的集團,而從理論—實踐的關係中具體地區分出來的理論方面,也就不可能成為有組織的群體。但是,造就知識分子的過程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它充滿著矛盾、前進和倒退、分散和重新集合。
葛蘭西從政黨政治的角度對「有機知識分子」的經典論述,與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大眾文化的論述相映成輝,說明這其實是世界範圍內共產主義運動共同面對的結構性問題。區別僅在於,身陷囹圄的葛蘭西只能從失敗經驗出發進行理論化的分析,毛澤東則在廣袤的中國西北大地上展開了實踐性的探索。從列寧到葛蘭西、毛澤東,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此展開了自己複雜而曲折的歷史邏輯。
知識分子的犧牲是中國革命的一個重要面向,它無法與整個二十世紀中國革命中無數革命者的犧牲相分離。
1936年,早期無政府主義的信仰者巴金翻譯了屠格涅夫的散文〈門檻〉,它立刻成為整整一代五四啟蒙知識分子走向革命的「聖經」:
我看見一所大廈。正面一道窄門大開著,門裡一片陰暗的濃霧。高高的門檻外面站著一個女郎……一個俄羅斯的女郎。
濃霧裡吹著帶雪的風,從那建築的深處透出一股寒氣,同時還有一個緩慢、重濁的聲音問著:「啊,你想跨進這門檻來做什麼?你知道裡面有什麼東西在等著你?」
「我知道。」女郎這樣回答。
「寒冷、飢餓、憎恨、嘲笑、輕視、侮辱、監獄、疾病,甚至於死亡?」
「我知道。」
「跟人們的疏遠,完全的孤獨?」
「我知道,我準備好了。我願意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擊。」
「不僅是你的敵人,就是你的親戚,你的朋友也都要給你這些痛苦、這些打擊?」
「是……就是他們給我這些,我也要忍受。」
「好。你也準備著犧牲嗎?」
「是。」
「這是無名的犧牲,你會滅亡,甚至沒有人……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尊崇地紀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我不要人憐惜。我也不要名聲。」
「你甘心去犯罪?」
姑娘埋下了她的頭。
「我也甘心……去犯罪。」
裡面的聲音停了一會兒。過後又說出這樣的話:
「你知道將來在困苦中你會否認你現在這個信仰,你會以為你是白白地浪費了你的青春?」
「這一層我也知道。我只求你放我進去。」
「進來吧。」
女郎跨進了門檻。一幅厚簾子立刻放下來。
「傻瓜!」有人在後面嘲罵。
「一個聖人!」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傳來了這一聲回答。
這篇具有極大預言性的散文,已經用「傻瓜」和「聖人」界定了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肖像。這也是今天中國知識分子研究的關鍵詞,不過歷史語境卻有了很大的轉換。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語境下,「聖人」和「傻瓜」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只有甘做「傻瓜」才能成就「聖人」。今天,這兩個名詞卻彼此分離。作為「傻瓜」的歷史內容隱匿了,成為不被理解的歷史之謎。「理想」如屠格涅夫所預料的那樣被否認了,只剩下被強加的「苦難」,以及建立在空洞的苦難基礎上的自我神聖感。
如果當年中國的知識分子是認定了一切犧牲而邁入革命的門檻,那麼建立在一個被自己否決的理想上,還有可能獲得「神聖性」嗎?中國的知識分子到底為什麼要承擔革命的十字架,只是為了否定十字架本身嗎?這樣的「神聖性」其實是自我消解的。把知識分子從血與汙的革命中分離出來,恰恰也構成了對整個二十世紀知識分子的否決,這樣的知識分子研究只能陷入了無法自我解脫的悖論中。正是因為二十世紀中國社會歷史性的城鄉分裂,才有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為此前赴後繼。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是二十世紀總體性悲劇的一部分,知識分子的苦難是二十世紀可歌可泣的革命內在組成,因為革命正是由新型知識分子啟蒙和領導的。
1982年,蕭軍再版了書稿《側面—從臨汾到延安》,他在新版前言中寫道:「我們能有今天這局面:祖國獨立了,民族解放了,人民翻身了,以及開始走向一個沒有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的現實大路上,這是來之不易的!歷史上每一寸小小的改革和進步,那全是由若干革命先行者的熱血和頭顱,生命和汗水,辛勤勞動,艱難忍耐……而換得來的。……我為什麼要寫這段旅行記,也就是要對比地觀照一下當時的政治、社會……制度:什麼是應該肯定的,發揚的;什麼是應該改造的,消滅的;也觀照一下『人』,人之中,什麼是應該肯定的,發揚的;什麼是應該否定的、消滅的,這裡並無任何個人的恩、怨、愛、惡……在其間,――一切以人民革命利益為依歸。」
這就是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最後自白。丁玲在生命的最後歲月裡,把重回延安看成晚年一大宿願。1985年4月,她在延安大學講話:沒有延安,就沒有我以後的50年,我是在這塊土地上,由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轉變為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有了延安墊底,我才能戰勝以後的艱難。這次訪問中,丁玲還參觀了清涼山的解放日報社舊址。這時距離她去世已不到一年。
今天,當我們站在歷史的界碑前,重新回顧延安新聞傳統的時候,這會是一個新的「重新集合」的時代嗎?
2020年5月 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