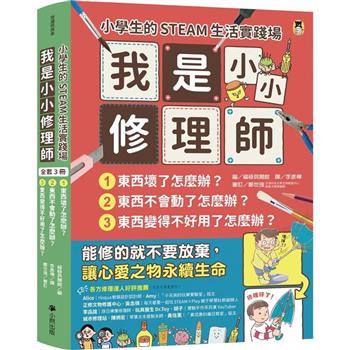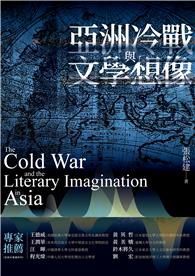圖書名稱:乩童警探
張國立全新三部曲犯罪小說
《乩童警探》愛與救贖的第一彈:
豪宅祖孫三人同時暴斃,報警的孫女恨透了這個家
死刑犯卻因心臟偏移逃過一死。
這是巧合還是冤情?
家庭變故讓羅蟄從神壇走向警壇,家族命案竟又帶他回到宮廟?
真凶,難道只有天知道?
那時大家都說他離開了神明,只有他知道:是神明不要他了。
十七歲那年,他幾乎每天擲出兩個笑筊,
直到下定決心去台北念書,神明給了答案:聖筊。
離家多年的羅蟄,唯一的心願卻是將弟弟帶回家
如今回到壇前,他得先面對自己,才能面對這樁懸案……
林家滅門案的凶手朱俊仁,因罪大惡極判處死刑。
儘管朱俊仁矢口否認殺人,他還是在檢察官、法醫、看守所所長的共同見證下執刑完畢,由法務部長於深夜記者會宣布死亡。參與見證的刑警羅蟄(小蟲)卻覺得氣氛不對,他衝進行刑現場查看,果然朱俊仁因為器官轉位,心臟不在左邊並未死亡。
回到案發當下,富商林添財、其父、其子同時在豪宅中死亡,除了所屬生化科技公司的工程師朱俊仁外,最有可能的嫌疑犯就是有不在場證明的美豔妻子林吳瓊芬、拖油瓶女兒林家珍和印傭莉塔,四人皆有動機,卻苦無證據。
在朱俊仁未死的情況下,法務部該如何因應?這案件是否有其他隱情未明?曾被溫府千歲收為義子的羅蟄,又如何演出一場「上天審案」大戲呢?
本書特色
★張國立全新三部曲犯罪小說
★乩童X警察,帶有冷硬派色彩、又有著台灣本土風味的主角
★一樁命案帶出家庭、官場政治與情感的精采糾葛,究竟誰是誰的救贖?
作者簡介
張國立
知名作家/美食、旅遊達人/擅長推理小說、歷史小說等。
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畢業,曾任《時報周刊》總編輯,得過國內各大文學獎項與金鼎獎,文筆既可詼諧亦可正經,作品涵蓋文學、軍事、歷史、劇本、遊記等各類題材。近期作品:《炒飯狙擊手》、《金陵福 史上第二偉大的魔術師》、《海龍改改》、《一口咬掉人生》、《戰爭之外》、《鄭成功密碼》、《張大千與張學良的晚宴》、《棄業偵探:不會死的人,一直在逃亡的億萬富翁》、《棄業偵探01:沒有嘴巴的貓,拒絕脫罪的嫌疑犯》、《偷眼淚的天使》……等,小說《炒飯狙擊手》已售出北美、尼德蘭(荷蘭)等國外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