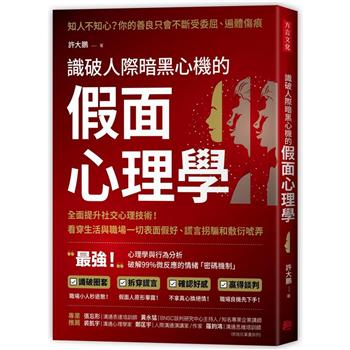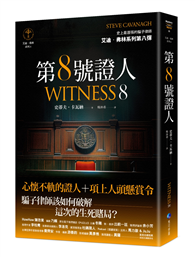第一章
上TED的那一刻:他的頭安在機器人身上
在TED三十周年研討會上,沒有肉體的史諾登(Edward Snowden)忽然現身,震撼了群聚在現場的科技業巨頭們。一個仔細裁切過的史諾登臉部影像,被放映在一個小螢幕上,這個小螢幕則貼在一個能行走的「網真」(telepresence) 機器人上。但是,並不是這種科技巫術讓現場滿座的一千二百位來賓大呼驚訝,而是他們事前完全不知道,付了七千五百美元,坐在普通座位區,竟然能聽到讓當今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蒙羞的間諜現身說法。
在二○一四年三月十八日這一天,史諾登真實的身體還安全地隱藏在莫斯科,因為如果他真的以肉體形式現身在溫哥華,很可能馬上就被引渡到美國,面對歐巴馬政府對他從事間諜活動的起訴。因為他披露了政府機密檔案,大量由美國間諜機構和科技大廠與電信公司合作,聯手主導的全球監控計畫,因此公諸於世。不過,他的臉部影像訊號很清晰,顯然也讓採訪他的人,也就是TED的策畫人與數位先驅安德森(Chris Anderson) 感到欣慰。
安德森之前是新聞從業人員,他的非營利基金會種子基金會(Sapling Foundation)在二○○一年接管TED。在花了數個月的時間,努力完成全世界最知名(或最聲名狼藉,端視你的角度)告密者的虛擬外觀後,安德森看到史諾登的臉時,一定放下心中的一塊大石頭。安德森事前先找到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的一個人幫忙,而史諾登也花了點心思學習如何使用這部機器。這部機器讓他可以聽、可以看,還能投射他的影像與聲音,甚至還能啟動「聚會模式」,以開啟更多環繞麥克風,而進行這些訓練的場所就在ACLU的紐約辦公室。當史諾登第一次能掌控這部機器時,安德森告訴新聞部落格Mashable的威爾斯(Amanda Wills):「他讓機器人走到窗邊看自由女神像。」
現在,這個受過牛津教育的安德森,以一身極具個人風格的輕鬆穿著,身著藍色格子長袖襯衫、黑色長褲,沒打領帶,對著觀眾正式宣佈此刻要探討的主題:「公民權利與網路的未來」。這些人都知道史諾登批露政府監控個資的恐怖事實,也知道其他人正威脅到網路文化中的消費者信心,最終將影響到在網網相連的世界中,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的跨國公司其優異的獲利能力。
「所以,我非常歡迎揭發這件消息的幕後人士來到TED講臺上,」安德森繼續說著,觀眾也報以熱烈的掌聲。「艾德(按:史諾登的暱稱)此刻正在俄羅斯某個遙遠的地方,從他的筆電遙控這部機器,所以他可以看見這部機器能看見的任何東西。艾德,歡迎你來到TED,你現在到底能看到什麼呢?」
史諾登的聲音從音響系統播放出來,他回答:「哈,我可以看見每一個人,這真是太神奇了!」現場觀眾也跟著大笑。安德森稍早問過觀眾,是否認為史諾登「其實是英雄」,只有半數觀眾舉手同意。但稍後,當史諾登遙控的機器人在整個大廳走動時,很多人都要求要和「史諾機器人」一起玩自拍。
安德森發了一則推特訊息:「你永遠不會知道在TED會遇見誰。」並附上谷歌共同創辦人布林(Sergey Brin)的照片,布林的手臂還環抱著這部機器。
在喧鬧的氣氛中,讓人很容易忘記,史諾登其實和他的科技同業置身於非常不同的處境。他們可以隨意自由來去,還可以把他們和也許是全世界最想尋獲的人虛擬相遇的有趣經驗,說給其他人聽。但史諾登本人則無從選擇,只能繼續躲藏,他的人身安全完全仰賴俄羅斯領導人普丁(Vladimir Putin)的保護。普丁此刻也面臨與美國作對的極大壓力,且因為他當時正在入侵克里米亞,而必須同時面對西方強權的憤怒。
史諾登的壓力也不小,他能成功自國家安全體制叛逃,其實受益於他已經揭露的政府單位合約,而這些合約可能會轉而流到這些看似支持的群眾手中。谷歌的布林就是這樣的情形,他看起來似乎很高興能和史諾登有個人的接觸機會,但他也知道,他自己與國安局和其他情報機關的關係已經開始被質疑。谷歌、微軟(Microsoft)、蘋果(Apple)、雅虎(Yahoo)與臉書(Facebook)等最高主管,在採訪與社群媒體貼文以及聯合聲明中,都對國安局侵犯他們的消費者資料而表達憤怒,但他們心知肚明,跟國安單位的關係其實比表面上的嫌棄更緊密。
兩天之後,安德森透過視頻技術採訪了另一位TED來賓,國安局副局長萊傑特(Richard Ledgett)。在史諾登確定現身之前,安德森其實邀請了國安局參加這場研討會,但國安局拒絕參加,直到史諾登與他的機器人現身之後才答應,很顯然此舉震驚了國安局。
「我們不知道他會在這裡出現。你們這群人實在太厲害了,可以安排這樣的場合,實在令大家驚訝。」萊傑特冷冷地回應了安德森。
雖然這段話說得還算友善,但他對史諾登卻沒說一句好話。他認為,「把史諾登視為告密者,事實上是傷害了合法的告發活動。」但是,他在沒有詳細說明下也坦承,「我們必須更透明」,但不是對「壞人」更透明。 他也承認,國安局連帶讓美國科技公司名譽受損。
那麼,史諾登揭露政府與企業合作進行大規模的隱私破壞行動,國安局首腦的主要辯詞是什麼?基本上就是:「大家都在做。」
「企業和我們的處境一樣艱難。我們強迫企業提供資料,就像這世界的其他國家做的事一樣。」萊傑特說,「每一個工業國家都有某種強迫企業提供資訊的合法攔截計畫,而且企業也多半會配合計畫,就像俄羅斯、英國、中國、印度或法國,你可以隨便說一個國家,都是這樣。這些洩密行為被廣泛描述為『你不能信任A公司,因為他們可能會威脅到你的隱私』,但這種說法只對世界上那些與這類國家打交道的公司才成立。」
基本上,他說,美國科技公司因為協助政府的監控行動,而被全球譴責,因為這些公司剛好主導相關市場。「有些國家,包括我們的友邦,推出的行銷語言是『你不能相信美國,但你可以相信我們(非美國)的電信公司,因為我們是安全的。』他們這種說詞是為了反擊美國公司在雲端領域大規模的前衛技術。」
一天後,谷歌的另一位共同創辦人佩吉(Larry Page)接受羅斯(Charlie Rose)採訪,試圖努力擺脫他與同事面對的責難。
「對我而言,政府祕密進行這些勾當卻沒告訴我們,真的很令人氣餒,」佩吉說,「如果我們必須保護你,以及我們的使用者,讓我們從未討論過的資料免於受到政府的侵犯,那我認為,我們也就不會有民主了。」
佩吉認為,政府從谷歌與其他公司取得資料的方法,實在很不智,「政府祕密從事這些行為,事實上對自己造成很大的傷害。」他說,「我們必須對這個做法公開辯論,否則我們就不會有一個機能完善的民主。那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政府的行動到底有多隱密?谷歌與其他科技集團,真的可以誠實地宣稱自己很意外嗎?
究竟誰知道什麼,以及何時浮出檯面的問題,六個星期之後揭曉了。曾經和史諾機器人看起來親密互動的布林,將出現在媒體報告中,因為國安局局長亞歷山大(General Keith Alexander)寄了一封耐人尋味的信函,對像是谷歌總裁舒密特。
半島電視台美國頻道的利奧波德(Jason Leopold),根據《資訊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提出要求,這封信才得以解密。寫這封信的時間是二○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這是一封邀請函,邀請舒密特參加一場高度機密的合作會議,各方與會代表包括國防部(Defense Department)、國土安全部(Homeland Security)與國安局,以及十八位美國公司總裁。
在這封信中,這項合作行動被描述為「長期安全框架(Enduring Security Framework, ESF)工作,也就是在重要的(通常也是機密的)安全議題上,將協調政府與企業的行動。」 這封信邀請舒密特出席會議,因為谷歌創辦人「布林已經出席過先前的會議,但是無法參加這次預定的會議。」舒密特也很遺憾,因為他在這場簡報進行時,人並不在城裡。
在更早的時間,也就是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時,情報頭子國安局局長亞歷山大寫電子郵件給布林:「感謝你的團隊參與長期安全框架工作。我認為,長期安全框架對於國家反擊網路的威脅,實在不可或缺,因此真的非常感激瑟夫(Vint Cerf,谷歌首席網路佈道官,普遍被公認為「網路之父」之一。)、格羅斯(Eric Grosse,谷歌安全與隱私工程副總裁)與盧德維格(Adrian Ludwig,安卓安全系統首席工程師),在過去這一年,對這項工作的貢獻。」
很顯然,這些高層參與者以及來自其他十七家參與「長期安全框架」計畫的同業,至少對國安局與其他情報機關入侵其他公司數據網路,有些基本的想法。而且,根據亞歷山大的說法,這個計畫從二○○九年就已經開始進行了。
數位民權組織電子前線基金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律師卡多索(Nate Cardozo)評論這封亞歷山大寫給谷歌高層的郵件重要性時指出,其中隱含的矛盾是,國安局這隻老狐狸假惺惺地扮演谷歌雞舍網路的守衛。
「國安局從後門駭入網路,並接上連結谷歌基地中心的光纖網路時,才不會幫谷歌確保設施在中國的安全性。」卡多索說,「事實就是,同時做這兩件事的機關,顯然充滿矛盾而荒謬。」
布林似乎一直是國安局的關鍵連絡人,他也一定暗示過,與政府的關係可能會影響谷歌保護全球消費者隱私的職責。這封解密的郵件顯示,他與國安局的關係非比尋常。
郵件中說,「你最近收到長期安全框架行政指導小組會議的邀請,會議將在二○一二年一月十九日舉行。」、「這個會議是確認我們在二○一一年的成就,並為來年設定方向的機會。我們將會討論長期安全框架在二○一二年的目標與特定對象,也會討論我們看到的某些威脅,以及我們正在嘗試削弱這些威脅的作法。很期待能看見你,並能參與討論。你是國防工業基礎(Defense Industrial Base)的關鍵成員,對於確保長期安全框架能做出可觀成果,你的獨特見解將極具價值。」
這倒是很坦率:國安局把谷歌與其他公司當成工具,讓美國軍方方便做事。根據國土安全部,「國防工業基礎部門是遍布全球的工業綜合體,不只研發,還設計、生產、運送,並維護軍事武器系統、次系統與零件功能,以達到美國軍方的要求……國防工業基礎公司包括國內外的企業,在很多國家也有生產基地與資產。這個部門提供產品與服務,對於動員、部署與支撐軍事行動,實在不可或缺。」
國安局局長亞歷山大在郵件中提到布林時,稱他為美國國防工業基礎的「關鍵成員」,這實在是太有啟發意義了。關於這個國防工業基礎,美國前總統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七日的告別演說上,曾經警告美國:
最近數十年的科技革命是造成工業軍事情勢巨變的主因。在這場革命中,研究已經成為核心工作,同時也變得更制式、更複雜,也更昂貴。在聯邦政府的指示下,已經穩定增加比例。今天,單打獨鬥的發明家在自己的店裡胡搞瞎搞,已經因為實驗室裡的科學家與實地測試的任務而相形失色。同樣的,自由的大學,傳統上是自由點子與科學發現的源頭,也已經體驗到研究的革命性變化。部分原因是因為牽涉到的金額太龐大,因此,政府的合約實際上已經變成一種追求知識好奇心的替代品。每一個舊黑板上,現在都換上了數百個新電腦。聯邦政府雇用的學者、計畫的配置與金錢的力量,前所未有地主導著未來,也很嚴肅地被看待。然而,就科學研究與發現而言,我們應該也必須警覺一種相對的危險,也就是公共政策本身可能會成為科學技術菁英的囊中物。
即使我們能從布林與其他谷歌領導人的各種採訪與聲明中,嗅出一點什麼,但還是無法相當肯定,在軍事工業綜合體中,他們的參與到底承擔了哪些工作。他們扮演的角色是首腦,還是尾巴,或者是完全獨立的怪物?
事實上,藉由聰明承接在電腦革命之後大量出現的軍方資助計畫,這些公司在股票市場與大眾知名度上都衝到巔峰。在艾森豪總統任內,網路本身一開始就是一項軍方資助的計畫,軍方的技術合約也流向灣區的大學,因而打造出矽谷的基礎建設。這些新崛起的科技巨人,雖然很多人都相當年輕,但真的會天真到以為,他們可以真的可以與艾森豪激動描述的龐然大物劃清界線,獨立行事?
| FindBook |
有 12 項符合
隱私危機:當他們對你瞭若指掌 數據公司和政府機構如何竊取個資、窺視隱私、破壞民主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隱私危機:當他們對你瞭若指掌 數據公司和政府機構如何竊取個資、窺視隱私、破壞民主
網路暴政下的數位裸奔時代來臨!
購物廣告、銀行貸款、色情廣告怎麼都找上我?
一旦註冊會員同時,就等於免費把個資送出去了!
Google表示:「自願將資訊交給第三方的人,就不該對隱私有合法的期待。」
數位時代該如何在網路上自保?
瀏覽器五花八門,該如何使用比較安全的方式保護個資?
在網路暴政時代,需要建立新的個資保護意識!
否則小至網路數據商操弄購買意願,
大至國家監督你的一舉一動是否違法!
作者簡介:
羅伯特‧席爾(Robert Scheer)
線上雜誌《挖真相》(Truthdig)總編輯,該雜誌曾獲頒專門評選最佳網站的國際大獎威比獎(Webby Award)。他也是南加大安納堡傳播與新聞學院教授,每周一次的廣播節目Left, Right & Center共同主持人。一九六○年代,曾是Ramparts雜誌總編輯,後來成為《洛杉磯時報》全國特派員與專欄作家。寫過六本書,包括《美國大盜》(The Great American Stickup)。現住洛杉磯。
譯者簡介:
林麗雪
專職譯者。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畢業。曾任職國會助理、記者與編輯。喜歡有生命力的人、事、物;熱愛文字工作。 譯有《QBQ!就是要傑出》、《我用死薪水,讓錢替我賺錢》、《數位口碑經濟時代》、《政治制度的起源》(下冊)、《攻擊者優勢》、《當收入只夠填飽肚子》,合譯有《怪咖成功法則》、《虛擬貨幣經濟學》、《如何打造營收上億的App》等書。
章節試閱
第一章
上TED的那一刻:他的頭安在機器人身上
在TED三十周年研討會上,沒有肉體的史諾登(Edward Snowden)忽然現身,震撼了群聚在現場的科技業巨頭們。一個仔細裁切過的史諾登臉部影像,被放映在一個小螢幕上,這個小螢幕則貼在一個能行走的「網真」(telepresence) 機器人上。但是,並不是這種科技巫術讓現場滿座的一千二百位來賓大呼驚訝,而是他們事前完全不知道,付了七千五百美元,坐在普通座位區,竟然能聽到讓當今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蒙羞的間諜現身說法。
在二○一四年三月十八日這一天,史諾登真實的身體還安全地隱藏在莫斯科...
上TED的那一刻:他的頭安在機器人身上
在TED三十周年研討會上,沒有肉體的史諾登(Edward Snowden)忽然現身,震撼了群聚在現場的科技業巨頭們。一個仔細裁切過的史諾登臉部影像,被放映在一個小螢幕上,這個小螢幕則貼在一個能行走的「網真」(telepresence) 機器人上。但是,並不是這種科技巫術讓現場滿座的一千二百位來賓大呼驚訝,而是他們事前完全不知道,付了七千五百美元,坐在普通座位區,竟然能聽到讓當今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蒙羞的間諜現身說法。
在二○一四年三月十八日這一天,史諾登真實的身體還安全地隱藏在莫斯科...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上TED的那一刻:他的頭安在機器人身上
Google一開始就知道是怎麼回事?
其實Google才是始作俑者?
當諾貝爾獎得主開始侵犯網路人權
第二章 政府話術精選
中情局也有份
比小布希更沉迷於「愛國者法案」的人
使用搜尋引擎,可能會讓你被盯上?
第三章 連網的狂人
你的個資,50元折價券就賣了
他們災忽地不是你,而是沒有錢賺
第四章 隱私就是自由
你被臉書惹毛過幾次?
科技越進步,你越沒隱私
當竊聽變簡單
第五章 軍事情報綜合體
當國防外包出去…
「前金二十萬,尾款是兩百萬」
Google─「請勿作惡」
第六章 告密者才能讓我們...
第一章 上TED的那一刻:他的頭安在機器人身上
Google一開始就知道是怎麼回事?
其實Google才是始作俑者?
當諾貝爾獎得主開始侵犯網路人權
第二章 政府話術精選
中情局也有份
比小布希更沉迷於「愛國者法案」的人
使用搜尋引擎,可能會讓你被盯上?
第三章 連網的狂人
你的個資,50元折價券就賣了
他們災忽地不是你,而是沒有錢賺
第四章 隱私就是自由
你被臉書惹毛過幾次?
科技越進步,你越沒隱私
當竊聽變簡單
第五章 軍事情報綜合體
當國防外包出去…
「前金二十萬,尾款是兩百萬」
Google─「請勿作惡」
第六章 告密者才能讓我們...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