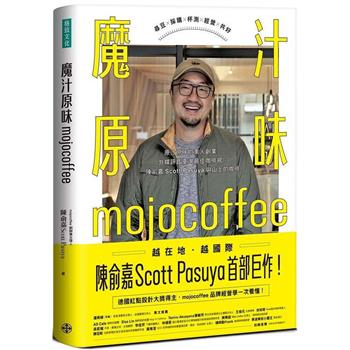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5 項符合
日人之蝕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3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
日人之蝕 出版日期:2020-07-08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歷史真實事件改編,被朝鮮偷走的日本人
敵國綁架他們,母國息事寧人
國際政治風暴中,是否還有他們回家的路?
法蘭西學院院士:「菲耶的才華即在於將深度藏在表面。」
1970年代晚期,北韓情報單位曾經從日本綁架了十三人,都是普通市民、甚至家庭主婦。北韓綁架普通日本人的目的,是為了訓練情報人員學會日本人的說話方式,甚至複製他們的日常回憶,創造出「外表和普通日本人一模一樣」的朝鮮特務。1987年南韓客機被行李炸彈炸毀,機上115人罹難,執行的朝鮮特務就是經過上述的特訓後,成功假扮為日本籍乘客而完成任務。這是真實的歷史。2002年,在北韓平壤舉辦的日朝首腦會議中,當時北韓國防委員長金正日才首次鬆口向日相小泉純一郎承認此事。
菲耶以這段真實歷史為靈感來源,講述了被捲入這個瘋狂敵對的國際政治關係之中,有家歸不得的人們。當中有被綁架的日本高中生、護士、考古學家,也有因恐懼厭戰而逃離前線的美國士兵,更有執行任務後才發現國家的謊言的朝鮮菁英情報員。加害者、被害者,監視者、無辜者,叛逃者、愛國者……,各式各樣不同立場的角色人物卻是共同迫降在一個不得已的國度,菲耶以小說家之筆鑿穿失語的壁壘,為他們發出聲音。
這段歷史畢竟太匪夷所思。日方從開始懷疑,到獲得證實,到交涉朝鮮還人,中間有十多年的時間,這些日本人和他們的家人獨自被留在不見光的黑暗裡。在小說中,菲耶也探討了母國因為國際政治局勢而息事寧人,要家屬忍耐﹔甚至在真相揭露之前,始終自欺欺人地認定「不可能」的心態,彷彿與敵國形成共犯結構,使得被綁架的日本人難以找到回家的路。
幾個在故事中出現的聲音:
★以為世界上的戰爭和自己很遙遠,卻竟被綁架到朝鮮的普通日本人:「這些蛤蜊,跟我一模一樣,以為自己躲在沙粒的遮蔽下安全無虞,安逸的日子卻被猛然剝奪。」
★厭戰逃離前線,卻滯留朝鮮的美國人:「我還清楚記得第一次讓孩子們聽韓語版的美國之音那天。我這樣告訴他們:你們所知道的世界不是真正的世界。你們生長在這個韓國,它只是一道裂縫,時間掉了進去,被困在裡面出不來。」
★曾經對朝鮮共黨政權懷抱幻夢的考古學家:「在日本海的另一邊,並非一片我曾經想像的人間樂土。那裡所上演的是一齣兩千萬個臨時演員演出的一場戲,一場悲劇,到最後,說錯台詞的人都在後台被消滅。」
★發現真相,卻受到有關單位關切的記者:「永遠不要猶豫,把你們覺得最古怪荒謬的事寫出來。把你們的直覺已經預先感受到,但理智卻放棄了的事,寫出來。」
世界可以暴衝,可以脫序。世界會被意識形態與權力分割,使人類落入荒謬的處境。被敵對時空綁架的人們,是否還有機會回到家人的身邊?是否還可能重新信任這個世界?
歷史造成的荒謬處境,被國家暴力抹去的生命權利......,書中出現的每一段故事,遭遇都令人唏噓。多線交織之下,菲耶呈現了一個冰冷的世界,但臨到極冷處,落到極底層,卻又閃爍出微微的希望。
與本書有關的真人真事歷史報導 |
北韓綁架日本人四十多年事件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5941
1987年北韓特務炸毀南韓班機事件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1165089
被綁架受害者家族會創立人橫田滋甫於今年辭世
https://news.tvbs.com.tw/world/1336861
導讀作者 |
朱嘉漢 (法國第五大學社會學博士,小說家)
推薦人 |
彭仁郁 (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
作者簡介 |
艾力克˙菲耶
1963年生,曾任路透社記者,1991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隔年出版第一部小說,著作甚豐,獲獎頻繁。散文、遊記、評論及小說等作品三十餘部,包括《我是守燈塔的人》(雙叟文學獎)、《雨海上的郵輪》(法蘭絲瓦‧伽利瑪聯合國文教組織獎)、《我的未來灰燼》、《一段沒有你的人生》、《我的夜車》、《可憐蟲工會》、《不留痕跡的男人》(弗朗索瓦‧畢耶度獎),等等。2010年以《長崎》獲得法蘭西學院小說大獎。在台灣已出版的作品有《長崎》、《三境邊界秘話》、《巴黎》。即將出版的有2019年最新小說力作《蕭邦的傳聲者》。
譯者簡介 |
陳太乙
資深法文譯者,譯有小說、繪本、科普、人文哲史等各類書籍近五十冊。在衛城出版的作品有:《哈德良回憶錄》、《長崎》、《三境邊界秘話》、《巴黎》。
| |||
| |||
|
|

 2021/05/03
2021/05/03 2020/09/21
2020/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