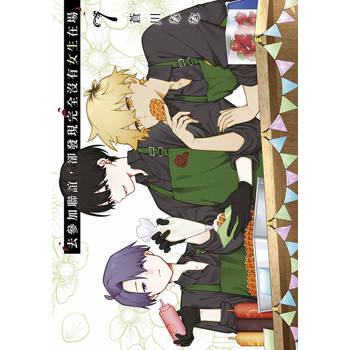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最澄大師:日本天台宗初祖的圖書 |
 |
最澄大師:日本天台宗初祖 作者:大久保良峻 出版社:經典雜誌 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 出版日期:2020-09-08 語言:繁體中文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66 |
佛教 |
$ 300 |
Religion & Spirituality |
$ 342 |
中文書 |
$ 342 |
其他 |
$ 342 |
宗教命理 |
$ 342 |
佛教 |
$ 342 |
Social Sciences |
$ 342 |
宗教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已受朝廷供養的高僧最澄,為了追求甚深法義,
仍冒險渡海,前往大唐修習天台教義與密法;
歸國後於比叡山開創日本天台法華宗。
比叡山作為佛教學問及修行的聖山,
日本佛教的各宗祖師幾乎都曾於此修行;
天台宗更可視為孕育日本文化與思想之母胎。
最澄圓寂後,受天皇賜封為「傳教大師」,
乃是日本佛教史上最初的「大師」名號,
由此可見最澄大師的歷史地位與重要性。
※本系列高僧傳叢書,以古典《高僧傳》及《續高僧傳》之原著為基,含括日、韓等國知名高僧;嚴謹參照人物評傳的現代寫法,另參酌相關史著,對高僧事蹟探討省思,亦探究其社會背景和思想,或重要經典之傳承。期盼此系列叢書,讓讀者得見歷代高僧之風範、智慧及悲心,亦能一覽相關佛教史地、典籍與思想。
作者簡介
大久保良峻
一九五四年日本神奈川縣生。一九七八年早稻田大學第一文學部(心理學專修)畢業,一九八三年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完成碩士課程(東洋哲學專攻)。一九八九年同博士課程滿期退學,二〇〇二年獲得早稻田大學博士(文學)。現為早稻田大學文學學術院(文學部)教授,天台宗勸學。著作有《天台教學と本覺思想》(法藏館)、《台密教學の研究》(法藏館)、《最澄の思想と天台密教》(法藏館)。編著《山家の大師最澄》(吉川弘文館)、《新.八宗綱要》(法藏館)、《天台學探尋》(法藏館)、《日本佛教の展開》(春秋社)等。
譯者簡介
胡建明
生於一九六五年,上海市人,文學博士、哲學博士。一九九〇年留學日本東京,一九九六年留學德國海德堡。現任職於日本東京駒澤大學佛教經濟研究所,兼中國人民大學高等宗教研究院客座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哲學、華嚴學、禪宗美術史等方面的研究。
目錄
「高僧傳」系列編輯序
令眾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
編撰者序
與中國佛教淵源甚深的「傳教大師」──最澄
日本語序文
『最澄大師』
大久保良峻
【示現】
序章
天台宗與最澄
滿又然公高弟,語澄曰:「昔智者大師告門人曰,我滅後二百餘歲,我法傳東國;祖讖不虛,子其人也。」
從鑑真到最澄
最澄的師資相承
密教的展開
與法相宗的論爭
大乘戒獨立
日本天台宗的重要性
第一章
從誕生到青年時代
最澄生年十三,投大和上,即當國國分金光明寺補闕得度,即稟和上可歸心一乘。
最澄的出身
從誕生到成長
專論:天台密教
第二章
入比叡山
愚中極愚、狂中極狂、塵禿有情、底下最澄,上違於諸佛,中背於皇法,下闕於孝禮。謹隨迷狂之心,發三二之願,以無所得,而為方便,為無上第一義,發金剛不壞不退心願。
〈願文〉──青年最澄的誓願
專論:四教與行位
探求天台文獻以及一切經論
法華十講
在高雄山寺的天台講演
第三章
入唐及歸朝
最澄闍梨,形雖異域,性實同源。特稟生知,觸類懸解。遠求天(台)妙旨,又遇龍象邃公,總萬行於一心,了殊途三觀。
立志入唐求法
出航前往唐土
陸淳與道邃
專論:關於兩位「道邃」的問題
與行滿邂逅於天台山
拜別台州
在越州得密教法門
雜密的傳承以及歸國
歸朝復命以及傳法
天台宗的獨立
天台宗的年分度者
第四章
最澄與空海
新來真言家,則泯筆授之相承;舊到華嚴家,則隱影響之軌模。沉空三論宗者,忘彈呵之屈恥,覆稱心之心醉;著有法相宗者,非濮陽之歸依,撥青龍之判經。
空海歸國以及兩人之間的交流
與空海決裂
泰範的離去
專論:最澄的諸國歷訪
第五章
最澄與德一
常平等故,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常差別故,流轉五道,說名眾生;反流盡源,說名為佛。以有此平等義故,無佛、無眾生;為此緣起差別義故,眾生須修道。
「三一權實論爭」的開始
德一與最澄的著作
最澄思想之探討
第六章
大乘戒獨立.最澄圓寂
《仁王經》百僧,必假般若力;《請雨經》八德,亦屈大乘戒。國寶、國利,非菩薩誰?佛道稱菩薩,俗道號君子;其戒廣大,真俗一貫……
天台法華宗年分學生式(六條式)
勸獎天台宗年分學生式(八條式)
天台法華宗年分度者回小向大式(四條式)
《顯戒論》的奉呈
天皇勅許.最澄圓寂
【影響】
壹.最澄的著作以及思想
最澄以後的日本天台,為致力於不斷充實當時尚不完備的密教、以及圓密一致教門的建立,付出了相當的努力。
《守護國界章》
《內證佛法相承血脈譜》
《法華秀句》
《註無量義經》
《末法燈明記》
《法華長講會式》
《天台法華宗學生式問答》
貳.日本天台宗的後繼者──最澄入寂後的幾位重要代表人物
圓仁、圓珍這兩位入唐求法僧,對於日本天台宗的密教──即台密,開創了蓬勃發展的氣象,甚至使台密凌駕於空海系密教。
義真
圓仁
圓珍
安然
參.日本佛教的母胎
鐮倉佛教的各宗祖師大多曾在比叡山修學;稱比叡山為「日本佛教之母胎」,可謂當之無愧。
附錄
最澄大師年譜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