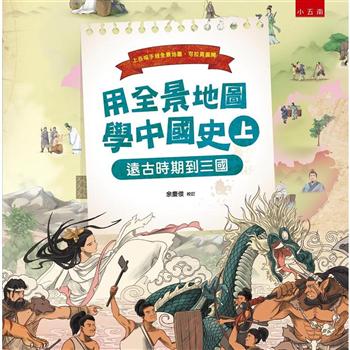序
存在價值的追尋與辯證──我讀《吟遊‧奧圖》
敘事詩(Narrative Poem)指的是以敘事作為主體的詩文本,無論是在於篇幅、體製,或者是風格上,都以陳述事件與人物言行為主,不同於一般的分行詩作,敘事詩的篇幅通常較多,經營上也側重於事件過程的發生結構;而「史詩」(epic)的特性往往以敘事為主,涉及的主題不僅是單一的事件或人物,多半是以重要的歷史事件、民族部落、宗教傳說作為描寫主體,其特點是背景龐大、出場人物眾多。因而史詩本身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大型的敘事長詩,以歷史、神話傳說、民族或部落為敘述主體,並呈現作者的史觀與價值思維,而作者的敘事視野與敘事策略,就變成一首史詩主題、價值以至於藝術風格的重要核心。亦即是說,敘事史詩(Narrative Epic)就是以敘事做為詩作的主體,主題則是以前述的歷史、族群、傳說等作為描述對象,且涉及大量的實際或虛構的地理空間與器物年譜,是一種時間向度較大的敘事文本。
其實台灣現代詩中的長詩書寫,在簡政珍與蔣美華的論述建構下,隱然產生了一個脈絡可循,對我而言,長詩的書寫如果放在前述的脈絡中,其實可以發現幾種趨向,譬如陳克華的《星球記事》,屬於一種抒情高過於敘事的科幻長篇史詩,我的《新特洛伊。NEW TROY。行星史誌》則是敘事性高過抒情性,然而這兩類型的作品雖然都有敘事主軸與趨向,但實際上卻又不同於西方敘事詩的傳統,若要在台灣的現代詩中找到一個偏向於西方希臘悲劇與但丁神曲甚至於聖經詩篇的史詩性書寫,其實是相當不容易的。
張至廷的《吟遊‧奧圖》是我初識他時期的作品,那時候我就相當驚訝,他居然能夠在習詩不久的情況下,寫出了〈奧圖行腳〉與〈吟遊詩囚〉兩首看似迥然相異,但內在哲思卻遙相呼應的長詩作品,只不過當時的我們,從來不覺得在台灣出版界的商業機制下,這兩首詩會有以紙本面世的一日。沒想到十五年後,因為出版形式的改變,我力勸至廷到秀威一試,便促成了出版此詩的契機。
我不打算在序中引用詩作任何一段,因為那是對這兩首詩的割裂,這兩首長詩應該是個自完整卻又相互互文的文本。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首先提出「互文性」的觀念,其思維根源自巴赫汀所謂「眾聲喧嘩」的理論,認為任何獨立的文本都不自足,文本的意義來自於與此文本與他文本互涉對映的過程中誕生。因此任何文本都可以不同程度地互涉其他的文本,並且與其他的文本交相衍義。換言之,若你購買了這本詩集,你就可以透過對於這兩首長詩的閱讀,展開一段從先知對於生命存在價值的反思與歷鍊,進入到吟遊的現實沉澱,兩者看似無關的敘事,卻交相指涉著存在價值與現實世界之間的相互辯證,對於這本詩集的讀者而言,若您能如此行旅在至廷的詩作中,您將會得到從未有過的生命撼動。
而這就是悲劇的本質,這本詩集繼承的並非是中國敘事詩的傳統,而是在西方與印度的悲劇和史詩文本,拓出一條華語現代長詩的全新道路,奧圖在行旅中的生命追尋,與自我的存在辯證,其實就像是我認識的至廷,他自身的形象似乎就是奧圖的形象,那悲劇般的命運,似乎就是先知必須面對的自我矛盾。但〈吟遊詩囚〉卻讓先知睜開凝視現實的眼睛,掙扎於自身和世界的連結,面對愛情這個主題的辯證,希望自身能夠從精神的囚籠中脫離,將一種普世性的存在關懷,力圖透過詩作呈現,那不是宗教的救贖,而是自我的完成。
寫到這兒,本來是不想引用他的詩作,想讓各位自己去探索生命的旅程,但我還是忍不去想各引他兩首長詩中的一段,作為結尾,那也是影響我這十五年來與他兩兄弟生命共振的段落:
旅人
我只是個貧困的學者
幾乎一輩子挖掘著
真理之塚 一回也不曾挖掘出什麼(〈奧圖行腳〉)
歸來,不解之歌
她便笑著掩住我的口
你一直在囚禁
也不斷在流浪(〈吟遊詩囚〉)
各位,去讀詩吧!讀詩之前,打開古典愛樂台,讓自己的背景充滿著一種崇高的悲劇美,你將會發現,在這本詩集中,你會找到一種身心療癒與安頓的力量。
新竹教育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後中生代詩人,以及張至廷的投名狀兄弟 丁威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