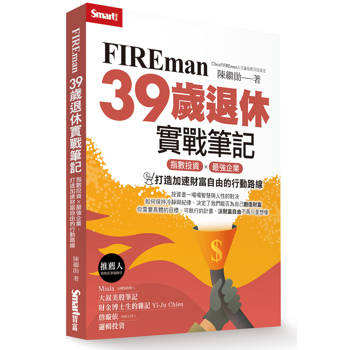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明清閨閣危機與節烈打造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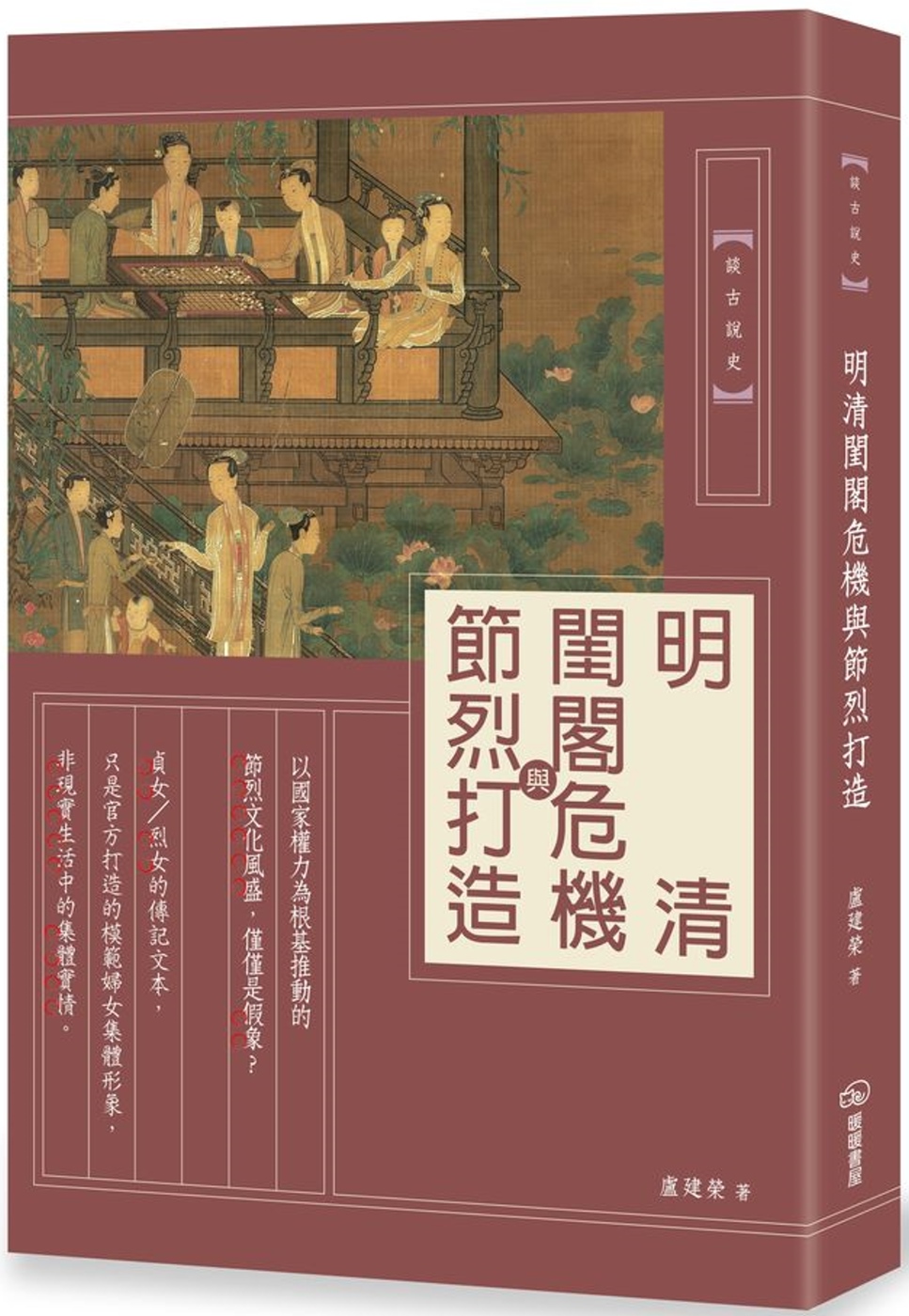 |
明清閨閣危機與節烈打造 作者:盧建榮 出版社:暖暖書屋 出版日期:2020-12-15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44頁 / 14.8 x 21 x 1.8 cm / 普通級 / 部份全彩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99 |
中國歷史 |
$ 316 |
Social Sciences |
$ 340 |
社會人文 |
$ 360 |
明史 |
$ 360 |
中文書 |
$ 360 |
中國歷史 |
$ 360 |
社會人文 |
$ 360 |
歷史 |
$ 360 |
Others |
電子書 |
$ 400 |
中國史地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明憲宗時,曾抓到姦淫少女182位的淫魔派高手桑沖,但對於潛藏各地的淫魔,卻顯得無能為力,受害者父母為保障女兒一生幸福,大都隱匿案情不報,受性侵少女最終實踐的是反節烈。明期官方所製作的《元史.列女傳》,在抗拒性侵這一情節編織上有造假之嫌,像是敘及女性在受辱當頭仍有餘裕辱罵施暴者,但文本作者是事發現場的缺席者,不可能得知受害者向施暴者如何振振有詞;又或是將許多戰時蒙難婦女湊數,全說成是節烈楷模。晚明開始,貞烈廟的普遍興築,使得小傳統的經濟弱勢女性,也多少向大傳統的大戶閨女仿效,走向實踐節烈之路。這是受到貞烈廟的視覺傳播影響,非女教書教示,晚明清初社會上的貞女/烈女數因此增加。不過清朝官方製作的《古今圖書集成.閨烈部》,由於對種族意識敏感,再也不敢說出羞辱種族標幟的話;另也有婦女因貧困或子嗣等複合因素造成的輕生,不見得單純只為節烈驅使。
即令明清節烈漸增,本書仍要鄭重指出,不實踐節烈的女性,相對來說仍居絕對多數。透過種種線索,包括官方製作節烈文本的造假手法、淫魔輕易進出大戶閨房的形跡、戰地受俘女性的遣送安置、文化菁英同情夫亡和受辱的婦女等幾處突破口,揭開節烈實踐並非集體實情。由於女性不具備為自己發聲的話語權,枱面上的節烈論述雖響徹雲霄,但節烈風熾僅是假象。
本書特色
◎本書有別於過去婦女節烈史的探究過於依賴和相信官方文本所造成的誤導,由於作者對官方宣稱的明清節烈婦女人數起了疑心,故將這些疑難一一解破。畢竟官方製作的列女傳,是一種官方意識形態的節烈規範操作,與民間日常實踐的現實情況大不相同。
◎本書舉出許多過往不查的實際案例,或從官方文本不合理的蛛絲馬跡中,推敲出婦女殉死情節不乏編造和臆斷,或非單一因素使然。
作者簡介
盧建榮
現任《社會∕文化史集刊》(新高地)主編,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也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立台北大學以及佛光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
作者是台灣僅見全方位思維的史家,古今中外史蹟皆其獵場,長年提倡「敘述史學」與「新文化史」,將多項獨到研究成果,改寫成平易故事版本與讀者分享。1990年代起,大量引介西方新文化史學巨作(麥田出版叢書),膾炙人口,引領兩岸年輕世代開創史學新風。
盧氏早期敘述史著作《曹操》出版於1980年;《入侵台灣》獲2000年「中央日報」十大本土創作獎;2003年《分裂的國族認同》獲書評家晏山農許為台灣史界勇於挑戰當權第一人;《咆哮彭城:淮上軍民抗爭史》2014年獲北京權威書評專欄4顆星獎。
其他重要著作:《鐵面急先鋒:中國司法獨立血淚史》(2004)、《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2006)、《聚斂的迷思:唐代財經技術官僚雛形的出現與文化政治》(2009)、《陳寅恪學術遺產再評價》(2010)、《白居易、歐陽修與王安石的未竟志業:唐宋新聞傳播史》(2013)、《唐宋私人生活史》(2014)、《沒有歷史的人:中晚唐的河北人抗爭史》(2020)、《唐宋吃喝玩樂文化史:園林遊憩、飯館餞別與牡丹花會》(2020)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