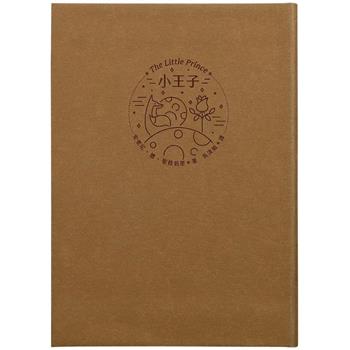當人們展望未來,我卻回看歷史
二〇一五年五月,當我結束在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為期半年的訪學,我發現我的手機被一個互聯網流行語給洗版了,它叫:互聯網+。
眾所周知,中國政府正式提出「互聯網+」這一概念,其相關表述是:「制定『互聯網+』行動計畫,推動移動互聯網、雲端運算、大數據、物聯網等與現代製造業結合,促進電子商務、工業互聯網和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引導互聯網企業拓展國際市場。」至此,從電視到報紙,從學術圈到產業界,大家爭相討論「互聯網+」,貌似是否談論這個語詞成了檢驗是不是與時俱進、緊跟潮流的標準。對於當時的氛圍,真可用「亂花漸欲迷人眼,滿城盡說互聯網+」來形容。
然而,就在「互聯網+」被加以強調、委以重任之前,曾迎來過另一個流行語:互聯網思維。它是隨著「小米」的迅速崛起的雷軍的商業成功而開始受到關注。
正如在去美國交流前的差不多近一年時間裡,我作為網路與新媒體領域的研究者和教學者,曾多次受邀為各級政府組織、媒體單位講課,主題基本上是「互聯網思維」或「媒體融合」,這裡面既有我個人興趣要分享的內容,也有對方 「指定動作」而要求的內容。所以,承蒙各界友人的信任與抬愛,我收到了許多會議、論壇的邀請,讓我談談在美國的訪學經歷、觀察心得,尤其是那裡的傳媒和互聯網業的現狀,當然,主題要圍繞「互聯網+」展開。
很多時候,我為此而迷茫。一是美國沒有「互聯網+」,少許有點沾邊的或許是「工業互聯網革命」(Industrial Internet Revolution)。另外,我認為要全面理解「互聯網+」,必須從德國的「工業4.0」說起,這既是必要的追根溯源,也是應當的脈絡梳理,可惜,邀請方對這些不感興趣。二是按我的理解,「互聯網+」是用互聯網的資訊技術去融合其他行業,並試圖連結人、物、服務、場景乃至一切,旨在打破資訊不對稱、減少中間環節、高效對接供需資源、提升勞動生產率和資源使用率。它和「互聯網思維」在很多地方有相似。可為什麼就把後者拋之腦後,隻字不提了?三是要把理念轉化為實踐,把口號落實到行動。在「互聯網+」的問題上,我認為當務之急要著重解決四個實際問題,或者說理順四個思路。一個是策略:為什麼要加,為什麼能加?一個是規則:其中誰為主,誰為次,換句話說,究竟誰說了算?一個是結構:互聯網與X是什麼關係,是顛覆還是互補?催生的是新產業還是新業態?再一個是行動:是否貫徹落實、說到做到?我奇怪為什麼很多明明不是互聯網業的人對「互聯網+」如此感興趣,而且大談特談,我認為即便要談(加),也應該是「X+互聯網」而不是相反,這裡「X」指的是一切傳統行業。
當很多人不明就裡、盲目跟風,然後人云亦云,他們事實上已經被詞或概念所「挾裹」,但是作為「一根思想的蘆葦」,人不應該僅僅去牢記語詞或句子,而忽略了思考乃至批判。我們都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但別忘了,還有一句古話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回顧歷史或捫心自問,對於概念、口號,我們還見得少嗎?從「互聯網思維」往前推,我們還經歷了「影視IP」、「互聯網金融」、「新常態」、「風口論」、「雲端運算」、「大數據」……所以在一次公開演講場合,我曾就「媒體融合」作了題為《當我們談融合的時候,看看我們都做了些什麼?》的演講,觀點和態度已經很明確了。因此對於回國後邀約的第一次「互聯網+」主題演講,我給主辦方擬定了一個標題:《從「互聯網思維」到「互聯網+」:一地雞毛與一以貫之》。「一地雞毛」的是層出不窮、喧囂塵上的概念,「一以貫之」的是前呼後應、一脈相承的思想。
時間倒退至一年前的七月二十八日,晴,微風至,黃曆上說月空、解神、金堂、鳴犬,宜祭祀祈福,緊接著我補了一句「著書立說,忌空口大話」。這一天,本書寫作正式啟動。按照計畫,整一部「互聯網史」將耗時一年,不求事無巨細面面俱到,但求提綱挈領把握主線——在行文框架上,我不否認「主題先行」,用概念(沒錯,就是它)引出歷史、劃分章節。當天,我嘗試寫了第一章的部分篇章,它正是你們看到的「分布式網路」,直至一年後全書完成,收錄概念詞條二十三個,包括「互聯網+」,涵蓋半個多世紀的互聯網歷史,時間起始一九五〇年代末,一直寫到眼下的二〇一五年年中。因為畢竟不是第一次寫書,算上這本,前前後後滿意和不滿意的也出了十一本書,所以寫作還是按照「設定路線」有條不紊的進行,到寫完最後一章作為「番外篇」的「互聯網+」,真的如預計的那樣,用了一年左右時間。如果有「計畫外」,那便是不知道後來去了美國訪學大半年以及成品不是起初以為的「一部大部頭」。
鑒於本書的定位不是一部學術專著,它更像是一本面向大眾的互聯網啟蒙讀本,所以書名「互聯網:一部概念史」在邏輯上未必十分嚴謹。至於以章節名形式出現的「概念」,它們既不同於哲學意義的使用,也區別於詞條維度的解釋,它可能指代「觀念」,也表示「思想」,有時還代表「理論」,甚至它還可以被當作「模式」、「趨勢」的近義詞。總之,用「概念」的視角去梳理與回顧互聯網史,可以對其每個發展階段和歷史時期的把握上避免傳統審視歷史時常犯的「直線發展的錯覺」。
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恩比就說過:「把進步看成是直線發展的錯覺,可以說是把人類的複雜的精神活動處理得太簡單化了。我們的歷史學者們在『分期』問題上常常喜歡把歷史看成是竹子似的一節接著一節的發展,或者看作現代的掃煙囪者用來把刷子伸入煙囪的可以一節一節的伸長的刷子一樣。」
你會發現,從最早的出於軍事目的的「阿帕網」到「全球資訊網」再到後來的「互聯網」一直到今天的「移動互聯網」、「物聯網」等,整個互聯網的發展就像是凱文.凱利觀察的「蜂巢」或傑夫.斯蒂貝爾筆下的「蟻群」一樣,整個群體都基於各自利益有意識的行動。隨著個體數量的增加,整體的密集程度會突破某個臨界點。這樣,「集群」就會從「個體」中湧現出來,最終使得最初用於部門聯絡的「局域網」發展成為可以連結一切的「互聯網」。其中,差不多每一個歷史階段總會興起或流行各式各樣的概念,它們或源於學界,或出自業界;或有意為之,或事出偶然,總之都一度推動著互聯網科技向前邁進。
以「概念」的視角來回溯互聯網歷史在已有的相關作品中是不多見的。在印象中,以互聯網/IT產業史為主題的作品大致有三種寫作模式:其一,編年體寫法,以時間軸(年代、階段)為貫穿,記述互聯網的誕生、發展,如英國人約翰.諾頓(John Naughton)寫的《互聯網:從神話到現實》 (A BriefHistory of the Future: The Origins of the Internet)、阿倫.拉奧(Arun Rao)和皮埃羅.斯加魯菲(Piero Scarruffi)合著的《矽谷百年史——偉大的科技創新與創業歷程(1900—2013)》(A History of Silicon Valley: The Greatest Creationof Wealth in The History of The Planet)以及「矽谷必讀經典書目之一」的大衛.卡普蘭(David Kaplan)的《矽谷之光》(The Silicon Boys)、「互聯網老兵」財經作家林軍的《沸騰十五年:互聯網一九九五至二〇〇九》等。
其二,列傳式寫法,以人物或公司為線索,在互聯網、IT產業宏觀歷史背景下講述它們各自的創業史和商業故事。這一類代表作有前Google公司研究員現為騰訊公司搜尋業務副總裁的吳軍博士寫的《浪潮之巔》、方興東和王俊秀合寫的四卷本《IT史記》、著名傳播理論家美國人埃弗雷特.羅傑斯(EverettM. Rogers)的《矽谷熱》(Silicon Valley Fever:The Growth of High-TechnologyCulture)、保羅.弗賴伯格(Paul Freiberger)和麥可.斯韋因(MichaelSwaine)合寫的《矽谷之火》(Fire in the Valley: The Making of The PersonalComputer)等。
其三,記述式寫法,其通常是為了闡明主題的需要,作者用一定的篇幅簡單回顧互聯網歷史,如有著「科技的牛虻」之稱的美國科技批判作家安德魯.基恩(Andrew Keen)的新書《互聯網並非答案》(The Internet Is Not theAnswer)。書的開始兩章,基恩就帶領讀者回顧了互聯網的發展簡史,譬如如何從「冷戰」產物的軍用阿帕網逐漸變成今天的互聯網,以及互聯網的商業化(大量風險資本的進入、矽谷創業和網景上市等)。還有像另外一位我欣賞的互聯網文化責罵家葉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他在代表作《技術至死:數位化生存的陰暗面》(To Save Everything, Click Here: The Folly of Technological Solutionism)也採取了同樣的處理手法。相較而言,本書用歷史上曾先後冒出過的新詞、概念去把互聯網作「橫向」的切割,再「縱向」的連結到一起,一部別樣的互聯網史便呈現在了諸位面前。我希望本書能帶給讀者有別於其他同類作品的全新的閱讀體驗,我也自信於這一點。
正如前面提到的莫洛佐夫,他愛挑流行觀念和熱門事物的刺,擅長從人文、社會的角度去討論科技對現今世界的影響,往往不按常理出牌,以毒辣的眼光和銳利的筆鋒去審視互聯網科技領域。這樣做的結果,正如「賽博朋克」的定義者《差分機》的作者布魯斯.斯特林所講的那樣「他的新書就像砂紙,用來打磨那些『互聯網權威人士』的作品」。當然,還可以加一句,他把大眾偶像拉下神壇的同時,透過自己一部部深刻的作品、一次次理性的發聲,使得自己成了這個時代最新銳的科技批判者與數位思想者。就在二〇一三年,莫洛佐夫對「Web 2.0之父」蒂姆.奧萊利提出了質疑。當人們習慣認定奧萊利是「矽谷的意見領袖」、「趨勢布道者」時,以及包括「開源」、「Web 2.0」、「作為平台的政府」、「參與架構」等眾多科技流行語的締造者,莫洛佐夫就提醒人們注意,這些概念真能救人民於水火嗎?盲目膜拜創新與高效真的所向披靡嗎?以及光鮮亮麗的詞語安慰著我們,但是他真的能夠拯救一切嗎?在他看來,奧萊利更像是一個經過精心策劃、商業包裝靠兜售觀念發財的「彌母騙術師」 [「彌母」一詞最早出自英國著名科學家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所著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書,其含義是指在諸如語言、觀念、信仰、行為方式等的傳遞過程中與基因在生物進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相類似的那個東西]而非「矽谷天才」。隨後,這篇題為《奧萊利的「詞媒體」帝國》(The Meme Hustler: Tim O'eilly’ Crazy Talk)的責罵文章發表在了《異見者》(The Baffler)雜誌上。
然而更早之前,同樣的細究、質疑落在了一度神一般存在的蘋果公司創始人史蒂夫.賈伯斯身上。對於這位在全球享譽盛名的企業和科技界天才,莫洛佐夫毫不客氣的分析了賈伯斯的思想源流。他指出,賈伯斯之所以是賈伯斯,關鍵在於兩大觀念支撐:一是德國的包浩斯,二是克萊頓.克里斯坦森的《創新者的窘境》。也就是說,產品本身純粹的至善至美成為了賈伯斯追求的目標,而且是唯一的目標,至於封閉體系、權力控制、冷酷偏執、暴躁傲慢、一意孤行等則在所不惜。雖然這篇《iGod》的文章只有三四萬字,但就角度、力度和高度來看,甚至優於沃爾特.艾薩克森版的《史蒂夫.賈伯斯傳》。有評論就說:「我本期待艾薩克森會寫出這樣的賈伯斯傳,卻由莫洛佐夫在此寫出來了。」
如果我對本書還有更多期許的話,那就是希望能向莫洛佐夫的《技術至死》以及他之前的那本《網路錯覺:互聯網自由的陰暗面》(The NetDelusion: The Dark Side of Internet Freedom)致敬,後者能就人們關心的科技話題給出真知灼見、指引清晰方向,況且文本本身文筆上乘、可讀性極佳。不管能在多大程度上借鑑和受啟發,我希望本書能傳遞理性的聲音,給熱衷於傳播科技流行語和身陷「互聯網中心主義」、「解決方案主義」兩種思潮而難以自拔的大眾敲記警鐘:當心,可千萬別被美麗的表象和動聽的修辭給矇騙了!
正當「互聯網思維」氾濫、什麼都可以「互聯網+」,而且大數據、雲端運算、可穿戴設備、3D列印、網真技術等在主流媒體版面隨處可見,並一度借由商業暢銷書籍傳遞著貌似主流、大勢所趨的商業見地,人們眾聲喧譁、歡欣鼓舞,不禁樂觀憧憬,訊息科技將創造美好未來。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就像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教授、「網路中立」理論提出者吳修銘(Tim Wu)在《總開關:訊息帝國的興衰變遷》(The Master Switch:The Rise and Fall of Information Empire)一書中所揭露的訊息帝國中不容忽視和不容忘卻的真相:
互聯網同廣播、電視、電影等訊息媒介的發展週期規律是一致的,必將經歷如下這樣的輪迴:新資訊技術的發明,新產業的建立,一段開放的發展期,最終由幾個行業巨頭占據統治地位,掌握著訊息流的總閥門(the master switch)。
所以,你會更加明白:為什麼在他們忙著展望未來時,我卻安靜的回看歷史。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互聯網進化史:網路AI超應用 大數據×雲端×區塊鏈的圖書 |
| |
互聯網進化史:網路AI超應用大數據×雲端×區塊鏈 出版日期:2020-07-03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56 |
Computers & Technology |
$ 383 |
輸入法 |
$ 405 |
資料處理/大數據 |
$ 405 |
資料處理/大數據 |
$ 405 |
網路/通訊 |
$ 405 |
科學科普 |
$ 427 |
中文書 |
$ 428 |
硬體/網通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互聯網進化史:網路AI超應用 大數據×雲端×區塊鏈
「當人們展望未來,我卻回看歷史。」
隨著時代的發展,
網路發展如同滾雪球一般越來越大、越來越快,無法遏止。
「工業4.0」、「互聯網工業革命」、「物聯網」……
一個又一個新生的名詞目不暇給的冒出水面,占據我們的生活,
於是當互聯網+的概念被提出,
你忍不住要停下來問一問自己,這一切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網際網路(Internet)的在阿帕網(ARPANET)的基礎架構下發展,網路與網路之間的點與點,無數的電腦和裝置之間互相透過網路連接在一起的串連,這些網路之間以特定的通訊的協定,形成了龐大的網路體系。
Internet的基礎上發展出全球性的網際網路,儘管網路的發展經歷了西元兩千年的路泡沫化,但隨著科技的發展以及網路的便利性,網路在現代正發揮著強大的重要性。由於網路的便捷讓世界形成了地球村,催生了許多BBS、PTT、Blog(部落格)、Facebook(臉書)、Youtube等虛擬社群的網路文化發展,便利性的通訊軟體如MSN、Line、Wechat等,強大的網站巨人谷歌、微軟、亞馬遜、eBay、維基百科等。
本書徹底分析網路從無到有,從有到發展盛況的精練解說以及精彩的案例,絕對是您不能錯過的一部網路發展概論史。
作者簡介:
楊吉,法學博士,知名媒體人和財經作家。主要關注領域:知識產權、網路新媒體傳播、互聯網產業。
作者序
當人們展望未來,我卻回看歷史
二〇一五年五月,當我結束在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為期半年的訪學,我發現我的手機被一個互聯網流行語給洗版了,它叫:互聯網+。
眾所周知,中國政府正式提出「互聯網+」這一概念,其相關表述是:「制定『互聯網+』行動計畫,推動移動互聯網、雲端運算、大數據、物聯網等與現代製造業結合,促進電子商務、工業互聯網和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引導互聯網企業拓展國際市場。」至此,從電視到報紙,從學術圈到產業界,大家爭相討論「互聯網+」,貌似是否談論這個語詞成了檢驗是不是與時俱進、緊跟潮流的標準。對...
二〇一五年五月,當我結束在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為期半年的訪學,我發現我的手機被一個互聯網流行語給洗版了,它叫:互聯網+。
眾所周知,中國政府正式提出「互聯網+」這一概念,其相關表述是:「制定『互聯網+』行動計畫,推動移動互聯網、雲端運算、大數據、物聯網等與現代製造業結合,促進電子商務、工業互聯網和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引導互聯網企業拓展國際市場。」至此,從電視到報紙,從學術圈到產業界,大家爭相討論「互聯網+」,貌似是否談論這個語詞成了檢驗是不是與時俱進、緊跟潮流的標準。對...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前 言
第一章 分布式網路
第二章 阿帕網
第三章 電子郵件
第四章 傳輸控制協議/互聯網協議
第五章 全球資訊網
第六章 搜尋引擎
第七章 商業化
第八章 風險投資
第九章 電子商務
第十章 對等網路
第十一章 互聯網泡沫
第十二章 互聯網2.0
第十三章 社群網路
第十四章 社會化媒體
第十五章 移動互聯網
第十六章 可穿戴設備
第十七章 大數據
第十八章 雲端運算
第十九章 3D列印
第二十章 中國網路概念股的發展
第二十一章 互聯網金融
第二十二章 國家網路安全
第二十三章 番外篇:互聯網+
第一章 分布式網路
第二章 阿帕網
第三章 電子郵件
第四章 傳輸控制協議/互聯網協議
第五章 全球資訊網
第六章 搜尋引擎
第七章 商業化
第八章 風險投資
第九章 電子商務
第十章 對等網路
第十一章 互聯網泡沫
第十二章 互聯網2.0
第十三章 社群網路
第十四章 社會化媒體
第十五章 移動互聯網
第十六章 可穿戴設備
第十七章 大數據
第十八章 雲端運算
第十九章 3D列印
第二十章 中國網路概念股的發展
第二十一章 互聯網金融
第二十二章 國家網路安全
第二十三章 番外篇:互聯網+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