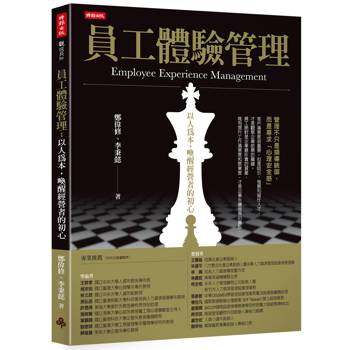圖書名稱:被搶劫的人生
一九八六年,家具行老闆蘇炳坤因涉嫌結夥搶劫被警方逮捕。雖然他矢口否認犯行,卻換來無情的刑求,就算他一路喊冤,警方仍逕行宣布破案,最後被法院判處十五年徒刑。
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他選擇「一邊逃、一邊喊冤」,事實上每天都待在家裡四處寄陳情書,成為「在家逃亡」的通緝犯。這一逃,就是十年,直到一九九七年意外被捕為止。
沒有被冤枉過的人,無法瞭解清白有多麼重要。雖然二○○○年已獲得總統特赦,但蘇炳坤以為司法體制並沒有真正還他公道,年近七十的他決心展開下一階段的戰鬥,再次挑戰再審的超高門檻。
本書記錄蘇炳坤三十年來為平反而奮鬥的漫長旅程。盼望這樣舊時代的冤獄,能在新時代的期許中真正地畫下句點,因為只有直視過去,重新串接記憶斷裂之處,才能在如霧般籠罩的現實中重新確立航道,找到未來的路。
作者簡介
陳昭如
臺大人類學系畢業,曾任職首都報社、自立早報、超級電視臺等媒體,現為自由撰稿人。
著有《CALL IN!地下電臺》《歷史迷霧中的族群》《活在拜物星球》《福爾摩沙愛情書》《被遺忘的一九七九──臺灣油症事件三十年》《沉默:臺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幽黯國度:障礙者的愛與性》《沉默的島嶼:校園性侵事件簿》《無罪的罪人:迷霧中的校園女童性侵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