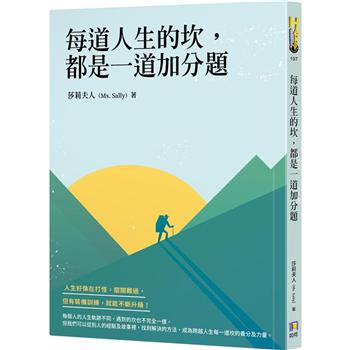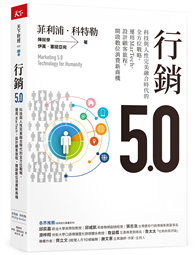自序
這不僅是一本回憶父親的書。更多的,是寫父親的朋友們。
這些朋友中,有電影編劇,有導演,有與父親同代的,也有下一代的。隨著歲月的流逝,他們有的離去了,有的已近古稀。父親一生雖然寫了十幾個電影劇本並都搬上銀幕,可他生前最想念的,是那些與他共同合作過的朋友和夥伴們,從來沒有忘記劇本中的某一個精彩細節是誰誰提供的,某一個故事題材是誰最先發現的……當我翻閱數不過來的文檔資料,憑著記者的好奇和敏感去採訪和接近父親生前的朋友時,我瞭解到那一代電影人深厚的藝術造詣,他們的追求,他們的理論和實踐,以及他們的命運──一些父親最知已的朋友,在政治鬥爭風暴中失去人身和創作自由,直至失去生命,已成為父親心中永遠的痛!
父親曾趴在農家的炕桌上寫文章懷念他的創作摯友,在書中與他們對話,在信中與他們探討文學和電影理論,在夢中和他們相對而坐,默默無語……
父親和他朋友們的友情,記錄了那一特殊時期特別的中國電影史!
這本書中,也收進了我對兩位母親的回憶。我曾細心聆聽生母的述說,我也靜靜地坐在繼母面前,聽她敘述對父親的思念。
她們是父親的親人,也是父親的朋友。
我的一生中,最難忘的是下鄉當知青的四年,還有二十多年的電視記者生涯。我記不清自己拍了多少部紀錄片,挑出兩部印象較深的也收入書中,讓漸行漸遠的思緒,重新回到人生的酸甜苦辣之中……
如今父親已經去世二十八年了。向父親學習什麼?學品行,學道德,學情操;向他的朋友們學習什麼?學他們不懈的創作嚮往,以及留給後人的寶貴的探索……這是我寫此書的目的。當父親知道我把他放在大家中間,以一個普通朋友形象出現的時候,他一定會點頭,向我露出那麼熟悉的、飽含豐富內容的微笑……
李蘊
202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