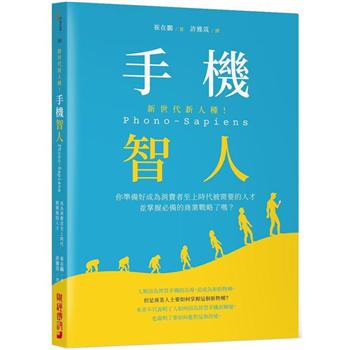噓,這裡有一隻野生的哨兵,你可以嘗試馴養他。
從背後慢慢地接近,小心不要發出任何聲音。他會伸出爪子撓你,假裝掙扎得很厲害。
你可以用親吻堵住他的嘴,讓資訊素在他周圍彌漫。他逐漸軟化。
於是你和他一起製造出一種神奇的液體,其蛋白質是牛肉的六倍……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將我馴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00 |
大眾文學 |
$ 342 |
華文 |
$ 342 |
文學作品 |
$ 353 |
中文書 |
電子書 |
$ 380 |
中國創作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將我馴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