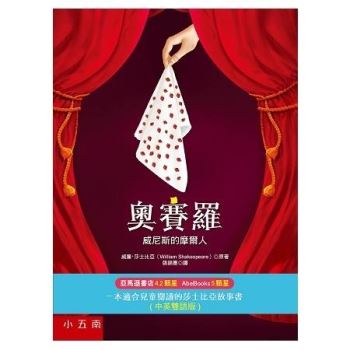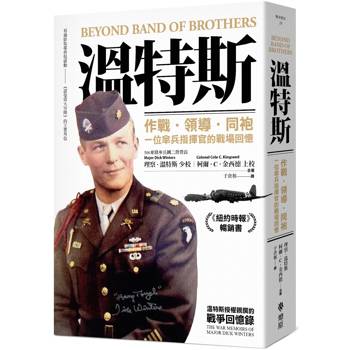第一章、凱蜜
許多人以為,妖怪喜歡大吼大叫,發出尖銳得足以刺穿耳膜的叫聲,或在狺狺低吼之後,爆發震耳欲聾的咆哮,為了恐嚇,隨後致人於死地,大啖人血人肉,碎內臟和啃得毫無肉沫的白骨橫飛之間,背後稱著大得不可思議的滿月,仰天長嚎勝利的戰吼。
嗯,這一切都大錯特錯。妖怪們要是聽到這些,肯定會一臉不屑的拍手,稱讚人類的想像力,但暗地裡希望自己真的有他們想像得那麼帥。
在物資缺乏的年代,妖怪吃人很普遍,但這個道理就和人類上山狩獵或豢養家畜一樣,肚子餓總不能吃同類,而我敢拿我的錄音機打賭,動物們也有另一個版本的妖怪傳說,只是主角換成人,法術還從弓箭演變成一整個屠宰場,比虎姑婆有效率多了。另外,我可以用卡式錄音帶再打賭,如果有人開一間主打妖怪料理的餐廳,肯定會大排長龍。
人類絕對更擅長把其他物種當成食物。結案。
而在人們的幻想中,還有一個錯誤的點。妖怪的叫聲,比他們所想的還要豐富,有怒號也有悠揚的歌聲,例如我身旁的這一窩婆娑鳥。
我躺在鐵皮屋頂,望著藍得會讓任何有翅膀的生物想起飛的天空,大團大團慵懶的白雲翻了個身,擋住太陽,熱烘烘的光線灑在皮膚上。早晨的陽光正好,再晚一點就會逼出濕淋淋的汗,我也沒辦法再假裝,自己只是在曬太陽。
睜開一隻眼睛,我微微轉頭,瞄向鐵皮通風口底下的鳥巢,在距離一個手臂長的地方,灰黑相雜的雌鳥正在孵蛋。她低頭整理羽毛,不再像幾個星期前那樣瞪著我,或召喚群鳥進攻。
我坐起身,按下懷中卡式錄音機的錄音鍵,錄音帶轉動沙沙聲,流向四方捕捉聲音。錄音機放在屋脊上,一點一點推向婆娑鳥,我也悄悄靠近,相距小於半個手臂,最後只剩下一個手掌,我抬起頭,剛好與她四目相交。
她張開鳥嘴。當我以為她要發出嚇阻的叫聲時,她唱歌了。
時而清朗,時而渾厚的歌聲流淌而出,單純的音樂,不帶任何語言,卻像是從藍天,從白雲,從行道樹,甚至屋瓦都擷取一小塊,將無可言說之物化為聲音,欲言又止的聲響譜成音符,萬物在高音時亮了,低音時變暗,整個世界都在共鳴。我怔怔望著她,直到歌聲覆蓋眼光,像是變為組成空氣的新分子,吸入體內,在大腦褶皺間流轉,攫獲思路的運行。
我伸手,朝向她。
傳說中,婆娑鳥的歌聲能夠魅惑萬物。麻雀或老鷹,百鳥循著聲音追本溯源,如朝貢般帶來蟲豸魚蝦,而當他們欲飛欲離,鳥群亦隨侍而行。
又往前一點,膝蓋貼近鳥巢邊緣,手在婆娑鳥的頭側,幾隻綠繡眼停在腳邊。她扭扭頭,靠在我的掌心,我幾乎能觸摸到天籟震動的頻率,卻無法測量,我的感受和思考間夾著歌聲揚起的迷霧,或許山中的旅人就是如此迷了路。
「凱蜜!」
迷幻嘎然而止,歌聲哽住一般驟然消失。我縮起手,霧散了,回神的瞬間婆娑鳥露出兇光,方才演奏美妙音樂的喉嚨,張嘴暴露出舌頭,炸裂粗啞的長鳴。
我趕緊爬起來想跑,卻重心不穩,抱著錄音機滾下屋頂。天空和草綠色鐵皮圍繞著我打轉,咚咚咚綿連著巨響,我滑出屋簷,在最後一刻緊抓鐵皮邊緣,雙手吊直,在半空中左搖右晃,而嚇到婆娑鳥的兇手正倚著敞開的窗戶,彎起一邊嘴角,戲謔的笑容鑲嵌在皺紋裡。
阿嬤先接過的,是被我咬著吊繩的錄音機。
「一大早的,學什麼貓屍。」她按下錄音機的暫停鍵。「這次又在錄什麼?」
「貓死是掛樹頭,不是屋簷。要不是妳嚇到婆娑鳥,我才不會變成這樣。」我的手臂發酸。「阿嬤,借過。」
她聳聳肩,一屁股坐到窗台上。「我怎麼知道,妳在屋頂上幹嘛。」
「是妳告訴我那裡有鳥巢的。」
她戳戳我的肚子,身體晃動,我用力扳住屋頂。「啊,好像是呢。」
「別鬧了,快借過。」
「那隻婆娑鳥真可惡,誘拐我可愛的孫女。」
手指發軟。「借過。」
「害我少了一個好幫手。現在店裡忙不過來。」
我脹紅了臉。「我會幫忙啦。快走開,我要掉下去了。」
陰謀得逞,她笑咧咧的移開身體,我一腳勾著窗台,手攀著窗框,邊爬邊滾的把自己丟回屋內,臀部砰的一聲著地。我哀嚎,還在想該先揉屁股還是手臂,阿嬤就把錄音機丟還給我。
「好啦,下來幫忙上架。」
我坐在地上,噘著嘴。「我是送貨員,上架又不是我的工作。而且妳明明可以找其他人。」
「別抱怨了。任何和紙箱有關的都是妳的業務範圍。」她揉揉我的頭頂。「而且妳會喜歡的。」
在她的理論裡,孫女們都是一群熱愛當免費勞工的乖孩子。
我嘆了口氣,跨過堆在地板的水晶球、塔羅牌、道教符紙和神樂玲,跟著她下樓。阿嬤經營一間小店,卻很難定義這裡在賣什麼。二樓除了起居室以外,只有兩張靠牆的大桌,蒸餾器霧氣蒸騰,周圍放著大把自己種的鮮花和香草,一滴滴精油通過冷凝管,緩慢墜入錐形瓶裡,另一邊水正沸滾著,幾隻貓鬼將大豆蠟和蜂蠟丟進鍋裡,隔著照過滿月的水加熱。
滴入精油,倒進模具,等待蠟燭成形,但阿嬤做的不是普通的香氛蠟燭,其中配方來自譚界,神和妖怪居住的世界,而她也為此得到女巫的稱號。但我想,如果威脅妖怪叫她女巫,最後以訛傳訛,也是有可能的吧。
和沒有勞健保,可能也沒有薪水的貓鬼們打後招呼,我走下樓。不同於工作室,店面昏暗,夏日陽光穿透落地窗,只有店門口的地板一片金黃,頂到天花板的書櫃佔據兩面牆,中央還有幾個矮櫃,擺滿書本,沙發和小椅子靠在角落,裸露的牆面被貼滿海報,掛上畫,還有塗鴉裝飾。這是一家獨立書店,而且還不到開店時間,根本沒有阿嬤說的人手不足。
我把錄音機放到櫃檯上,旁邊是我的筆記本和四散的橡皮擦屑屑,爬上後方的小樓梯。牆上有一隻閉著眼睛,貓的身軀融合貓頭鷹的角羽和翅膀的擺飾——至少客人問起時,我們都說是裝飾品——我在棲木前的小水盆倒黑糖水。
爬下來的時候,踢到一箱白色的包裹。我瞇起眼,在昏暗的燈光下辨認上面的文字,隨後瞪大眼睛。這就是阿嬤說,我會喜歡的原因。
紙箱上寫著朔詩社。
生命中第一首詩,教我讀詩的那個人,都來自朔詩社。剛學會閱讀的年紀,月份便是用每一期的朔詩刊來計算,一本一本翻了幾百遍,還是不懂詩,但我知道那裡有文學和安定,是真實世界永遠缺乏的力量。而在這個離家出走時總會收留我的地方,無預警停刊後,我的心又開始在其它書頁間流浪。
三年後復刊同樣突然。我想,在瀕危動物之中聽見新生兒的哭啼,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然而,或許也不是那麼出奇不意。
我拿起美工刀,拆開滿滿一箱新書,手撫過書背。多久沒讀詩,又多久沒寫了呢?抬起頭,我望著貼在牆上好幾個星期的海報,朔詩社的徵文比賽的文案。
國中畢業後就沒有繼續升學,在阿嬤的店安安穩穩的當個送貨員,人生就是如此了,這樣的我不需要寫詩,沒有太多話想說。明明是這麼想的,卻忍不住望著徵文海報發呆,白白浪費筆芯和橡皮擦。
那個人看到現在的我,會感到很失望吧。
砰——
嘎——
巨響伴隨鳥叫,我猛然回神,跑出店門口查看。雌鳥在周圍盤旋,我望著腳尖前破裂的磁磚,一顆比花崗岩還硬的婆娑鳥的蛋剛剛砸下來,在人行道上撞出一個大洞。
而且這顆蛋要孵化了。
鳥蛋顫動,左搖右滾,在出生之前,必須擊碎無比堅硬的阻礙。加油啊,小傢伙。蛋殼破裂,鋒利的鳥喙刺出,小小身軀鑽出裂縫,妖怪雛鳥一出生便羽翼豐滿,目光銳利,牠張開瘦弱的翅膀,享受生命的第一道微風。
雌鳥輕啄他的腦袋後,立即撲翅飛起,身旁跟著其他新生的小鳥,對著還在地面的孩子聲聲叫喚。雛鳥揮動雙翼,想跟上母親。
他奔跑著,鼓動羽翼,其他人卻越飛越遠。
這麼瘦巴巴的小鳥,辦得到嗎?我追了上去,看他邊叫邊跳的踏過老街的石磚路,從一起飛就掉下來,到能懸浮在空中三秒,似乎很有希望,但沒過多久又下墜,翻了個跟斗。快啊,再不起來,他們就要走遠了。
小鳥沒有放棄,他拍動氣流,一下,兩下,三下,漸漸高飛。終於在陶瓷老街的下坡路之前,飛向天空,追逐天邊的家人。
我揚起頭,站在原地,微笑著。今天的天空,好像又更藍了一點。
「咪!」
我轉身,卻沒看到任何人,但有一個小東西正在蹭我的小腿。夜貓子,或者我和姊妹們都叫這隻長著貓臉的妖怪貓嘴獸,用深藍色的貓身軀和黑色犄尾在我的腳踝之間打轉,墨黑帶銀色斑點的翅膀收在背上。
「魔嚕嚕,妳怎麼出來了?」
「我被掉下來的鳥蛋吵醒,又看到妳店門都沒關就跑出去。」我蹲下來,把她抱在懷裡。她動動頭上的角羽。「婆娑鳥都成功了,妳不試試看咪?」
「這可能沒什麼意義。」
她不置可否的咪了一聲。「你們人類不是有一句話咪?要奮力衝破蛋殼之類的。」她說,抓抓我的衣服。「能有什麼損失?」
我想反駁什麼,但被貓掌推了推下巴,強迫往上看。仰望著天空,振翅高飛的黑點漸漸消失在藍天邊緣,卻從他們的方向吹來一陣風,翠綠的樹葉沙沙作響,七月的陽光使萬物蓬勃生長,造成凡事都有可能的錯覺。我的心臟在跳動。
「可能……沒有吧。」
她露出貓嘴微笑。「去咪。」
我沿原路走回去,踩在凹凸不平的石磚上,一步接一步,腳步輕盈,步伐增快,不知為何我開始奔跑,渴望越跑越快,期待著不曾想像的遠方。或許慢慢走久了,原地踏步久了,會讓人懷念埋頭狂奔的風動和瘋狂。
回到店裡,我把魔嚕嚕放在櫃檯上。而後抓了筆記本又要出門。
「凱蜜,」阿嬤叫住我。「妳要去哪裡?」
我半開著店門,門上的鈴叮噹響,外頭一片璀璨的朝陽,天光正美好。我從頭到腳沐浴著金黃。
轉過頭,我對她笑著。「我要去寄信。」
第二章、亞紹
最近看了一部英國影集,片頭曲不錯,劇中穿插不少經典的歐美搖滾樂和流行樂,讓我想買的專輯又增加好幾張。Mayaw(馬耀)常說,我的CD購物清單可以一路從花蓮排到墾丁,他太小看我了,這份名單延伸到東沙群島也沒有問題。
重點是,其中一句台詞特別吸引我的注意,翻成中文的意思大概是:明智的選擇自己示人的容貌。
神有很多形象,在不同神話中,可以是人、動物或石頭。最常見的是人形,畢竟藝術品和文學作品都是人類創造出來的,但神若使用人的形貌在陸地上行走,便牽涉到男人或女人,白人、黑人或黃種人的問題,太多爭議,神不喜歡吵架,那是人類的工作。祂們總是打一架解決爭端,喚起幾個海嘯或地震,原始又方便。
基於石頭沒辦法說話和走路,動物是更好的選擇。譚界之人祭拜的,便是神的動物形象。
而朔詩社祭拜的,是荷蘭人、西班牙人、日本人和漢人來到這座島嶼以前,更古老的台灣之神。祂們存在於故事之中。
我坐在陽台的扶手上,仰望著天。東台灣的天空特別寬廣,一大片高爽的黑色布簾,塵埃般的殘雲在天黑前被抖落,滿天星子繡出銀色星座,北斗七星和仙后座圍繞著小米收成後的第一個朔月。今日是儀式之夜。
也是一年中,最讓我感到麻煩的兩個晚上之一。背後未開燈的房間像一只巨大的音樂盒,音響播著我剛放進去的CD,音樂從一片漆黑傳出,是我從小聽到大的台灣樂團,正好唱著寂寞、童年玩伴和星星。縱谷的晚風吹過我黑色和深金色交雜的瀏海,我吸吸鼻子,寧願坐在這裡久一點,但乾淨的夜空中,雲霧逐漸累積。
這麼多種妖怪,偏偏選擇我最討厭的類型。
遮住月亮就不好了。我轉半圈,滑下扶手,弄皺綁腿褲和長背心,迅速溜出房間,輕手輕腳下樓,路過廚房時偷了點toron和酒,檳榔就免了,擁有不老的身軀不代表不會死於疾病。
我走向農舍的後院,朝著遠方的火炬前進。儀式場地已經布置好,石板桌擺上祭品,神燭的蜂蜜味從祖靈屋擴散到整片農田,然而在這香甜的氣味中,是兩名面色凝重的祭祀者,他們穿著繡有華麗圖騰的苧麻織品,戴著獸牙和羽毛裝飾的頭飾,髮間插著鮮花。
其中一人先看到我,但以普通人的標準,紜祺的外貌或許不能被稱為人類。她扭動布滿硬鱗的腦袋,向我瞇起眼睛。
「亞紹,你這小子終於出現了。」
我聳聳肩。「我是主祭者,有充分的理由在儀式前放鬆心情。」
「你不會緊張。我花了很多功夫,但你就是養不出這種情緒。」她皺眉,倚著柱子,望向農舍三樓。「站在後院都聽得到你在放音樂。今天聽什麼,〈雨夜花〉?」
我彈指,音樂瞬間消失。「不,紜祺,我聽的至少是二十世紀的歌。」
「好吧。」她斜睨我。「我真不明白,荒獸神為什麼沒有因為你濫用神器,而懲罰你?」
「祂們才沒空管我。」我微笑,露出牙齒。「要麻煩的事情已經夠多了。」
她和坐在長板椅上的男人交換眼神,站直身體。「什麼意思?」
後方傳來聲響,有人踏過石磚步道。淡棕色頭髮的年輕男人穿過夜色,出現在燈火下,Mayaw抱著一個牛皮紙袋,腳步很急卻面無表情。
「亞紹,紜祺,社長。」他在我面前停下,喘口氣。「我盡力了。能辨認出來的都在這裡。」
我接過紙袋,拿出幾張泡過水又被吹風機吹乾的紙,字跡模糊,不過看得出來是詩。這次的徵文比賽是來自荒獸神的旨意,但每件作品送到我們手中之前,總會被雨水蹂躪一番,可惜了,我們拜的不是雨神,這可不是受神垂青的表現。
但我們確實被什麼給盯上了。
「做得好。」我把紙袋塞回Mayaw懷裡,扶著肩膀,轉回建築物的方向。「現在,快跑。」
同時,四周颳起大風。地面的草枝搖曳,偃倒,連根拔起,隨著土石向上捲成數公尺高的龍捲風,我們壓低身體,髮梢和衣服下擺隨著強風暴動著,頂上烏雲聚集,氣壓驟降,風中夾雜吱吱吱的聲響越發嘈雜,而在龍捲風的風口,隱約可見黑雲邊緣垂下幾百條細細的長尾,如鞭子般抽打著空氣,脅迫氣流攪拌出最殘暴的風。
紜祺的身上冒出火焰,聚集火團,聽從主人的指揮,火球義不容辭衝向風捲,爭奪與氧氣共舞的權利。光芒乍現,沿著末端燒灼一圈又一圈迴旋,竄至雲端,轟的一聲,黑夜亮起,雨雲被燒毀,蒸發。肇主現出原形。
燒焦的雲的邊緣,數百顆腦袋探頭,眼發紅光,露出齧齒類的巨大門牙。鼠尾妖,住在雨雲上的妖怪,攪動尾巴能成雲至雨,製造足以把人捲上天際的暴風。但他們應該在白天出沒。
真不巧。這是一場貓捉老鼠的遊戲。
鼠尾妖收回風,火龍捲頓時消散。我抓著Mayaw的肩膀。「快回屋子裡!」
「等等,」社長出聲。「祖靈屋裡比較安全。」
Mayaw愣在原地,來回看了我和社長一眼,轉過身去,頭也不回的往農舍直衝。
「紜祺,」我大喊。「掩護他。」
「知道了!」
Mayaw橫越草皮,風暴瞬間匯集,呼呼風聲比方才更加憤怒,雨雲移動,下起暴雨,牽動龍捲風追著他跑。龍捲風不停斬斷他奔向後門的路徑,大雨浸濕草坪,每一步都濺起泥濘,他緊抱著紙袋閃躲雨水,卻在拐彎時滑了一跤,半邊身體擦過地面。
鼠尾妖尖叫著,帶著雨和破壞衝上前。
而後被大火燒盡。
紜祺追上去,更多火光爆發,與風糾纏,將氣流解體。空氣中瀰漫著瞬間蒸發的水氣,綠草被火星燒焦,此時的氣味惹惱了鼠尾妖,下一個龍捲風形成,紜祺壓低身體,火焰預備,濃黑的夜在閃光中失去神秘的意味。
光照著臉龐,一閃一滅,我拉著社長,退回祖靈屋內。五十多歲的男人一臉擔憂,他的髮色到是如同正常人類,隨著年歲花白,而我找了個位置坐下,翹著腳,靠著椅背,頭微微轉向戰場。
社長交抱著雙臂來回踱步。「你不去幫忙嗎?」
「就算是鼠尾妖,一個小爪子都能把我撂倒。戰鬥從來不是我的風格。」我看向他,勾起單邊嘴角。「動腦才是。」
「我還是很擔心,」他說:「那幾首詩是最後的希望。」
「相信我,祖靈屋並沒有比較安全。」
一聲拔高的尖叫,遮蔽整片星空的烏雲分裂成小塊,鼠尾妖分別進攻。四周捲起小龍捲風,大雨毫無死角的淹死每一株小草,Mayaw漸漸逃不出暴雨的圍城,紜祺的火焰漸弱。
此時,一團風暴衝向祖靈屋。
社長一臉驚恐,無路可退,咬著牙,張開雙臂用肉身也要護住祭壇。然而,當他閉上眼睛時傳來撞擊的暴響,風團撞上隱形的屏障,妖怪慘叫,強光閃現,圍成線段和半透明的面,整個祖靈屋被包覆在金色的立方體之內。
我的眼中亮起同樣的光芒,力量湧現。
他睜開眼,轉向我。「你什麼時候……」
我搖一搖掛在腰間,有動物頭的保溫瓶。「隨身攜帶神器才是好習慣。」
他笑了。「我真是服了你。」
又一個龍捲風,不斷衝撞屏障,金光隨著撞擊的節奏閃爍,比起紜祺的火,在夜晚中更顯叛逆。鼠尾妖氣惱著呲牙裂嘴,雨淋不進來,風暴撞散了只好再聚集一個,而我打開保溫瓶喝水,震動的頻率改變,開始唱起我剛剛在聽的歌,唱著「陪著我」,掩蓋暴雨聲。
直到攻勢突然消退,狂風禁聲,雨只剩下墜落屋簷的滴答響。我起身,走到祖靈屋邊緣,看著烏雲散去,鼠尾妖吱吱叫遠離,星空眨著眼,無辜的香不知道剛才發生什麼事,朔月依舊微笑著。我伸了個懶腰,空氣終於恢復夏夜該有的清爽。
但走來的兩人,可能無法享受這些。
Mayaw低著頭,很短的瀏海邊緣還滴著水,手捧著一團糊爛的紙。紜祺摟著他的肩,低聲說了些什麼。
他站在我面前,嘆了口氣。「Asaw,對不起……」
「沒事,」我說:「鼠尾妖的雨沒人能躲得掉。你沒被捲上去就不錯了。」
「但是,儀式全毀了。」
我挑眉。「也不盡然啦。」
他抬起頭,皺著眉。「你又在想什麼?」
我轉向正門的方向,對黑暗招了招手,一個少年急急忙忙跑出來,面容清秀,頭髮黑得發亮,貼服在耳後。他環顧四周,與其驚恐,不如說是滿腹疑問。
「荒獸神啊,這是怎麼一回事?你們看這片草地,這些樹木,全部燒焦了又淋濕了!我只是去一趟郵局,回來差點變成流浪狗。」他比手畫腳,語速很快。「但我們可以重新整理好,對吧?買些人工草皮,修剪樹枝,說不定我能趁機種一些小花……」
「安靜,」Mayaw舉起一隻手指,要他閉嘴。奧然最大的缺點,就是多話到常常讓人想掐死他。「你說郵局?」
他點點頭,一臉委屈。「亞紹叫我溜進郵局,把給朔詩社的信都拿來。還說回來後要躲在車庫,無論發生什麼事都不可以出來。所以我整整躲了三個小時,三個小時!」
其他人看向我,而我聳聳肩。如果那些泡水發皺的紙是荒獸神要的東西,最初寄來的時候就會包在保鮮袋裡。
「所以說,」我向前一步。「你拿到了什麼?」
「喔,」他摸摸口袋。「有電費繳交通知、大賣場的廣告傳單、紜祺的信用卡帳單……」
「奧然,說重點。」
「還有一件投稿作品。」他微笑,交出一個對摺好幾次的紙袋。「投稿者在截止日當天寄出,晚了幾天才到。」
我撕開紙袋,抽出裡面的詩。乾的。扭頭示意祖靈屋。「看來,儀式可以繼續了。」
眾人面面相覷,像是不相信在二手唱片行可以挖到絕版專輯,這當然可行,首先是要和店員混熟。他們依然跟著我走回祖靈屋,不管一身狼狽,只要還有一首詩在,我們的心意便能傳遞,與神溝通。
譚界之神與民間信仰不同,不需要香和金紙,或喝下代表血液的葡萄酒,卻同樣繼承了經文和讚美歌的意義。我們的神出於故事,祂們的力量也來自故事的傳唱不絕,來自一首首創新的詩作,包含祂們的神話,以及後續再造的傳說。
我朗誦了手中的詩——〈蛋黃〉,韻律從喉間鏗鏘洩出。我知道這首詩對了,音律對了。
我以為我是鳥
卻只是一顆蛋黃
先來到這個世界的
雄性的蛋
吸取我的養分
他輾壓我的身體
流出濃濃的血和蛋液
我滲入巢中
誰當初堆疊起這些枝枒
我用破裂的眼睛望向天空
看見一對成鳥
站在遠方枝頭
我想說沒關係
變成一盤炒蛋也好
至少我很美味
拿去做成蛋糕也罷
至少我很香甜
卻難以忘記
油鍋燒得太過熾熱
打蛋器將一切弄散
我被端到餐桌上
再一次被吃得到處都是
就算變成鳥
我也無法飛翔
羽翼中夾雜太多悲傷
氣流討厭我的不自由
我想學飛
先學會擺脫樹枝疊成的高牆
學會說沒關係
學會體諒
我會飛的
畢竟天空是那麼廣大
藍得好像沒有傷痕
自私的忽略烏雲
閃電打下的痛
瞬間消失
平靜底下的原諒
瞬間破碎
我以為我可以
我試著要回
一雙翅膀
在否認的反面
卻得到另一個盤子
連鼠尾妖的風都吹不熄的燭火,在無風的半夜搖曳生光,濃霧漸起,是有著香甜蜂蜜氣味的大霧,將我包裹,與其他人隔絕,並竊取一切雜音,我的聲音傳響四方,龐大卻充滿力量,如同搖籃曲,放送至整片農田,迴盪在整個花東縱谷。
這是神要的故事,祂所指望的,新的詩人。霧散去,但留下甜蜜的滋味,而在我以為今晚將一夜好夢時,很難得出乎我意料。祭壇上出現新的神器,是來自朔詩社悠遠傳統的主祭神,賜下的珍貴寶物。
而我低頭讀著詩,讀著隨詩附上的作者資料。竟然是她的名字。
如同在這次祭祀之前,我沒預料到,從今以後的儀式之夜,我再也不會感到麻煩了。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食肉目的謠唱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90 |
二手中文書 |
$ 342 |
中文書 |
$ 343 |
現代小說 |
$ 343 |
小說 |
$ 343 |
小說 |
$ 343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食肉目的謠唱
「傳說沒有不見,只是變成你不認識的樣子。」
在女巫阿嬤撫養與保護下長大的凱蜜,以為自己這一輩子只是個獨立書店送貨員,卻在寄出的詩作得獎的那一天,遭遇到神秘妖怪的追殺。在千鈞一髮之際解救她的神秘男人亞紹,隨後帶領她進入了奇幻與現實並存的神秘地「譚界」……。
半人半穿山甲的女子、以詩侍神的社團、作為備受期待的主祭,凱蜜必須在短暫的時間內學會侍奉神明,找出想殺害自己的內鬼,重要的是,她必須解開自己的身世之謎......。
★第二屆後山新人文學獎得獎作品
★臺灣類型文學的新里程碑
★少女的英雄之旅,也是台灣記憶的刻畫
這是一部融合了原住民傳說、地方歷史和社會議題的台灣當代奇幻小說。文學與神話,在故事中以「詩歌」為介質被巧妙地揉合,轉化成獨特且迷人的台灣奇幻世界觀。
吳鈞堯 作家
郝譽翔 教授
廖鴻基 作家
須文蔚 教授
——驚喜推薦
作者簡介:
星冽81
上個世紀出生,新北鶯歌人。現就讀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二分之一自閉症,四分之一漢人,八分之一日本人,十六分之一原住民,其餘的部分由陶土填滿。以上是人類型態,咪一聲之後就會變成百分之百的貓嘴獸。
章節試閱
第一章、凱蜜
許多人以為,妖怪喜歡大吼大叫,發出尖銳得足以刺穿耳膜的叫聲,或在狺狺低吼之後,爆發震耳欲聾的咆哮,為了恐嚇,隨後致人於死地,大啖人血人肉,碎內臟和啃得毫無肉沫的白骨橫飛之間,背後稱著大得不可思議的滿月,仰天長嚎勝利的戰吼。
嗯,這一切都大錯特錯。妖怪們要是聽到這些,肯定會一臉不屑的拍手,稱讚人類的想像力,但暗地裡希望自己真的有他們想像得那麼帥。
在物資缺乏的年代,妖怪吃人很普遍,但這個道理就和人類上山狩獵或豢養家畜一樣,肚子餓總不能吃同類,而我敢拿我的錄音機打賭,動物們也有另一個版...
許多人以為,妖怪喜歡大吼大叫,發出尖銳得足以刺穿耳膜的叫聲,或在狺狺低吼之後,爆發震耳欲聾的咆哮,為了恐嚇,隨後致人於死地,大啖人血人肉,碎內臟和啃得毫無肉沫的白骨橫飛之間,背後稱著大得不可思議的滿月,仰天長嚎勝利的戰吼。
嗯,這一切都大錯特錯。妖怪們要是聽到這些,肯定會一臉不屑的拍手,稱讚人類的想像力,但暗地裡希望自己真的有他們想像得那麼帥。
在物資缺乏的年代,妖怪吃人很普遍,但這個道理就和人類上山狩獵或豢養家畜一樣,肚子餓總不能吃同類,而我敢拿我的錄音機打賭,動物們也有另一個版...
顯示全部內容
推薦序
「充滿想像,同時又與土地、文化接軌的新奇小說,新一代作者星冽81用迷人且自信霸道的口吻,寫了瑰麗的後山景觀,以及她自己。」——吳鈞堯(作家)
「這是一部驚人的奇特之作,文字流暢,想像力恢弘奔放,讓人不敢想像作者竟是如此的年輕!將來必是台灣文壇備受矚目的一顆新星!」——郝譽翔(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語創系 教授)
「年輕是創意的火種,燃出一步步踏實的火花。」——廖鴻基 (作家)
「四海都有神獸,八方都有傳說,但星冽81來到了花蓮,她筆下的奇幻孕育自文學史和部落神話,故事環繞在詩的創造與愛的萌發,本書絕對...
「這是一部驚人的奇特之作,文字流暢,想像力恢弘奔放,讓人不敢想像作者竟是如此的年輕!將來必是台灣文壇備受矚目的一顆新星!」——郝譽翔(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語創系 教授)
「年輕是創意的火種,燃出一步步踏實的火花。」——廖鴻基 (作家)
「四海都有神獸,八方都有傳說,但星冽81來到了花蓮,她筆下的奇幻孕育自文學史和部落神話,故事環繞在詩的創造與愛的萌發,本書絕對...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2020後山文學年度新人獎出版緣起——以文學新人之姿漫步後山
序〈陰影的誕生〉
第一章
|
第三十八章
後記:〈我在山與海之間創作〉
序〈陰影的誕生〉
第一章
|
第三十八章
後記:〈我在山與海之間創作〉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