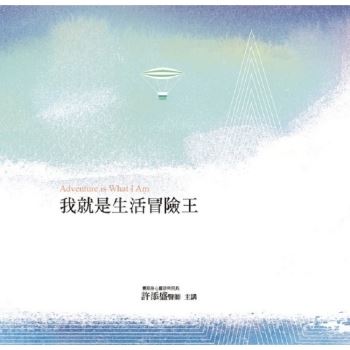第一篇:會出事就是會出事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朕茲護持國體而得之,信倚爾忠良臣民之赤誠,常與爾臣民共在。若夫情之所激、濫滋事端,或如為同胞排擠、互亂時局,為誤大道、失信義於世界,朕最戒之。宜舉國一家,子孫相傳,確信神州不滅,念任重而道遠,傾總力於將來之建設,篤道義,鞏志操,誓發揚國體精華,可期不後於世界之進運。爾臣民,其克體朕意哉!」
放送完畢,研究室裡呈現兩種情緒,一種感到安心,因為戰爭終於結束,不再需要躲空襲;另一種則是不安,因為戰敗了。
有前一種反應的大多是台灣人,而後一種,則是內地人。
不過,其實還有第三種反應,只有一人。
村田圭一,日籍研究員,是位灣生,兩個月以前才來到帝國大學醫學部就職,還是軍部派過來的。
他想著這些東西怎麼辦,名義上是來整理軍方研究所的研究資料,實際上他手上的東西不止文件,還有一罐密封的東西,存放在冷凍櫃裡面,鎖在地下室。
只有他知道那玩意是什麼,那是一顆人頭,冷凍的人頭。
外表看來有著高砂族的特徵,但不大確定。
不算活著,但可以動的人頭。
偶而他會下去查看一下狀況,在低溫狀態下,基本上這人頭看來就跟一般死人頭一樣,只是顏色灰白,表面有如樹皮一般龜裂,但只要解凍,很快就能發現異樣。當人頭表面溫度來到零度左右,眼睛就會睜開,那是充滿白翳的眼睛。不過,除了一些反射動作,這個人頭沒有絲毫可以稱為意識的反應。
文件的部份是加密過的,內容完全是天書,由假名、羅馬字與符號構成,村田被交待要保管好,不能交給任何人,直到軍部派員接收,但現在戰敗了,然後呢?沒有這類指示。
也沒能力將這顆人頭偷渡出去,軍方背景會讓他優先被撤出,而他知道這人頭不該被看見。
心裡征戰著,因為良知告訴他應該把這玩意銷毀,但理智告訴他,這玩意在學術上的價值幾乎是無限大。
這是間獨立的軍方祕密研究室,不但防燄抗炸,而且不存在於帝大醫院的設計圖上。
於是他著手封閉,說起來就體力活而已,這是他做得到的事情。
一週以後,他乘船離開台灣。
二〇三〇年夏季
還有這房間? 李宗勁搔著頭,一臉疑惑。
隨著醫院擴張,舊台大醫院有很多部份雖然算是古蹟,卻也面臨補強甚至改建的工程。這類工程自然會引起文化界的重視,總是要經過好幾年的協商與會勘才能定案。
結果現在冒出一個不該存在的房間。
作為拆除隊的工頭,李宗勁很想裝作不知道,直接把這深埋在地下的房間給拆了,畢竟這標工程正好碰上原物料大漲,老闆覺得很划不來,想要快點結束,所以工期逼得很緊。但只要想到那個書念太多,正在大學城鄉研究所,成天跑歷史建物田調的兒子會怎麼罵他……
還是報告一下好了。
「這什麼奇怪的房間?」說話的是台大醫院的院長,但話說回來,台大裡有幾個人曾經把整個院區全都看過的?恐怕沒有,幾十年來的增建改建,台大醫院跟迷宮一樣,根本沒人搞得清楚那些通道,何況是這個原本被偽裝成磚牆封住的房間。
「還沒人進去過嗎?」開口的是文化部的承辦人,有博物館背景的他對這個很有二戰軍事風格的鋼製窄門很感興趣,何況這門上還有一個同樣被水泥封住的大鎖頭。
門上還寫著一個大大的「凶」。
就是這個字,讓工班裹足不前,天知道門裡面是什麼東西,而李宗勁也解釋了,要破壞門並不難,甚至可以直接從旁邊的圍牆下手連門一起拆下來,因為旁邊只是一般的磚頭而已。
可是這門看起來有點歷史價值。
「看來開鎖是不可能的,」一位研究員檢查了一下鎖頭,但其實一眼也能確認這鎖頭完全鏽蝕卡死。研究員接著說:「先鑽孔好了,這門本身並不特別,小規模破壞無妨,但要先確認裡面的狀況,例如瓦斯之類的。」
總之,負責拆除的李宗勁在這需要精密工作的場合派不上用場,他唯一要負責的就是確認可以繼續執行拆除任務,所以暫時只能在旁邊看戲。
結果光鑽一個小孔,再加上用光纖之類技術東張西望,居然用掉半天時間,而從監視器前面離開的人,臉色一個比一個難看。
「裡面有什麼?」李宗勁終於耐不住好奇心,開口問這些跟他差距很大的高級知識分子。
「你自己看。」一位官員開口邀請,李宗勁立即靠近,然後嘴巴就合不起來了。
「幹!」開口的是被緊急找過來,一來就先看過的行政院副院長,而沒人對這句話有意見。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李景暉開口發問,畢竟老爸已經有三天不大講話,表現非常反常。
「啊知,就恁台大那件無,電視有播,恁阿爸抵遐轉來就按呢欲死欲死,毋知去卡到啥。」老媽看老爸那副德性,一肚子不爽。
「我會記得停工有補償是否?」大概老媽擔心收入問題吧?李景暉安慰老媽,但也覺得老爸很反常。
「阿爸,你是去看到啥,新聞也攏無講,只是一件小工程,竟然是行政院長出來開記者會,你有什麼消息否?」
但李宗勁閉口不語,只是「哼」一聲。
老實說挖到日本時代的遺跡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新聞,但行政院長開記者會實在很有違常理,像這種新聞怎麼可能壓得下來,偏偏這次新聞界一反過去對勁爆新聞的喜好,安靜得很,只是輕描淡寫台大醫院底下有其他日本時代遺跡,留下台大醫院舊院區一個被政府接管的地下室入口,而問題就出在底下一個原本不該存在的入口。
因為父親負責拆除工程,所以有把施工圖拿回家過,而基於專業興趣,李景暉自然也趁機好好研究過這棟歷史建物。
一個在圖上只是牆壁的地方,被發現其實是被磚砌起來的入口,而入口之下,則是那個寫著「凶」字的鋼製窄門。資訊到此為止,那個「凶」字還是他老爸第一天回家就講,他才知道的,因為隔天消息就全都被封鎖了。
雖然不是念醫學院,好歹自己也是台大學生,李景暉抽空跑去台大醫院閒晃,卻只見到施工圍籬,還有幾位理著平頭的大漢在周圍看似悠閒的站著,但脖子上的線路與外套下的鼓起透露了他們的身份。
都三十幾度了誰穿外套啊!李景暉這樣想著,卻也沒轍,他好奇心再強,也沒強到要去挑戰公權力。
但如果沒意外,故事哪能繼續前進,當你沒有好奇心,意外就只好發生在別人身上,而故事主角就換人當了。
文化部的承辦人跟一位軍方生化兵一起研究這扇鋼製窄門,雖說負責開啟的是工兵。總之,上面決定暴力開門,不想管什麼文史價值了,因為裡面的東西顯然問題更大,而高層一點也不希望事情拖太久。
說是希望快一點,其實也都已經拖三天了,因為從內視鏡看到的東西實在讓人很難安心,所以大家從醫學院史、校史之類著手,也從當年國民黨接收日本財產時的文件去找,就是沒找到任何資料。
總之,最終還是回到暴力解決,這次可是連文化部都沒意見。
理論上要開這古董門應該不難,於是工兵拿著切割器,不抱任何期待的開始動手。
「比預計的還難切,根本是潛艇的外殼。」負責的工兵這樣抱怨著,這個二戰時期的古董門居然這麼麻煩。
但切開之後才是挑戰的開始。鋼製的門被拉開之後,等了十分鐘左右,讓煙塵散去,也讓內部氣體稍微交換一下。劉素琴,故宮的資深研究員,專門研究日本時代文物的她,被直接徵招,打斷她的美國訪問行程,現在正一臉大便,瞪著眼前的黑洞。
「我們進去。」劉素琴下令,旁邊的生化兵遞過來一副N95,但她揮手拒絕了。
「不用太大驚小怪,如果真有什麼鬼怪,我們剛剛站在這裡早就中鏢了。」
說完就拿著手電筒帶頭進去了。
文化部的承辦人吐了吐舌頭,對生化兵做了個「你先請」的手勢,然後跟著下去。
門後的光景很不詳,牆壁上畫了很多骷髏,但不是很精緻的畫作,反倒像是在恐懼當中匆忙撇下的,不過若只有這些,倒也不至於引起恐慌。真正讓人不安的,是牆壁上一段用漢字寫的文字:
此間之物至為不祥
乃末日之源
還有一堆「死」寫在下面。
不管你有沒有什麼迷信,總之這很顯然是日軍非常慎重處理的東西,而讓行政院副院長罵髒話的東西,就擺在進門第一眼的正中央。
那是個擺在辦公桌上的大玻璃罐,透明的罐子裡面有個人頭泡在液體當中。不過這人頭乍看之下有點像木雕,很無機的感覺。
後面則有一些檔案櫃,不過檔案數量看來不算多,大概幾十卷,櫃子一半是空的,看來因為經過幾次地震,部份物品散落。
「感覺這該找法醫來。」劉素琴觀察了一下這個人頭,雖然看來不大像有機物,但雕刻的話也不大可能這麼精緻,何況泡在液體裡面。
讓劉素琴感到怪異的部份在於,經過將近百年,這罐子上面其實沒積什麼灰塵,她注意到漂浮的灰塵似乎會被微微推開,彷彿有某種靜電場。
這裡無疑是日軍留下來的遺跡,但又像混合了某些迷信的元素,平常來說她會很興奮沒錯,但因為這次的地點居然就在她生活的都市裡面,牆面隔幾公尺還傳來捷運經過的振動,而這玩意很顯然不吉利,或至少引起日軍極大顧忌的。
「要拿起來嗎?」工兵開口,但文化部承辦人搖搖頭說:「該不會有陷阱?」
「你是電影看太多還是電動打太多?」劉素琴嘆口氣,觀察了一下,說:「罐子看來還很堅固,應該沒什麼問題。」邊說邊拿出皮尺來量尺寸,量夠了以後,伸手捧起玻璃罐。
「沒想像中那麼重。」劉素琴稍微把罐子舉高,因為她想看人頭頸部的切口。
「這到底是不是真的人頭啊?沒看過這樣的處理方式。」
這時,突然傳來大叫聲,讓劉素琴一陣不快。「現在是怎樣?」她瞪了一下身邊文化部的承辦人,但這時連工兵也跟著大叫。
於是她注意力回到人頭上面,發現這人頭眼睛張開,而且張口做出囓咬的動作,讓她大吃一驚,把手鬆開。
當天中午,外送員來便當,一樓的人員簽收之後,來到密室門口向下招呼可以用餐了,但沒人回應。
幾分鐘以後,他再次前去招呼,只見黑暗中有兩個陰森白點逐漸靠近,從門口伸出乾癟的雙手,以及劉素琴的套裝,但在照射到陽光的時候,出現淒厲的慘叫聲,而那雙手在陽光下灰飛煙滅。
當天下午,國安局封鎖現場,並派出小型無人機進入調查,發現上午下去的三位工作人員呆立在密室內,研究員劉素琴沒了雙手。
三位對無人機沒有反應,而從攝影鏡頭中,但見三人全都變成禿頭,兩眼發白,皮膚乾癟碎裂。
「這叫殭屍吧?」操縱無人機的幹員歪著嘴一臉不敢置信,這不是他想像中的值勤狀況。
有了「殭屍」這種刻板名詞,現場的人員大多直接想到天色再幾個小時就要變暗了,假如底下的玩意真的是僵屍……。
三人對於呼喊沒有任何回應,顯然已經沒有認知能力,指揮官做了冒險的嘗試,親自踩進通往密室的樓梯,果然無人機立刻拍到反應,三具「殭屍」開始往樓梯移動,直到指揮官退到陽光下為止。
從無人機鏡頭中傳來的畫面,可以稱為飢渴。
三「人」(這時大家還不知道到底要用殭屍還是人來稱呼)身上都有明顯的咬痕,這時指揮官想到應該還有個人頭,於是讓空拍機繞了一下,發現地上有個破碎的人頭,不知道是打碎還是踩碎的,反正已經毀了。
「封鎖,不管用什麼,封鎖。」指揮官下令,於是眾人用施工用的鋼筋等物品焊死出入口。
夜間,密室傳來敲打的聲音。
隔天,連美國也介入了,特戰隊與AIT派來的海軍陸戰隊以鋼製獸籠圍住密室出入口,並在天黑前解除原本封住的密室,進行引誘。這種大陣仗理所當然地引起民眾恐慌,原本被解散的親中政治勢力更是趁機大作文章,不過這次政府資訊封鎖可說滴水不漏,鐵了心什麼都不讓人知道。
當晚,三具殭屍被困在獸籠內,移至台大醫院新院區地下室。
一週過後,大家開始關注藝人緋聞,解除封鎖的台大醫院不再引人注目。
二〇三〇年秋季
「你說有反應是怎麼回事?」劉雲側著頭,對丹米克的表情感到好奇。
丹米克是美國CDC派來的研究員,作為交換條件跟著來的還有一堆過去怎麼申請都不能引進的尖端設備,還有「附帶」的先進武器採購案,看來美方對於插手這件事情可是卯足了全力。於是這個原本只是尋常研究部門的台大醫學院地下室,突然變成需要層層認證才能進入的禁區,更沒想到威權時代用來供領袖祕密行動的通道中,原來還有更多密室存在。
「名字。」
「名字?」
「我試一次給你看。」丹米克轉過頭去,對著強化玻璃打開麥克風,用憋腳的中文念出「劉素琴」三個字。
編號〇一的感染者(大家自然以殭屍1號當成別稱),也就是研究員劉素琴,原本只是呆立的狀態,突然開始顫抖,而且有「表情」,雖然持續時間不久,但那一瞬間,看起來的確比較「像人」,卻也讓人感到更恐怖,那是種無法歸類,彷彿同時好幾種表情一起顯現的面孔,可以帶來強烈的不安。
「還有認知功能嗎?」劉雲對這點感到懷疑,雖然困難重重,他們還是設法對感染者做了各種採樣、切片,甚至還做了斷層掃描。
資訊很少,比較能確認的是受感染者的確是「受到感染」,有種前所未見的病毒擴散到受感染者全身,而病毒RNA在傳遞過程中並非只會一成不變的複製,而是在不同器官與細胞產生不同作用,彷彿這病毒有幹細胞功能一樣,又好像按照計畫進行一般,最終掌控受感染者全身,而且擴散速度前所未見,順著血液,只要幾分鐘就足以接管認知與神經系統,這一點從最初三人進入地下室直到發現問題只有一個多小時可以看出端倪。
但病毒的分析一直很不順利,因為找不到造成感染的原始病毒,只有在全身各地找到分化後的種類,找到幾種新的核酸片段組合,這些變異雖然造成人體細胞各種奇特的表現,包括脫水、冬眠化等等,卻無法證實跟殭屍化有關。
因為這些「殭屍」無法被麻醉,而且遇人就開始攻擊,就連兩隻手已經消失的劉素琴也同樣充滿攻擊性,因此台美兩國緊急著手設計能派得上用場制服殭屍的機械手臂,順利的話再幾天就會送到。
看來必須從牙齦或牙齒採樣,因為三人身上都有咬痕,可能傳染方式就是用咬的,或許唾腺之類地方能找到原始病毒,而這兩個地方是目前研究單位還不敢冒然接觸的部份。
雖然沒確實證據,但最早發現的詭異人頭,在破碎之後很快就失去採檢的價值,因為這古老的人頭迅速的腐爛,從零星的基因片段跟顱骨的復原,可以確認屬於台灣原住民,但也只有這樣。
地下室的文件間接證明了這一點,這人頭是日軍從嘉義山區找來的,地點在達邦南邊的山區。雖然派出人員搜索,但一無所獲,田野調查也問不出所以然來,雖然鄒族有一些獵首的禁忌與傳說,甚至提到未經過完整祭祀程序的人頭會帶來詛咒,但因為這種說法太過一般性,各族都有,雖說或許可以因此證明可能性,但也同時變得沒太多參考價值,因為可能真的就只是要尊敬死者的道德訓規。
「這反應昨天還沒有。」丹米克回答,畢竟三位受感染者都名字的,偶而總會有心軟或帶有罪惡感的研究員會用他們的本名稱呼,但這還是第一次光名字就有反應。
三位殭屍化的受感染者,基本上已經沒有認知功能,雖然沒有完整生理檢查,但視力大概退化至只能辨別光影,聽力也退化,或者說極化,因為似乎對人耳聽不見的極低頻有反應,反而中高頻聲音沒感覺,但觸覺或振動覺變得很敏感(雖然皮膚看起來像石頭或者樹皮一樣粗糙),平常基本上都是呈現呆滯狀態,會有明顯而且直接反應的,就是人類的靠近。只要感受到人類,會立即發動攻擊,雖然動作遲緩,但也同時不會控制力道,往往採取極具破壞力的方式動作,〇二的手就是在攻擊的時候,因為用力砸在防爆盾牌上整個碎裂,但也因此取得大量研究用的「檢體」。
總之大家暫時不敢直接靠近。
研究員倒是用掃地機器人進去開過幾次玩笑,結果是完全沒反應。
「名字嗎?」劉雲感到好奇,想到〇一跟她同姓,多少有點感嘆,接著她轉向另外兩間隔離室,同樣呼喚了感染者。
一樣的反應。
看來是可以列入病理紀錄了,因為雖然受到感染,而且很快就佈滿全身接管身體,但病毒對全身細胞的控制是漸進式的,或許還會有進一步反應。
或者這本來就是病毒設定的感染進程。
但病毒會接手管理記憶嗎?這有點難以想像。如果可以,等於證明人類的認知功能與記憶,是以某種化學物質的型態儲存的,畢竟這三個殭屍都沒有腦波,擺明是死透了。
或者代表靈魂被困住……,沒特別信奉宗教的劉雲對這種想法感到恐懼,畢竟身為不可知之論者的她,多少是「希望」靈魂存在的。
「把劉素琴先關進籠子裡,明天採樣。」劉雲下達指示,丹米克一臉陰沉的點頭,這代表有人要當誘餌在籠子後面吸引殭屍,雖然明知安全無虞,但氣氛實在太過陰森,而團隊中最年輕(三十九歲)的傑克總是要負責做這件事情。
可惜沒時間做進一步檢驗,當晚劉雲遇害,眼珠與手掌被切除,然後有人用這恐怖的生體鑰匙闖入管制區,同時殺害了值班的丹米克與三位戒護的軍人,偷走〇一。
然後美方抗議台灣保安不力,最後硬是運走了〇二。
受感染第九十二天,被偷渡到上海的劉素琴咬了一位解放軍士官。
第一百四十五天,一位台大法醫研究生被受感染的文化部研究員的唾液噴到眼睛。
第一百六十天,丹佛的醫療廢棄物清潔工在處理唾液檢體的時候劃傷手指頭。
二〇三五年冬季
「我寧願死。」總理環顧身邊的人們,有她女兒,還有因為總司令剛剛陣亡而繼位的陸軍副司令。還有大約二十位軍士官。
「媽咪,我會怕。」莎拉抓著自己的母親,抓到指節發白。
「就這樣,我們輸了。」總理摸了摸至愛女兒的金色頭髮,如果變殭屍,頭髮可是會掉光的。
「威靈頓?」
「準備好了。」司令拿起手上的筒狀物,有三位軍官也做了同樣的動作。
碉堡外的慘叫聲越來越淒厲,他們已經完全被困住了。
「紐西蘭萬歲。」
「紐西蘭萬歲。」
插銷被拉開。
舊世界最後的據點――紐西蘭正式滅亡,人類時代結束,殭屍時代來臨......。
覓光者
一頭年輕母鹿信步走到溪水邊,左邊右邊張望一下之後,搖了搖尾巴,低下頭,開心地享用著附近唯一乾淨的水源。
小溪位在一處危險的山溝當中,到處都是容易鬆動的土石,基本上大型掠食者是不會下到這邊來的,就連她都是小心翼翼地用那分邊的蹄爪子緩慢嘗試,才能安全下到底部來的,而一踩到谷底的河床地,母鹿整個就鬆懈了,完全沒注意到後方有對眼睛正緊緊盯著她看。
金褐色的毛皮、雪花般的斑點、潔白的腹部、修長的四條腿,以及優雅的脖子。脖子是重點,那是最好的目標。
緊盯著母鹿的那雙眼睛貪婪地搜尋著,彷彿只用眼睛就足以發動攻擊,但母鹿渾然不覺。
原本緊繃的手指鬆開,颼一聲,箭響之後,黑色的箭羽還在顫抖著,而黑色的箭簇從母鹿脖子的另一邊穿出,還帶著幾滴血花。近距離的精準射擊,母鹿幾乎在瞬間喪失反應能力,整個身子癱軟地就要往溪裡倒下。
罵了一聲,大榕從隱蔽處跳出來,一個箭步衝到母鹿身邊,匆忙地要拉住他得來不易的獵物。如果讓牠掉進溪裡,這幾天的辛苦埋伏就沒任何意義了,自從在附近發現不少鹿的足跡之後,他可是搓了一整個月的繩子才有辦法下來這邊,說什麼也不能讓這母鹿溜走。
右手環抱著母鹿的脖子,射穿脖子的箭正好卡在大榕手肘窩上,安穩得很,大榕踏實腳步,左手不住撫摸著光滑柔順的毛皮,咧嘴開心地笑著。這下他不但有新鮮的鹿肝可以吃,還有不少多餘的肉可以做成肉乾,鹿皮的話他倒是不缺,但也許可以跟村子裡的雄哥換個新的鍋子來用,舊的那口都快要被燒穿了,撐不了多久啊!他可不希望在冬天來到的時候還要為了煮不了熱湯在那邊懊惱,畢竟,附近已經沒有足夠的黏土讓倖存者取用揑製器皿了。還有,小珍她媽一直說需要鹿蹄子熬膠的,上次拿了人家上等的醃肉可還沒還人家人情呢!總之,這母鹿可來得真是時候。
但母鹿看來沒打算要乾脆的認命,尚未死透的身軀猛然掙扎了一下,四隻腳往大榕身上一蹬,一個失足,人跟鹿雙雙都跌落溪裡去了。
雖然會游泳,但掉在湍急的溪流裡絕不是開玩笑的,大榕拼命想要穩住身子,但水流依然將他推往溪中的大小石塊,突然頭部受到一陣撞擊,大榕失去了意識。
歷史早就灰飛煙滅,大榕從小就住在山谷裡的黑厝,掙扎著要活下去。作為倖存者的一員,從會走路開始就必須負擔工作,先是學會採集,然後學會縫補修復,接著是狩獵與建造。但永遠要警醒的,是對殭屍的戒備。
一代又一代的人們,恐懼著殭屍的國度,在日光時分努力求生、於黑夜降臨時拼命躲藏,哪怕已經有好幾年沒人被殭屍殺死,但殭屍城的燈光與高聳城牆一直存在,夜間的殭屍巡邏依然沒有停止,也聽得到城裡傳來的各種聲響。
大榕在這種情況下日漸成長,成為村子裡最強壯的獵人,娶了最美的女人,生了最可愛的女兒,一切都是如此美好,直到命運的那一日。
女兒是那樣可愛,可愛到獲得大家無條件的溺愛,也許太過了,每個人從小就被三申五令不可跨越的界線,他女兒毫不在乎。一天,在沒人注意到的情況之下,女兒走出村子的警戒範圍,消失在芒草叢裡。找不到孩子的妻子慌張得不顧危險,在陽光即將隱沒的鬼魅時刻,隻身跑到荒野尋找孩子。
等隔天大榕跟著狩獵隊光榮凱旋,接到噩耗後飛速衝出去尋找,已經太遲了。
被野狗破壞的屍首,意味著至少沒遇到最壞的結局,大榕的妻女雙雙罹難,雖然淒慘無比,但大家都知道,這總比成為殭屍醒過來要好太多了。
但屍體上有不屬於野狗的咬痕,是人的咬痕,殭屍的咬痕。
看來是先被殭屍攻擊,然後才被野狗啃食的。
大榕從此離開村子,一次也沒回家過,只帶著當初外出打獵的工具,獨自住在深山裡面,偶而才到村子外邊交易。雖然大家都要大榕再娶個老婆,但大榕執意獨身,而且期待著殭屍出現。
山裡的野狗,幾年以後絕跡,全被大榕給殺了。
但他從沒見過殭屍。
從小躲到大,大榕很想要親自面對這個倖存者長久以來的詛咒。
但,一到晚上,他依然躲了起來,恐懼依舊獲勝,只偶而聽到夜間的怪異聲響,以及天亮以後地上奇怪的長條痕跡。
「車輪」,這是村子裡智者給的答案,相傳是遠古時代倖存者與殭屍同住在一起時的產物,一種讓人坐在上面移動,力氣奇大無比的怪獸。
其實路上跟一些遺跡裡面也找得到廢棄的車輪,有些簡直像房子一樣大,可以讓人躲在裡面,但經過幾百年,早就全都鏽蝕、崩解了,只剩殘骸讓人憑弔。
相傳殭屍與倖存者原本是兄弟,原本相處和樂,共同創造出各式各樣不可思議的東西,例如可以在天上飛的巨型鐵鳥,一次可以讓幾千人飛上天際,但他一點也不相信,雖說殭屍國度從遙遠的地方看起來,的確有著許多高聳的剛直山丘,有著許多不可思議的景觀,而且每每在傍晚時分發出點點星光,直到清晨才熄滅。智者說那叫大樓,是遠古時代倖存者與殭屍一起居住的地方,因為又高又雄壯,所以古時候叫高雄城,如今只屬於殭屍。
殭屍,又被稱為不死者,相傳在遠古時代,殭屍跟倖存者都是壽命有限的種族,直到某天殭屍智者發現了不死的秘訣,而倖存者希望殭屍能分享這份秘密,卻意外發現,倖存者若想要獲得不死的能力,必須接受殭屍的囓咬,在死亡之後,才可以獲得重生。
但重生後的倖存者就不再是倖存者,只是殭屍。
更糟的是,殭屍突然不願再與倖存者分享世界,想要把倖存者全部消滅,全部轉化成殭屍,因此發動攻擊。
於是很多倖存者變成殭屍,殭屍越來越多,而倖存者被逐出城市,躲進荒野,直到今日。
倖存者,永遠躲避著殭屍,唯一值得慶幸的,是殭屍害怕日光,只在夜間活動。
「懼光者」是殭屍的別稱,而倖存者則自稱為「擁光者」。
如今,大榮的妻女被懼光者殺害了,但大榕自己也無法解釋,為何自己心中沒有怨恨,只有懊悔。他無法憎恨這些他從沒見過,傳說中的不死者,他只是害怕。
但至少,他想要在死前看看殭屍,如果這些真的是不死者,那麼他們就是遠古時代留下來的族裔,曾經跟大榕的祖先共同生活過。
他很想知道,傳說中那個不需要打獵、採集就能有東西吃的年代是否真的存在。
他很想知道,那些傳說中能在天上飛,一次載走好幾個倖存者聚落的鐵鳥是否存在。
他很想知道,那種可以用來跟山的另一頭的人講話的魔法方塊是否真有其物。
偶而,可以在地底挖到過往的遺物,顯示殭屍城裡那種人造山丘,在古時候其實到處都是,而這些人造山丘裡,還有很多用途不明的東西,有些上頭有各種顏色、圖案,甚至有非常逼真的倖存者圖像。
有些符號,智者說那叫「文字」,可以用來紀錄,但如今已經沒人懂那些符號了,唯一稍微理解的智者,也只認得幾個字,數字比較容易懂,大榕也認得一些,不過生活中用手指頭跟腳指頭已經夠了。
尤其有一種被稱作「書」的東西,通常一碰就碎掉,但上面有非常多的「文字」。大榕不大能理解為何要把字弄在這種容易壞掉的東西上面,智者推測可能是要用來當符咒的,因為智者幫人收驚的時候也會找東西在上面畫符咒,然後燒掉,而這些書的確很容易燃燒。
所以古時候的倖存者跟殭屍都需要使用大量的符咒嗎?是否因為他們懂很多符咒,所以才能製造出那麼多神奇的東西?
有太多想要知道的,卻總在夜幕低垂時,被恐懼徹底淹沒。
大榕感受到肩膀刺痛,驚醒過來,發現自己身處陌生的河岸邊,周圍全是殭屍城才有的高大人造山丘--那些「大樓」。
因為城外的早被破壞殆盡了,換句話說,這是牆內,大榕身處殭屍城的內部。
沒什麼草叢樹木,到處都是灰黑色的。
雖說長久以來期待著能看見殭屍,這個傳說中會咬人,把倖存者變成殭屍、把世界毀滅的兇手,但真的身處殭屍城內,心裡的懼怕在尚未天黑的時候就被強勢喚醒,大榕忍痛起身,發現陽光只剩一拳的弧度,而這個地方有太多巨大人造山丘,遮蔽處很多,陽光可能消失得更快。他沒時間逃出去了,必須立即找地方躲藏。
但這是個陌生的地方,完全不像黑厝村。
這些高大、灰色的人造山丘,全都是筆直向天,不像人類居所那樣埋藏地底,建物上面還有許多的孔洞,一點也不在乎夜間光線外洩,但白天陽光不會照射進去嗎?殭屍不是怕陽光嗎?大榕狐疑了一下。所有的建物都非常的工整,像用繩子拉出來的一樣剛直,雖說看得出歷史久遠,呈現一種破敗的色澤,但依舊是非常壯觀的古老聚落。隨處可見的黑灰色道路足以提供好幾十個人並排行走,同樣都是直線,而有些建物上面有著各種顏色、圖案、符號,跟地底挖出來的那些遺物一樣。
那是殭屍嗎?大榕看著一棟建物上的巨大圖案,很像人類,但皮膚是灰色的,眼睛也是灰色的,那不是人類應該有的顏色。
突然,亮光出現,讓大榕的心跳瞬間又來到讓他飆出冷汗的程度。每棟建物都發出亮光,那幅巨大圖案的周圍更是有著五顏六色的光球,還會依序閃耀,讓大榕害怕到極點,只差沒有叫出聲來。
智者說過殭屍城內那些地面的星光叫做電火,是早已失落的科技,源自雷電的力量,只剩殭屍擁有。
有這種不會冒煙的光線,晚上在地底就可以有足夠照明不怕被嗆到了,但害怕陽光的殭屍要這些光線幹嘛?還五顏六色的,看了眼睛好痛。
壓抑著想吐的感覺,大榕匆忙地尋找躲藏的地點。習慣性的,他想找可以躲到地底的地方,而眼前正好有個階梯通往地底,於是大榕迅速移動,進入更黑暗的地下。
看得出來這裡已經久無人煙,證據就是這裡居然有新鮮的羊糞,還有羊騷味,接著他辨識出這個地穴裡有十來隻夜行羊。這種無毛的羊聽說是遠古大滅絕時期之後才出現的,在山裡面偶爾可以見到,但只有逼不得已才會有人想吃,因為味道非常恐怖。
殭屍除了人以外不吃任何東西,至少傳說是這樣的,不過夜行羊很怕人,所以這個地方應該是沒人下來才對,當然,他不知道夜行羊會不會怕殭屍就是了。
再繼續深入,就是光線無法到達的地方,從地上的塵埃狀況判斷,僅有的足跡是他自己跟夜行羊的,大榕覺得這裡不是殭屍會靠近的地方,於是大膽掏出火石,從這裡到處散亂的各式雜物中挑出一根方形的木棍。
方形的,大榕讚嘆了一下,這材質摸起來是木頭沒錯,但居然是方形的長棍,看來大滅絕之前的人的確擁有非凡的技術,因為這裡居然到處都有這種方形的木棍,或者各種很難以置信、非常大片的木板。
看來這裡也是垃圾場,充滿了各式他完全不認得的雜物,翻找一下,拿地上的碎布包裹了幾根木棍之後,大榕燃起火把,然後往地底深處前進。
他必須找一個可以讓他躲到天亮的地方,一個讓他活下去的地方。
終於,在走過數不清讓他讚嘆不已的工整階梯之後,他來到一處讓他無法理解的地方,一個非常長的洞穴,地上還有兩條看不到盡頭的金屬無限的延伸。
這麼多金屬,大榕搖搖頭,整個黑厝村的金屬器具加起來可能還不到他看到的一角,就算連著更遠的三個村子加起來也絕不到他眼前的一半,如果能搬回去,大家不知道會有多高興。
不過這些金屬條都固定在地上,堅固得很。
其實外界也有不少金屬,往地底挖掘尤其多,如果是靠近殭屍城週邊的過往遺跡,那金屬更是隨處可見,問題在於,倖存者已經沒有足以融化這些金屬的技術了,這種挫折已經延續很多代,因為他們沒能力興建足以融化、分離不同種類金屬的熔爐,畢竟,晚上殭屍會出來巡邏,沒有東西可以擺在地面上,而燒東西的火光只要持續到日落,等於在邀請殭屍蒞臨。
大榕逐漸忘卻恐懼,沿著平行的金屬條漫步前行,直到一個發出綠色微光的長方形物品前面才停下來。
長方形物品就在一扇門的上方,上頭有著「文字」,當然他不認得,但有個人形的圖案倒是可以理解的,看起來像是在跑的樣子,或者說,他覺得這應該是門,可以通往其他地方。
在好奇心驅使之下,大榕伸手推門,發現推不動,接著發現門上有條橫置的金屬。又是金屬,大榕感動地摸了摸,發現這金屬可以被壓下去,於是向前推,結果門被打開了。
在大榕眼前的,是數不清的殭屍,但大榕其實沒親眼見過殭屍,也不知道這些就是殭屍,何況,這些殭屍全都站著不動,因為他們被覺醒者封印,沒有任何反應。
在火把照耀下,這些「人」呈現怪異的膚色,皮膚狀況很糟,簡直像白千層的樹皮一樣,充滿細小的裂紋,比較像死透的人。
但這些人形就是站著,而且還會輕微晃動,跟大榕自己閉著眼睛站立時一樣。
在火光照耀下,他無法分辨眼前這些人的膚色,如果他看得到那些「人」灰色的皮膚,也許他會立即聯想到殭屍,不過眼前的年輕女性,讓他完全無法跟殭屍有所聯想。
好像他女兒,好像,像到讓他瞬間淚眼盈框,根本看不到其他東西了。
「阿如……」大榕伸出顫抖的手,觸碰了眼前的女性。明知道不可能,但大榕依然激動。眼前的女性不可能是他的女兒阿如,阿如遇害時只有十歲,還是個小孩,這女性比阿如高多了,幾乎跟他一樣高,但這臉真的好像好像。
擦了擦眼淚,大榕捧著女性的臉頰,不住端詳著。
這觸感好乾,但依然有些彈性。比較像老人,但肉多了些,不過觸感非常的冰冷,一如死屍,直到這時,大榕才警覺到這些「人」全是殭屍的可能性,因為這些人全都是光頭,與傳說中的殭屍相同。
這女性左前臂上有個深深的咬痕,一整片爛肉,但已經乾掉,是人的咬痕,或者說,殭屍的咬痕。
是殭屍嗎?雖然開始害怕起來,但眼前的女性實在太像自己深愛的女兒長大以後可能的樣子,讓他的恐懼感整個被壓抑了下來。
「阿如……」又叫了一聲,接著大榕突然洩氣,他完全搞不懂自己在這裡做什麼。
搖搖頭,舉起火把,大榕繼續深入,發現裡面聚集了有五六個村子那樣多的「人」,假如這些是人的話,但其實他也搞不懂這些是什麼?畢竟傳說中殭屍是會動的,而且見人就咬。
等心情穩定下來,大榕發現這房間另一個出口被石塊堵死,只能原路折返,這地方越看越毛,實在不宜久留,於是大榕打算離開。但離開前,他還是停下來看看這位酷似他女兒的女性。這位女性看來應該是十多歲,身材雖然很高,卻依然有著少女的稚嫩,有點太過單薄,尚未成熟。
不夠強壯,是活不下去的,而這位女性也不是活著的。
那微微凸起的胸口,沒有任何呼吸心跳存在。
「我來走了,阿如。」一如過往要出門打獵前的道別,大榕溫柔地訴說著。
說完大榕轉身,卻突然聽到:「汝是誰?」的回應。
吃驚之餘大榕迅速轉身,還抽出防身的小刀。
只見酷似阿如的女性張開眼睛,盯著大榕。
溷濁的眼睛,殭屍的眼睛。
被那眼睛盯上,大榕開始發抖,小刀也掉在地上,只見那女殭屍僵硬地往前踏一步,接著第二步,來到大榕面前。
「汝叫我?」
那是倖存者的語言,雖然口音很重,但大榕聽得懂。
「汝是誰?」大榕發抖著提問。
殭屍居然笑了,跟他妻子一樣的笑法,說:「我叫陳欣茹,汝勒?」
聽見殭屍那空洞乾燥的聲音,雖然感到恐怖,但可以溝通本身就是一種正面訊號。大榕稍微鎮靜下來,回答說:「我叫大榕。」
殭屍看了看周圍,露出困擾的眼神,說:「只有大榕?」
大榕點了點頭,但他不是很了解這位殭屍的意思,雖然陳欣茹這樣的名字比較長沒錯,但大榕這樣的名字很正常,而且他也的確長得跟榕樹一樣高大。
但這女殭屍幾乎跟他一樣高,而他在村子裡可有巨人的稱號,從沒有人比他高大的。殭屍開口對著大榕說:「這是叨位?發生什麼代誌?」
這句大榕聽不大懂,但看得出來殭屍也很困惑,至少,這殭屍似乎沒有要攻擊他。
「我也毋知。」大榕搖搖頭,表示自己不知道,他什麼都不知道,已經完全搞不清楚狀況了。
自稱陳欣茹的殭屍開步走到門口,動作越來越順暢,靠近門邊的時候,走路的姿勢跟一般人已經沒有兩樣。毫不意外地,她知道如何開門,直接拉開門之後走到外圍。
大榕跟了上去,火把的光芒瞬間照亮附近,在閃光當中,軌道不住往黑暗中延伸。
「捷運?」殭屍開口說了一串語言,大榕聽不大懂,大概是「我怎麼會在這邊」這樣的意思吧?總之,這殭屍看起來也是一臉困惑。或者說,該叫她陳欣茹。
阿茹。
(待續)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光明繼承者LIKADO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光明繼承者LIKADO
公元2030年,殭屍病毒橫掃全球,
人類幾近滅絕,文明由殭屍主宰。
永生不死的殭屍對未來有何盼望?
曾經輝煌的人類又要如何延續星火?
誰又能成為光明繼承者,引導全新的未來?
且看南島語系原鄉的台灣,如何再一次成為波濤中的燈塔。
疫情中的聖域傳說《光明繼承者LIKADO》
帶您見證長達千年、失而復得的文明旅途!
商品特色
【中華科幻學會】會長 難攻博士
美國娛樂分析家 POPO
【中華科幻學會】常務理事 馬立軒
自由作家與編輯 劉揚銘
名家聯手推薦!
深具「本土意識」的末日史詩
以台灣為故事主舞台 展開波瀾壯闊的冒險
橫跨千年,格局恢宏、氣勢磅礡
讓人熱淚盈眶的感人故事
當殭屍末日源自台北 導致人類全體滅亡
文明 能以何種方式再臨?
呼應疫情時代的末日幻想
『捷運╳殭屍』系列首部長篇史詩!
作者簡介:
子藝
看過銀英傳之後,發願要變不良中年。等真的來到中年,而且的確不良之後,頓失人生目標。於是開始努力敲打鍵盤,瘋狂紀錄自己思緒,意圖在世上留下腳蹤。
章節試閱
第一篇:會出事就是會出事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朕茲護持國體而得之,信倚爾忠良臣民之赤誠,常與爾臣民共在。若夫情之所激、濫滋事端,或如為同胞排擠、互亂時局,為誤大道、失信義於世界,朕最戒之。宜舉國一家,子孫相傳,確信神州不滅,念任重而道遠,傾總力於將來之建設,篤道義,鞏志操,誓發揚國體精華,可期不後於世界之進運。爾臣民,其克體朕意哉!」
放送完畢,研究室裡呈現兩種情緒,一種感到安心,因為戰爭終於結束,不再需要躲空襲;另一種則是不安,因為戰敗了。
有前一種反應的大多是台灣人,而後一種,則是內...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朕茲護持國體而得之,信倚爾忠良臣民之赤誠,常與爾臣民共在。若夫情之所激、濫滋事端,或如為同胞排擠、互亂時局,為誤大道、失信義於世界,朕最戒之。宜舉國一家,子孫相傳,確信神州不滅,念任重而道遠,傾總力於將來之建設,篤道義,鞏志操,誓發揚國體精華,可期不後於世界之進運。爾臣民,其克體朕意哉!」
放送完畢,研究室裡呈現兩種情緒,一種感到安心,因為戰爭終於結束,不再需要躲空襲;另一種則是不安,因為戰敗了。
有前一種反應的大多是台灣人,而後一種,則是內...
顯示全部內容
推薦序
[推薦序1]
不瘋魔不成活,不成殭屍,怎保存人類文明的燈火?
劉揚銘(自由作家)
曾聽小說家講,有時不用自己虛構,因為當故事找上門來,不寫都不行。故事像有機生命,會自行長大成熟,作家只是挖通某條水路,讓情節從源頭流洩出一條完整河流。尚未體驗過的我好羨慕如此經歷,而《光明繼承者》就是這樣的故事:開始是短篇創作,但在作者子藝腦中不斷發酵膨脹,成為橫跨六百年時間的殭屍架空歷史小說。
從人類到殭屍的視野
一開始是人類的故事,然後是人類抵抗殭屍的生存歷險,再來是殭屍覺醒的故事,以及殭屍國度彼此戰爭與毀滅...
不瘋魔不成活,不成殭屍,怎保存人類文明的燈火?
劉揚銘(自由作家)
曾聽小說家講,有時不用自己虛構,因為當故事找上門來,不寫都不行。故事像有機生命,會自行長大成熟,作家只是挖通某條水路,讓情節從源頭流洩出一條完整河流。尚未體驗過的我好羨慕如此經歷,而《光明繼承者》就是這樣的故事:開始是短篇創作,但在作者子藝腦中不斷發酵膨脹,成為橫跨六百年時間的殭屍架空歷史小說。
從人類到殭屍的視野
一開始是人類的故事,然後是人類抵抗殭屍的生存歷險,再來是殭屍覺醒的故事,以及殭屍國度彼此戰爭與毀滅...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推薦序] 不瘋魔不成活,不成殭屍,怎保存人類文明的燈火?
[推薦序] 從遊戲到史詩——光明繼承者
插曲 信件A
第一篇:會出事就是會出事
第二篇:貝多芬第五號交 響曲:殭殭殭殭
插曲信件B
第三篇:覓光者
第四篇:日出之前,面朝東
插曲信件C
第五篇:上母
插曲遺落紙條
第六篇:傳說黎明
第七篇:創造歷史的人們
附錄短篇:殭屍的採訪
後記
光明繼承者年表
補遺
[推薦序] 從遊戲到史詩——光明繼承者
插曲 信件A
第一篇:會出事就是會出事
第二篇:貝多芬第五號交 響曲:殭殭殭殭
插曲信件B
第三篇:覓光者
第四篇:日出之前,面朝東
插曲信件C
第五篇:上母
插曲遺落紙條
第六篇:傳說黎明
第七篇:創造歷史的人們
附錄短篇:殭屍的採訪
後記
光明繼承者年表
補遺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2021/04/29
2021/0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