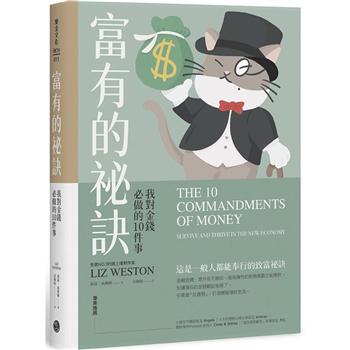圖書名稱:尋找代號八
────《妹妹的墳墓》作者最新力作────
羅伯‧杜格尼 開創間諜小說新巔峰!
◣貓捉老鼠的致命遊戲,諜對諜的頂尖對決◥
★AMAZON、《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三冠王!
★全球銷量超越4,000,000冊!
★美國亞馬遜推理驚悚文學No.1,讀者5顆星高度讚譽!
詹金斯來到人生的十字路口,
他有美麗的妻子、快出生的寶寶,以及一間瀕臨破產的公司,
焦頭爛額之際,重操舊業的機會從天而降,
──臥底前往莫斯科,找到神祕的「第八位姊妹」。
拯救國家,同時也拯救他的生活……真的是這樣嗎?
七位長期潛伏於俄國的美國間諜,人稱「七姊妹」,
近來疑似身分外洩,已有三人遇害。
謠傳俄國總統普丁誓言查出這七個人的身分,
派了一名女性特工「第八位姊妹」,負責調查並消滅這群美國間諜。
為了家人的幸福,以及拯救即將破產的公司,
前CIA特務詹金斯同意重出江湖,假借「出賣情報」之名,
企圖從俄國特務口中吊出第八位姊妹的真實身分。
天上掉下來的任務,到底是危機還是轉機?
一回神,詹金斯驚覺自己可能成為叛國罪人,
危及其他美國特務的性命,甚至賠上家人的生命,
而他的對手,正是自己的國家……
作者簡介
羅伯‧杜格尼Robert Dugoni
美國亞馬遜暢銷作家,受《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盛讚,作品廣受全球讀者好評,目前已賣破四百萬本。出生於愛達荷州,成長於加州,他在十個手足中排行中間,因此常開玩笑說自己沒有什麼機會說話,才會轉而寫作。作品「大衛.斯洛恩」系列皆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風格被譽為堪比《無罪的罪人》史考特.杜羅和《將軍的女兒》尼爾森.狄麥爾,《普羅維登斯期刊》推崇他是「道地的法律驚悚小說之王」、「《黑色豪門企業》作者約翰.葛里遜的接班人」。
「警探崔西」系列小說《妹妹的墳墓》、《她最後的呼吸》榮登亞馬遜排行榜第一名,以及《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暢銷書排行榜。其中第一部《妹妹的墳墓》更被《圖書館期刊》、《懸疑雜誌》選為二○一四年最佳驚悚文學。
他兩次進入國際驚悚小說奬決選、哈波.李法律小說獎、銀刀獎(the Silver Falchion Award)之推理小說奬,以及美國推理作家協會愛倫.坡獎。他的書已出版至二十五餘國,並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
作者官網:www.robertdugoni.com
電子信箱:bob@robertdugoni.com,
推特:Twitter@robertdugoni
臉書:www.facebook.com/AuthorRobertDugoni
譯者簡介
清揚
台大外文系,現為自由譯者。對世界充滿好奇心,喜愛大自然、文學藝術和自助旅行。翻譯作品:《聖骨拼圖》、《黑色密令》、《猶大病毒》、《最終神論》、 《不安的靈魂》、《靈感來了:50部經典文學的幕後故事》、《巫行者1~3》、《長夜盡頭(01):擴散》、《異星記》等作品。


 2020/12/31
2020/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