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位於這條彷彿無窮無盡卻又要陡不陡的漫長坡道頂上的,就是我的目的地──京極堂。
梅雨時節即將過去的夏日陽光,實在稱不上清爽宜人。坡道上連一株樹木之類的遮蔽物也沒有,只見整排的白褐色油土牆連綿不絕。我並不清楚牆壁背後的究竟是民家,還是寺院、療養所之類的。搞不好是公園或庭園也說不定。冷靜一想,牆內的佔地面積未免也太廣大了,應該還是庭園這類的比較有可能吧。
這條坡道沒有名字。
不,說「或許有但我不知道」才正確。自從每個月來拜訪京極堂一次,不,經常還兩三次──總之自從有這習慣以來,已經快要兩年了。這段時間內不知走過這條道路多少次。
但奇妙的是,由我家到這條坡道之間的市鎮景觀,以及途中林林總總的事物,在我的記憶中總是模模糊糊的。別說是坡道的名字,就連這一帶的地名住址我也完全不清楚。更別說這片牆壁背後究竟為何,我壓根兒沒有興趣。
天色驟然轉陰,氣溫沒變。
來到坡道七分之處,我稍作喘息。
快來到坡道頂上時,兩旁出現小路,油土牆在此朝左右兩方彎曲。挾著小路,對面是竹林與幾家老房子。再往前走,便可見到零星的雜貨店與五金行。若再繼續前行,就會進入鄰町的鬧區。
這麼說來,京極堂應該算是位於町與町的交界附近吧。搞不好住址上是隸屬鄰町也說不定。我曾擔心這裡的位置太偏僻,沒有客人上門,這麼看來或許對鄰町居民而言反而很近。
京極堂是家舊書店。
京極堂的店主是我的老朋友。也不知他是否真有心經營,店內老是擺著一些看就知道賣不掉的書。如前所述,這店的地理位置也實在令人難以恭維。雖然店主自稱常客多,經營上不勞我費心,但是真是假我倒是頗感懷疑。
據他所言,京極堂專進一些專門書、漢籍等這類其他舊書店不想賣的書籍。同業者要是不小心收購到這類書籍,便儘管往這裡送,結果這類書籍反而變得只能在此買到。因此學者、研究者之輩便成了這裡的常客,當中還有人迢迢遠路專程跑來這兒購買。但這些都只是店主的片面之辭,真相為何則不得而知。
依我個人猜想,副業的收入可能還比較安定吧,但他本人對此不願表示任何意見。
京極堂位於稀疏竹林圍繞的蕎麥麵店旁,再往前有座小森林,森林裡有間小神社。京極堂的店主原本是這間神社的神主[ 譯註:原專指神社中的神職者之長,不過今日已常用來泛指神職者。],而且至今也仍繼續擔任。聽說每逢節慶時他都會出來唱誦一、兩篇祝詞[ 譯註:於慶典時由神職者唱誦的禱文,內容多為讚頌神明,祈求上天賜福等。其文章的構成有固定的形式。],不過我倒是從來沒看過他的神主打扮。
我抬頭望了望主人親筆寫的,不知該說神妙還是拙劣的『京極堂』三個大字的匾額後,走進門戶大開的正門,立刻見到店主一如往常擺著一張彷彿痛失父母般的臭臉看著日式裝訂的古書。
「喔。」
我發出稱不上打招呼的怪聲,坐上櫃臺旁的椅子,同時兩眼掃視椅子旁堆積如山的未整理書籍。
當然,我是在新進貨的書中尋找珍品。
「你這傢伙真靜不下來。要打招呼就專心打,要坐就專心坐,要看書就專心看書。看你這樣害我也分心了。」
京極堂目不轉睛地看著書說。
但我完全不在意他的話,繼續專心瀏覽沾滿灰塵的書背。
「喂,有沒有什麼有趣的新貨啊?」
「沒。」
京極堂間不容髮地接著說:
「所以我才在看這個。不過哪──雖說所謂有趣不有趣確實會受到個人標準影響,但大體說來這世上沒有不有趣的書,不管什麼書都有趣。所以沒看過的書很有趣,但看過一次以後要獲得同等以上的樂趣就得多花一點時間,就只是如此罷了。這麼一來,對你而言有趣的書就不僅限於那堆未整理的,也可能隱藏在那邊書櫃上堆放了好幾年生灰塵的書籍裡。那邊的書比較好找,快快選一選就買了吧,要我算你便宜一點點也成。」
一口氣說完這一大串後,怪脾氣的舊書店店主略抬起頭來露齒一笑。
「可是我只看能觸動我心弦的書啊。當然啦,只要肯認真讀或許不論什麼書都有趣,但我追求的讀書之樂跟你可不同呀。」
我則是一如往常,東飄西晃地迴避對方的話鋒。
因為不管我是否願意,他老是會像個偏執狂般地把話題牽扯得越來越大,不管話題的開端是多麼無聊的小事,最後他總能論到國家天下大事這類誇張的話題上去。或許是看我也樂在其中,有時他還會故意轉移話題,做出一些古怪的回答。
店主依舊以一副瞧不起人的眼神看著我,接著以更瞧不起人的口氣說:
「我從沒看過像你這麼不熱心的讀書人。會來我這兒的客人個個都對書本有一股非凡的熱情。可是沒想到像你這種讀書慾勝於常人數倍以上者,居然對書本毫無執著之心。別的不說,光是你老是一一賣掉看過的書這點就很不應該。」
確實,我看過的書有八成會賣掉,每次賣掉都被這個怪脾氣的朋友嘮叨責難。但囉唆歸囉唆,最後買下這些書的還不是我眼前的這傢伙。
「沒我這種人你的生意怎麼做?沒人賣書的話,舊書店就像抓不到魚的漁夫。書櫃上擺著的大量魚獲,還不都是從我們這些不遜之輩手中釣來的。」
「哪有人把書跟魚混為一談的。」
京極堂說完,一時似乎不知該接著說什麼。
在這種你來我往的辯論中我大多會敗在他的手下,所以見到朋友一時想不出話來回答,心情頗是愉快。平時的話早就被他做出有效的反擊,為了不錯失好時機我趕緊開口:
「不,書跟魚都一樣。歸根結底,你就是把要拿來賣的魚在上架前全都嘗過,可說是最沒有天良的商人了。想想看,書店的老闆不好好看店居然看起書來,這還像話嗎?如果剛好有客人想買這本書又該怎麼辦?」
「哼,舊書店的書是店主的所有物,既不是出版社寄放在這的,也不是幫人代售的。這家店裡所有的書都是我自己買來的,不管我想拿來看還是當枕頭,都輪不到別人插嘴吧。客人前來是想分享我的收藏,而我則是能體諒客人的心情才會大方出售。更何況,我現在在看的也不是要賣的書哪。」
京極堂似乎很愉快地說著,揚起手中的日式裝訂古書,把封面朝向我這邊。
他讀的是江戶時代一個叫做鳥山石燕的畫家所寫的《畫圖百器徒然袋》。確實,這本並非要拿來賣的,而是他個人的收藏。只不過,就算現在讀的剛好不是,他把要店內的書幾乎全部讀過了也仍是事實。當然這沒什麼不好,只是我老會拿這件事來揶揄他。
因為,我一直都很懷疑京極堂是否真的有心經營買賣。就我所知,他批進來的書主要都是他自己想看的。只不過剛好他的興趣廣泛得令人咋舌,所以店內的貨色反而顯得齊全。
京極堂的表情似乎更添一層悅色地說:
「哎,上來坐吧。」
我終於獲得准許,得以進入客廳。
「老婆不在就不請你喝咖啡了,反正你這條鈍舌頭連咖啡跟紅茶的差別也分不出來,請你喝杯淡茶充充數就好。」
主人伸手到津輕漆器[ 譯註:津輕為青森縣西半部之習稱。此地所產漆器的塗法特別,在凹凸不平的器物表面上分數回塗上不同顏色的漆,再磨成平滑表面便會產生獨特的斑紋。]的桌子上,拿起肯定在我來之前就已擺放很久的茶壺,一如往常說出很失禮的話。
「說什麼笑話,別看我這樣,我可是光靠聞香就能分辨咖啡種類呢。」
「哼哼哼,我看在開玩笑的才是你吧。之前去咖啡廳你點了杯哥倫比亞,結果女服務生弄錯了給你端來摩卡,在不知情下你大言不慚地說什麼你其實比較喜歡摩卡的酸味,還作了一堆講解。像你這種三流文士有機會就想賣弄知識的心情我也不是不能理解,但那次實在太糗,害我這個同行者都覺得丟臉丟死了。」
京極堂邊著說我的糗事,還真的端出一杯淡得不能再淡的淡茶給我。
幸虧登上坡道途中流了不少汗,就算是淡茶也依然美味。
五坪大的客廳裡有一整面牆壁全是書櫃,感覺起來跟在店裡沒什麼兩樣,不過主人的房間比這還要更誇張。常聽他的夫人抱怨家裡容易積灰塵,我完全能理解她的心情。只是,這並不是店裡的書太多了才入侵房子裡,而是相反,如同先前店主自己所言,說藏書太滿了不得不擺到店裡賣才是正確的。
每次只要我來拜訪,書店就形同開店歇業,兩人經常會聊到連晚飯都忘了。
我原本靠拿大學的研究費研究黏菌為生,但只靠微薄的資金實在難以過活,所以現在則是靠寫寫雜文來餬口。這類工作在時間上比較有彈性,除了截稿前夕以外,就算像現在這樣浪費整個白天也完全沒問題。只是京極堂好說歹說也是做生意的,一開始還擔心會不會妨礙到他。但就如前面不知說過多少次一般,我看他根本無心經營,於是久之我也變得不再在意。
只不過我眼前的這位朋友雖然願意陪我殺殺時間,對我寫的文章卻絲毫不能諒解。我自認是寫文學的作家,但為了生活,有時也不得不匿名在給青少年閱讀的科學冒險雜誌上或在荒誕不經的劣酒雜誌[ 譯註:日本戰後一時蔚為風潮的三流雜誌類型,內容多以腥羶八卦的不實報導為主。由於取締甚嚴,與同樣流行於當時的劣酒相同,取其三杯(三期)就倒之意來名之。]上寫寫文章,因此被他笑作是三流文士我也百口莫辯。
「言歸正傳吧,今天又是為了什麼事而來了?關口大師。」
京極堂說完,叼起香菸。
與京極堂的交往可溯及學生時代,說來也有十五、六年了吧。學生時代的他像個肺癆患者一般,氣色極不健康。一天二十四小時總是繃著一張臭臉看著一些又硬又臭的書籍。
當時的我患有輕微的憂鬱症,性格上實在學不來硬派作風,但也無法徹底當個軟弱的文學青年,只好耍起自我孤立。那時與孤僻的我特別親近的,就只有這名怪脾氣的朋友。
但是在本質上他與我完全不同。
比起沈默寡言又憂鬱的我,他實在是非常能言善道,而且交遊的範圍也意外的廣闊,害得我常得陪著他頻繁地與原本不想打交道的人來往,實在是苦不堪言。
憂鬱的我不願與這些人來往是理所當然的,可是拉著我到處跑的他本人卻也常露骨地顯出不愉快的神情,這實在令人難以費解。既然討厭,別做不就得了,但這個奇怪的朋友卻老是邊罵著傻子笨蛋還繼續跟這些傻子笨蛋們交談,然後每次都會搞得自己怒不可遏。
我想,京極堂那時其實是在享受著憤怒行為本身吧。結果害得我也得一直配合他的步調,不知不覺間連憂鬱症都治好了。現在想來,對於情感起伏消失、不斷鑽進牛角尖的憂鬱症患者而言,像這樣到處與人來往意外地很有療效也說不定。
另外,京極堂在與日常生活無關的知識上也驚人地博學。
尤其他在從佛教、基督教、回教、儒教、道教,到陰陽道、修驗道等等各國各地的宗教習俗、口傳故事等類的知識上特別豐富,令我很感興趣。而我在接受憂鬱症治療時累積的神經醫學或精神病學、心理學等等的知識則成了他求知的對象。
因此我們之間經常進行討論議論。我想我們的議論與當時學生們喜好的議論在內容上有很大不同吧,在我們之間,不管是政治還是金魚的養殖方法、或者那個冰果室的招牌姑娘比較可愛等等,都能以同樣認真的態度來討論。如今,這些青春歲月的回憶均已成了往事。
那之後又過了十幾年。
兩年前結了婚,讓我下定決心辭去自大學畢業以來持續進行的黏菌研究,專心靠原本長期當作副業的寫作工作來討生活,並搬來現在的住處。而京極堂也在同一時期辭去任教了有一段時間的高中講師工作。原以為他會專心於當個神主,沒想到卻改建房子,開起舊書店來了。
爾來,每當我小說題材枯竭或者有什麼有趣事件時,總會來此叨擾,像回到學生時代一般長篇大論地閒聊起來。說來這算是寫作工作的一環,但這麼一想,或許也是為了回想起在煩勞生活壓力下逐漸淡忘的學生時代心情才來拜訪的。學生時代瘦過頭的京極堂,在大學畢業的同時結了婚後稍微有變胖了點,但他那張不健康又不高興的臭臉倒是與過去毫無兩樣。
「你覺得,人真有可能懷胎超過二十個月嗎?」
我緩緩地開口問道。
咚、咚、不知由何處傳來了鼓聲。
我想應是夏日慶典的練習吧。
京極堂一點也不覺得訝異,似乎也毫無興趣,只悠悠地吐出煙霧來。
「你特別跑這一趟,為的就是來問我這個既不是接生婆也不是婦產科醫生的人這種問題?這就表示,你認為我這個人應該會知道接生婆跟醫生都想不到的奇妙解答了?」
「唔,你這樣反問我我也沒辦法回答什麼。我只是在想,假設說有個懷胎二十月的女性,其腹部大上普通孕婦一倍,卻一直生不下來。如果這是事實的話,果然是很不尋常的事吧?你不覺得這很不可思議嗎?」
「這世上沒有什麼不可思議的事,關口。」
京極堂說。
這句話是京極堂的口頭禪。
不,說是座右銘也無妨。
只看話語的表面,彷彿就像是近代理性主義的具體化身一般,但他想表達的似乎不是這種意義。
京極堂深深吸了一口只剩菸屁股的香菸,裝出味道很糟的表情後,繼續接著說:「說真的,這個世上只會存在著應該存在的事物,只發生應該發生的事情。人們錯以為僅憑著自己所知的一點點常識與經驗的範疇就能瞭解宇宙的一切,所以才會一遇到稍微超乎常識與經驗的事件時,就異口同聲地喊著不可思議千奇百怪而騷動起來。說實在的,這些連自己的本質與來源都沒思考過的傢伙們,又能瞭解這世上的什麼了?」
「你這些話是衝著我說的?確實我不可能瞭解世上的一切事物,但我至少知道我自己是『不瞭解的』。正因為不瞭解所以才會覺得不可思議,難道不是嗎?」
「我這番話也不是針對你講的──。」
京極堂態度隨便地說著,拿起放置在煙灰缸旁的壺狀物,擺到自己手邊。
「──這只是一般論。」
「那就算了──。」
我沒好氣地回答。
「──的確,就如你所言,我只能在陳腐的常識範圍內理解事物,所以現在才會來聽你的高見啊。」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姑獲鳥之夏(經典回歸版)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姑獲鳥之夏(經典回歸版)
你將會聽到一個女子懷胎二十個月的詭異故事……
20世紀末的日本推理小說新浪潮,
京極夏彥傳奇的起點,就從這裡開始。
★全新導讀與解說,讓我們以嶄新角度重新閱讀「百鬼夜行」系列。
★1994年版「《週刊文春》推理小說BEST10」第7名
★1995年版「這本推理小說了不起」年第7名
★2005年改編電影,由堤真一主演。
【名家推薦】
京極夏彥想書寫的,並非單純的事件或人心的形狀,而是想透過「百鬼夜行」這一系列,
重新書寫傳統、理解現代的根由,對這個世界做出專屬於他的解釋。──曲辰(大眾文學研究者)
《姑獲鳥之夏》是一部運用日本豐富的妖怪文化,將美國於八十年代興起的心理懸疑小說和本格推理結合而成的混種小說。
要了解當代日本文化,京極夏彥是不能略過不讀的作家。-冒業(科幻、推理評論人及作者)
【故事大綱】
婦產科醫院久遠寺家族的女兒懷胎20個月始終無法生產,
更詭異的是,她的丈夫在一年半前居然在宛如密室的房間裡,如煙一般地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夏日的午後,作家關口巽行經傾斜的坡道,來到坡道盡頭一家叫做「京極堂」的舊書店,
造訪他大學時期的朋友中禪寺秋彥──他的朋友都以店名「京極堂」來稱呼他。
關口為京極堂帶來這麼一個奇怪的故事,期望得到解答。
兩人卻赫然發現在密室中消失的男人是他們的大學同學。
京極堂和關口是否曾經在這無法生產的女人和消失的男人事件裡,扮演了什麼樣關鍵的角色?
傳說中的姑獲鳥這種妖怪的形象和傳說,不時困惑侵擾著關口巽。
白天是舊書店老闆的京極堂,有需要時會以陰陽師裝束出現除祆。
儘管時序已進入到現代,妖魔仍在作祟。
在這個號稱理性時代卻百鬼夜行的時空裡,經常將「這世上沒有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掛在嘴上的京極堂,
又該以何種方式解明這一樁不可思議的事件?
姑獲鳥:
原為中國傳統怪物,又名「夜行遊女」、「天帝少女」或是「鬼鳥」,形象殊異。
《齊東野語》中形容為「身圓如箕,十脰(脰:脖子)環簇,其頭有九,其一獨無,而鮮血點滴,如世所傳每脰各生兩翅,
當飛時,十八翼霍霍竟進,不相為用,至有爭拗折傷者」。
《本草綱目》則說它是「鬼神類也。衣毛為飛鳥,脫毛為女人。云是產婦死後化作,故胸前有兩乳,喜取人子養為己子。
凡有小兒家,不可夜露衣物。此鳥夜飛,以血點之為志。兒輒病驚癇及疳疾,謂之無辜疳也。荊州多有之。亦謂之鬼鳥。
......此鳥純雌無雄,七八月夜飛,害人尤毒也。」
作者簡介:
京極夏彥Kyogoku Natsuhiko
1963年生於日本北海道,曾任職廣告公司,擔任平面設計師、藝術總監。
1994年將心血來潮寫成的「百鬼夜行系列」首作《姑獲鳥之夏》投稿至講談社,立刻獲得出版,並且大受歡迎,成為日本出版史上的傳奇之一。
1996年「百鬼夜行系列」第二作《魍魎之匣》獲得第49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
之後以驚人速度發表此系列新作,至2012年為止共有長篇9作,短篇集4作。暌違7年後,於2019年連續三個月發表「百鬼夜行系列」最新作。以京極堂之妹中禪寺敦子與《絡新婦之理》中登場的女子中學生吳美由紀為主角搭檔的《今昔百鬼拾遺──鬼》、《今昔百鬼拾遺──河童》、《今昔百鬼拾遺──天狗》等三作。
☆得獎紀錄
1997年《嗤笑伊右衛門》獲得第25屆泉鏡花文學獎。
2003年《偷窺狂小平次》獲得第16屆山本周五郎獎。
2004年《後巷說百物語》獲得第130屆直木獎。
2011年《西巷說百物語》獲得第24屆柴田鍊三郎獎。
2016年《遠野物語remix》獲得遠野文化獎。
2019年獲得第62屆埼玉文化獎。
相關著作:《今昔百鬼拾遺―河童》《今昔百鬼拾遺--鬼》《書樓弔堂 破曉》《眩談》《百鬼夜行―陰(獨步九週年紀念版)》《百鬼夜行-陽》《怎麼不去死》《邪魅之雫(上)》《邪魅之雫(下)》《百器徒然袋-風》《今昔續百鬼--雲》《冥談》《幽談》《百器徒然袋-雨》《百鬼夜行─陰》《陰摩羅鬼之瑕(上)》《陰摩羅鬼之瑕(下)》《塗佛之宴—撤宴(上)》《塗佛之宴—撤宴(下)》《塗佛之宴-備宴(上)》《塗佛之宴-備宴(下)》
譯者簡介:
林哲逸
專職譯者,愛好閱讀與妖怪。譯有《姑獲鳥之夏》、《魍魎之匣》以及多部輕小說,並擔任《嗤笑伊右衛門》的校潤。
章節試閱
1
位於這條彷彿無窮無盡卻又要陡不陡的漫長坡道頂上的,就是我的目的地──京極堂。
梅雨時節即將過去的夏日陽光,實在稱不上清爽宜人。坡道上連一株樹木之類的遮蔽物也沒有,只見整排的白褐色油土牆連綿不絕。我並不清楚牆壁背後的究竟是民家,還是寺院、療養所之類的。搞不好是公園或庭園也說不定。冷靜一想,牆內的佔地面積未免也太廣大了,應該還是庭園這類的比較有可能吧。
這條坡道沒有名字。
不,說「或許有但我不知道」才正確。自從每個月來拜訪京極堂一次,不,經常還兩三次──總之自從有這習慣以來,已經快要兩年了。這段...
位於這條彷彿無窮無盡卻又要陡不陡的漫長坡道頂上的,就是我的目的地──京極堂。
梅雨時節即將過去的夏日陽光,實在稱不上清爽宜人。坡道上連一株樹木之類的遮蔽物也沒有,只見整排的白褐色油土牆連綿不絕。我並不清楚牆壁背後的究竟是民家,還是寺院、療養所之類的。搞不好是公園或庭園也說不定。冷靜一想,牆內的佔地面積未免也太廣大了,應該還是庭園這類的比較有可能吧。
這條坡道沒有名字。
不,說「或許有但我不知道」才正確。自從每個月來拜訪京極堂一次,不,經常還兩三次──總之自從有這習慣以來,已經快要兩年了。這段...
顯示全部內容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2022/10/20
2022/1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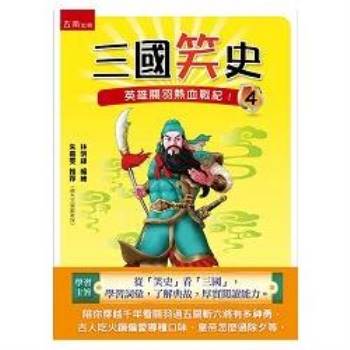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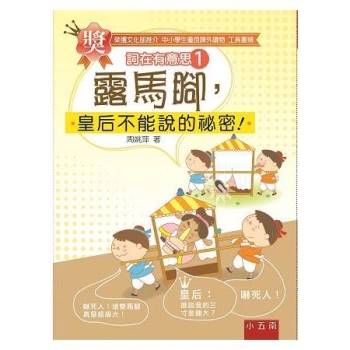






![114年台電新進雇員配電線路類超強4合1[國民營事業] 114年台電新進雇員配電線路類超強4合1[國民營事業]](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1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