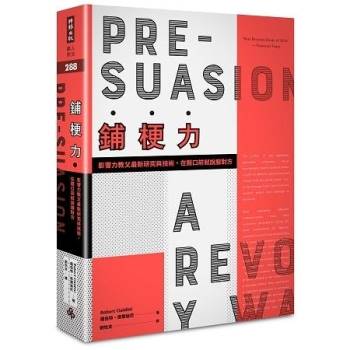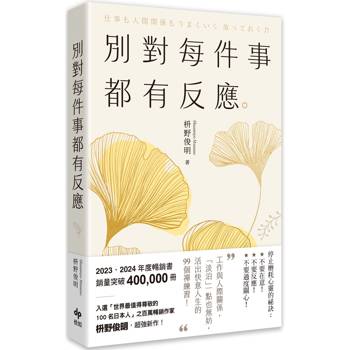詩確實就是對庸常的干擾,詩的敵人不是他者,而是外在的建制與生活。這本詩集裡就是一堆剩餘,歷經生命的輾壓而未消失。究竟能否以詩來思考?或詩只是承接思考的失敗?主體本為殘缺,當隆隆的生命列車依時奔馳過,臥軌的剩餘物再度改變形狀,「我們被世界聽到的歌聲/其實是慘叫」。夠了麼?好像還未夠。睽違八年,鄧小樺第二本詩集《眾音的反面》,接近她,或者等於接近她的反面。
我見過太多開口閉口「論定」香港的人,但是錯誤百出。例如,說香港人港英時期從不抗爭,九七後卻鬧得這麼厲害,沒心沒肺。香港有大量關於七十年代保釣的書籍,如果看過,就知道當年香港人怎樣上街被皇家警察打個頭破血流。之後的「中文運動」,更是如火如荼。香港人是通過抗爭,才確立了中文在香港的官方地位。不了解的人,怎能體會背後的滋味?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眾音的反面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眾音的反面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鄧小樺
著有《不曾移動瓶子》、《斑駁日常》、《問道於民》、合集《所以美好》。編有《走著瞧——香港新銳作者六家》、《是她也是你和我——準來港婦女訪談》(合編)、《一般的黑夜一樣黎明》(合編)。
文學雜誌《字花》創刊編輯之一,曾獲中文文學獎及大學文學獎等。於各大報章及雜誌撰寫專欄、訪問及文化評論。並於各大專院校及中學教授創意寫作。為本土行動及藝術公民成員,2010年參選藝術發展局文學範疇代表選舉。曾任電台文化節目及青年意見節目主持,及曾任職誠品書店。近年策劃不少文學及跨媒體表演計劃(包括西九「自由野」戶外藝術節、港台「好想藝術是麵包——草地.文藝.咬一口」等)現為香港文學館總策展人及理事會召集人,水煮魚文化製作藝術總監,文藝復興基金會理事。
鄧小樺
著有《不曾移動瓶子》、《斑駁日常》、《問道於民》、合集《所以美好》。編有《走著瞧——香港新銳作者六家》、《是她也是你和我——準來港婦女訪談》(合編)、《一般的黑夜一樣黎明》(合編)。
文學雜誌《字花》創刊編輯之一,曾獲中文文學獎及大學文學獎等。於各大報章及雜誌撰寫專欄、訪問及文化評論。並於各大專院校及中學教授創意寫作。為本土行動及藝術公民成員,2010年參選藝術發展局文學範疇代表選舉。曾任電台文化節目及青年意見節目主持,及曾任職誠品書店。近年策劃不少文學及跨媒體表演計劃(包括西九「自由野」戶外藝術節、港台「好想藝術是麵包——草地.文藝.咬一口」等)現為香港文學館總策展人及理事會召集人,水煮魚文化製作藝術總監,文藝復興基金會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