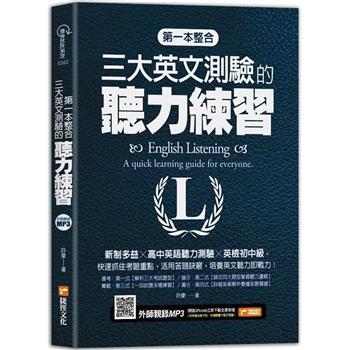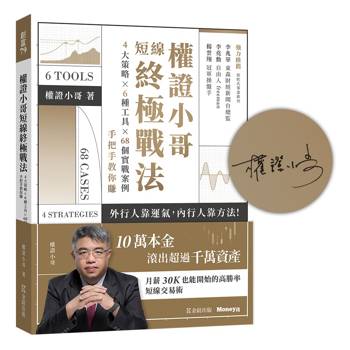詩人不清旅居加拿大,受香港和台灣現代詩影響外,更閱覽前衛的英詩,尤其崇拜John Ashbery。因此,不清的作品雖然不以修辭或語感取勝,卻在形式上不拘一格,表現出強烈的實驗性。
本詩集是不清十多年來首本結集,包括多首獲獎作品外,也獲得著名文學評論家彭礪青及詩人梁匡哲作序言及推薦。他的詩觀獨特,大概可以從他以下的一段詩略窺一二:
沒甚麼
比物件所呈現的象徵性更加充滿危機,
他因為一朵花所包含的意思
被驅逐,房間
希望把秘密上鎖所以她在門上
掛上玫瑰;一朵紅色的玫瑰
因為愛,死於剪刀然後被插在
營養的水份中
再死一次。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卌二排浪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27 |
二手中文書 |
$ 279 |
文學 |
$ 310 |
現代詩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卌二排浪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不清
作者不清,本名李清華,香港出生。二〇〇〇年開始創作詩歌,關於詩社成員。曾獲「香港本土文學大笪地詩歌文學獎」首獎、台灣「喜菡文學網新詩獎」佳作獎等。作品散見於香港及海外的詩刊及其他媒體。作者身居外地,除了汲取了香港文學的養份外,也受北美英語詩歌及台灣現代詩影響,詩作獲得香港及台灣等地方的詩壇認同。
不清
作者不清,本名李清華,香港出生。二〇〇〇年開始創作詩歌,關於詩社成員。曾獲「香港本土文學大笪地詩歌文學獎」首獎、台灣「喜菡文學網新詩獎」佳作獎等。作品散見於香港及海外的詩刊及其他媒體。作者身居外地,除了汲取了香港文學的養份外,也受北美英語詩歌及台灣現代詩影響,詩作獲得香港及台灣等地方的詩壇認同。
目錄
7 一半的流程圖、詩帝或其他 梁匡哲
15 自序詩
【海】
18 1 以潛
19 2 我確信這些門都能通往海
21 3 你說這是無可解譯的遠古寓言
23 4 光管舞
24 5 我所認識不曾失戀的空中飛人
26 6 暗戀是這樣的
26 7 無詩可寫
37 i 只有一把鈍刀/才能裁剪出時間的輪廓/才能裁剪出
你在我夢中/犯過的戒
38 ii 迷路於字裡行間
39 iii 分行詩
40 iv 必要的詩
41 v 有人在他們的耳邊說
42 vi 我大概已經不愛詩了
43 vii 情詩寫出來像一條藥方
44 viii 無詩可寫
45 8 如染上一種遺傳病
46 9 夢以黑暗統治它們自己
50 10 下一站天國
53 11 我們曾是半畝移動的土地
54 12 而唯有在完全的黑夜裡我們才能感知我們真正所欠的
56 13 體溫都在火藥庫裡
57 14 其實有一種稱之為混沌的緊密系統把它們維繫著
67 15 那些微弱的密碼必然屬於我們的
69 16 送你僅剩的這一瓣
70 17 灌溉一切跟海有關的敏感詞
71 18 安全這個問題
72 19 跟一雙被冠上簡單定義的手跳起短暫的舞
73 20 風中找尋著她的罅隙
75 21 我是真的不願再見自己掩泣流連的
77 22 張開眼你和我一同消失
80 23 My dear,而他們誤稱你為鹿
81 24 CANTO OSTINATO
104 25 而偶然有些句子會在夢中倒行譯詩
109 26 而當你走到熟悉的門前
111 27 已經準備好了
114 28 一首有關沙灘的詩而沙灘完全不曾貼貼實實的存在過
116 29 Hey Joe 他們為你拔除背上的刺
119 30 四月之後的每一天
121 31 沒有鳥在觀看
122 32 揮出彩虹灑一點點淚
124 33 一束束聖誕燈閃爍我枕上徹夜的夢境
127 34 而想念的其實不是海
130 35 試圖填滿她的身體
131 36 回南天氣在你我之間衍生
133 37 走完這幅不得履行的路線圖
134 38 只不過是異國人民遊歷過後所購買的明信片
136 39 故此我們積極開墾沙
139 40 如果月球不再存在
141 41 告別書
142 42
147 42.1 究竟那是濕潤的黃昏還是黎明
【岸】
150 祭野豬
152 族譜
155 北京,仍然是中國的首都
157 謊言
159 其實有一種浪的運動把詩歌維繫著 彭依仁
15 自序詩
【海】
18 1 以潛
19 2 我確信這些門都能通往海
21 3 你說這是無可解譯的遠古寓言
23 4 光管舞
24 5 我所認識不曾失戀的空中飛人
26 6 暗戀是這樣的
26 7 無詩可寫
37 i 只有一把鈍刀/才能裁剪出時間的輪廓/才能裁剪出
你在我夢中/犯過的戒
38 ii 迷路於字裡行間
39 iii 分行詩
40 iv 必要的詩
41 v 有人在他們的耳邊說
42 vi 我大概已經不愛詩了
43 vii 情詩寫出來像一條藥方
44 viii 無詩可寫
45 8 如染上一種遺傳病
46 9 夢以黑暗統治它們自己
50 10 下一站天國
53 11 我們曾是半畝移動的土地
54 12 而唯有在完全的黑夜裡我們才能感知我們真正所欠的
56 13 體溫都在火藥庫裡
57 14 其實有一種稱之為混沌的緊密系統把它們維繫著
67 15 那些微弱的密碼必然屬於我們的
69 16 送你僅剩的這一瓣
70 17 灌溉一切跟海有關的敏感詞
71 18 安全這個問題
72 19 跟一雙被冠上簡單定義的手跳起短暫的舞
73 20 風中找尋著她的罅隙
75 21 我是真的不願再見自己掩泣流連的
77 22 張開眼你和我一同消失
80 23 My dear,而他們誤稱你為鹿
81 24 CANTO OSTINATO
104 25 而偶然有些句子會在夢中倒行譯詩
109 26 而當你走到熟悉的門前
111 27 已經準備好了
114 28 一首有關沙灘的詩而沙灘完全不曾貼貼實實的存在過
116 29 Hey Joe 他們為你拔除背上的刺
119 30 四月之後的每一天
121 31 沒有鳥在觀看
122 32 揮出彩虹灑一點點淚
124 33 一束束聖誕燈閃爍我枕上徹夜的夢境
127 34 而想念的其實不是海
130 35 試圖填滿她的身體
131 36 回南天氣在你我之間衍生
133 37 走完這幅不得履行的路線圖
134 38 只不過是異國人民遊歷過後所購買的明信片
136 39 故此我們積極開墾沙
139 40 如果月球不再存在
141 41 告別書
142 42
147 42.1 究竟那是濕潤的黃昏還是黎明
【岸】
150 祭野豬
152 族譜
155 北京,仍然是中國的首都
157 謊言
159 其實有一種浪的運動把詩歌維繫著 彭依仁
序
序
一半的流程圖、詩帝或其他
這篇序我拖了很久,拖了一個聖誕,又拖了一個新年假期。
然後想著擱著,這本詩集不就是表現「拖的藝術」嗎 ?「拖」並不是沒話找話說,而是綿延的、超越話語的,直接指向對象的,所以就有這本不清情詩精選 42。
《卌二排浪》幾乎每一首詩都以海為經,以抒情為緯,貫穿為航道。每一首詩就是航道各異的風景。這本詩集的意象密集而豐富,排山倒海而來。可是,能寫出一手意象密集的詩,大概不是甚麼稀奇之事。不清又是怎樣開始他的寫作呢?
不清在他的文章〈我的語言詩歌筆記本〉闡述了他的詩觀,一種強調「過程」的詩觀:他引用伯恩斯坦(Charles Bernstein):「我們居於過程(process)裡,而當我們意識到我們正朝著一個預設的目的地(predetermined result)時,我們便需要背棄這個過程。我們的旅程不會結束,我們的事業仍未完成,我們的詩歌將引發更多新的詩歌。更完美只是一個方向,一場運動,而不是一個終極的、理想的完美(idealized perfection)。」如此一來,詩歌充其量只是一個半完成品。每一首詩都是為了準備下一首而寫,微調的藝術,創造便是一連串無休止的「出發」。
香港現代詩向來有「由生活出發」之說,意在反映生活百態的現實主義。(恕我不客氣地講句,也是由生活終結罷。)事實上,所有「寫實」都少不免摻雜著「想像」,就算是自身的經驗,由於記憶的破碎和不穩定性,寫作時也會有所潤色與改動。由是,「過程」是一種可行的出路,於寫實想像的揉雜之間,它不停留,取多元而捨單一。另一方面,現當代詩歌有情感隱晦的特色,由於技巧的高度往往被視為藝術性的來源(即所謂詩味)。對於情感的闡發便相對次要(當然是偏見)。現代生活所帶來的情感壓抑,反映在破碎的語言裡,卻未有足夠的正視。此時不清振臂一呼:「我就是要濫情,誰奈得我何」。
詩歌發展至今,幾已成為各種議題的角力場。而不清專心致志地鑽研情詩的套路,使我常想像一個情景:熟悉現代詩的讀者可能會搖搖頭,而不清彷彿是一個惡作劇的小孩,在一旁掩著嘴笑。不清的詩,處處返樸歸真,以小孩的視點/後現代童話觀察這個光怪陸離的世界:「就像一位患上習慣性說謊的小孩」、『「你是米奇,我是烤鴨。」/昨天我們就能夠擁有新的角色了!』〈下一站天國〉、「一個個童話故事因此而被虛構/在這個城市的晚上」〈夢以黑暗統治它們自己〉、「沿出發反方向的路出發離開睡公主/前世的城堡,而一路上有路燈」〈下一站天國〉、「成年人取笑我們把/圓點畫得太像張牙的太陽」〈我們曾是半畝移動的土地〉。我必須說,這種童真不是刻意飾演用作逃避現實的,相反地,是對世界種種荒誕的體會,以赤子的形態再度介入。或許對於任何的規範和體制,正面的衝擊未必奏效,唯有以反諷的形式令它們暴露自身的矛盾和窘態,那就是黑色幽默。對於主流,他像一個死小孩在玩泥巴,弄髒自己也打算弄髒別人,興奮的自言自語著。譬如〈無詩可寫〉是無聊教人莞爾的。如果詩題就是詩,詩就是詩題,那麼詩題還有存在的價值?詩的分行:竟然是打蟑螂?寫詩之必要性,也寫「無詩可寫」的尷尬情況。不清詩中常思考「字」與「詩」的關係,特別是「漢字」與「詩」那種若即若離的特性。事實上,漢語的每一個「字」本就是一個「詞」。看看這些詩:〈安全這個問題〉、〈灌溉一切跟海有關的敏感詞〉、〈跟一雙被冠上簡單定義的手跳起短暫的舞〉,均有不俗的發揮。說到底這是對「定義」的反撥。誰來定義?為甚麼要定義?譬如「My dear」和「My deer」的讀音是一樣,意義既然約定俗成,也意味著它背後有某種權力機制在運作,如果一層層地揭開來,定然會觸動某些人的神經(說不定好像鎢絲斷掉)。
就算回到不清的情詩,依然「搞怪」。不清最強的地方就是自嘲:「究竟我們需要多少顆太陽才能/看清整個宇宙」、「我坐在你家門外,觀察行人/與行人之間的芒刺」、「午飯時吃過太多咖喱雞而誤解了愛」,「一直以來,海岸線不斷膨脹/像我們步入中年的體形」。「許多剛剛脫胎的手/在一場競技賽中替彼此換骨」,「故此我的信心是核電廠/而我的精神狀況在荷蘭」,「快樂和痛皆單純/凝聚於掀動的手指和手槍」。愛的光譜啊不就是千奇百怪的嗎,各式各樣的畸戀,是資格實踐大愛(是挪亞方舟嗎),許多「動物」,每每在詩中「不該出現」的地方出現,而且是龐然大物:如海豹、長毛象,梅花鹿、或小到無法與主體分離如鯡魚的卵子,「自然」穿來插去,來去自如,疏離而特別的城市景觀,彷彿連綿交配、增殖的夢境,彷彿水族館那禁閉且寧靜的狀態。
雖說如此,寫抒情詩的作者面對的首要難題仍是:避免重複自己,避免重複他人。情感來來去去都是那幾種,只能在呈現手法和切入角度方面推陳出新。影響的焦慮無處不在,極快構成陰霾。不清是建築師,他的工作講求精確,他在詩中卻在擬造另一種精確:「精確的模糊」。不清曾經跟我說,他有不少的詩歌意念都是在火車的車程中形成。所以不難發覺,相對於外部世界的急速流動,他多數沈緬於緩慢的內心世界,慢慢地醞釀出腔調。
沒錯,是「情感的失落」,「正在悼念昨晚/沒有如期浮現的夢境」〈我確信這些門都能通往海〉,「不然就把記憶棄置於獅子的口腔裡」〈我所認識不曾失戀的空中飛人〉,「我們只是純粹的雨/著地後就失去名字」〈張開眼你和我一同消失〉、「你閃亮的世界,永遠/輪不到我」〈已經準備好了〉、「以一股孤獨在魚缸中找尋同類者」〈我確信這些門都能通往海〉。情並非因為「擁有」而抒發,更多是因為「空想」而充滿著,此消彼長著。
那種空想是如何達致的?再細心留意,不清最慣常用的人稱是「我們」。「我們」可以是「我和你」、「我和他/她」,所以「我們」的存在是突出了「我」在二人之間的意識,在詩中一起行動,以及共同想像。大概,他受到林禹瑄的詩集《那些我們名之為島的》的影響,並顯示在他的長句與句式(而我們⋯⋯/譬如⋯⋯開頭的句子)。怪叔叔不清固然不會複製少女的愁緒,但那種潮濕多疑的氣氛始終是嗅得出來的。
其實有一種稱之為暗戀的緊密系統把它們維繫著以下我打算以兩首詩的閱讀作一示範,不清是怎麼一回事。而是次示範,同樣希望作為反面教材,請大家請狠狠地誤讀吧。
〈其實有一種稱之為混沌的緊密系統把它們維繫著〉(真的好長好長),這可能是詩集中的難點。在詩題中,重點在於片語「混沌的緊密系統」和「它們」和「維繫著」。驟看是那種探討寫作的「後設」詩,但抒情的意圖仍是相當明顯的。
如上所述,「混沌的緊密系統」就是「精確的模糊」的努力形構,一種有別於一般的意義系統。既然是「混沌」,何以「緊密」,又何以成「系統」?唯有明白我們的世界的龐雜性,我們才能夠開展討論。正如黑格爾(G.W.F. Hegel)曾經說過「一般來說,熟知的東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東西,正因為它是熟知的。有一種最習以為常的自欺欺人的事情,就是在認識的時候先假定某種東西是已經熟知了的,因而就這樣地不去管它了。」
在結構主義底下,有一門名為符號學的學科應運而生,有所謂「能指」與「所指」的概念,緣自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結構語言學,後來廣泛用到不同人文學科的領域。為方便解釋,在此我借用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一書的理論,符號的流程圖式如下:
發送者/意圖意義(我)→符號載體/信息意羲(瓶中信及信中的文字)→接受者/解釋意義(他者)
「瓶中信」者,發信者往往不能肯定收信人的身分,或者這樣說,他根本一開始就沒打算收信人收到信,讓瓶永遠飄浮著,而收信者彷彿也是一直飄浮著。「那只是一則單向性的指示」,瓶中信的流程注定無法到接受者的手上。「意義」只停留在發送者與載體兩個階段,攜帶的「意義」沒有消失,造成意義停留的尷尬/錯覺。
在核心的外緣游走而不進入。由此可見,意義不是點對點的,而是線與線的交織而成。
首先在詩中,所有的情節,處於眾聲交響的狀況之中。而對於飄浮這個動態而言,時間是沒有意義的,就像一個永遠循環著的系統。
「你醒來的時候她已經離開了/留下孤獨」
「我醒來的時候祂們已經離去了」
「Are we / there yet ?」
對於飄浮,「那裡」是不可能的。唯有周而復始地詰問,方能換取一種似有還無的「醒來」,而醒來不代表旅程中止。因此他如此說:「白色的海浪聲將成為一種永恆的鼓舞/一種無可預知的生命力」。第二,便是「抒情」的系統,「情感」會否過期,會否變質而「濫情」起來?有沒有可能是情感的果實本就蘊含一顆濫情的果核,而「變壞」是它的必然方向及本質,指向「抒情」的無效化?不清的詩中不見得如此悲觀,至少是中性的,「如讓彼此的生命和呼吸聲/延續急速自轉和濕潤」。而面對命運不對等的權力關係,「這是一種對主宰的信任/從開始的那一天就存在著」,因此傳達甚麼不是重點,而是「傳達」此一行為背負著的命運。此一命運,代表意義的權威性之佚失:「設計師在佈置一局沒有預設立場的『方格』」,把意義邊緣化,把符號降解為物,逐層逐層剝落。而對於壓迫與被壓迫者情景的描述,「可惜有一種性格極度害怕窗/他們需要一堵圍牆」這句教人拍案叫絕,這種「需要」是變態的,真正令人害怕的無形牢籠,同時也是對於「意義」不能順利抵達某地的恐懼,甚至是對於不能歸類之物的恐懼。這首詩像一股巨大的洋流,衝擊思維,還有衝擊「詩的思維」。
如果想要看點輕鬆的詩,我推介他的暗戀組詩,是寫給 M 的(即是我本人)。詩題〈暗戀是這樣的〉。但是我讀完整首詩之後,不但沒有更加清楚暗戀是怎樣的,反而是更加疑惑了。不清開了這樣一個玩笑,不料卻擊中那種暗戀的「狀態」。詩用時間分組,而且非常隨意(由黃昏的 18:00 開始),正好表達暗戀的來去無由。有時像瘋子一樣喃喃自語(我腦裡全是你的⋯⋯我腦裡全是你的⋯⋯),講的還是同一句話。有時又顧影自憐,但無論如何你已經住在我裡面(你住進了我望遠鏡中最遙遠的/玻璃窗),不惜一切用所有方式想要去親近(郵票是我的舌尖,9:00 鼻尖在附近),但換來(世界所有的廢話都埋伏在那裡),除了指的是海浪聲音的無意義之外,若言者有意,但聽者無心,綿綿情話也終將無用。有時非常壓抑(夢是她的同謀⋯⋯受騙而醒來手上卻完全沒有證據),卻沒有說出其實是我主動甘願「被騙」的。至嚴重處就像一種病,失眠之餘,連時間的流逝也無法感知(因此 2:00 連續出現兩次,也可解為看鐘看了兩次),痴情至此(你沒有察覺我的夢中/我偷偷看著你/多一個小時),直至清晨,進而幻想與你交往的過程(為夢境穿上鞋子,打上蝴蝶結),將凝視反過來想像(你就在車廂的遠角最貼近我眼睛的地方),暗戀出現在不存在的時間(8:60),同樣能解釋為物理世界不足以容納暗戀。也有色迷迷的遐思(因為雲在彼此摩擦而/洩了一陣夜雨)暗引巫山雲雨之典故,可惜那只是打手槍而已(有時候在戶外做點不禮貌的事/把舌頭伸進她的字與字之間),你的午餐在一位女生的嘴巴裡/唇邊和指尖之間的非流動性,在眼裡),強裝理性的面貌卻無法掩飾暗戀的不理性。最後一節,結果是結果了,得到的只是一陣陣的酸澀。這詩還沒有完結,時間是 17:00,下一小時是 18:00,正好可以接上詩首,不斷不斷地輪迴⋯⋯很可怕吧?
這首詩充分表現暗戀的窺視與隱藏。戀人在詩中的缺席,引發敘述的動力。「你」其實沒有在詩中真正出現過。那哀戚的當代少年維特,含蓄又大膽,藉此時間的流逝對照相應的心理狀態。很不
幸地,這就是魯蛇的我了(抽泣)。
就像〈42〉所言:「所以所有建設都應該從建築一座廢墟開始」。成功的解構,恰恰是在結構的準確認知之上,才得以成功的。
解構者正是結構的專家。所謂的繼承與創新,就是處於一種辯證的關係。「我們的眼神,被囚禁四十二光年/卻依然能夠觸動彼此的靈魂?」豈不是〈混沌〉一詩的餘音?從島到島,從夢到夢,究竟那是濕潤的黃昏還是黎明?所有的愛情,是從焦慮中成熟起來的,或半生熟的,失敗者的實錄。
作為一張半完成的流程圖,你絕對可以說激進/很愛演/鬆散/佬味太重,但這些不同的評價正好表達詩集的兼容性,它的基本立場是拒絕定型的:
「詩是海浪/沒有一排相似的浪是相似的。」——〈CANTO OSTINATO〉
請你忘掉上面我說的胡話,隨便找條船,帶上你的背包就是了。
一半的流程圖、詩帝或其他
這篇序我拖了很久,拖了一個聖誕,又拖了一個新年假期。
然後想著擱著,這本詩集不就是表現「拖的藝術」嗎 ?「拖」並不是沒話找話說,而是綿延的、超越話語的,直接指向對象的,所以就有這本不清情詩精選 42。
《卌二排浪》幾乎每一首詩都以海為經,以抒情為緯,貫穿為航道。每一首詩就是航道各異的風景。這本詩集的意象密集而豐富,排山倒海而來。可是,能寫出一手意象密集的詩,大概不是甚麼稀奇之事。不清又是怎樣開始他的寫作呢?
不清在他的文章〈我的語言詩歌筆記本〉闡述了他的詩觀,一種強調「過程」的詩觀:他引用伯恩斯坦(Charles Bernstein):「我們居於過程(process)裡,而當我們意識到我們正朝著一個預設的目的地(predetermined result)時,我們便需要背棄這個過程。我們的旅程不會結束,我們的事業仍未完成,我們的詩歌將引發更多新的詩歌。更完美只是一個方向,一場運動,而不是一個終極的、理想的完美(idealized perfection)。」如此一來,詩歌充其量只是一個半完成品。每一首詩都是為了準備下一首而寫,微調的藝術,創造便是一連串無休止的「出發」。
香港現代詩向來有「由生活出發」之說,意在反映生活百態的現實主義。(恕我不客氣地講句,也是由生活終結罷。)事實上,所有「寫實」都少不免摻雜著「想像」,就算是自身的經驗,由於記憶的破碎和不穩定性,寫作時也會有所潤色與改動。由是,「過程」是一種可行的出路,於寫實想像的揉雜之間,它不停留,取多元而捨單一。另一方面,現當代詩歌有情感隱晦的特色,由於技巧的高度往往被視為藝術性的來源(即所謂詩味)。對於情感的闡發便相對次要(當然是偏見)。現代生活所帶來的情感壓抑,反映在破碎的語言裡,卻未有足夠的正視。此時不清振臂一呼:「我就是要濫情,誰奈得我何」。
詩歌發展至今,幾已成為各種議題的角力場。而不清專心致志地鑽研情詩的套路,使我常想像一個情景:熟悉現代詩的讀者可能會搖搖頭,而不清彷彿是一個惡作劇的小孩,在一旁掩著嘴笑。不清的詩,處處返樸歸真,以小孩的視點/後現代童話觀察這個光怪陸離的世界:「就像一位患上習慣性說謊的小孩」、『「你是米奇,我是烤鴨。」/昨天我們就能夠擁有新的角色了!』〈下一站天國〉、「一個個童話故事因此而被虛構/在這個城市的晚上」〈夢以黑暗統治它們自己〉、「沿出發反方向的路出發離開睡公主/前世的城堡,而一路上有路燈」〈下一站天國〉、「成年人取笑我們把/圓點畫得太像張牙的太陽」〈我們曾是半畝移動的土地〉。我必須說,這種童真不是刻意飾演用作逃避現實的,相反地,是對世界種種荒誕的體會,以赤子的形態再度介入。或許對於任何的規範和體制,正面的衝擊未必奏效,唯有以反諷的形式令它們暴露自身的矛盾和窘態,那就是黑色幽默。對於主流,他像一個死小孩在玩泥巴,弄髒自己也打算弄髒別人,興奮的自言自語著。譬如〈無詩可寫〉是無聊教人莞爾的。如果詩題就是詩,詩就是詩題,那麼詩題還有存在的價值?詩的分行:竟然是打蟑螂?寫詩之必要性,也寫「無詩可寫」的尷尬情況。不清詩中常思考「字」與「詩」的關係,特別是「漢字」與「詩」那種若即若離的特性。事實上,漢語的每一個「字」本就是一個「詞」。看看這些詩:〈安全這個問題〉、〈灌溉一切跟海有關的敏感詞〉、〈跟一雙被冠上簡單定義的手跳起短暫的舞〉,均有不俗的發揮。說到底這是對「定義」的反撥。誰來定義?為甚麼要定義?譬如「My dear」和「My deer」的讀音是一樣,意義既然約定俗成,也意味著它背後有某種權力機制在運作,如果一層層地揭開來,定然會觸動某些人的神經(說不定好像鎢絲斷掉)。
就算回到不清的情詩,依然「搞怪」。不清最強的地方就是自嘲:「究竟我們需要多少顆太陽才能/看清整個宇宙」、「我坐在你家門外,觀察行人/與行人之間的芒刺」、「午飯時吃過太多咖喱雞而誤解了愛」,「一直以來,海岸線不斷膨脹/像我們步入中年的體形」。「許多剛剛脫胎的手/在一場競技賽中替彼此換骨」,「故此我的信心是核電廠/而我的精神狀況在荷蘭」,「快樂和痛皆單純/凝聚於掀動的手指和手槍」。愛的光譜啊不就是千奇百怪的嗎,各式各樣的畸戀,是資格實踐大愛(是挪亞方舟嗎),許多「動物」,每每在詩中「不該出現」的地方出現,而且是龐然大物:如海豹、長毛象,梅花鹿、或小到無法與主體分離如鯡魚的卵子,「自然」穿來插去,來去自如,疏離而特別的城市景觀,彷彿連綿交配、增殖的夢境,彷彿水族館那禁閉且寧靜的狀態。
雖說如此,寫抒情詩的作者面對的首要難題仍是:避免重複自己,避免重複他人。情感來來去去都是那幾種,只能在呈現手法和切入角度方面推陳出新。影響的焦慮無處不在,極快構成陰霾。不清是建築師,他的工作講求精確,他在詩中卻在擬造另一種精確:「精確的模糊」。不清曾經跟我說,他有不少的詩歌意念都是在火車的車程中形成。所以不難發覺,相對於外部世界的急速流動,他多數沈緬於緩慢的內心世界,慢慢地醞釀出腔調。
沒錯,是「情感的失落」,「正在悼念昨晚/沒有如期浮現的夢境」〈我確信這些門都能通往海〉,「不然就把記憶棄置於獅子的口腔裡」〈我所認識不曾失戀的空中飛人〉,「我們只是純粹的雨/著地後就失去名字」〈張開眼你和我一同消失〉、「你閃亮的世界,永遠/輪不到我」〈已經準備好了〉、「以一股孤獨在魚缸中找尋同類者」〈我確信這些門都能通往海〉。情並非因為「擁有」而抒發,更多是因為「空想」而充滿著,此消彼長著。
那種空想是如何達致的?再細心留意,不清最慣常用的人稱是「我們」。「我們」可以是「我和你」、「我和他/她」,所以「我們」的存在是突出了「我」在二人之間的意識,在詩中一起行動,以及共同想像。大概,他受到林禹瑄的詩集《那些我們名之為島的》的影響,並顯示在他的長句與句式(而我們⋯⋯/譬如⋯⋯開頭的句子)。怪叔叔不清固然不會複製少女的愁緒,但那種潮濕多疑的氣氛始終是嗅得出來的。
其實有一種稱之為暗戀的緊密系統把它們維繫著以下我打算以兩首詩的閱讀作一示範,不清是怎麼一回事。而是次示範,同樣希望作為反面教材,請大家請狠狠地誤讀吧。
〈其實有一種稱之為混沌的緊密系統把它們維繫著〉(真的好長好長),這可能是詩集中的難點。在詩題中,重點在於片語「混沌的緊密系統」和「它們」和「維繫著」。驟看是那種探討寫作的「後設」詩,但抒情的意圖仍是相當明顯的。
如上所述,「混沌的緊密系統」就是「精確的模糊」的努力形構,一種有別於一般的意義系統。既然是「混沌」,何以「緊密」,又何以成「系統」?唯有明白我們的世界的龐雜性,我們才能夠開展討論。正如黑格爾(G.W.F. Hegel)曾經說過「一般來說,熟知的東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東西,正因為它是熟知的。有一種最習以為常的自欺欺人的事情,就是在認識的時候先假定某種東西是已經熟知了的,因而就這樣地不去管它了。」
在結構主義底下,有一門名為符號學的學科應運而生,有所謂「能指」與「所指」的概念,緣自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結構語言學,後來廣泛用到不同人文學科的領域。為方便解釋,在此我借用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一書的理論,符號的流程圖式如下:
發送者/意圖意義(我)→符號載體/信息意羲(瓶中信及信中的文字)→接受者/解釋意義(他者)
「瓶中信」者,發信者往往不能肯定收信人的身分,或者這樣說,他根本一開始就沒打算收信人收到信,讓瓶永遠飄浮著,而收信者彷彿也是一直飄浮著。「那只是一則單向性的指示」,瓶中信的流程注定無法到接受者的手上。「意義」只停留在發送者與載體兩個階段,攜帶的「意義」沒有消失,造成意義停留的尷尬/錯覺。
在核心的外緣游走而不進入。由此可見,意義不是點對點的,而是線與線的交織而成。
首先在詩中,所有的情節,處於眾聲交響的狀況之中。而對於飄浮這個動態而言,時間是沒有意義的,就像一個永遠循環著的系統。
「你醒來的時候她已經離開了/留下孤獨」
「我醒來的時候祂們已經離去了」
「Are we / there yet ?」
對於飄浮,「那裡」是不可能的。唯有周而復始地詰問,方能換取一種似有還無的「醒來」,而醒來不代表旅程中止。因此他如此說:「白色的海浪聲將成為一種永恆的鼓舞/一種無可預知的生命力」。第二,便是「抒情」的系統,「情感」會否過期,會否變質而「濫情」起來?有沒有可能是情感的果實本就蘊含一顆濫情的果核,而「變壞」是它的必然方向及本質,指向「抒情」的無效化?不清的詩中不見得如此悲觀,至少是中性的,「如讓彼此的生命和呼吸聲/延續急速自轉和濕潤」。而面對命運不對等的權力關係,「這是一種對主宰的信任/從開始的那一天就存在著」,因此傳達甚麼不是重點,而是「傳達」此一行為背負著的命運。此一命運,代表意義的權威性之佚失:「設計師在佈置一局沒有預設立場的『方格』」,把意義邊緣化,把符號降解為物,逐層逐層剝落。而對於壓迫與被壓迫者情景的描述,「可惜有一種性格極度害怕窗/他們需要一堵圍牆」這句教人拍案叫絕,這種「需要」是變態的,真正令人害怕的無形牢籠,同時也是對於「意義」不能順利抵達某地的恐懼,甚至是對於不能歸類之物的恐懼。這首詩像一股巨大的洋流,衝擊思維,還有衝擊「詩的思維」。
如果想要看點輕鬆的詩,我推介他的暗戀組詩,是寫給 M 的(即是我本人)。詩題〈暗戀是這樣的〉。但是我讀完整首詩之後,不但沒有更加清楚暗戀是怎樣的,反而是更加疑惑了。不清開了這樣一個玩笑,不料卻擊中那種暗戀的「狀態」。詩用時間分組,而且非常隨意(由黃昏的 18:00 開始),正好表達暗戀的來去無由。有時像瘋子一樣喃喃自語(我腦裡全是你的⋯⋯我腦裡全是你的⋯⋯),講的還是同一句話。有時又顧影自憐,但無論如何你已經住在我裡面(你住進了我望遠鏡中最遙遠的/玻璃窗),不惜一切用所有方式想要去親近(郵票是我的舌尖,9:00 鼻尖在附近),但換來(世界所有的廢話都埋伏在那裡),除了指的是海浪聲音的無意義之外,若言者有意,但聽者無心,綿綿情話也終將無用。有時非常壓抑(夢是她的同謀⋯⋯受騙而醒來手上卻完全沒有證據),卻沒有說出其實是我主動甘願「被騙」的。至嚴重處就像一種病,失眠之餘,連時間的流逝也無法感知(因此 2:00 連續出現兩次,也可解為看鐘看了兩次),痴情至此(你沒有察覺我的夢中/我偷偷看著你/多一個小時),直至清晨,進而幻想與你交往的過程(為夢境穿上鞋子,打上蝴蝶結),將凝視反過來想像(你就在車廂的遠角最貼近我眼睛的地方),暗戀出現在不存在的時間(8:60),同樣能解釋為物理世界不足以容納暗戀。也有色迷迷的遐思(因為雲在彼此摩擦而/洩了一陣夜雨)暗引巫山雲雨之典故,可惜那只是打手槍而已(有時候在戶外做點不禮貌的事/把舌頭伸進她的字與字之間),你的午餐在一位女生的嘴巴裡/唇邊和指尖之間的非流動性,在眼裡),強裝理性的面貌卻無法掩飾暗戀的不理性。最後一節,結果是結果了,得到的只是一陣陣的酸澀。這詩還沒有完結,時間是 17:00,下一小時是 18:00,正好可以接上詩首,不斷不斷地輪迴⋯⋯很可怕吧?
這首詩充分表現暗戀的窺視與隱藏。戀人在詩中的缺席,引發敘述的動力。「你」其實沒有在詩中真正出現過。那哀戚的當代少年維特,含蓄又大膽,藉此時間的流逝對照相應的心理狀態。很不
幸地,這就是魯蛇的我了(抽泣)。
就像〈42〉所言:「所以所有建設都應該從建築一座廢墟開始」。成功的解構,恰恰是在結構的準確認知之上,才得以成功的。
解構者正是結構的專家。所謂的繼承與創新,就是處於一種辯證的關係。「我們的眼神,被囚禁四十二光年/卻依然能夠觸動彼此的靈魂?」豈不是〈混沌〉一詩的餘音?從島到島,從夢到夢,究竟那是濕潤的黃昏還是黎明?所有的愛情,是從焦慮中成熟起來的,或半生熟的,失敗者的實錄。
作為一張半完成的流程圖,你絕對可以說激進/很愛演/鬆散/佬味太重,但這些不同的評價正好表達詩集的兼容性,它的基本立場是拒絕定型的:
「詩是海浪/沒有一排相似的浪是相似的。」——〈CANTO OSTINATO〉
請你忘掉上面我說的胡話,隨便找條船,帶上你的背包就是了。
梁匡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