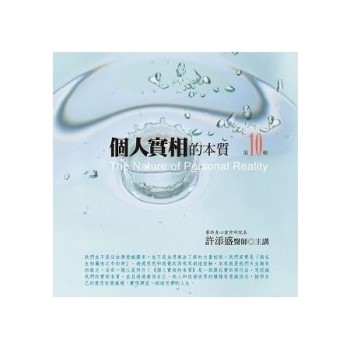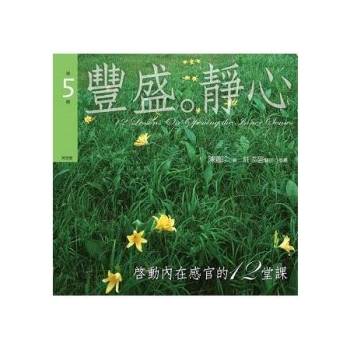陳滅《市場,去死吧》於二〇〇八在香港出版,三個月旋即售清,絕版至今,已成小小 的傳奇。詩集中滿佈沉鬱而狂放的濃郁意緒,寫及七一、六四、皇后碼頭、反世 貿、巿區重建、旅遊經濟等反抗主題,復與懷舊流行曲、貝拉塔爾等經典電影、 經典文學作品作文本互涉,將晚期資本主義、都市士紳化時期的荒謬語言重鑄再 造,以虛無點燃反抗的意志,背後是人文主義與知識份子,在香港這個城市裡的 哀歌,既孤零,又普遍。
九年之後,香港主權移交二十年之際,《市場,去死吧(增訂版)》面世,收入新 作十首,以及洛楓的導讀長文。
名人推薦
陳國球、董啟章、梁文道、廖偉棠、 謝曉虹、張歷君、李維怡、李智良、 須文蔚、楊佳嫻、莫昭如、劉小康、 黃耀明、羅永生、朱凱迪、陳劍青
「城市最後一個迷戀「垃圾」的詩人,簡直像《過於喧囂的孤獨》裡那個打包文 化死屍的老頭那樣偏執、滑稽而又瘋狂──去死吧!然而又溫柔得讓你猝不及 妨。」—— 謝曉虹(小說家、浸大人文及創作系助理教授)
「畢加索雖然也畫了不少沙灘上如荒廢建築物般的巨獸;但是此前大量遠逝家鄉 的室內風景、酒瓶和結他,卻讓人幾乎忘了他無處爆發的悲劇能量,以及他想觸 及所謂「外在世界」的掙扎。直到《格爾尼卡》,我們才看到了一個足以界定一 場戰爭,以至於世間一切人禍的畢加索。 《市場,去死吧》幾乎就是詩人陳滅 的《格爾尼卡》。」—— 梁文道(文化評論人)
「於皇后碼頭聽陳滅讀〈市場去死吧!〉,當下就有衝動拿刀跟資本主義搏 命!」——朱凱迪(立法會議員)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市場,去死吧(增訂版)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54 |
二手中文書 |
$ 315 |
文學 |
$ 350 |
現代詩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市場,去死吧(增訂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