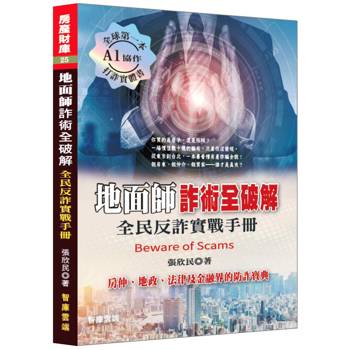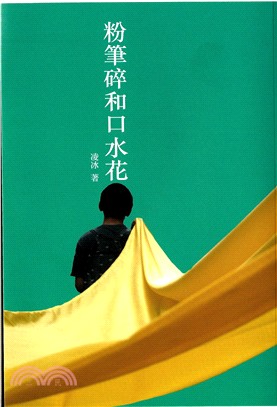 |
| 粉筆碎和口水花
出版社:點出版
出版日期:2016-11-0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40頁 / 15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目前評分: 評分:
圖書名稱:粉筆碎和口水花 商品資料
-
作者: 凌冰
-
出版社: 點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11-01
ISBN/ISSN:9789881439932
-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40頁
開數:寬15 X高21(公分)
-
類別: 中文書
|
|
|
|
|
 | 作者:姬野友美 出版社: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01-29 66折: $ 18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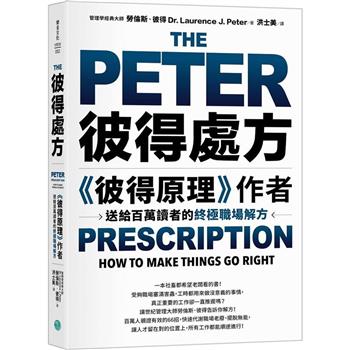 | 66折: $ 25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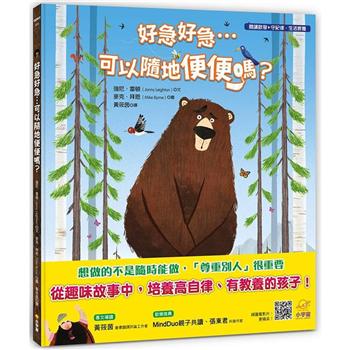 | 66折: $ 198 |  | 作者:張晴琳(圈媽) 出版社:采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08-05 66折: $ 238 | |
|
|
 | $ 458 |  | 作者:手名町紗帆 出版社:東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07-17 $ 15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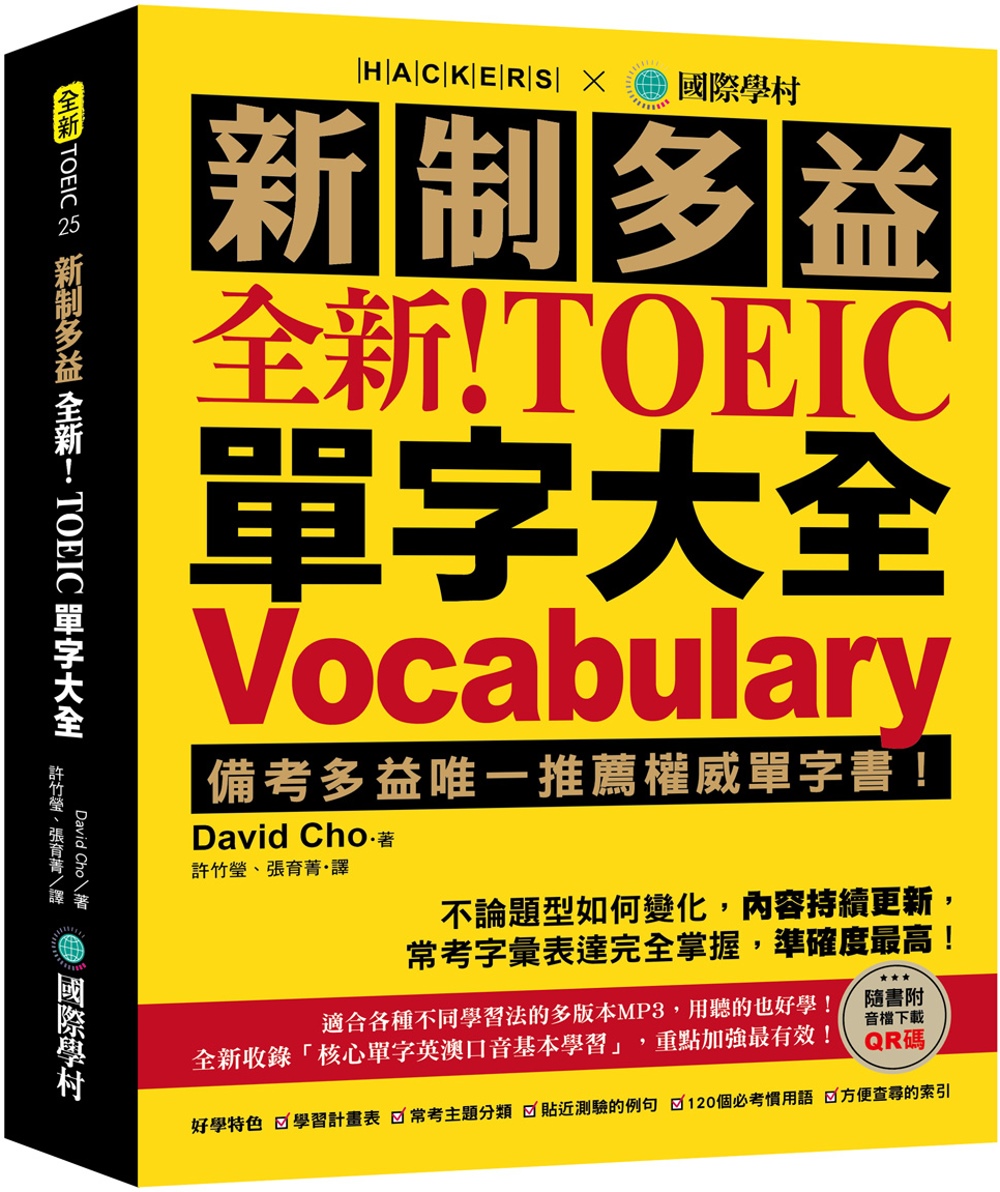 | 作者:David Cho 出版社:國際學村 出版日期:2022-08-04 $ 394 | ![不花錢讀名校MBA[10周年全新增訂版] 不花錢讀名校MBA[10周年全新增訂版]](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973171) | 作者:喬許.考夫曼 出版社:李茲文化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01-05 $ 434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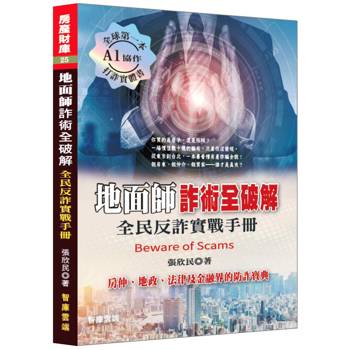 | 作者:張欣民 出版社:智庫雲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5-07-09 $ 332 |  | 作者:佐伯さん 出版社:東立 出版日期:2025-07-18 $ 221 |  | $ 387 |  | 作者:青山剛昌、櫻井武 出版社: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5-07-09 $ 174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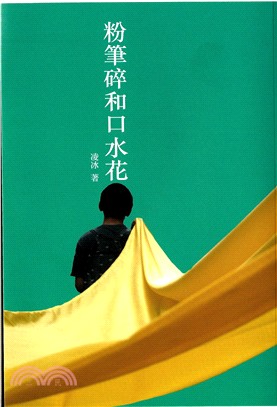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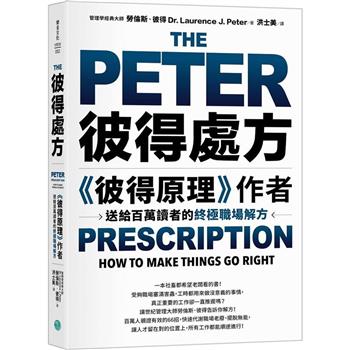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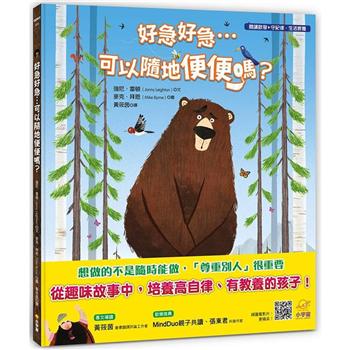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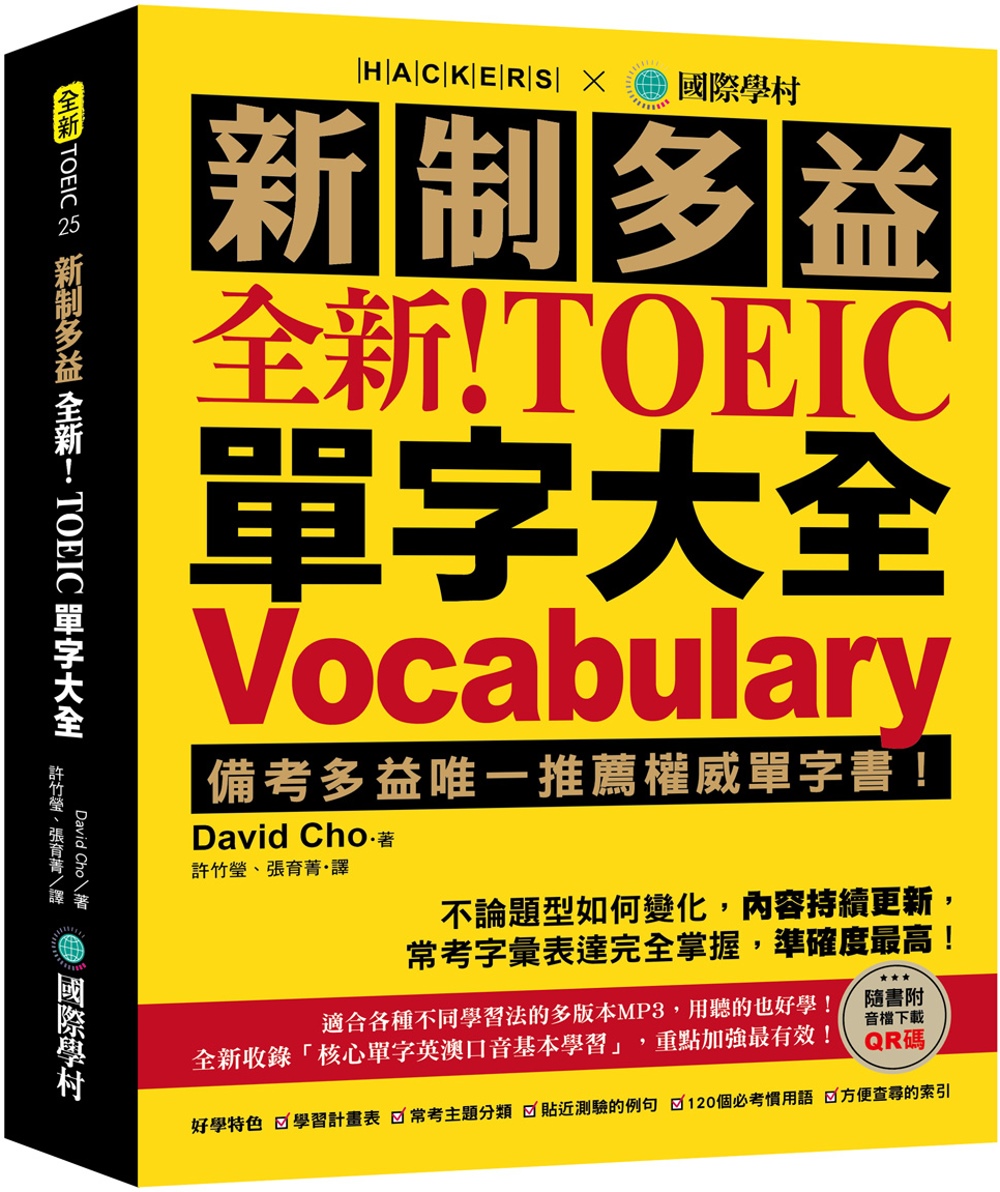
![不花錢讀名校MBA[10周年全新增訂版] 不花錢讀名校MBA[10周年全新增訂版]](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973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