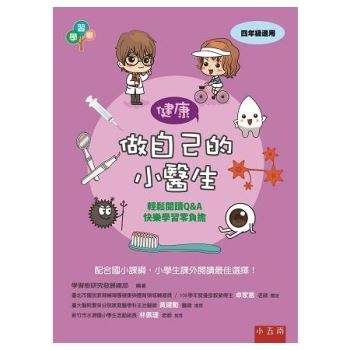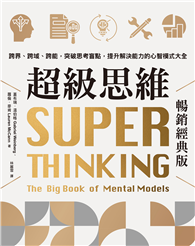窗外淅瀝淅瀝,天又下着大雨。
阮秋童坐在沙發上,凝望窗台,上面擺着幾盆由舊居搶救回來的鐵線蕨,覺得怵目驚心。一年前由山花下村被迫遷的經過歷歷在目。他找到舊城區這幢連天棚的小單位安居,也是得到保衛山花下大聯盟的社工于佩幫助,才找得到的。他記得當日警察在自己住的村屋外重重布防,自村長在村口扶着石油氣罐與警察僵持,直到後來警察衝進來,由大家的手臂組成的人鏈被硬生生地拆散,成員一個個被警察抬走,他才知道自己住了十多年的家沒有了。
阮秋童猶記得他們被抬出村屋時,天已經開始黑,他覺得四周都很光,有身穿防暴裝備的警察與記者令人眩目的鎂光燈,還有天上一輪幽幽的太陽散佈下來的冷冷光線。他聽不到一絲聲音,他知道警察在吆喝,記者在報導,還有大聯盟成員大聲呼叫,可是他除了嗚嗚聲,以及警察將屋門用大鐵鎖鎖上的咔嚓一聲,其他甚麼聲音都聽不到。他腦中想着家中兩隻貓與小魚池中的錦鯉,盤算着山花下村幾時才可以解封,貓會不會因為缺人餵飼而到池中撈魚止飢。他在大聯盟成員被丟上警車後,站在村口回望自己的小村屋,產生了生死永隔的悲哀,他自覺好像永遠回不去了,心也涼了一大半,虛虛浮浮。
山花下村被封翌日,秋童住在阿哥家,他在電視新聞聽到前來做秀的定例局議員在差館前拿着喇叭,嘰哩呱啦地説話,之後又有律師到差館向警方交涉,老鬼一行人最後被釋放了。
秋童看完新聞後,腦中一片空白,只想到自己的貓與魚與小村屋。于佩打電話跟他説,大聯盟的成員這時要繼續留在差館前抗議,問他去不去。秋童覺得很累,借詞身體不適拒絕了。他乘搭顛簸的小巴回到村前的大空地,有十幾位警察留守,他向警察説自己是村民,想回家收拾,警察卻説整條村都被封鎖了,要遲幾天才能讓村民回家。秋童無奈,只有坐車到市區,回阿哥家。
「很久前已經叫你正正經經在市區租屋住,再在市區找正職做。你偏説要過寧靜的田園生活,靠做freelance維生。那你生活怎會安定,怎會有保障?阿爸阿媽早死,我只有你一個細佬,你若果有甚麼事,那我怎向阿爸阿媽交待?」
每次到阿哥家,阿哥總會絮絮不休地説着同一番話,他每次聽到便想提早離去,可是今次自己的家被封了,要寄住阿哥家,唯有忍受下來。他們這時圍着飯桌吃飯,頭頂的燈泡昏昏黃黃的,映得每個人面上都掛上一片愁苦的黃色。大嫂見秋童的飯碗空了,便説:「秋童,多添一碗飯,你平時賺得不多,家中又沒有人煲湯給你喝,伙食不好。現在趁來到,多吃點。」説完似笑非笑地向阿哥乜斜一眼,大嫂的微小動作看在秋童眼中。每次大嫂總是有意無意向秋童示威,嘲弄他的經濟環境與工作,令秋童聽得心中忿忿不平。現在寄人籬下,唯有當聽不到大嫂的話,這餐飯吃得毫不自在。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田園誌的圖書 |
 |
田園誌 作者:黃可偉 出版社:練習文化實驗室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2-24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84 |
中文現代文學 |
$ 316 |
中文書 |
$ 317 |
小說 |
$ 324 |
小說 |
$ 324 |
文學作品 |
$ 342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田園誌
阮秋童在很多年前參與過社會運動,但早已退出江湖,隱居小村山花下。只是社會不斷高速發展,現在政府決定夷平山花下,在這裏興建高鐵總站。這時有一班新世代的社運搞手老鬼與于佩等人來到花下抗爭,希望拯救這條小村,秋童早已對社運心灰意冷,但自己的家園快要毀於一旦,那他要不要與他們連成一線?究竟事情會怎樣發展?秋童與老鬼等人以至社會大眾又有甚麼互動?這是一個老社運心理掙扎的歷程。
作者簡介:
黃可偉
香港土著。2003年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畢業,2007年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文學碩士,2012年獲科大人文學部哲學碩士。
2014年任香港石磬文化事業出版社編輯,至2015年6月與友儕合資成立練習文化實驗室(Culture Lab Plus Ltd.),任副總編輯。
2014年8月開始擔任香港網上媒體《線報》(LinePost)專欄作者,定期發表文章。
自2000年開始,曾獲兩岸三地大小文學獎若干個,如:香港之中文文學創作獎、大學文學獎、青年文學獎;臺灣之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梁實秋文學獎;內地之孫犁散文獎、漂母杯文學獎、深港兩地短小說大賽獎等獎項。
TOP
章節試閱
窗外淅瀝淅瀝,天又下着大雨。
阮秋童坐在沙發上,凝望窗台,上面擺着幾盆由舊居搶救回來的鐵線蕨,覺得怵目驚心。一年前由山花下村被迫遷的經過歷歷在目。他找到舊城區這幢連天棚的小單位安居,也是得到保衛山花下大聯盟的社工于佩幫助,才找得到的。他記得當日警察在自己住的村屋外重重布防,自村長在村口扶着石油氣罐與警察僵持,直到後來警察衝進來,由大家的手臂組成的人鏈被硬生生地拆散,成員一個個被警察抬走,他才知道自己住了十多年的家沒有了。
阮秋童猶記得他們被抬出村屋時,天已經開始黑,他覺得四周都很光,有身穿防暴裝備的...
阮秋童坐在沙發上,凝望窗台,上面擺着幾盆由舊居搶救回來的鐵線蕨,覺得怵目驚心。一年前由山花下村被迫遷的經過歷歷在目。他找到舊城區這幢連天棚的小單位安居,也是得到保衛山花下大聯盟的社工于佩幫助,才找得到的。他記得當日警察在自己住的村屋外重重布防,自村長在村口扶着石油氣罐與警察僵持,直到後來警察衝進來,由大家的手臂組成的人鏈被硬生生地拆散,成員一個個被警察抬走,他才知道自己住了十多年的家沒有了。
阮秋童猶記得他們被抬出村屋時,天已經開始黑,他覺得四周都很光,有身穿防暴裝備的...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黃可偉
- 出版社: 練習文化實驗室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2-24 ISBN/ISSN:978988146193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20頁 開數:32
- 商品尺寸:長:190mm \ 寬:130mm \ 高:18mm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