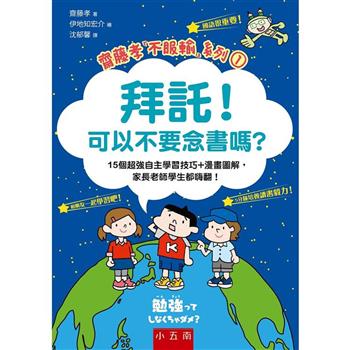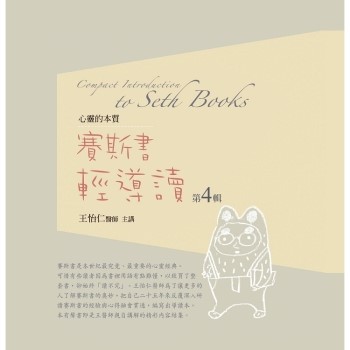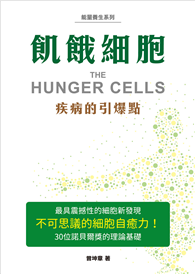圖書名稱:變態的中國文化
隋煬帝本是一個弑父、殺兄、篡位的畜生,卻也想為中國打造一個“禮儀之邦”的形象。連首都街邊的大樹,他都讓人給它們裹纏上綢緞,還強迫國內大小飯館免費招待“老外”,以顯示帝國的富足和慷慨,卻根本不管自己的子民是否衣衫襤褸、饑腸轆轆!從這一點上來看,隋王朝有些像當今的朝鮮——單從平壤街頭,你很難看出這是一個正在遭受饑荒的國家——人們衣著光鮮,神采奕奕,彬彬有禮。但只要你來到郊區,一切便會真相大白。 唐朝的情況比隋朝也好不到那去,太宗李世民和大周女皇武則天都是靠滅親、篡位起家的。盛唐時期,當西域的商人和日本的遣唐使來到帝國的 “首善之地”時,看到的是滿街的翩翩少年和謙謙君子;而在幅員遼闊的鄉野,農民們仍舊衣不遮體,食不果腹。在唐朝的大部分時間裏,普通人(特別是農民)大 都生活在饑謹與屈辱之中,正如杜甫所看到的—— “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婦無消息,城中斗米換衾衣,向許寧論兩相值。”(《秋雨歎》)為了活命,連“詩聖”杜甫都不要臉了——“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 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奉贈韋左丞丈》)更何況貧苦農民?到了大唐帝國的彌留之際,當黃巢麾下的“義軍”們用人肉做軍糧時,誰也不再提什麼“禮儀”、“ 廉恥”了。 宋朝三百多年裏,貫穿了戰亂和饑荒,自始至終都是農民暴動不斷、外族戰事不斷、災荒不斷。由於天災人禍,河北一帶還發生過大規模吃人肉、賣人肉的慘劇,人們私下稱之為“兩腳羊” ,並且分等級,兒童肉叫做 “和骨爛” .這個時候給他們講禮儀,恐怕太不合時宜了吧。 對於明朝,文中那位視唐朝為“禮儀之邦”的學者似乎也很有意見: 明中葉以後,隨著人口增多,遊民越來越多,社會問題無法在家族內部解決,遊民們組成秘密教門、會黨、行幫、商幫等“江湖組織”,社會生活日益粗俗化、江湖化。 但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咎于明初的朱元璋和朱棣——這對父子對國人所幹過那些禽獸不如的暴行以及這些暴行對明朝的深刻影響。 至於我們歷史課本裏盛讚的“康乾盛世” ——一個生活在康熙四十年的人披露了“盛世”的真相: 清興五十餘年矣。四海之內,日益貧困:農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賤而艱於食,布帛賤而艱於衣,舟轉市集而貨折貲,居官者去官而無以為家,是四空也。金錢, 所以通有無也。中產之家,嘗旬月不觀一金,不見緡錢,無以通之。故農民凍餒,百貨皆死,豐年如凶,良賈無籌。行於都市,列肆琨耀,冠服華腆,入其家室,朝 則熄無煙,寒則蜷體不申。吳中之民,多鬻男女于遠方,男之美為優,惡者為奴。女之美為妾,惡者為婢,遍滿海內矣。(唐甄) 到了“康乾盛世”的後期,國人的“文明素質”就是再包裝也不行了。英國訪華使節馬戛爾尼親眼見到過我們的“乾隆爺”,應該知道大清是何等的氣派吧,回國後,對中國人的印象卻很不好,他語帶輕蔑地回憶道: 他們穿的是小亞麻布或白洋布做的衣服,非常髒也很少洗,他們從來不用肥皂。他們很少用手絹,而是隨地亂吐,用手擤鼻子,用袖子擦鼻涕,或是抹到身邊的任何東西上。這種行為很普遍。更令人憎惡的是有一天我看見一位韃靼人讓僕人在他的脖子裏找蝨子 ,這東西咬得他難受! 在馬戛爾尼及其同行人的眼中,中國“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人們衣衫襤褸甚至裸體”,“象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的軍隊”,“我們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搶著吃”,“我不得不懷疑以前傳教士(指明末傳教士)的回憶錄是編造的 ”。 到 了大清帝國的末年,我們“禮儀之邦”的“ 首善之區” ——北京城已成了一座名副其實的“垃圾場”,市民們為了保住自家小院的乾淨,都跑到街上隨地大小便。結果是“糞除塵穢滿街頭” (《燕京雜詠》), “京城二月通溝,道路不通車馬,臭氣四達……”(《燕京雜記》),到處是“小人之風” (見宋玉《風賦》)。 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後,分區佔領 的聯軍開始著手解決這個禮儀的底線問題,他們開始在街上建公廁,組織人員定期打掃,安設路燈,嚴格查禁隨地方便者,查到了罰去打掃廁所,做苦工。八國聯軍 中的德軍火氣最大,有的士兵見了隨地方便的中國人抬手就是一槍。結果北京的文明程度立杆見影,全城的公共衛生狀況大大改善,真正成了“首善之區 ”,其中尤以美占區和日占區搞得最好。對此,我想當時中國所有的有識之士和愛國者們的共同感受只有一個——無地自容。 再來看看同一時期的國際大都會上海,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悲憤而絕望地寫到: 余見上海租界街道寬闊平整而潔淨,一入中國地界則污穢不堪,非牛溲馬勃即垃圾臭泥 ,甚至老幼隨處可以便溺,瘡毒惡疾之人無處不有,雖呻吟僕地皆置之不理,惟掩鼻過之而已。可見有司之失政,富室之無良,何怪乎外人輕侮也。 中國最大的兩座都市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難怪當時的知識份子“更多抱怨不能變法自強勝過對於受異族侵淩之憤慨”。 而我們那些傳統知識份子自己又做得怎樣呢?以儒家文化為基石的科舉考試曾被公認為是體現“禮儀之邦”特色的重要文化盛事。陳獨秀曾於一八九七年在南京參加科舉考試,他親眼見到舉子們只因蹲馬桶不方便,便到處拉 “野屎”的盛況: 不 但我的大哥,就是我們那位老夫子,本來是個道學先生,開口孔孟,閉口程朱,這位博學的老夫子,不但讀過幾本宋儒的語錄,並且還知道什麼“男女有別”、“男 女授受不親”的禮教,他也是天天那樣在路旁空地上解大手,有時婦女在路上走過,只好當作沒看見。同寓的幾個荒唐鬼,在高聲朗誦那禮義廉恥,正心修身的八股 文章之餘暇,時到門前探望,遠遠發現有年輕婦女姍姍而來,他便扯下褲子,蹲下去解大手,好象急於獻寶似的,雖然他並無大手可解。(《實齋自傳》) 就他們這種排泄方式而言,顯然與“克己復禮”是背道而馳的,說得不好聽一點,完全是一群野狗的作為。進入彌留之際的科舉,已將其低俗、醜惡、荒謬的本質暴露 無遺。至此,大清帝國的禮義廉恥喪失殆盡。“知書達理”的知識份子尚且如此,普通百姓就更不必說了,本文開頭提到的有著供奉關公習俗的晉商,我們都知道他 們的山西大院,那裏家家戶戶都將自家的庭院打掃得乾乾淨淨,卻將垃圾掃到大街上,難道他們不知道這些垃圾最後還是會臭到自己的嗎?而我們的慈禧太后仍舊很 驕傲地向世人宣稱:“文化禮俗,總是我國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