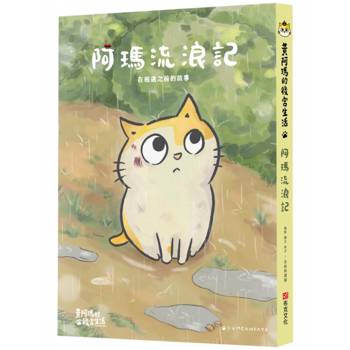在地下室的第五天,上午,給丈夫寫一封信。寫完了信的最後一個字,他的名字,突然湧上了我的腦海暗角,我及時抓住那幾個字。文。保文。保文陳。已經不知有多少年,我沒想起過丈夫的名字,彷彿他原本就是個沒名字的人。被憶起的名字在我的身體裡貫通了一道暖流,意義不明。
地下室沒有任何可以跟外界聯絡的通訊設備(安裝在牆角的監視器,無法提供雙向溝通),退休教授說,這是為了保留「故事」裡的靈。「現代的資訊科技會干擾甚至輾碎那些靈。」他說。
「你怎麼知道?」我疑惑。他領著我走進這所房子時,重複地說了幾遍,他從不知「故事」是什麼。就像對大多數的人來說,「故事」早已成了一個空蕩蕩的名詞,丟失了內容的空殼。人們既沒有切切實實地感受過任何故事,也沒法抓住、捕捉或保留任何「故事」。不僅如此,能辨別「故事」的人也愈來愈少,少得就像沉迷研究外星人、保護流浪動物,或在深夜遠足的人。如果在街上隨便抓著一個人(或在網絡上隨便呼喊出)問:「『故事』到底是什麼?」那麼,會得到的答案可能是,一個畫面、一道疤痕、空的酒瓶、一個已經碎裂的片段、咒罵、一張照片。如果有人願意給出一個答案的話。
「所謂的『故事』就像瀕危的鳥,牠們必須飛翔,無法被豢養,而這裡本來就是籠子,我們早已適應囚禁,但牠們不可以。」匿名者在網上發出了這樣的言論,被一份報章摘錄,放在本地新聞的側旁。那天的主要新聞,關於一名研究「故事」的學者被問及對於「故事」最近成為熱議的話題,人們關心的是,「故事」是否早已消失?他的說法是,人類的基因裡本來就有創造和編撰「故事」的能力,這種能力不會無故消失,但有可能局部退化。
有時候,我不禁懷疑,當人們討論「故事」的時候,每一個人所說的,是相同的東西嗎?
如果「故事」確實存在於人類的基因裡,那麼,那很可能是一根已然完全退化的尾巴。
「我當然,不懂得『故事』」。退休教授把我的行李背包放在地下室的長木櫈上。淺灰色的牆壁和深灰色的水泥地面。我第一次走那個地下室,就感到那是個陰涼幽暗之處。退休教授說,地下室是房子的心臟,他的客人全部住在「心臟」。經過一段很長的停頓之後,他說:「不過,這個地下室曾經有多少人待過,你知道嗎?經過半年的隔離,他們的『故事靈』都恢復得非常迅速。」
「他們也是販賣故事的人?」我問。
「不。」他搖著頭說,他們來自各種行業,但沒有一個人擁有『故事』。這種事,甚至不必仔細審視,一嗅就嗅得出來。」
「我研究過的人類樣本,一定比你這輩子所見過的人的總數更多。」他看著我,示意我去注意安裝在冷氣機之旁的一個圓形鏡頭,底下有一顆紅色小燈,確實像一顆無辜的眼球。他告訴我,住在這裡的人都會被拍攝一切生活起居。「我當然也翻看錄影,尤其是在客人離開了這裡之後,翻看那些片段,會一次又一次重新認識他們,即使在現實中,我們或許再也沒有見面的機會。不過,我對於窺視一點興趣也沒有,所有資料只會用於研究的用途,這個鏡頭懸在這裡,全是為了確保住在這裡的人的安全。沒有人能確定,一個人獨自活在地下室裡,會不會出現精神異樣的狀況。」
出走旅遊顧問鯨替我安排旅行期間的工作時對我說:「即使你身無分文,仍然可以先出發,到了那邊,找到工作,再把旅費分期攤還給我們。」他說,在我前往當地之前,會替我聯絡目的地的僱主。
「那是怎樣的工作?」我問。
「你可以向客人販賣『故事』。」他說,旅館就是一個熱鬧而方便的交易場所。「許多必要的買賣都在公共的場所私密地進行。」鯨向我保證這種工作絕對安全。「人們無法想像那些獨自公幹或旅遊的人,孤單地住在異地的一個陌生小房間內的人如何渴求『故事』。」那時候,在咖啡室裡,我第一次跟一個人面對面地討論「故事」這東西。
「『故事』?」我有一點不明所以。「但,我身上從沒有這東西,我怎樣賣給他們。」
「你會有。」鯨扶了一下黑邊眼鏡,就像在審視我。「當顧客出現時,你就會發現,你一直擁有他們渴求的東西。很久很久以前,旅館曾經非常流行性和藥品的買賣,但這年代,人們都喪失了做愛所必要的熱情、體力和純粹,與其服用藥物,生病或跑步更容易令他們上癮。但,沒有人能抗拒『故事』,各式各樣的『故事』。」他甚至說,只要手中握有絕對的「故事」,就差不多等於擁有上佳的武器和權力。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人皮刺繡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87 |
二手中文書 |
$ 306 |
文學作品 |
$ 334 |
中文書 |
$ 335 |
小說 |
$ 342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人皮刺繡
到底我們能否觸及真實的自己?日常的謊言在身體裡積疊,使其變形,成為另一種語言,用以建立關係。當謊言崩潰,語言消失,沒有人可以回頭。香港作家韓麗珠以四個亮麗故事,刻劃被謊言包裹的人生,人皮刺繡之下,有無法看見的、遍佈全身的傷口。
「他總是會從假寐之中,及時張開眼睛,回答我的問題。他說,他常常覺得,遺留了什麼在店子裡。「但我不知道那是什麼。」他以乾澀的聲音說:「或許,我會在店裡找到,總有那麼的一天。」在那搖搖晃晃的車廂裡,他說在以往的許多年,總是無法確切地感到失去。不管是家裡飼養多年的老狗死去的時候,父親突然發現罹患末期癌症被送進醫院再沒有回來的期間,還是相交多年的戀人毫無先兆地提出分手之後,他心裡也是空蕩蕩的,什麼也沒有。「就像站在一堵牆壁前,沒有門可以開啟,無法通向另一個地方。」他這樣說的時候,臉上帶著莫名的失落。可是為什麼要失落呢?我想,為什麼他會以為,必定有一扇門,必定可以通向另一個所在?」──〈人皮刺繡〉
作者簡介:
韓麗珠
著有小說《空臉》、《失去洞穴》、《離心帶》、《縫身》、《灰花》、《風箏家族》、《輸水管森林》、《寧靜的獸》以及散文集《黑日》、《回家》。曾獲香港書獎、2008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中文創作類、2008及2009亞洲週刊中文十大小說、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推薦獎、第20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篇小說首獎。長篇小說《灰花》獲第三屆紅樓夢文學獎推薦獎。2018年藝發局藝術家年獎(文學藝術)。
章節試閱
在地下室的第五天,上午,給丈夫寫一封信。寫完了信的最後一個字,他的名字,突然湧上了我的腦海暗角,我及時抓住那幾個字。文。保文。保文陳。已經不知有多少年,我沒想起過丈夫的名字,彷彿他原本就是個沒名字的人。被憶起的名字在我的身體裡貫通了一道暖流,意義不明。
地下室沒有任何可以跟外界聯絡的通訊設備(安裝在牆角的監視器,無法提供雙向溝通),退休教授說,這是為了保留「故事」裡的靈。「現代的資訊科技會干擾甚至輾碎那些靈。」他說。
「你怎麼知道?」我疑惑。他領著我走進這所房子時,重複地說了幾遍,他從不知「故事...
地下室沒有任何可以跟外界聯絡的通訊設備(安裝在牆角的監視器,無法提供雙向溝通),退休教授說,這是為了保留「故事」裡的靈。「現代的資訊科技會干擾甚至輾碎那些靈。」他說。
「你怎麼知道?」我疑惑。他領著我走進這所房子時,重複地說了幾遍,他從不知「故事...
顯示全部內容
推薦序
後記
謊言學
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
我知道你在說謊
我也知道我在對自己撒謊
謊言在腦部地圖上,位於不被記錄的位置,邊界以外的邊界
如果我們的謊言有重叠的部份
就可以靠近對方更多一點
他們給我們定了罪
罪名是拒絕接受他們的謊言
抵抗活在謊言的邏輯裡
指出謊言是謊言
會危害國家和每一個人的安全
人命建基於適量的隱暪
同意被騙是成熟所需要的妥協
那些擢破國王沒有穿衣的孩子
不是死於非命,就是被判長期監禁
安全是我們最後的房子
但命理師說過
我們註定流離失所
你沒有給我定罪
我把你送贈的謊言視為珍貴的禮物 ...
謊言學
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
我知道你在說謊
我也知道我在對自己撒謊
謊言在腦部地圖上,位於不被記錄的位置,邊界以外的邊界
如果我們的謊言有重叠的部份
就可以靠近對方更多一點
他們給我們定了罪
罪名是拒絕接受他們的謊言
抵抗活在謊言的邏輯裡
指出謊言是謊言
會危害國家和每一個人的安全
人命建基於適量的隱暪
同意被騙是成熟所需要的妥協
那些擢破國王沒有穿衣的孩子
不是死於非命,就是被判長期監禁
安全是我們最後的房子
但命理師說過
我們註定流離失所
你沒有給我定罪
我把你送贈的謊言視為珍貴的禮物 ...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種植上帝〉
〈灰霧〉
〈以太之臍〉
〈人皮刺繡〉
〈後記──謊言學〉
〈灰霧〉
〈以太之臍〉
〈人皮刺繡〉
〈後記──謊言學〉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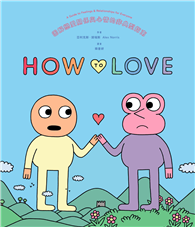
![114年國語文歷年試題解題聖經(十四)113年度[教師甄試] 114年國語文歷年試題解題聖經(十四)113年度[教師甄試]](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0896)